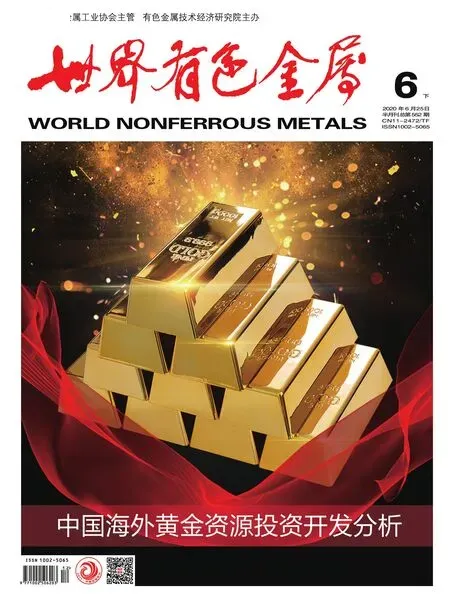郯廬斷裂帶白堊紀伸展活動對合肥盆地的制約
黃 蒙
(安徽省地質調查院(安徽省地質科學研究所),安徽 合肥 230000)
郯廬斷裂帶中段是區域上重要的控盆構造,合肥盆地是郯廬斷裂帶所控制的中新生代斷陷盆地之一,位于該斷裂帶西側。其沉積格局受郯廬斷裂帶中新生代伸展活動的制約。本文通過斷層擦痕應力場反演方法,獲得了郯廬斷裂帶晚中生代時期的拉伸方向及其演變規律。在此基礎上,結合前人研究成果,總結了晚中生代時期,郯廬斷裂帶伸展活動與合肥盆地沉積格局之間的制約關系,結合盆地地層的沉積格局、沉降中心分布等特征綜合分析,深入了解郯廬斷裂帶晚中生代伸展活動對合肥盆地的控制。
1 區域地質背景
郯廬斷裂帶是東亞大陸上的一系列北東向巨型斷裂系中的一條主干斷裂帶,該斷裂帶經歷了多期構造。郯廬斷裂起源于中三疊世末(印支期)華北陸塊與楊子陸塊造山作用產物(趙田等,2016),中侏羅世末,郯廬斷裂帶首次復活,構造變形以左行走滑韌性剪切帶形式保存于大別造山帶東緣的張八嶺巖群中。晚中生代期間,郯廬斷裂帶走滑與伸展活動交替發生(Zhu et al.,2010,2012)。沿斷裂帶發育了潛山盆地、合肥盆地、嘉山盆地、蘇北盆地等。
合肥盆地是受郯廬斷裂帶所控制的典型斷陷盆地之一,位于華北克拉通東部南緣。東西長約200km、南北約150km,盆地東以郯廬斷裂與張八嶺隆起相鄰,南抵大別造山帶,北以潁上-定遠與蚌埠隆起相接,西以吳集正斷層為界與長山隆起緊鄰。盆地起源于早-中侏羅世大別造山帶北部的后陸繞曲盆地(劉國生等,2006),晚侏羅世期間,盆地普遍隆起,缺失沉積記錄。早白堊世-古近紀,合肥盆地轉變為受基底斷裂控制的斷陷盆地(李雙應等,2002)。印支期形成的基底斷裂在盆地伸展活動中對沉積格局具有重要的影響(朱光等,2013)。古近紀末,盆地反轉,整體抬升,從而結束了斷陷盆地發育階段(劉國生等,2006)。
2 白堊紀斷裂與盆地伸展方向
郯廬斷裂帶是中國東部規模最大的邊界斷裂帶,其斷裂帶及其兩側廣泛發育斷陷盆地,表面斷裂帶經歷過強烈的伸展活動。
通過對五河地區野外調查結果發現,郯廬斷裂帶晚中生代時期至少經歷了三期不同方向的伸展。第一期以正斷層為主。該期斷層是在北西西-南東東向區域拉伸背景下形成的,活動時間為早白堊世早-中期第二期為正右行平移斷層。在WH04-2測量點上,該期斷層錯斷了早期正斷層,被切割的斷層面因牽引作用而變得陡立。第三期為右行平移斷層。該期斷層形成于新莊組沉積之后,古近紀玄武玢巖侵位之前,是晚白堊世近南北向拉伸的產物。
合肥盆地受郯廬斷裂帶控制,通過對合肥盆地內姚李地區地層特征及斷層擦痕數據反演,得出合肥盆地晚中生代時期同樣經歷了三期不同方向的伸展,早白堊世早-中期為北西西-南東東向拉伸,早白堊世晚期為北西-南東向拉伸,晚白堊世轉變為近南北向拉伸。與五河地區郯廬斷裂帶上各期張斷層反演出的應力場方位基本一致,皆具順時針旋轉特征。(鄧佳良,2020)。
3 伸展活動對合肥盆地的制約
3.1 早白堊世早-中期
大量研究表明(趙宗舉等,2000;劉國生等,2006;朱光等,2013),合肥盆地形成之前同樣存在一系列基底斷裂,這些基底斷裂形成于印支期,包括北北東向和近東西向兩組。北北東向斷裂主要有郯廬斷裂(盆地東界)和吳集斷裂(盆地西界);近東西向斷裂主要有(自南向北)信陽-舒城斷裂、六安斷裂、蜀山斷裂、肥中斷裂和潁上-定遠斷裂,其中信陽-舒城斷裂和潁上-定遠斷裂分別為盆地的南界和北界。據前文研究顯示,早白堊世早-中期的區域拉伸方向為北西西-南東東向,垂直于北北東向基底斷裂,說明當時盆地東、西邊界斷裂(郯廬斷裂和吳集斷裂)處于正向拉伸狀態,垂直落差最大,控制著盆地的北北東向沉積格局。朱光等(2011)利用盆地內鉆井及勝利油田所做的地震剖面等資料重新編繪了合肥盆地晚中生代各時期不同地層的殘留等厚圖。早白堊世早期朱巷組的沉積格局主要受控于復活的郯廬斷裂和吳集斷裂,沉降帶呈北北東向展布,沉積厚度隨著接近控盆斷裂而變厚,為典型的半地塹式盆地沉積。從朱巷組殘留的沉積厚度來看,郯廬斷裂復活時的伸展活動明顯強于吳集斷裂,所控制的沉積厚度更大。最大沉降中心位于肥東東部的郯廬斷裂西側,殘留厚度大于3000m。
3.2 早白堊世晚期
繼北西西-南東東向區域拉伸之后,在早白堊世晚期區域拉伸方位順時針轉變為北西-南東向。盆內北北東向及近東西向基底斷裂與區域拉伸方向斜交,復活時處于斜向拉伸狀態,垂直落差不大,具顯著的平移分量。從理論上講,當時的盆地沉積格局主要受北北東向和近東西向基底斷裂共同控制,且最大沉降帶應在伸展活動活躍的郯廬斷裂與近東西向斷裂交匯處。但從早白堊世晚期響洪甸組的殘留等值線圖上來看,最大沉降帶僅有一處,位于北北東向郯廬斷裂與近東西向潁上-定遠斷裂交匯處。據鉆井及地震剖面資料顯示,這套沉積地層在盆地中廣泛缺失(朱光等,2011),說明當時伸展活動開始減弱,控制發育的盆地沉積范圍明顯萎縮,最大沉降中心位于定遠南,沉積厚度大于2000m,相對于早白堊世早期最大沉降中心向北北東遷移。
3.3 晚白堊世
晚白堊世期間的區域拉伸方向再次發生改變,由早白堊世晚期的北西-南東向轉變為近南北向。盆地南、北邊界上的信陽-舒城斷裂和潁上-定遠斷裂及盆內大型斷層(包括六安、蜀山和肥中斷裂)在復活時處于正向拉伸狀態,垂直落差較大,控制著當時合肥盆地的總體沉積格局。而盆地東、西邊界上的郯廬斷裂和吳集斷裂為斜向拉伸,具明顯的右行平移分量,垂直落差較小,控制的盆地沉積也較薄。因此,晚白堊世期間,合肥盆地內上白堊統沉積格局應發生顯著變化,最大沉降帶由北北東向轉變為近東西向延伸。朱光等(2011)重新編繪的上白堊統張橋組的殘留等值線圖為此提供了有力證據。從其沉積格局來看,上白堊統張橋組的空間展布主要受控于復活的近東西向基底斷裂,沉積厚度隨著接近東西向斷裂而明顯增厚,為典型的半地塹式沉積。盆地東、西邊界斷裂雖然也控制了盆地沉積,但厚度明顯小于盆內近東西向斷裂。另外,張橋組具多個沉降中心,在東西向上呈串珠狀展布,最大沉降中心位于曹廟附近,沉積厚度大于2000m。相對于早白堊世晚期最大沉降中心向南西遷移。
綜上可知,伸展活動是以盆內基底斷裂為媒介控制盆地沉積格局的。最大沉降帶往往平行于復活時處于正向拉伸狀態的基底斷裂。沉積厚度隨著接近基底斷裂而變厚,具典型的半地塹式沉積特征。早白堊世早期,合肥盆地東、西邊界上的郯廬斷裂和吳集斷裂處于正向拉伸狀態,控制發育了北北東向延伸的半地塹盆地。當時郯廬斷裂伸展活動比吳集斷裂更強,控制的沉積厚度更大,最大沉降中心位于肥東東部的郯廬斷裂西側;早白堊世晚期,盆地沉積格局受北北東向和近東西向基底斷裂共同控制,且伸展活動開始減弱,盆地的沉積范圍明顯萎縮,沉降中心向北北東遷移至定遠南部;晚白堊世期間,近東西向基底斷裂處于正向拉伸狀態。
4 結論
(1)郯廬斷裂帶白堊紀伸展活動主要經歷了三次演變。第一期拉伸方向由北西西-南東東向、第二期北西-南東向拉伸,第三期轉變為近南北向拉伸,總體具順時針旋轉特征。
(2)合肥盆地晚中生代時期同樣經歷了三期不同方向的伸展,早白堊世早-中期為北西西-南東東向拉伸,早白堊世晚期為北西-南東向拉伸,晚白堊世轉變為近南北向拉伸。
(3)早白堊世早期,合肥盆地主體為由郯廬斷裂帶控制發育的北北東向半地塹盆地,最大沉降中心位于肥東;早白堊世晚期,伸展活動開始減弱,盆地沉積范圍明顯萎縮,最大沉降中心向北北東遷移至定遠南;晚白堊世期間,盆地沉積格局發生顯著變化,沉降帶由北北東向轉變為近東西向,最大沉降中心向南西遷移至曹廟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