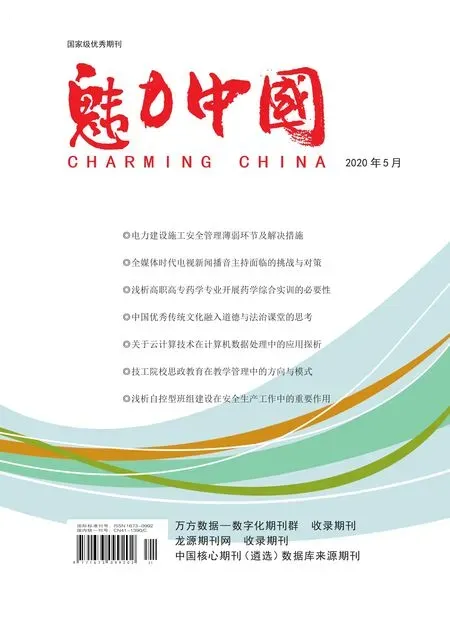“非遺”與群眾文化的聯系與價值研究
李小華
(廣東省惠州市瀝林文化站,廣東 惠州 516023)
我國歷史悠久,在數千年的歷史發展進程中積淀了極具民族特色的、深厚的文化底蘊與內涵,一些具備研究價值且亟待保護的則被納入了非物質文化文化遺產名錄(以下簡稱“非遺”)。“非遺”的表現形式多樣,有文學詩歌、文字、表演藝術、傳統手工、節日、活動儀式等,它對一個民族、國家歷史、精神、思維、價值、道德、審美的留存與敘述,具有相當高的歷史價值,不僅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財富,也是全人類的寶貴財富。
目前在世界范圍內,“非遺”都面臨著消亡的威脅。比如說在城市化的沖擊之下,很多古建筑、古民居都存在毀棄、濫用和過度開發的問題。再加上新時代,人們的生活方式、審美觀念等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民族傳統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存環境日益惡劣,甚至已經消失,因此“非遺”的保護已經成為了世界范圍內熱切關注的問題。就當前研究情況而言,“非遺”保護的主體歸屬,保護的手段研究都已經取得了相關進展,倒是如何使“非遺”以“活態”的生命形式得以在新環境中繼續傳承,成為了一個世界性的難題。
當前,我國各地蓬勃發展的群眾文化活動為“非遺”的傳承與發展提供了新的方向。借助于多元化的群眾文化活動為載體,能夠讓“非遺”隨著群眾文化活動的普及與發展得以承繼;另一方面,將“非遺”與群眾文化相聯系,甚至是融合發展,豐富了我國群眾文化活動內容,加深了其文化內涵,有利于我國群眾文化體系的完善與發展。因此探討“非遺”與群眾文化中的聯系與價值體現,既有一定的理論價值,又極具現實意義。
一、“非遺”與群眾文化的關系
要想讓“非遺”借助群眾文化活動這一載體,在新時代、新環境中以“活態”的生命形式存在、傳承、發展,先要找出“非遺”與群眾文化之間的聯系。
(一)群眾文化能夠成為“非遺”的載體
“非遺”的“活態性”就在于其生命力,最核心的關鍵載體便是人。有人將滿腹經典的老人比作一座“圖書館”,當老人逝去之時,便是圖書館倒塌之日。這種情況并不罕見,不少古文字、音樂、技藝、民俗禮儀的消亡便是由于掌握它的老人的去世所引起。正因為如此,大家才普遍認為“非遺”的傳承者便是這些掌握了特殊、關鍵技藝的少數人。但問題是,僅僅依靠這些少數人便能將“非遺”傳承下去嗎?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不管是文字、音樂、技藝還是禮儀,沒有了互動、使用與欣賞,就失去了其存在的現實意義,只不過是空洞的形式而已。即便是持有者本人,也會因此失去熱情與動力,更談不上發揚與承繼。所以從廣義上說,“非遺”的“傳承者”并不能以個體論,而應該以群體來論。群眾文化正是根植于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和藝術,恰恰滿足了“非遺”傳承主體的群體性要求。
(二)“非遺”與群眾文化起源與發展基礎相同
“非遺”是人類的文化傳承,是數千年意識形態、智慧凝結的實存形態,是以生活化、藝術化的形式對社會變遷和時代精神進行記錄、反映和再創造的過程,而我國的特色群眾文化也是我國民族特色和生活習慣的展現,因此兩者的起源與發展有著共同的基礎。
(三)群眾文化受到非遺的滋養
盡管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人們的審美發生了一定的改變,但是“非遺”作為極具代表性,并且是比較成熟的文化,具備一定的先進性和時代性,能夠為群眾文化的發展提供思路。另外“非遺”的表現形式較為靈活,與群眾文化的貼合性和適應性較好,能夠在群眾文化的各個層次得到滲透,因此,比較容易被大眾接受,起到滋養與促進的作用。
二、非遺在群眾文化中的價值體現
(一)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與“非遺”有著緊密聯系
隨著我國物質生活水平的提升,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在我國社會發展與進步中占據的比重越來越大,是國家發展、民族進步的重要思想保障,也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精神助力。但是,相較于物質而言,思想的滲透與轉變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因此,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也要不斷創新方式方法,豐富渠道,全方位、多角度地滲透到群眾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這個過程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與“非遺”建立起了密不可分的聯系,兩者互相促進,協同發展,比如利用我國傳統佳節的特色活動進行傳統文化的宣傳便是兩者共建的代表之作。重陽節的登高,傳遞了“尊老、敬老”的道德觀,端午節的賽龍舟、包粽子等群眾文化活動喚起了人們對偉大詩人屈原的紀念,也對我國傳統詩詞文化進行了宣傳。人們在參與傳統節日活動時,感受到了“非遺”的魅力,更得到了思想的熏陶,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題中之意。
(二)群眾文化無法脫離“非遺”而獨立存在
在當今世界,文化已經成為了衡量國家實力與競爭力的關鍵所在,在我國,群眾文化與“非遺”是助力社會文化發展的重要動力,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非遺”豐富的內涵為群眾文化提供了養分,而群眾文化為“非遺”傳承提供了載體,擴展了受眾,兩者發展式地融合,共同促進了我國社會文化的繁榮與創新。
三、結語
綜上所述,“非遺”是我國文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其精髓所在。當前,我國群眾文化與“非遺”已經建立了緊系的聯系,同時“非遺”在群眾文化的發展中也有著重要的價值體現,一方面與群眾文化一起,共同助推我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體系的構建與完善,另一方面它豐富的內涵為群眾文化的創新、發展提供了養分,促進了它的發展與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