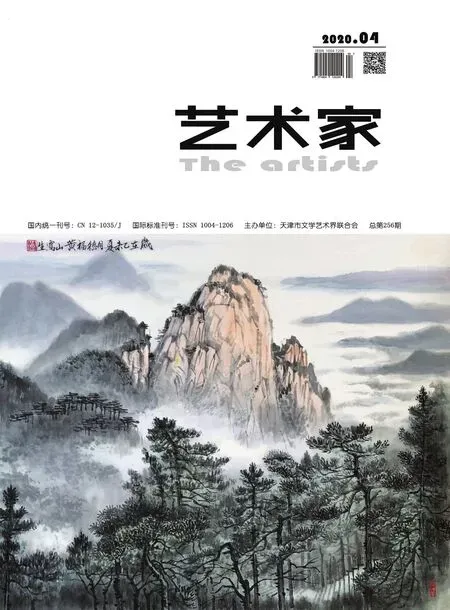淺談戲曲舞臺道具藝術之功能
□劉海英 定西市非物質文化保護中心
道具是我國傳統戲曲中舞臺美術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道具在戲曲中反映人物的生存環境及事件與人物的相互關系,對事件的起因起到開窗明意的作用。
一、傳統戲曲道具
中國戲曲在高度繁榮時期出現過諸多頗有寫意之美的道具,單就以道具為名的戲就有很多,如《鎖麟囊》《琵琶記》《玉簪記》《拾玉鐲》《寶蓮燈》《紅燈記》《掛畫》《八大錘》等。每一種道具從使用的角度、審美的意義、涉獵的領域分析,都是為了服務劇情、塑造戲曲舞臺形象、揭示人物心理、交代戲曲環境背景、揭示人物身份、表達特定情感、烘托氣氛及渲染人物情緒等,戲曲舞臺道具諸多特點的應用都有其獨到的功能意義。
二、戲曲舞臺道具功能
戲曲舞臺道具功能之一,從嚴格意義上來講,隸屬舞臺藝術造型元素的范疇,與布景、燈光、服飾、化妝等各種造型藝術一樣,構成完整舞臺視覺形象的一部分,并參與到戲曲演出中,甚至會為一整出戲的線索、推動劇情發展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拾玉鐲》,玉鐲左右著劇情的發展,玉鐲本是傅朋給孫玉嬌的愛情信物,卻成了殺人的罪證,是全劇的核心道具,也就是說沒有玉鐲,也就沒有劇目《法門寺》之說。
戲曲舞臺道具功能之二,可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物心理。演員與道具產生聯系,即憑借道具完成自我展示來塑造劇中人物,那么這一非要出現在舞臺上的道具必須有其價值,甚至有些時候是以達到物隨戲變人變、隨規定情境而變的絕妙。例如,《殺廟》中的韓琦,手持駙馬所賜之刀,追殺秦香蓮母子,按常規,韓琦進廟持刀殺了母子三人,回宮交差完事,當秦香蓮說出原委,才知陳世美殺妻,出于義憤,反贈銀兩,助母子出逃,又想到要回宮交差,駙馬要刀頭驗紅,在殺與不殺之間糾結,終于良知戰勝邪惡,持刀自刎,成功塑造了韓琦的正義形象,一把鋼刀成了包文正鍘陳世美的有力證據。
戲曲舞臺道具功能之三,可交代劇中環境背景,揭示人物身份。戲曲雖為綜合藝術,但多數劇目以講故事為根基,歌舞也好,戲曲也罷,無關乎表現形式,而舞臺上的道具承載著故事的一部分,就是故事的基本要素,包含時間、地點、人物等。傳統戲中的龍椅、大印、圣旨、文房四寶;現代戲中的高腳杯、電話機、水壺等,以及絢麗的風景,無非都在向觀眾敘述著劇中故事發生的時間、地點和劇中人物的身份、品味。這都需要道具根據劇本提供的場景,依據人物的身份、階層一一設計出來。
戲曲舞臺道具功能之四,也可表達特定情感,烘托渲染氣氛及情緒。道具往往伴隨演員在舞臺上同步出場入戲,不僅講述著主人公周圍的環境,而且也講述著他們本身的理想、興趣、愛好,講述著他們心靈不可見的活動,甚至當主人公的形象在舞臺上已不復存在的時候,道具仍能“講述”他們身上發生的故事,“延續”他們的生命,而且還能突出主要人物的精神世界。例如,在古典劇《竇娥冤》中的殺場片段,下場口設一根竹竿,上面掛一吊七尺白簾,過去曾用油瀝子兌紅藥水噴灑,現在人們改進成可用針管吸上紅顏料去噴,很形象地表現了斬竇娥時血濺七尺白簾的場景,更增加了舞臺殺人場面的陰森氣氛。再如,《紅燈記》中的李玉和第一次上臺,“手持紅燈四下看,上級派人到龍潭”,舞臺側旁則是火車站前的粥棚,喝粥的人來來往往,觀眾一看,時間、地點、環境、主人公身份,一目了然。李玉和被日本鬼子殺害,李奶奶給鐵梅講述了紅燈的故事,是革命和紅燈將他們又聚成一家人,鐵梅再次手舉紅燈,繼承先輩遺志,繼續完成爹爹未完成的革命事業,以“打不盡豺狼,決不下戰場”的決心,終于將密電碼送到北山游擊隊的手里,一舉將敵人殲滅。紅燈照亮革命路,革命自有后來人。一件普通的鐵路信號燈——紅燈,它在劇中從頭至尾,貫穿全劇,《紅燈記》最能體現道具在劇中的功能和意義,紅燈的故事撼動觀眾的心魂,不得不使人肅然起敬,使人們情緒為之激動而振奮。
戲曲舞臺道具可以說是舞臺藝術的一個剪影,其能揭示功能,但又不能涵蓋整個舞臺藝術之美,所占比例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有時能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道具與戲曲舞臺上所有組成部分一樣,誕生于戲曲,又服務于戲曲,歸屬于戲曲藝術本源,而戲曲藝術發展至今,舞臺道具的定義也依然被定義為“除布景裝置外,舞臺上的一切陳設、用具和演員攜帶的物件”,其他舞臺藝術隨著藝術和時代的發展,在原基礎上可以超越變更,唯獨戲曲舞臺道具藝術,是不能隨意變動、更改的,從更深意義上來講,道具是反映事物存在的“眼睛”,又透視著整個事件的行為和目的,以物的存在反映事件的特性,這便是戲曲舞臺道具藝術獨特的功能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