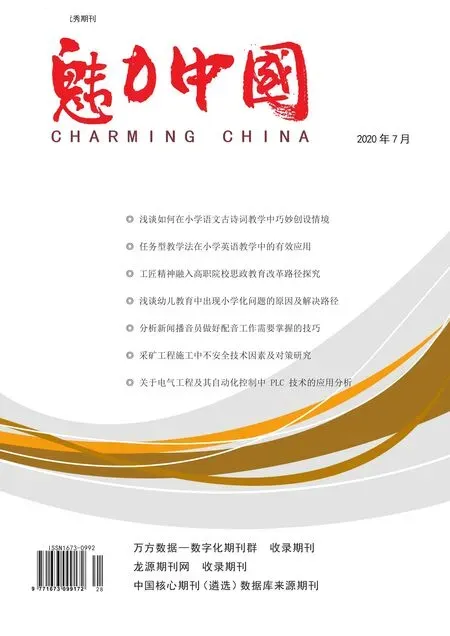區域性民間信仰的建構
——以臺州地區胡公信仰為例
(臺州技師學院(籌),浙江 臺州 318000)
胡公,民間稱胡相公、胡公大帝,是金、衢、嚴、臺等地民間信仰的區域性神祇,在浙東地區影響尤深。胡公原名胡則(963—1039),北宋前期婺州(明清金華府)永康縣胡庫村人,宋代婺州第一個進士。他曾在睦州、溫州、信州、福州、杭州、池州等地任地方官,“逮事三朝,十握州符,六持使節”,[1]所到之處皆有政績。《宋史》稱胡則“果敢有材氣”。[2]范仲淹為其作墓志銘,稱贊他“進以功,退以壽,義可書,石不朽,百年之為兮千載后。”[3]胡則以奏免衢婺兩州身丁錢(人頭稅)而為百姓深切感念,后在民間和朝廷共同推動下,變成屢顯靈跡、“若水若旱,若疫若癘,有求無不應,有禱無不答”的萬能神。
胡公信仰延續千年,至今仍有較大影響。金華永康作為胡則家鄉,是胡公信仰的核心區。臺州是胡公信仰的輻射區,同胡公信仰核心區永康相比有獨特之處。臺州用自己的方式,結合地域特色,在中心之外構建了包括信仰標志、信仰心理和信仰行動在內的區域性信仰綜合體系,這也是臺州地區胡公信仰延續至今的重要原因。
一、建廟立祠,另一種“在場”——胡公信仰的標志化
胡公信仰是臺州民間信仰的重要組成部分,最明顯最直接的證據,就是史載九個縣(市、區)皆建有胡公廟(殿)。時至今日,除玉環胡公殿被毀無存外,其他各縣(市、區)皆存胡公廟(殿)。僅天臺一縣,見諸統戰部門所編《一廟一故事》的胡公廟(殿),就有7 處之多。臺州現存規模最大的胡公廟,是天臺方山胡公廟,廟中刻碑題壁,對胡公事跡、胡公與方山關系記述較詳。據《方山胡公廟簡史》載,該廟建于南宋咸淳二年(1266)。若記錄屬實,此廟當為臺州最早的胡公廟。仙居皤灘胡公殿也有碑記,說此處廟宇建于南宋期間,具體時間無考。據此兩處胡公廟(殿)推斷,臺州的胡公信仰最遲從南宋開始。
學者陸敏珍認為,胡公廟最早出現于北宋宣和年間(1119-1125),紹興年間(1131-1162)延伸到方巖以外臨近地區,逐漸擴展到衢、婺。[4]元明清時期,胡公信仰繼續擴散,到清朝達到鼎盛,“浙東千里,幾無一邑一鄉無公廟”[5]。成書于清光緒年間的《臺州府志》卷五十四如此記載黃巖胡公廟:胡公廟,俗名方山寺。在縣西南永寧山上,祀宋永康胡則。康熙己巳重建,乾隆辛卯重修,咸豐辛酉寇毀,同治初重建。[6]《臺州府志》卷五十五對仙居胡公廟有記載:胡公廟,在縣西四十里皤灘鎮,祀宋侍郎永康胡則,各鄉皆有廟祀,不能盡志。[7]
胡公信仰以胡則家鄉金華永康為中心,逐漸輻射臨近地區,遍及浙東、杭州等地,特別是胡則曾經任職的地區,其信仰尤盛。胡則生前并無在臺州為官,其政績也并無福澤臺州百姓,但胡公信仰卻對臺州民間影響很深。胡公信仰在臺州形成乃至繁盛的標志,就是胡公廟(殿)的建立。胡公廟建成后,祈福、祭禱、求簽等信仰活動便有了固定場所,民眾對胡公的信仰便成了一種社會宣示。作為精神內容的意義如果不轉換為具有一定物質形式的符號,是不可能在時間和空間中得到傳播和保存的。[8]在這其中,廟(殿)及其中的高大胡公塑像,便以一種虛擬的“在場”代替了胡公神的“不在場”,增加了“一切都在胡公神視界”的莊嚴感。法國著名詩人馬拉美說,“如果冥思默想卻不留痕跡,那它總歸會逐漸消逝的。”[9]“由于保留了痕跡,才使個體的記憶客觀化,具體表現出它的社會性,并在不同的個體中體現出來。”[10]
臺州盡管不是胡則生前任職所在地,但也經民間選擇而成為胡公信仰區,以建廟立祠方式參與了胡公信仰的構建,成為浙東胡公信仰圈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沾親帶故,與“我”相關——胡公信仰的心理認同
杭州、嚴州、溫州等地,利用胡則曾在這些地方任過地方官的經歷,杜撰出了胡則在任期間,曾給當地百姓帶去恩惠的傳說。至于那些與生前胡則扯不上關系的地區,如縉云、海寧等地,其信仰可能是受產生于婺州的胡則信仰的影響而出現的。[11]在臺州,民間以各種傳說構建了胡公的形象,實現了胡公神的本土化。
一種為“友誼說”。《方山胡公廟簡史》載:方山下胡崷村季氏祖先季孟賓與胡則同朝為官,前者為吏部侍郎,后者為兵部侍郎,互相傾慕。卸任后,胡則與季孟賓同游方山,胡深為方山美景吸引,表示死后愿長伴方山。胡則去世后,季孟賓囑咐子孫為胡塑像立廟,后季氏第八世孫季斯可完成祖先遺命,獨資建成胡公廟。胡崷村季氏宗譜里,也有這個記載。第二種為“親眷說”。仙居皤灘古鎮胡公殿內碑文記載:“胡公之妻陳氏思蘭是皤灘人士,對胡公具有敬愛之心。之所以在南宋期間建造胡公殿。”范仲淹作《胡公夫人陳氏墓志銘》,說陳思蘭出身“金華郡之令族”。[12]目前尚無證據證明陳思蘭是皤灘人。第三種為“祖先說”。黃巖高橋街道高橋頭村,流傳著胡則為村民老祖宗的傳說,村里建靈福廟就是祭祀他。據歷代《黃巖縣志》,靈福廟始建于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13]第四種為“斷案說”。天臺白鶴天宮自然村村民說,胡公為官時曾路過天宮村,斷案時無案桌可用,就拿一塊石板代替,這塊石板至今還保留在天宮廟。
上述各說是胡公信仰在臺州傳播的主觀因素,它們拉近了信眾與胡公神的心理距離,讓胡公信仰獲得了傳播的心理基礎。這與胡公在寧波等地變成水神是同樣的道理,即胡公神借此實現了本土化。“改變或重新編撰傳說,使胡則的生前義行、死后靈異傳說與各個地區掛上鉤,由此這些地區也有了祭拜胡公的理由。”[14]
三、廟會興盛,神人共娛——胡公信仰的行動體現
胡公崇拜對民間產生深遠影響的另一表現,就是廟會的舉辦。以天臺為例,“每年農歷八月十三胡公壽誕之際,各廟均舉行規模盛大的祭祀和廟會活動。”[15]天臺方山胡公廟會始于1723 年,胡公壽日之時,從農歷八月十一晚上開始演戲,八月十二演出通宵達旦,八月十三結束。時至今日,天臺方山胡公廟會、白鶴天宮自然村胡公廟會依然盛行。仙居朱溪懸空寺也舉辦廟會,只是沒有演出,信眾活動以祈福為主。
胡公廟會既為信眾提供了互相交流、溝通感情、自我凈化的機會,也增加了集體拜祭的莊嚴感,將個體活動上升為集體一致行動,更能增加神靈崇拜的同理心。民間信仰作為一個社會子系統對自身系統內個體與群體的能動作用:民間信仰對信徒個體(群體)具有個體社會化功能、心理調適功能、交往交流功能。[16]每逢廟會活動舉行時,許多村民借機聚在一起嘮起了家常,同時一些出外打工的村民也加入了進來,胡公信仰事實上提供了一個村落領域交流的難得機會。[17]藉由廟會,信眾實現了自我認同、群體認同,達到了內外和諧,其積極作用是不能忽視的。
宗教通過某種特定的儀式把社會價值觀念神圣化,使人們按照既定的社會秩序來約束自己,使行動規范有序,從而對社會起控制作用。這種超自然的神秘主義對人們的心理具有調節作用。[18]一種說法認為,舉辦廟會是為了取悅胡公神,如果胡公廟所在村并沒請戲,那么胡公自己也要化身為老者以村民名義請戲。但從實際功能來看,娛神根本上也是出于信眾的主觀需求,畢竟個人愿望的滿足是靠神來實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