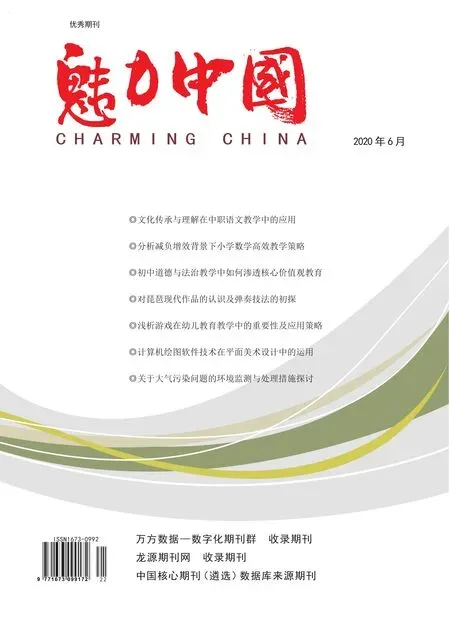中國古代禮與法對當代社會的影響與啟示
(江南大學,江蘇 無錫 214122)
一、中國傳統的禮與法的發展
在西周之前,法律制度仍以“奉天罰罪”、天意的神權法思想為指導,主張以占卜為主要司法手段的神明裁判。但自西周起,周公制禮,將夏禮、周禮發展成一整套以維護宗法等級制為核心的行為規范,成為治理國家的唯一準繩。因而,在西周,法律的主要形式看似是禮和刑,但在一定意義上,刑也只是由禮分化出來的一部分,禮實質上具有法律甚至國家根本大法的性質。禮的范圍十分廣泛,由社會風俗習慣直至國家關系、軍隊征伐、典章制度等諸多方面,不同社會地位的參與者都有各自不同的、嚴格的具體社會規范。可以說,禮是周朝法制的基本精神。
春秋中期以后,雖然禮樂文化秩序逐漸瓦解,但是經過孔子的加工,很多內容仍然對后世具有重要影響。同儒家的“禮治”相反,法家所提倡的“法治”則反對宗法等級制和世襲制,強調法是用以規范人們行為的客觀、公正的準則,具有權威性和普遍約束力。但也因其極端強調國家利益而忽視個人利益,難以維護社會的長治久安。
雖然秦朝采用嚴刑峻法,甚至焚書坑儒徹底摒棄儒家傳統,但儒家思想之火并未熄滅,漢及之后的統治者大多用儒家之禮來粉飾法律,形成了“外儒內法”的局面。漢代董仲舒“春秋決獄”,以儒家經典指導司法審判,代表了禮已經滲透進司法領域,統治者引禮入律,推動了法律的儒家化。至唐代,發展為“禮本刑用”,禮是根本,刑不過是為了保證道德施行的強制性懲罰手段,其實質實仍為外儒內法與泛道德思想現實政術的運作。
二、禮與法對社會的影響
必須承認,禮法結合確實對社會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一方面,禮為人們提供了一套道德上的行為模式,規范了人們的道德行為,又通過一系列的規范維護傳統倫理秩序,形成家族本位、倫理為重的觀念。另一方面,古代法律的表現形式多為刑,且刑罰手段多樣,可以切實維護整個社會的底線。法具有強制性,并對社會成員具有普遍約束力,也因而可以切實保障禮的實施。伏爾泰在《風俗論》中言:“在別的國家,法律用以治罪,而在中國,其作用更大,用以褒獎善行。”與禮相結合的法在懲惡的同時揚善。
但是,我們也要看到禮法結合所帶來的消極影響。中國古代一直沒有實現真正的法治,而是以人治局面為主,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長期實行禮法結合、法律倫理化的結果。以道德精神指導司法實踐便很容易引起隨意解釋的情況,有損法律的權威性和普遍性。中國今天的人情社會也與之不無關系,因為中國社會的鄉土性,自古時起,就依靠禮治來維護秩序,法制觀念淡薄,以至于在現代社會,人們仍然普遍缺乏對法律的尊重和信任。
再者,以法律保障禮的實施雖然確實具有一種道德上的引導作用,但是同時也意味著強迫性道德體制的形成,在這樣的社會中,人們所謂的道德可能不過是迫于法律的偽道德。而禮的規范并不都具有積極意義,此時再以法律進行強制保障,只是在鞏固錯誤。事實上,在封建社會形成后,禮治所維護的是不平等的君主專制集權等級社會秩序。而在家國同構的舊社會中,父權又是家庭關系的核心,禮嚴格維護父權,全面確認家長的權威;嚴格維護夫權,確保丈夫的優越地位。這實質上又造成了家庭內部的不平等,尤其在現代社會已經明顯過時。
三、禮與法對當代社會的啟示
我國現行的一些法律大多是借鑒或移植西方和日本等發達國家法律的結果,對中國社會的特殊文化傳統不具有針對性,因此在實施過程中難免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而禮與法卻是真正在中國自身的社會背景之下生根發芽的,有針對性和延續性。基于對禮與法的利弊認識,以及二者對當代社會的持續影響,我以為,禮法結合的治理方式仍然對當代社會具有啟示作用,我們仍然可以從中反省或者說吸收一些有價值的東西。
法所代表的是社會的公平正義,而禮所維護的卻是社會的等級秩序,這兩者其實是有實質性的矛盾的。在古代法制中,禮總是高于法,因此社會的公平并沒有真正實現,但在我們提倡“法治”的現代社會,法才是、也必須是維持社會秩序的根本。只有堅持依法治國,中國才有可能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法治國家,才有可能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
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要徹底摒棄禮。中國歷史上也曾經經歷過這樣的迷茫期,在新文化運動中,人們高舉著“民主”和“科學”的大旗,而喊著“打倒孔家店”的口號。這樣全盤否定禮也同樣是偏激的,錯誤的。法所提供的行為模式只是最低級的道德,如果一個國家只依靠法律來維護社會秩序的話,顯然是行不通的。并且,與古代社會相反,人們長期被壓抑的個性漸漸解放,反而形成了以自我為中心的社會,而禮注重家庭利益、國家利益,恰恰可以幫助彌補這一點。我們所要拋棄的,是禮中的等級觀念,但仍可借鑒其對道德教化的重視,對人格的尊重,因此其中符合時代發展潮流的道德規范仍應加以保留。但禮一定不能越過法,法一定是這兩種手段中的根本。
綜上,禮與法,是維護社會秩序的兩種互補的手段,二者都不可或缺,是當代法治社會的有機組成部分。而我們要做的,就是以辯證的眼光看待并合理運用,達到二者的平衡,從而推進我國的法治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