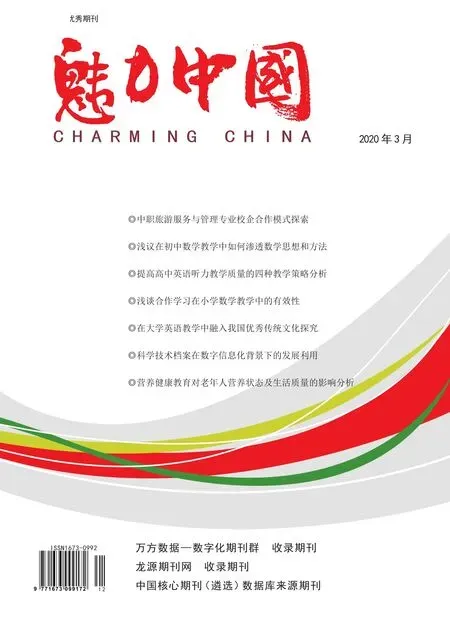從法律角度探析我國共有產(chǎn)權(quán)房制度
(河北大學(xué),河北 保定 071002)
一、共有產(chǎn)權(quán)房綜述
(一)共有產(chǎn)權(quán)房概念
共有產(chǎn)權(quán)房,是指政府作為主體以將房屋的產(chǎn)權(quán)比例化的形式,低價(jià)出售給中低收入家庭,使得購房者和政府按各自的出資比例擁有保障性住房部分產(chǎn)權(quán),并取得房屋的占有、處分、受益等相應(yīng)權(quán)利。地方政府將部分土地出讓的收益低價(jià)配售給符合條件的家庭,保障對(duì)象與當(dāng)?shù)卣炗喓贤s定雙方各自所享有的產(chǎn)權(quán)份額,形成共有產(chǎn)權(quán)房。
(二)共有產(chǎn)權(quán)房在我國的歷史沿革
盡管共有產(chǎn)權(quán)模式的發(fā)展在英美新等國已經(jīng)進(jìn)入相對(duì)成熟的階段,其在我國的歷史相對(duì)較短。2007年3月,淮安市政府出臺(tái)了《民生幫扶“九大工程”實(shí)施意見》,在全國首創(chuàng)以出讓土地的方式構(gòu)建共有產(chǎn)權(quán)住房保障模式。2017年9月,北京市正式將共有產(chǎn)權(quán)房界定到“住房供應(yīng)制度”中,并于9月30日正式實(shí)施,標(biāo)志著共有產(chǎn)權(quán)房在中國的發(fā)展迎來了小高峰。由此,各城市通過試點(diǎn)實(shí)踐,不斷完善改進(jìn)并形成了各具地方特色的模式化管理方式。
(三)完善共有產(chǎn)權(quán)房制度的意義
完善共有產(chǎn)權(quán)房在目前居高不下的房價(jià)面前,可緩解“夾心層”迫切的購房需求與房價(jià)居高不下的矛盾,實(shí)現(xiàn)人民住有所居的理想; 其退出機(jī)制使政府通過部分產(chǎn)權(quán)溢價(jià)等方式回收資金,重新投入到共有產(chǎn)權(quán)住房體系,實(shí)現(xiàn)資金的循環(huán)利用,減少財(cái)政負(fù)擔(dān); 還可以避免經(jīng)濟(jì)適用房領(lǐng)域的倒賣套利行為,減少腐敗行為。
二、現(xiàn)行國內(nèi)共有產(chǎn)權(quán)房現(xiàn)狀與不足
(一)理論層面
1.現(xiàn)行文件缺少對(duì)房產(chǎn)“共有”的法律定性共有產(chǎn)權(quán)房雖明面上為政府與購房人的按份共有,但也存在購房人享有完整使用權(quán)、缺少自有處分其份額的權(quán)利等特征,與傳統(tǒng)按份共有的特性不一。這種認(rèn)知偏差雖不會(huì)影響共有產(chǎn)權(quán)房的正常管理,但不僅使得共有產(chǎn)權(quán)房在法理上與傳統(tǒng)物權(quán)無法緊密銜接,在發(fā)生主體間的矛盾時(shí)也極有可能成為政府方所存在的疏漏,反而不利于維護(hù)其防止投機(jī)行為的功能。
2.制度設(shè)計(jì)不夠全面
(1)共有產(chǎn)權(quán)房缺少統(tǒng)一有效的法律文本規(guī)制。目前在共有產(chǎn)權(quán)房方面,擁有全國范圍效力的文件只有住建部等六部委在 2014 年發(fā)布的《關(guān)于試點(diǎn)城市發(fā)展共有產(chǎn)權(quán)性質(zhì)商品住房的指導(dǎo)意見》這一其他規(guī)范性文件,制定時(shí)間早且效力不高,與在其后制定的上海、北京的《共有產(chǎn)權(quán)房管理辦法》相比,存在滯后性,只能發(fā)揮保底作用,而缺少真正有效的規(guī)制,且各地也面臨同樣的問題。
(2)房屋土地供應(yīng)問題。雖然共有產(chǎn)權(quán)房的制度確實(shí)有效地減輕了購房人的經(jīng)濟(jì)壓力,有其需求之所在,但在實(shí)際購買上,各地均面對(duì)不同程度的“供過于求”的壓力,以北京為例。北京自2017年9月實(shí)施共有產(chǎn)權(quán)房政策起,在3個(gè)月內(nèi)就遇到了3塊共有產(chǎn)權(quán)房土地流拍的現(xiàn)象。
(二)實(shí)踐管理層面
雖然目前各地對(duì)共有產(chǎn)權(quán)房在準(zhǔn)入與再上市方面均做了較為嚴(yán)格的限制,但在管理上較為寬松,易出現(xiàn)漏洞。如淮安市在早期售房( 不附電梯)時(shí),未考慮到當(dāng)時(shí)購房人大多為中老年人的狀況,而使得部分設(shè)置于5--6層高的共有產(chǎn)權(quán)房中居住著老年人、兒童等特殊年齡群體,對(duì)其生活起居造成一定的不便。且在走訪中,我們發(fā)現(xiàn)了極少數(shù)房屋存在“人去樓空”的現(xiàn)象。
三、改進(jìn)措施與未來展望
(一) 法律定性“按份共有”,建立全國性共有產(chǎn)權(quán)房法律法規(guī)各地出臺(tái)的文件均不同程度模糊了“按份共有”的具體內(nèi)涵,使得共有產(chǎn)權(quán)房在法理上與傳統(tǒng)物權(quán)銜接出現(xiàn)裂痕,容易造成政府管理疏忽。為防止這種情況發(fā)生,就必須對(duì)“共有”進(jìn)行法律定性。要區(qū)分共有產(chǎn)權(quán)房與傳統(tǒng)物權(quán)的“共有”,把握其在法律上的定性。共有產(chǎn)權(quán)房的“共有”兼具有私法上的所有和公共福利性質(zhì),政府和購房者并不是簡單的按份共有人共同占有共有物,政府需要?jiǎng)討B(tài)監(jiān)管購房者的收入情況,及時(shí)安排購房者進(jìn)入或退出,其具有的行政性以及共有人之間的權(quán)利義務(wù)的特殊性需要明確。
(二)明確共有產(chǎn)權(quán)房的準(zhǔn)入機(jī)制、退出機(jī)制等
1.準(zhǔn)入機(jī)制
共有產(chǎn)權(quán)房制度可嘗試允許其它資本或社會(huì)機(jī)構(gòu)進(jìn)入,多渠道保障房屋來源,推動(dòng)制度走向市場(chǎng)化。隨著共有產(chǎn)權(quán)房主體資格的降低,房屋需求量持上升趨勢(shì),政府資金壓力與供地問題都將凸顯。因此共有產(chǎn)權(quán)房制度需要從“政府—購房者”模式轉(zhuǎn)型,可參考美國共有產(chǎn)權(quán)制度,重視市場(chǎng)的作用,鼓勵(lì)私人企業(yè)或者機(jī)構(gòu)參與經(jīng)濟(jì)調(diào)節(jié)。這樣既能確保資金充足、減少政府的資金壓力,也能保證房源供應(yīng)。
2.退出機(jī)制
共有產(chǎn)權(quán)房的全部產(chǎn)權(quán)購買需要相當(dāng)長的期限,在此過程中購房者的經(jīng)濟(jì)條件可能發(fā)生好轉(zhuǎn),甚至不再符合購房條件。根據(jù)李欣欣的研究,新加坡通過頒布《建屋居住法》等有關(guān)條例,規(guī)定申請(qǐng)購買家庭的月收入不得超過 800 新元,超過該標(biāo)準(zhǔn)應(yīng)當(dāng)適時(shí)退出。我國可以參考此類做法,動(dòng)態(tài)監(jiān)控購房者收入水平,督促不符合購房條件者及時(shí)退出,將共有產(chǎn)權(quán)房提供給其他需要住房的申請(qǐng)者。
四、小結(jié)
共有產(chǎn)權(quán)房制度從民生出發(fā),以政府入房屋產(chǎn)權(quán)的方式,分擔(dān)民眾買房的經(jīng)濟(jì)壓力,具有其先進(jìn)性。但各試點(diǎn)城市在實(shí)踐中,往往因各種局限使得制度無法長久地運(yùn)行。此類問題的出現(xiàn)多與地方政府直接從行政角度出發(fā),未使得主體權(quán)利義務(wù)法定化有關(guān)。在切實(shí)了解目前制度存在的問題的基礎(chǔ)上,采取措施,使得共有產(chǎn)權(quán)房制度呈現(xiàn)房源多樣化、管理透明化、監(jiān)管動(dòng)態(tài)化等特點(diǎn),能夠使制度具有更大的適用范圍,為更多“夾心層”人群減輕購房經(jīng)濟(jì)負(fù)擔(dā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