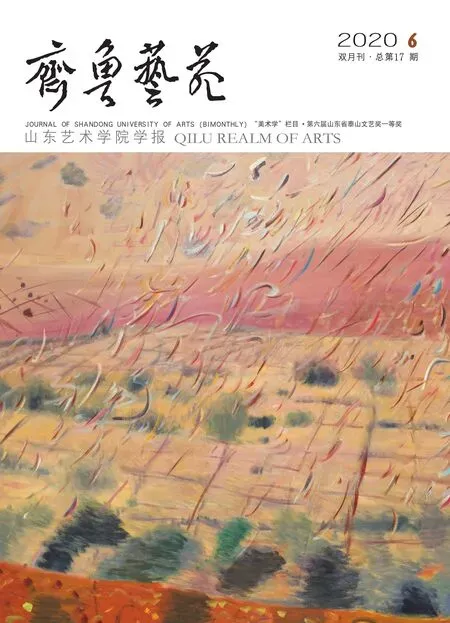媒介、新受眾與在線思維:新媒體時代電影受眾教學方法改革研究
謝 辛
(北京電影學院視聽傳媒學院,北京 100088)
新時代賦予我們新的認知和新的體驗,不僅指向時代、社會、文化等傳統宏大視角的場域性表征,更與新生存樣態緊密關聯。在新時代,我們借助新媒體,成為新受眾,人與智能化關系的融合探討頻現。就其根本——受眾而言,對受眾樣態的研究素來是傳播學理論研究和現象分析的主流,丹尼斯·麥奎爾(Denis McQuail)《受眾分析》(Audience Analysis,1997)對受眾理論進行了詳細的理論化闡釋,是后人選擇受眾研究的理論依據和充實完備的基石。而作為當下新時代新媒體環境中的新受眾,在線教學對教師/學生的傳-受雙方均產生不同以往的影響力,尤其是電影受眾教學受到電影本體、受眾、媒介、文化等多元因素的影響,其相關課程教學方法改革也迫在眉睫。
一、在線教學媒介到達效果分析
(一)教師/學生的傳—受表征
受眾(Audience)是對“傳播者-受眾”形成的傳-受關系中“接受者”(Receiver)的統稱。麥奎爾認為,“受眾被簡單地認為是一個或另一個媒介渠道、這一類或那一類媒介內容或表演的讀者、聽眾或觀眾”[1](P2)。在視聽新媒體時代,由于電影所屬的媒介環境改變,導致電影受眾發生多重形態的變化,呈現出某種拓撲式的重構/再建域視角,傳統意義的電影受眾概念,逐漸轉為具備生產與傳播能力的、傳-受合一的表征,但需注意,傳-受表征依然保有主次之分。
以電影受眾課程的在線教學為例,學生不再是傳統意義的“接受者”,也在教師的控制下具備信息生產與傳播的身份。如釘釘APP授課體驗功能包括連麥互動與點贊,學生對于實時教學的反饋與媒介到達的速率呈正比,但其行為由教師端控制;騰訊會議、小魚易聯等視頻會議平臺,以及雨課堂等慕課平臺更顯性地傾向教師主控性,在教學過程中借助教師端開啟學生視頻,促使學生對于信息的接受從單純的教學轉為對屏幕中所有信息的接受,進而借助截圖、評論、彈幕等功能實現其自主化、多媒介傳播,踐行斯蒂夫妮·諾曼(Stephanie Norman)所述的“You can learn whatever you want!”[2](你可以更自主的學習),從而達到傳-受合一之后更舒適、更開放和具有彈性的心理預期,有利于在較個體化和靜態端的環境中,增強理解學習內容本體的能力,實現較好的媒介到達。
因此,傳-受表征首先指向教師端作為主要“傳者”的控制力。當下出現的諸多“翻車”事件,比如新浪微博熱搜中打開不該播放的視頻、嘈雜的背景聲、教師忘開聲音導致靜音授課等,從某種意義上說,均指向教師端操作失誤。但也由此形成了再媒介化的傳-受主次倒置,學生將視頻截圖、事件以及表情包等上傳至社交網絡,形成對教學形態的再建域。由此給教師在線教學提出挑戰,我們身處視聽新媒體環境,我們生產并實現訊息傳播的前提是——避免出錯。
回溯學界對受眾最原初的理解,來自人們聚集在某個特定地點、場域的行為有關。比如古羅馬競技場內,圍觀人與猛獸爭斗的觀眾,即具有接受者意味的受眾。然而,早期受眾的這種“在場性”也決定其規模數量的標準遠遠低于今天媒介化的社會。新興媒介一次又一次的革新,也將受眾的范圍逐漸擴大,麥奎爾認為今天的受眾,“人數更多,更加分散,也更加個體化和私人化”。當下在線教育環境中,教師/學生的課堂環境屬于O2O形態,教師的“O”與學生的“O”很可能都在獨立的封閉空間內完成,將個體化和私人化的物理空間/心理空間發揮到極致。這也給我們帶來一個事實:媒介,成為新時代受眾生存的主場域,教學內容與形式需要適時的革新。
(二)“塊莖”化生存樣態與媒介到達
從傳統受眾研究視角來看,大眾傳播、效果研究及使用與滿足(Use and Gratification)研究等為主的結構性研究、行為性研究與文化研究構成研究主體,覆蓋受眾生存樣態的全部范疇。如今,對受眾生存樣態的著力點依然與受眾研究本體息息相關,卻又展示出前所未有的“塊莖”式(Rhizome)發展趨向。面對5G時代的到來,人類即將從4G媒介化生存走向5G智能化生存,“塊莖”的流行性與意指性將進一步得以增強。面對不斷井噴的新媒介、新文化,甚至教學方式的變革,我們將如何面對新受眾?也就是我們自身?
1. 分眾層次的“塊莖”化
在大眾逐漸轉為分眾的時代,效果研究的目標指向性和細化程度更為明確,使用與滿足不只局限于學生“使用”網絡“滿足”學習需求,教師“使用”網絡“滿足”教學需求,亦包括家長的監督、打卡甚至與學生同上課等行為,開發者對于軟件問題的反饋和修復,社交平臺對在線教學現象的持續關注等多維層次,都旨在展現在線教學“塊莖”化場域建構已然從單一走向整體的現實。
2. 媒介到達的“塊莖”化
當下新受眾的新媒介載體主要依托互聯網,借助羅杰·克勞斯(Roger Clausse)對媒介到達的五個圈層劃分:最外圈“提供的訊息”(Message Offered)指向潛在的所有傳播系統的受眾;第二圈“可接收的信息”(Message Receivable)指的是接收訊息的最大范圍,也就是潛在的媒介公眾,決定因素在于其是否有網絡、是否下載教學APP、受教育程度等;第三圈“接收的信息”(Message Received)指的是某教學APP的實際受眾;第四圈“注意到的訊息”(Message Registered)指的是打開某教學APP之后,可以學習的課程內容;第五圈“內化訊息”(Message Internalized)指的是受眾在第四圈基礎上,進行更進一步的課程門類學習選擇,表現出更為聚類的特點。當媒介到達第五圈之后,也就實現了教師/學生與家長之間的行為聯動,教學閉環也由此形成。
結合當下在線教學現狀來看,媒介到達的目標受眾(Target Audience)實際上超過預期,如果將教師在線教學的累計受眾(Cumulative Audience)劃定為學生群體,家長則成為“暗指”(Implied)受眾,在教學過程結束之后,又轉化為監督身份,以協助教師完成課程的整體效果。這一過程本身就是“塊莖”式的,顯示出多媒介、多受眾群體的重疊態。
(三)媒介、文化與新受眾
不難看出,互聯網媒介正如馬克·波斯特(Mark Poster)的時代劃分(1)馬克·波斯特將互聯網作為節點,互聯網媒介為“第二媒介時代”,之前的諸媒介為“第一媒介時代”。,顯示其強大的覆蓋面和影響力。互聯網影響我們作為受眾的身份建構/再建構,也影響文化生成。
在線教學形式正式基于互聯網媒介誕生的“互聯網+教育”新形態,借助網絡,實現國內外教育行業的聯動、“屏對屏”教學的落地,倘若技術尤其是5G技術普及之后,更為穩定和高速的技術支撐不再成為渠道阻礙,對于在線教育的認知是否應當轉向適應力、創新力等層面?
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依然回歸受眾本體,學界對受眾研究的重點需從受眾這一關鍵詞本身,移置于對其生存環境和其在傳-受狀態下制造文化能力的思考。
第一,受眾對教學內容的需求與再傳播,取決于“滿足群組”(Gratification Set)的精準度。最初,受眾處于某種媒介主動性狀態之中,媒介為廣大受眾群體提供訊息,等待受眾的反饋,從而引發社會效應;當下,媒介的發展也就是媒介的主動性逐漸增強,受眾的思維與技術進化之間存在某種差異性,這源自年齡、知識結構、職業等多重人類社會的身份維度和認知維度。在這種情況下,不斷進化的新媒介制造與之契合的新受眾。
此時,受眾的雙重性愈加明顯:媒介為滿足受眾而生產和傳播訊息;媒介變革帶來新受眾樣態。如此一來,就呈現出麥奎爾所謂媒介創造的需求(Media-created needs)和受眾“自發的”(Spontaneous)需求的雙重性,而這種雙重性在時代發展和技術進步的過程中,逐漸融合。如今,作為在線教學的接受者(學生、陪讀家長)與自發需求/傳播者(教師)創造需求的融合,更是因為受眾身份從單一受眾,逐漸轉為傳-受合一的維度,而形成更為緊密的關聯,那么如何實現更大范圍但更精準的“滿足群組”?從定義來看,“滿足群組”指的是基于與媒介相關的興趣、需求與偏好等多種可能性而形成或重組的受眾。[3](P41)其中,“群組”概念的引入,表明組成群組的個體之間原本是分散的、并無關聯的。當在不同空間的學生,因為網絡課程而聚在一個虛擬的教室中,此時教師要考慮的是如何用音視頻、白板等課件演示滿足所有學生學懂的目標性,而網絡技術工作者需保證APP使用流暢的效果,而作為群組內部的學生則需實現智能化、網絡化的自我滿足。
第二,在線教學內容涉及傳統/流行等多重文化,但其本體、傳播過程以及衍生文化等均指向流行文化,“品味文化”(Taste culture)概念理應重識。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在1957年提出“品味文化”概念,指“被同一類人選擇的相似內容的總和”,其指向的不是人組成的群體,而是媒介產品的相似性。從甘斯提出的年代來看,后現代的無原則、無中心、消解一切的特質影響廣大受眾的認知度,從而將傳統的意識形態、知識堡壘等打造的群體破除,形成更細化的群體形態。而到了視聽新媒體時代,這種細化程度越來越高。“滿足”的“群組”和“群組”“品味”的文化都帶有新指征,需要新思維的分析和闡釋。尤其對于電影受眾課程而言,電影內容自身所凸顯的文化適應性包含了高度多元的展示,既有電影故事的內核或現實性、或科幻性的驅動,亦有電影受眾或院線渠道、或視聽新媒體渠道觀影的場域區分,諸多變化的表征將課程指向的復雜維度加深,同時也促使教師在教學內容設置中需不斷加強自身“品味文化”的能力。
騰訊會議、釘釘、小魚易聯、雨課堂、云班課等APP在新冠疫情時期的運用,展示出媒介產品的“相似性”,但又因其界面設置、技術穩定性等差異,導致受眾對“相似性”的選擇趨于“滿足群組”的程度。也就是說,大部分人選擇一款APP并產生較好體驗度,將會影響其他群體的選擇。
因此,我們將電影受眾在線教學對應新受眾研究議題,焦點實際上主要指向以下四個方面:
根植當下技術發展影響下產生的受眾諸多樣態,以“身臨其境”的體驗式態度面對受眾和受眾研究。
聯系傳統受眾研究和當下受眾樣態發展現狀,對受眾研究進行有理論的、有思想的深度拓延。
建立媒介生態化思維,注重新受眾賴以生存的新媒介對受眾的影響。
教學需要與時俱進,體會學生的新偏好、新文化和新表征,用心去感知新時代的脈搏,并在這個過程中,強化主導意識和正能量。
二、在線教學方式破冰與到達策略
(一)以“交叉性”為核的教學關鍵詞
鑒于上文所述,無論以受眾研究作為分析教師/學生、家長的理論點,還是從在線教學行為的具體到達效果角度闡釋,都凸顯這一教學方式的前瞻性和創新性。網絡促使受眾之間的交互性增強,而具體到教學的互聯網式建構來看,建構的核心指向受眾依附于多學科的“交叉性”,以及受眾自身文化屬性、媒介屬性、多維需求等帶來受眾身份/關系的“交叉性”。
回溯麥奎爾曾在1994年提出三重傳-受關系模式:傳送模式(Transmission)、表現(Expressive)或儀式(Ritual)、注意(Attention)。可見,三重關系將受眾的身份定義為目標、參與者以及觀看者,也就是訊息到達之后受眾如何處理的方式成為受眾分化和演變的主要內核。而在當下視聽新媒體時代,這種傳-受關系中對受眾身份的認知,已然成為過去式。并不是說研究不再傾力于傳-受關系的演變,而是這種演變過程已經不再是傳-受關系的重心,受眾的新形態從一開始就是包含傳-受兩重身份的,我們應當以一種開放的、創新的視角,來看待受眾,看到新受眾的發生、發展和進化,即教學過程和教學目標的交叉、共融。
從媒介角度來看,當下新媒介的發展速度不容小覷,對電影受眾的理解無法僅限于電影端尤其是院線電影端,受眾觀看的內容與形式多樣化程度不斷加深。我們熟知的網絡電影、網絡劇、網絡綜藝、短視頻、直播等都打造了一批新受眾,主要有以下幾個特征:
1. 年輕化
如新群體樣態——Z世代(1990年代中葉至2010年出生的群體,統指伴隨互聯網、手游、智能手機等科技變革而成長的一代人)的誕生。
2. 媒介使用度較好
無論什么年齡段的受眾,在面對新媒介的時刻,能夠較快接受、較好使用的群體就迅速成為新受眾,而其余受眾與其之間則存在有明顯的媒介“代際”。
3. 媒介思維較強
新受眾對媒介的接受能力普遍超過傳統受眾,同時具備新媒介思維,打破傳統思維定勢,或者,根本沒有思維定勢。
新受眾的新特征,促使教學思路趨近更為開放和交叉的維度,此時的“交叉性”給多學科下設的專業課程教學提出挑戰。如何在電影受眾課程設置與教學中體現“交叉”,從而更好地完成互聯網在線教學目標落地與超預期效果?
(二)聯想性與發散性思維訓練的必要性
根據上文所述,在線教學逐步常態化,當課程名稱發生與時俱進的變化時,課程內容也應有新思路和新布局。教師需在適應在線授課的形式中,深度研究教學內容與受眾需求之間的對應關系,并從主控性角度實現事半功倍的教學效果。
借助網絡媒介的信息供給與獲取的普及優勢,教師可以將教學思路從“面對面”真正走向以“屏”為主導的在線教學視角,比如對聯想性和發散性思維的訓練,將因網絡“塊莖”式的知識覆蓋而使得學生較快、較易獲得可聯系的知識點,并通過再思考的不斷外延過程,將這種知識點的串聯變得更為廣闊,最終也形成基于某個教學知識點的“塊莖”。這在傳統的教室教學中較難實現,原因在于教室環境中的教師是信息中心,其自我的、個體的信息繭房(Information Cocoons)將在無網絡環境中實現學生群體的窄眾滿足,拓展的可能性也基于教師自身是否具有強大的聯想發散思維能力。雖然學生能夠在課下對知識點進行網絡查找和思路拓展,但由于時效性的降低,興奮點、渴求度等均弱于實時的在線教學。也就是說,在線教學過程中遇到的某個可以拓展的知識點,學生可以借助該終端或其他終端等多媒介平臺,實現知識點聯想發散的實時性,從而提高學習效率與到達效果。
基于聯想性與發散性思維訓練的必要性,首先在教學內容上,教師或將理論教學與實踐賦能結合,內容需激發學生潛在的學習興趣,加固學生對課程學習和受眾認知的黏性;注重橫向學科之間的交叉性和跨學科屬性,縱向的、垂直的延伸維度。其次,教學形式則更注重軟件的便捷性與功能性,如小魚易聯的PC端功能略多于蘋果端,對授課電腦終端的選擇有一定的幫助,亦可購買手寫板、演示版等第二塊屏實現授課內容與課堂監控的實時同步操作。再次,在板書設計上,如PPT或需遵循簡約設計理念,抓住核心關鍵詞,用較少的文字、較多的關聯圖表等靜動態結合的內容,吸引屏幕對面的學生;運用好白板功能,借助啟發、引導的思路連接線,引發學生強烈的好奇心與求知欲。如此,既避免在線教學可能源自傳統教學填鴨式的弊端,又能夠契合適應當下屏幕終端觀看的受眾心理需求。但不可忽視的是,在線教學對于教師破除傳統教學思維,進行自主革新的挑戰之艱巨可見一斑。
(三)教學反思推動媒介到達新思路
當教學思維產生主動變革的可能性之后,教師需產生與在線教學過程進行對應的教學反思。比如在線教學的直播形式,年輕教師與年長教師對直播環境的選擇呈現出兩極化的表征,疫情期間因教師/主播的身份關聯、環境背景人物/聲音、五花百門的教具等與教學內容無關的問題,導致在線教學直播成為熱搜。究竟什么樣的環境和教具最適合在線教學?是否應該對接相關產業的落地?
而平臺卡頓、服務器不穩定造成教學無法進行的現象頻出等問題,對于教師而言,又增加一個與教學完成相關的思路,即使用多平臺教學嘗試,從而發現最為適配的平臺,比如某高校教師在疫情期間通過微信群提供經驗:騰訊會議用于講課、雨課堂用于記考勤、SPOC用于作業與習題、微信用于一般性溝通。
當網絡媒介以常態化滲入人們生活中,在線教育實際上也將成為常態化的教學方式。對學生群體來說,優勢在于學習的全面性、交叉性的增強,缺點在于必要的“面對面”互動性和監督力的消解,但筆者認為,優勢依然大于缺點,由此對學生的學習目標提出如下幾點建議:
學生要在學習過程中,自主養成理論聯系實踐的思維方式,將所學知識體系與成果緊密結合當下視聽新媒體業態環境。
需將傳統的“面對面”視角,逐步轉向互聯網以及“互聯網+”所帶來的網絡媒介傳播新載體,以網生代的思維自主培養“屏對屏”教學適應性。
不斷加強問題意識,多思考,大膽試“錯”,多思考、多發散、多拓展,適應全新上課形式,在學習和實踐中感知社會、人性,最終實現認清自我的終極目標。
借助具備“交叉性”的共享資源,對同向課程及拓展課程進行自學,將教師授之以漁的“漁”作為自學能力培養的金鑰匙。
結語
綜上,本文借助電影受眾研究的視角,將視聽新媒體時代從傳統“院線”電影到視聽全影像的教師、學生作為主要受眾對象,研究在線教學方式的媒介到達與傳-受效果,足見到達率之高、效果之精準,傳-受關系也在不斷適應網絡賦予的諸多新能力。誠然,一種新教學方式的全民化普及,需要時間、經費與媒介等多方支持,但最重要的前提指向教學過程的參與者自身的思維轉變,此次疫情特殊時期的在線教學,給我們帶來諸多思考。而隨著智能化的不斷推進,教學方式的革新將進入更新、更具有想象力的領域,對于受眾而言,對傳統思維的挑戰將越來越多,反之亦促使新思維不斷拓延,最終實現人類個體/群體的全面進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