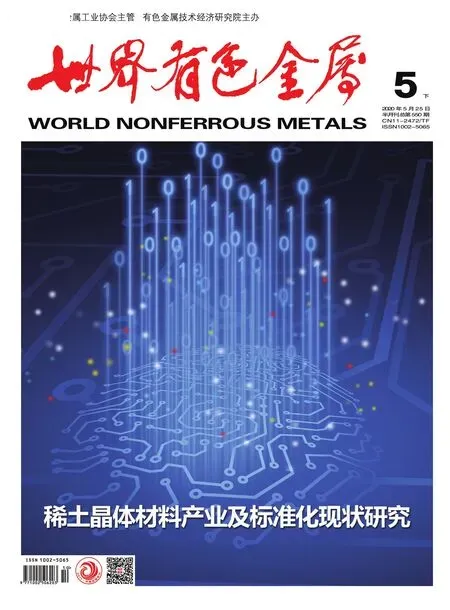德國魯爾區礦業可持續發展戰略概述
郗富瑞,張進德,張德強,余 洋,顏瑞雯
(1.中國地質環境監測院,北京 100081;2.中國礦業大學(北京),北京 100083)
魯爾工業區擁有得天獨厚的資源稟賦,便利的交通區位優勢,在工業化初期,是德國乃至歐洲重要的工業中心,為德國戰后經濟復蘇、創造經濟騰飛奇跡發揮了不可磨滅的重要作用。然而,隨著工業社會的快速發展,資源的過度開發利用使得魯爾區逐漸面臨資源耗竭、生態退化和環境污染的困境,以煤炭、鋼鐵為支柱產業的能源資源富集型城市經濟發展逐步陷入停滯,同時誘發了嚴重的社會問題。為了擺脫城市發展困境,提高城市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并改善人民生活質量,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魯爾區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逐步實施區內資源枯竭型城市的綠色轉型。我國擁有大量資源枯竭型城市,新時期生態文明建設進程中轉型升級任務迫在眉睫。借鑒魯爾區可持續發展的先進經驗,對于我國資源枯竭型城市的轉型發展、加快生態文明建設進程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1 魯爾區發展歷史
魯爾地區(Ruhr)擁有53個城市,人口超過500萬,是歐洲最重要的城市群之一。魯爾工業區是擁有200多年悠久采礦歷史的煤炭基地,硬煤開采可以追溯到19世紀初,并逐步形成了由數百家礦業公司組成的魯爾工業區,在埃姆舍爾河和魯爾河之間塑造形成了一個連續的礦業城市群。在工業革命進程中,這里豐富的煤炭資源為德國新興重工業的快速發展提供了重要的能源保障,并使之成為了德國的“工業心臟”。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經濟騰飛,即所謂的經濟奇跡,與魯爾工業區采礦、鋼鐵、化工行業的快速發展密不可分[1]。然而,從20世紀50年代后期開始,隨著國際能源市場競爭的加劇,本地煤炭資源的逐漸枯竭使得硬煤生產成本逐漸提高,魯爾區采礦行業開始逐步走向衰落。社會經濟發展速度滯緩,失業人口逐步增多。同時,煤炭、能源、鋼鐵和化工產業對于該地區的生態環境和數百萬居民生活條件的負面影響逐漸凸顯。地面沉陷、含水層破壞、水土、大氣污染、土地損毀、地形地貌景觀破壞等礦山環境問題以及地表植被蓋度下降、動植物棲息地破壞、生物多樣性降低等生態環境問題突出。為改變魯爾工業區社會、經濟和生態環境的衰退態勢,魯爾地區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有力措施,開啟了可持續發展的后采礦時代,逐步實施區域的綠色生態轉型升級。
2 區域規劃
區域的可持續發展要求其在社會、經濟和生態等方面應得到同等程度的正向發展,根據Iris Pufé[2]定義的可持續發展目標,區域的可持續發展應在保障人類生存的基本物質基礎、維持社會生產潛力的基礎上,確保區域今世后代持續發展的可能性。煤炭工業不可逆轉地改變了魯爾區的社會、經濟和生態結構,作為以煤炭行業為主導經濟支柱的魯爾工業區而言,要完成城市的轉型升級,需要包括政府、企業、民間協會、普通民眾在內的多個利益體的共同參與,統籌協調多方建議。其中,煤炭企業應承擔區域社會、經濟和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的主體責任。
區域規劃在魯爾區礦業可持續發展進程中發揮了重要的頂層設計作用。魯爾地區區域發展規劃有著悠久的歷史,1920年,魯爾礦區居民聯盟(Siedlungsverband Ruhrkohlebezirk,SVR)成立,SVR的主要任務是通過編制區域性的國土空間規劃,限制重工業生產造成的生態環境破壞來改善居民的生活條件。之后SVR的后繼組織,即魯爾區城鎮聯盟(Kommunalverband Ruhrgebiet,KVR,1979-2004)和魯爾地區聯盟(Regionalverband Ruhr,RVR,2004年以后)繼承了區域規劃任務。如今,RVR是魯爾區重要的公共區間協作組織(Kommunale Zweckverband),其全體成員由城市和地區授權成員組成,其他重要的利益團體,例如工會、雇主協會、體育和文化機構以及環境協會可向RVR提供建議。RVR主要負責編制魯爾區法定區域規劃、進行區域土地開發利用和用途管制,以及區域旅游發展和開放空間設計等工作。RVR的設立在魯爾區各地區成員間建立了有效的聯系,成為了各部門、各行業、各利益團體共商區域發展大計的紐帶。魯爾區作為統一規劃發展的地區聯盟,以區域空間規劃為引領,在地區建設、經濟發展、生態保護等方面能夠發揮各城市比較優勢,調整優化產業結構,因地制宜地開展分工協作,避免了因區域同化發展、惡性競爭造成的資源能源浪費,為魯爾區礦業可持續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3]。
3 礦企責任
礦業企業是魯爾區礦業可持續發展的責任主體。為了保障魯爾區能源資源儲備并確保行業轉型升級動力,魯爾地區大多數硬煤公司于1968年以魯爾煤炭公司(Ruhrkohle AG)為主體進行了合并,隨后重組為魯爾集團公司(RAG Aktiengesellschaft)。為了實現礦業可持續發展,依據德國礦業法規,必須將煤炭勘探、開發和閉坑的全生命周期采礦活動明確納入礦產資源開發規劃中統一實施,特別在閉坑規劃中明確規定了礦業公司應當承擔的善后責任。對于采礦活動造成的礦區生態環境影響,礦業企業必須采取相應措施,達到預期修復治理效果。閉坑治理工作必須根據由當局審核批準的閉坑規劃嚴格執行,未達到預期治理目標的采礦公司或其后繼組織必須承擔相應后果。僅當采礦責任主體不明確時,才由公共部門負責礦后生態修復治理任務。礦企按照礦業開發規劃進行的全周期礦業開采活動,為魯爾區礦業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有利的保障[4]。
4 再利用潛力
礦區再利用潛力為魯爾區礦業可持續發展另辟蹊徑。采礦業不可避免的改變了區域地形地貌,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生態環境影響。然而,通過必要的環境治理和生態修復,礦區遺留下來的工業遺跡和大量地表地下空間為礦區的綜合再利用提供了寶貴的物質和空間基礎。以魯爾區礦業博物館為代表的礦區旅游開發模式充分利用了礦區原有工業設施,真實還原了原有采礦場景,是變廢棄礦區為寶、弘揚魯爾區礦業文化的有效手段。同時,在德國能源結構轉型的戰略背景下,礦區特有的地表和地下空間結構為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利用提供了多種可能性。以廢棄礦堆光伏系統、風力電站、廢棄礦井地下抽水蓄能電站以及廢棄礦井水熱能利用等為代表的礦區新能源開發利用新方式豐富了魯爾礦區綜合再利用思路,是能源結構轉型升級條件下的有益探索與嘗試,為礦業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新的途徑[5]。
5 資金保障
礦業發展基金模式是魯爾區礦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資金保障。為了全面實施煤炭有序退出戰略,2007年,德國聯邦政府根據《硬煤融資法》的有關規定,通過與硬煤生產州北威州和薩爾州、RAG以及采礦、化學與能源工業聯盟(IG BCE)密切協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將原有的RAG分為三個戰略部門:RAG(負責硬煤的開采以及礦區的土地管理和開發)、Evonik(贏創工業公司,負責特種化學品生產)、RAG-Stiftung(RAG基金,由RAG和Evonik共同持有,負責承擔煤炭行業可持續發展的保障資金)以及RAGStiftung投資公司(負責RAG基金的投資運作)。RAG基金會的資產(包括固定資產和投資收入)主要用于后采礦時代礦區工礦廢棄地的治理以及RAG定義的包括廢棄礦區礦井水監測和土地復墾等在內的礦區生態修復永恒任務(Ewigkeitsaufgaben),極大的減輕了后采礦時代公共部門礦區治理的費用負擔。例如,2016年RAG基金會提供了總計3.93億歐元的永久性準備金,不僅應用于礦區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還致力于與煤炭行業相關的教育、科學和文化等領域的項目投資,在推動社會可持續發展方面也作出了行之有效的貢獻[6]。
6 結語
我國礦產資源豐富,長期以來,礦產資源對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國部分礦產資源型城市開始面臨與魯爾工業區60多年前相同的困境。據國務院發布的《全國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規劃(2013-2020年)》,全國共有262個資源型城市。截止2013年9月,我國審批確定了69個資源枯竭型城市,這類城市礦產資源累計采出儲量已達到可采儲量的70%以上[7],它們大都面臨著資源逐漸枯竭、經濟結構單一、產業布局不合理、“重開發、輕治理”,礦山生態環境堪憂等突出問題,礦業可持續發展困難重重。如何擺脫資源枯竭困境,實現城市轉型發展,是擺在它們面前一道亟需解答的難題。
德國魯爾區礦業可持續發展實例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堅持區域規劃的頂層設計作用,發揮區域城市間比較優勢,因地制宜的調整產業結構與布局,開展分工協作;發揮礦業企業的責任主體功能,嚴格按照全過程礦業開發規劃開展礦山有序開發和礦后恢復治理;堅持新發展理念,不斷探索礦山綜合再利用新方法、新模式;建立礦山可持續發展基金,提供后采礦時代資金保障,助推礦業城市轉型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