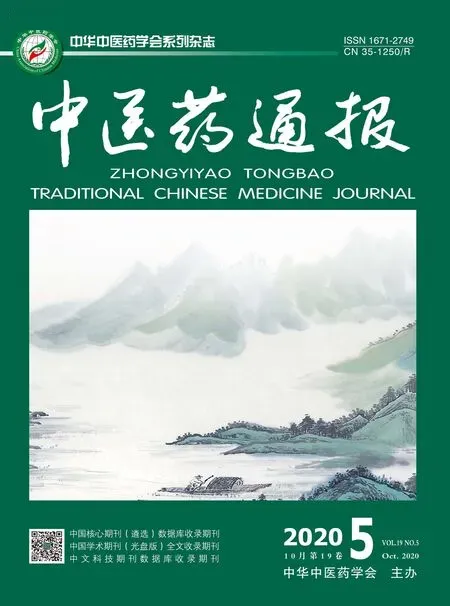六君子湯化裁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恢復期的應用
●張 晶 吳曉晨 陳志斌 王春娥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簡稱COVID-19)是一種新型呼吸系統傳染病,主要經呼吸道飛沫和密切接觸傳播,其發病迅速,傳染性強,易于流行,符合疫邪致病特點,屬中醫“溫疫”“疫病”范疇。而縱觀溫病發展史,葉天士提出“溫病熱變最速……劫傷津液,變證尤速”“熱邪不燥胃津,必耗腎液”;吳鞠通亦有“熱病未有不耗陰者”之論,認為溫病后期“邪氣已去八九分,真陰僅存一二”。歷代醫家多論溫病傷陰,重視“養陰”,但“壯火之氣衰”“壯火食氣”,溫病耗氣傷陽之弊卻易被忽視。COVID-19首發地武漢地處長江流域,境內多潮濕,再兼發病時節正值暖冬又陰雨連綿,故本病為溫邪戾氣兼夾六淫之濕導致。濕為陰邪,又具黏滯之性,濕邪浸漬,易傷陽氣,礙氣機。氣虛或運行失常均可引起人體臟腑功能失調,導致邪氣流連不舍,病勢纏綿難愈。筆者參加了福建省第二批援助宜昌的隊伍,多次參與宜昌當地衛生健康委員會組織的中醫專家組的會診,從溫病濕疫耗氣病機論治,基于氣的生成、輸布與肺脾密切相關,乃從肺脾論治,重視顧護脾土以滋肺金,治愈大量恢復期患者。以下結合筆者治療COVID-19 恢復期患者的經驗,探討六君子湯加減在肺脾氣虛證患者治療中的效用。
1 COVID-19 恢復期的病機特點
《黃帝內經》謂“正氣存內,邪不可干”“邪之所湊,其氣必虛”,COVID-19恢復期患者病情趨于穩定,未再出現發熱、氣促、喘憋、神昏譫語、四肢抽搐及出血等癥狀,但多數正氣已虛。濕邪為患,其性膠著,易結不易散,郁久又有痰、熱、瘀、毒之變,疾病后期呈現虛實夾雜、虛多實少的病機特點。
1.1 肺脾氣虛為本
1.1.1 病理 《溫熱論》云:“衛之后方言氣,營之后方言血。”瘟疫初感,首先犯肺。肺為華蓋,其質嬌嫩,戾氣因其暴烈之性在肺衛短暫交爭后迅速入里化熱,肺熱葉焦,肺氣耗傷,肺失宣降。此期正強邪盛,邪正在氣分劇爭,邪熱鴟張,逼津外越,氣隨津泄,癥見壯熱煩渴、憋悶氣促、便秘不暢、倦怠懶言等。此刻應急投黃芩、石膏、連翹之屬清解氣分實熱,不宜立時補氣以免助長熱勢。若病仍不解則漸入營血,營分受熱,氣隨營耗,血液受劫,氣隨血脫則見神昏譫語、視物錯瞀,或見斑疹隱隱、吐衄便血,當以犀角、玄參、竹葉等清透涼血之品解之;或溫邪逆傳心包,熱毒內閉,正氣外脫,癥見神昏躁擾、動輒喘息、汗出肢冷,則用參附等大補之劑以救時時欲脫之正氣。綜上,在溫病傳變的過程中“壯火”戕伐陽氣以致氣虛,且早期多用苦寒清涼藥物難免有傷脾胃陽氣之嫌,故恢復期邪氣幾去,正氣未復,治病當謹守病機,以氣虛為本,顧護脾胃。另外,葉天士在《臨證指南醫案》中指出“時令濕熱之氣,出自口鼻,由膜原以走中道”,說明濕邪裹挾疫癘之氣傷人,非僅從衛氣營血一途,也可由膜原直中中焦。薛雪認為“膜原者,外通肌肉,內近胃腑”,脾主肌肉,濕疫伏于肌肉筋膜之間,病發則直驅中焦脾胃。脾為濕土,喜燥惡濕,濕為陰邪,最傷脾陽,脾氣虧虛,無力轉樞,五臟六腑、四肢百骸皆不得稟水谷氣,導致五臟虛損,根據五行相生規律,母病及子,肺脾氣虛尤甚。
1.1.2 生理 前言濕疫戾氣耗氣傷陽之病機,那么氣所從來?《靈樞·營衛生會》曰:“人受氣于谷,谷入于胃,以傳于肺,五臟六腑,皆以受氣,其清者為營,濁者為衛,營在脈中,衛在脈外,營周不休。”脾主運化,水谷精氣上承于肺,肺司呼吸,合自然界之清氣生成宗氣,宗氣積于胸中,經肺的宣發肅降功能布散全身,故脾為氣之源,肺為氣之主。氣的生成與運行有賴肺脾的功能協調。肺脾不傷則正氣充足,易于驅邪外出,疾病向愈;反之則正虛陽微,余邪留戀,病情纏綿。
1.2 濕熱瘀毒為標
1.2.1 濕 參考《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七版)》[1],COVID-19核心致病因素為濕。驗之于舌,各階段多具舌體胖大、苔膩的特點;辨之于證,輕型(寒濕阻肺、濕熱蘊肺)、普通型(濕毒郁肺、寒濕阻肺)皆為濕作祟;校之于方,多用茯苓、薏苡仁、白術、半夏、藿香等,取其淡滲利濕、苦溫燥濕、芳香化濁之性。《溫病條辨》指出:“濕性氤氳黏膩,非若寒邪之一汗即解,溫熱之一涼即退,故難速已。”病程進入恢復期,濕濁雖已漸化而難盡除,濕邪又為疫癘邪氣之窠臼,濕邪不除則余邪不盡,病情遷延。外濕困脾,運化失司,聚濕生痰,上歸于肺,通調水道失職,水津不得四布,內客于肺,發為咳喘痰諸癥;流于胃腸,發為腸鳴腹瀉;外漬肌肉,發為肢節酸楚、困重。脾生濕,濕困脾,內外相合,造成惡性循環。
1.2.2 瘀 肺主氣、司呼吸,吸則肺張葉舉,清氣充盈,呼則肺收葉合,濁氣排出,一呼一吸間使周身氣機運轉不休。“溫邪上受,首先犯肺”,肺臟損傷則宣降出入失常。張介賓云:“經脈流通,氣主于肺,固為百脈之朝會。”肺為心行血,氣機不利則血行不暢,導致瘀血內停,是所謂“氣行則血行”“氣為血之帥”。又《靈樞·決氣》云及“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為血”,可見脾虛氣血生化乏源亦可因虛致瘀。COVID-19 恢復期肺脾功能未復,瘀血久稽為患,或見舌暗以及肺部殘留磨玻璃影。有研究表明丹參可促進纖維蛋白原溶解、改善血液流速、促進肺炎吸收[2],臨證可靈活運用活血化瘀法解除血液高凝狀態,促進肺組織修復。
1.2.3 熱毒 瘟疫致病暴戾,《素問·刺法論》有“避其毒氣”之說,其熱變最速;痰濕與瘀血郁久化熱,濕熱相合,熱得濕而愈熾;患者終日隔離,情志不遂,思慮氣結,郁而化火。早期以解熱、抗病毒治療為主,恢復期熱毒雖減,但尚有余溫,臨證可見低熱、口渴、便秘、舌苔黃膩等。
2 COVID-19 恢復期的治法及六君子湯加減立方依據
根據COVID-19 恢復期本虛標實之病機特點,其治療應以補益肺脾之氣為要,輔以利濕化濁、清解郁熱、活血行瘀、化痰散結、理氣導滯諸法,以法測方選用六君子湯化裁。
六君子湯出自《醫學正傳》,方由黨參、茯苓、炒白術、法半夏、陳皮、甘草組成,具有健脾補氣、化濕和中之功效。本病肺脾皆虛,據上述肺脾生理特點,當從脾論治,正如《石室秘錄·正醫法》所說“治肺之法,正治甚難,當轉以治脾,脾氣有養,則土自生金”。黨參味甘,性平,歸肺、脾經,《本草正義》言其“力能補脾養胃,潤肺生津,健運中氣,本與人參不甚相遠”,故以為君;白術、茯苓燥濕、滲濕,杜生痰之源,以為臣藥;半夏其性溫燥以制痰,陳皮辛散利氣以行痰,二者相伍,合“氣順痰消,痰除氣利”之意,祛已貯濕痰,故為佐藥;甘草補脾益氣,調和諸藥為使。全方具補運兼施、標本兩顧的特點,巧用培土生金之法,使脾氣健旺,精微敷布,肺病自除。由于患者所處地域、飲食、體質等因素影響,恢復期病情不一,臨床用藥需因人而異,隨證加減。若病人納差、痞滿、便黏、苔膩可選用藿香、砂仁等芳香化濁之品;若體虛自汗可用黃芪益皮毛、閉腠理以實衛;若低熱、口渴、便秘、苔黃膩,說明余熱猶存,以小劑量大黃、連翹瀉熱清解,勿妄投重劑損傷脾胃;若見舌暗、肺炎吸收延遲,酌加桃仁、丹參等行血化瘀。只要法中病機,自能藥到病除。
3 結合現代藥理學探討六君子湯對于COVID-19恢復期的效用
3.1 提高機體免疫力COVID-19 的發病是由新型冠狀病毒與機體免疫系統斗爭產生的結果。人體有兩道免疫防線,若病毒突破防線,就會在宿主體內不斷復制、繁殖。若免疫功能強盛,就會馬上消滅病毒恢復健康;兩者勢力此消彼長,若患者免疫力低下則易造成病勢纏綿難愈,預后不佳。因此,治療恢復期患者應以提高免疫力為首要任務。有研究表明,茯苓所含的茯苓多糖、三萜類化合物[3,4],以及黨參所含的多種糖類、酚類、皂苷、甾醇、揮發油及微生物堿[5]均有明顯的增強免疫力作用。武晏屹[6]等在研究藥物之間配伍關系對提升免疫力的影響的實驗中,得出最優5 組藥對,按其提升度高低分別為:茯苓-黨參(1.887096774)、茯苓-法半夏-陳皮-甘草(1.887096774)、茯苓-法半夏-白術-甘草(1.887096774)、白術-薏苡仁-黨參(1.857142857)、白術-薏 苡 仁 -黨 參 -茯 苓(1.857142857)。這些藥對多數為六君子湯的藥味組成,其中以甘味補虛藥為主,加之半夏、陳皮、茯苓、薏苡仁等化痰利水之品,說明甘溫培中、化痰利濕之法能改善免疫調節功能。
3.2 抗炎、抗氧化炎癥反應的持續有賴于炎癥因子及活性氧的作用。臨床上發現很多恢復期患者已符合出院條件,但胸片表現仍有淡斑片影,說明炎癥因子和氧自由基仍未清除完全。病毒通過刺激機體免疫系統釋放炎癥因子導致炎癥反應。在炎癥細胞吞噬病毒的過程中,細胞要制造氧自由基(包括一氧化氮、羥自由基、過氧化氫等)溶解病毒,氧自由基生成過多就會游出細胞外攻擊血管內壁及各器官。基于此病理,筆者通過搜集文獻發現六君子湯中多味中藥可通過抑制炎癥因子及氧自由基的活性達到抗炎、抗氧化的作用。如甘草次酸能夠減少血清中IL-6 和TNF-α 的含量[7];半夏多糖對氧自由基O2-和DPPH 有清除作用[8];陳皮有效成分二氫黃酮可通過降低脂質過氧化物、抑制細胞粘附分子表達、抑制炎癥因子、降低免疫細胞和炎性細胞浸潤等發揮抗炎、抗氧化作用[9]。綜上,六君子湯能有效促進炎癥吸收,保護氣道。
4 病案舉例
洪某某,女,68歲,2020年1月29日因“咽痛伴發熱6天”收入院。患者于6 天前受涼后出現咽痛,伴發熱,體溫最高38.8℃,無惡寒,繼之出現乏力、全身酸痛,無咳嗽咳痰、呼吸困難、胸悶痛等不適。2020 年1 月29 日行胸部CT 示:右肺感染(病毒性?),雙側胸膜肥厚。自服感冒藥物(具體不詳)后體溫降至正常。鼻咽拭子新冠病毒核酸檢測為陽性。入院癥見:咽痛,無惡寒、發熱,無咳嗽、咳痰,無胸悶、氣喘,納可,寐安,二便調。查體:咽部充血,扁桃體無腫大,雙肺呼吸音粗,未聞及干濕啰音,余無異常。診斷:新型冠狀病毒肺炎。1 月30 日血常規:白細胞計數1.5×109/L,淋巴細胞絕對值0.47×109/L。住院后先后予克力芝片、阿比多爾、喜炎平等治療后咽痛改善,發熱未復發,均予停用,但鼻咽拭子新冠病毒核酸檢測仍持續陽性。
2020年2月22日初診:患者出現腹脹、腹痛,疲乏,納差,寐欠安,二便調,舌淡紅,苔黃厚膩,脈細滑。CT 示肺部明顯磨玻璃樣改變(見圖1)。中醫診斷:疫病(恢復期),辨為肺脾氣虛,濕熱內蘊,中焦氣滯。予六君子湯加減,藥用:黨參15g,白術10g,茯苓15g,法半夏9g,陳皮9g,厚樸9g,枳殼9g,廣藿香9g,黃芩9g,木香6g,甘草6g。每天1 劑,水煎,早晚分服,連服3劑。
2020年2月25日二診:患者腹脹、腹痛明顯改善,疲乏、納差緩解,大便干燥難排,寐欠安,小便正常,舌淡紅,苔黃厚膩,脈細滑。予上方去木香加火麻仁15g、瓜蔞子15g、連翹9g、板藍根9g、北柴胡15g。再次連服3劑。
2020年2月28日三診:患者無腹脹、腹痛,疲乏、納差明顯緩解,大便兩日未排,寐欠安,小便正常,舌淡紅,苔黃厚膩較前改善,脈細滑。2月28日血常規示:白細胞計數3×109/L,淋巴細胞絕對值1.02×109/L。胸部CT提示肺部感染較前好轉(見圖2)。予上方加大黃6g、茯神15g、遠志9g。連服8劑。
2020 年3 月6 日四診:患者偶有咳嗽,咳少許白黏痰,無咽痛、發熱,夜寐欠安有所改善,飲食及大、小便正常。舌淡紅,苔黃厚膩,脈細滑。3月3日鼻咽拭子新冠病毒核酸檢測陰性。繼續前方調理。
按 瘟疫初起,患者高熱、咽痛、乏力、周身酸痛數癥并見,乃邪正相爭、上焦郁閉、正氣受傷之故,經服用抗病毒及清熱解毒藥物后熱退癥減進入恢復期。由于初期肺金受邪,子病及母,病后脾胃受損首當其沖。脾胃虛弱,升降失和,中焦痞塞不暢則見腹脹、腹痛;脾虛運化不及則水谷不得轉精,濕、食留滯于胃腑,郁而化熱,胃不和則臥不安,故納、寐欠佳;氣血生化乏源,無以灌溉四傍,故肢倦乏力;舌淡紅、苔黃厚膩、脈細滑皆為濕熱內蘊之象。投以六君子湯壯中氣,助運化;加枳殼逐宿食;厚樸燥濕痰;木香除痞滿;藿香化濕濁;黃芩清郁熱。全方標本兼顧,寓補于消。服藥三劑后復診,痞滿除,腹痛安,但大便難,寐欠佳,察舌脈知其濕熱未解。此濕毒未清,余熱猶存,暗耗津液,故去木香,加連翹、板藍根以清熱解毒,增火麻仁、瓜蔞子以潤肺通便,加北柴胡以解郁安神。繼診,病猶未解,循本求因,蓋濕熱膠著不解,以有形之質助無形之勢使邪熱不得外透,濕熱燥屎結于胃腸,熱盛津液急劇耗傷,當急下存陰,以大黃峻下熱結,茯神、遠志寧心安神。藥后諸癥減,白細胞及淋巴細胞有所回升,復查胸部CT結果提示病灶較前吸收,核酸轉陰,舌脈表現雖仍有濕熱之征,但舌體縮小,苔厚膩改善,效不更方,守舊方續服。

圖1 2月22日胸部CT

圖2 2月28日胸部CT
4 結論
對于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恢復期,患者往往病程遷延,西醫治療難有較好成效,此階段應發揮中醫藥的獨特優勢,抓病機,立治法,依法用方,隨證加減。本病以氣虛為本,關乎肺脾,以濕熱瘀毒為標,標本相互影響,互為因果。以“六君子湯”壯中氣足以運濕痰,酌用清熱、化瘀、行氣諸法,驗之臨床,頗具療效,結合現代藥理學也為六君子湯固本(提高免疫力)、治標(抗炎、抗氧化)的雙向療效提供了臨床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