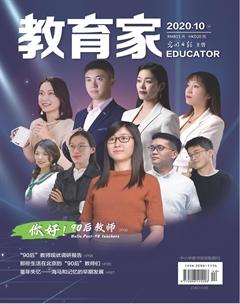童年失憶——海馬和記憶的早期發展
史東麟 耿鳳基


幾乎每個成人都有一個解不開的童年夢。雖然我們常常會試圖回憶童年時期豐富的經歷,但我們對兒時經歷的記憶卻大多是模糊不清的,往往需要通過長輩的敘述和提示才能構建起一個包含著圖像、聲音和感覺等信息的場景。我們為什么會記不清小時候的事情?關于這個問題,近百年來研究者們也一直在探索——為何人類早期的記憶如此“脆弱”?
記憶的能力會隨年齡增加而變化
早在1910年,奧地利心理學家弗洛伊德就提出了“童年失憶(childhood amnesia)”這一概念,指成年人無法回憶起在生命最初2-3年之中所經歷的事情,我們很難在約7歲以前建立穩固的記憶。最初人們在關注這一問題時認為,早期的經歷并沒有被編碼到記憶庫中,但后續的許多研究結果卻顯示事實并非如此。
研究表明,人類在早期是可以讓編碼信息進入長時記憶系統的。例如,生活經驗告訴我們,兒童很可能會記得幾年前發生的一些事情,大量的研究結果也支持了這種生活經驗。美國埃默里大學哈蒙德等人在1991年進行的一項自傳體記憶研究顯示,3歲的孩子可以回憶起6-12個月之前在迪士尼樂園游玩的細節,并且年齡越大,回憶起的細節就越多。基于這一標志性的研究,大量的實證研究都記錄和分析了整個童年對自傳體記憶的加速遺忘過程。例如,后續研究發現3-4歲的孩子雖然可以回憶起事情的細節,但很快就會又忘掉。尤其是在像自傳體記憶這樣的開放性記憶上,4-6歲的孩子會比8歲的孩子遺忘得更快。同樣的,一些經過嚴格變量控制的實驗室研究也得到了相似的結論:幼兒時期孩子對細節信息、空間位置等內容的記憶能力會隨時間變化而顯著提高,并在6歲左右達到一個相對較高的穩定水平。也就是說,回憶缺失可能會持續整個童年,但6-7歲以后記憶的穩定性和一致性會顯著增強。
記憶能力會隨年齡增長而變化的原因——海馬的發育發展
為了解釋童年失憶這個現象,研究者們提出了很多假說和可能。例如,弗洛伊德認為是“性創傷”壓抑了自己的早期記憶,但這種充斥著經驗主義的說法逐漸被實證研究結果所摒棄。后來,越來越多的研究認為童年失憶這一現象是由多種因素共同影響的。比如,5-7歲剛好是皮亞杰認知發展理論中從前運算階段向具體運算階段過渡的重要時期,孩子在認知、語言、心智理論、自我概念等許多領域都有著突飛猛進的發展,記憶也更具有目的性了,正式的學校教育對孩子的各方面發展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近些年,關于記憶的理論和來自動物實驗的證據表明,大腦的發育可能是導致童年失憶的根本原因。大腦自出生伊始就在飛速的發展中,以靈長類動物的大腦發育圖譜為例,我們可以觀察到大腦的體積在增加,連接大腦各個區域的神經纖維束發育變化也十分明顯。相似的,人類大腦的結構和功能隨著時間的推移也在逐漸地發展,直至結構完整、功能成熟。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通過各種感官獲取信息,通過神經傳遞抵達我們的大腦皮層,并被記錄下來,這些感覺信息需要經過整合加工之后才能最終形成記憶,而這個過程離不開重要結構——海馬體(hippocampus)(圖1)。海馬體一詞起源于希臘語,由于其形似海馬而得名。研究者們認為,海馬體是人類記憶的重要神經結構,出生后海馬體的發展變化是孩子的記憶能力隨年齡增長而提高的神經基礎。海馬體有特定的子區域,包括海馬頭部、身體和尾部,根據功能分化還可以將其分成齒狀回(dentate gyrus)、海馬角(cornu ammonis)等區域。來自非靈長類的神經解剖學結果顯示,特定子區域的結構和體積會隨年齡的增長而變化,并且這種變化會一直持續到5-7歲。也就是說,海馬及其子區域的結構和功能的逐漸發展成熟可能是導致兒童記憶“脆弱”的原因。與此同時,一些動物模型也支持了神經元新生(neurogenesis)會極大地影響生命早期的記憶,特別是海馬體中的神經發育,較高水平的神經新生阻止了穩定記憶的形成,并且很有可能是通過替換海馬記憶回路中已經存在的突觸鏈接而實現的。然而,海馬體只是記憶網絡中的一部分,精細記憶的形成和提取也離不開前額葉、后頂葉等區域的共同協作。而大量的科學研究也證明,這些皮層區域與童年和青春期后期的記憶能力變化顯著相關。尤其是前額葉皮層,被認為是記憶系統的必要部分。這一結論在動物和人類實驗上都得到了印證,但是關于這些皮層在生命早期是如何促進記憶的研究卻很少。總而言之,記憶能力隨發展變化的機制是多方面的,但海馬在其中的作用極其重要。
兒童早期大腦發展對記憶能力的影響
在探索“童年失憶”這一問題的初期,研究者們僅從行為實驗和理論模型中得到了初步的結論。直到諸如功能性核磁共振(fMRI)、腦磁圖(MEG)、腦電圖(EEG)等腦成像技術被應用,人們才逐漸明確記憶的發展變化與大腦結構和功能之間的關系。加之兒童的腦影像較難獲取,大腦發育與形成包含細節的長期記憶能力有關這一假設才被驗證。具體來說,大腦結構、功能的發展,以及大腦各區域之間的功能鏈接都與記憶能力的發展成熟有關。
從結構上來看,研究發現,海馬結構的發展變化呈現出了年齡差異。例如,6歲的孩子在記憶任務中的更好表現與更大的海馬頭部體積相關,但在4歲的孩子群體中卻沒有發現這樣的關聯。具體而言,海馬頭部中的齒狀回/CA-2區域的體積與記憶能力有關,但還是呈現出了年齡差異:在年齡更小的孩子中,更小的齒狀回體積與較差的記憶表現相關,而年齡稍大的孩子則相反。另外,白質通路與兒童早期記憶表現有關,并且和與記憶有關的腦區之間的連接情況也呈現出了年齡差異。總之,這些研究表明,海馬結構的發展至關重要,但海馬與其他皮層區域的連接也是十分重要的。
從功能上看,研究發現,成人在進行記憶任務時,海馬以及頂葉等皮層都被激活了,但在兒童的研究中還發現了一些不常在成人實驗中被激活的區域,例如背外側前額葉皮層(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等。這說明,年幼的兒童可能會依靠更廣泛或更分散的大腦網絡來編碼細節信息的記憶。另外,靜息態功能性核磁共振(resting-state fMRI,測量大腦各個結構在靜息狀態下的功能連接)也可以給我們帶來豐富的信息。例如,研究者發現,海馬與那些通常被認為與記憶形成無關的區域之間的功能連接在發育過程中也會下降,但與某些大腦區域的功能連接會隨年齡的增加而逐漸增強。總而言之,隨著年齡的增長,海馬與記憶網絡中其他的皮層在功能上逐漸整合,并且與記憶無關的腦區逐漸分離。
兒童早期的大腦發育不僅可以幫助兒童在實驗室實驗中表現得更好,還極大地促進了他們記憶真實世界事件的能力。然而,現實生活如此復雜,我們在考慮記憶的神經相關物的同時,也必須要考慮包括語言、自我概念、情緒、心智理論和孩子生長環境等其他因素。這些因素的神經基礎在一定程度上有重疊,比如海馬不僅在記憶網絡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同樣在語言和空間導航(spatial navigation)的發展中有著重要作用。因此,研究者們還將繼續探索大腦記憶系統中各個腦區之間的競爭與互補機制。
啟示
從神經科學的角度,童年的記憶丟失似乎是人類發育發展的必然結果,幾乎所有人都難逃童年失憶的困擾,不過我們也不必感傷。2016年一項發表在 Nature Neuroscience 上的研究表示,我們最初的那些回憶一直有跡可循,大腦在存儲上沒有問題,只是不能對那些記憶進行正確提取,但是只需要加以合適的刺激,就可以實現對其重新提取。
因此,孩子并不會遺忘得“一干二凈”。很多時候,雖然無法回憶起兒時經歷的原貌,但因為回憶起某件事而帶給我們的感覺卻真實存在,甚至可能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著我們對現在生活的判斷。記憶往往是很多因素的混合物,其中可能包含著真實回憶的碎片、每次回憶時的情緒狀態、腦中重現場景時的虛假記憶等。這也說明,我們雖然回憶不起童年事情的細節,但不代表我們完全喪失了過去的情感,我們大腦中的其他腦區會幫助我們記住童年的更多信息。例如,杏仁核讓我們記住了這個世界是充滿樂趣還是充滿恐懼,鏡像神經元系統讓我們記住了“感同身受”的奇妙感受,獎賞系統讓我們記住了每次獲得成功時的歡愉……這些都是童年時期就會形成并保存下來的回憶。這值得父母和早期教育工作者深思:我們是否為孩子創建了一個健康安全的學習生活環境?我們無意識的行為和言語是否造成了孩子的童年創傷?比如,當孩子開始探索新鮮事物時,老師是耐心鼓勵,還是嘲諷打擊?當孩子尋求幫助時,父母是細心指引,還是無動于衷?如果童年創傷帶有強烈負面情緒情感,就會影響我們對待世界和人際關系的看法,并且我們會在這個過程中不斷重復曾經不好的體驗。研究表明,童年創傷的首要來源往往都是家庭。我們的童年記憶也許一直都存在,只是在我們成長的過程中被深藏在大腦皮層中的某個角落里,等待著某一個合適的刺激去喚醒。而這個刺激也有著無數的可能,它可能是游樂園中緩緩飛上天空的一只紅氣球,也可能是陰雨天家中空無一人時窗外的一聲驚雷。因此,在引領和見證孩子成長的時候,父母和老師應該給予孩子充分的理解和耐心,為孩子創造一個充滿愛的環境,這對極速成長中的孩子而言至關重要。
通過研究大腦和記憶的發展變化,我們理解了人類可能不是徹底遺忘了童年的一些經歷,而只是封存了這些經驗。同時,生命伊始那看似已經被遺忘的記憶,可能對我們現在的行為和認知產生著深刻而長遠的影響。因此,父母和早期教育工作者要努力為孩子們創建一個健康安全的生活學習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