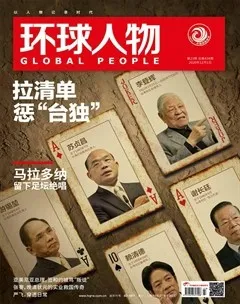張建平:RCEP讓23億人“抱團取暖”
尹潔
張建平,山西省平順縣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投資經濟學博士。現任商務部研究院區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西亞非洲所所長。研究員、博導。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陰霾中,全世界的目光再一次投向了東方。
11月15日,亞太地區的15個國家——東盟十國以及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正式簽署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簡稱RCEP),標志著全球規模最大的自由貿易協定達成。
統計數據顯示,RCEP的成員國覆蓋了23億人,占世界總人口的30%;成員國GDP總和超過25萬億美元(1美元約合6.6元人民幣),約占世界GDP的29%。協議簽署后,15個國家將遵守共同的關稅、原產地規則、投資準入、知識產權、競爭政策、電子商務等方面內容。
“中國加入RCEP帶來的益處很多。大家以后去新馬泰、日韓、新西蘭、澳大利亞旅游,住酒店、吃喝玩、購物花的錢就沒有過去那么多了,因為RCEP成員國會大幅削減關稅,降低商品成本。甚至你不用出國,在國內通過各種進口渠道,也能更容易地買到成員國的產品和享受服務。”商務部研究院區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建平對《環球人物》記者說。
未來,一件羊毛衫的制作、銷售流程可能是這樣的:澳大利亞的羊毛免稅出口到中國,在紡織廠里織成布料,再免稅出口到越南、泰國,由當地的加工廠制作成衣,最后又免稅出口到澳大利亞。在這個過程中,中小企業的生產和運輸成本大大降低,消費者能買到更多物美價廉的商品,成員國經濟、就業都將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
八年磨一劍
RCEP的談判經歷了漫長的8年時間,但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更遙遠的2008年。那一年美國爆發了禍及全球的金融風暴,整個亞洲都被波及,也間接導致中國出臺了刺激經濟的“4萬億計劃”。
張建平有一個觀點:每一輪經濟危機或金融危機,都有力地深化了東亞經濟合作和區域經濟一體化。比如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催生了中國與東盟的“10+1”領導人會議,后來韓國、日本、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都先后和東盟簽署了“10+1”的自由貿易協議。
2008年金融風暴后,東亞經濟一體化得到進一步加強。中國提出“10+3”(東盟十國與中日韓)合作倡議,并發展為現在的“10+3”首腦會議;日本則提出過“10+6”(東盟十國、中日韓、澳新、印度)合作倡議,衍生出現在的東亞峰會。正是在一次次的區域合作中,東盟有了構建RCEP的想法。
“在東盟看來,自己手里已經有5個‘10+1自由貿易協定了,一對一挺繁瑣的,為什么不把這些協定整合在一起,形成一個巨型自貿區呢?”張建平說。
此外還有一個“刺激”因素,就是TPP。
TPP是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的簡稱。這個由新西蘭、新加坡、智利和文萊發起,從2002年開始醞釀的多邊自由貿易協定,在2008年之后被美國前總統奧巴馬視為美國重返亞太的工具,積極參與和推動該協議的談判,希望達到“亞太再平衡”的目的。
2010年,當馬來西亞、越南也成為TPP談判成員時,東盟感到有被分裂的危機,于是RCEP被提上了日程。
2012年11月,RCEP談判正式啟動。它由東盟十國發起,邀請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6個對話伙伴國參加,旨在通過削減關稅及非關稅壁壘,建立統一市場的自由貿易協定。
起初大家都比較樂觀,認為在2015年底能夠達成協議,然而實際過程遠比想象的曲折。首先是日本,當時它更想加入的是TPP。相對于RCEP,TPP的市場開放門檻更高。日本作為發達國家,想追求更高標準的貿易自由化,在積極加入TPP的同時,也對RCEP提出了很高要求。比如,在日本具有優勢的工業產品方面,它要求發展中國家高度開放市場,但在發展中國家具有優勢的農產品方面,日本卻不愿開放大米、小麥等市場,目的是保護其國內農業。這就對RCEP其他談判成員造成了比較大的壓力。
另一個阻礙談判進度的因素,是15個成員國的發展水平差距巨大。從人均GDP看,既有超過6萬美元的新加坡,也有僅1000多美元的緬甸、柬埔寨,導致在降低關稅、市場準入方面的談判難度非常大。
因此,各國未能在2015年底達成協議。但很快,國際形勢出現了變化:特朗普上臺后,美國退出了TPP,開始走單邊路線。2017年和2018年,在特朗普政府掀起的“逆全球化”風潮中,RCEP成員仍在努力前行。
張建平認為,2019年是一個關鍵年份,談判艱難地進行到第二十七輪,各國就大部分協議內容達成了一致意見。2020年則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世界經濟再一次面臨嚴峻考驗,所有成員國都感到了巨大壓力,也更傾向于抱團取暖。同時,最早控制住疫情、實現GDP正增長的中國,給各國帶來了新動力,也使日本下定了加入RCEP的決心。
印度為何“退群”
從目前達成的協議看,RCEP的成果主要體現在4個方面:一是成員國之間90%的貨物貿易將實現零關稅;二是實施統一的原產地規則,允許在整個RCEP范圍內計算產品增加值;三是拓寬了對服務貿易和跨國投資的準入;四是增加了電子商務便利化的新規則。
作為目前全球唯一一個以發展中經濟體為中心的區域貿易協定,RCEP并沒有一味追求市場開放程度,而是本著以發展為核心的利益訴求,根據各成員國的比較優勢形成供應鏈和價值鏈,加速商品流動、技術流動、服務流動、資本流動,最大程度實現區域經濟利益平衡。
《環球人物》:RCEP的意義體現在哪些方面?
張建平:首要意義是中國參與到21世紀區域貿易規則的制定過程中,而且發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現在全球貿易規則體系正在演變,我們通過RCEP談判,在電子商務、政府采購、競爭政策、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參與了規則制定。其次是RCEP的簽署將進一步擴大中國與東盟、日韓、澳新的貿易規模,這對中國的新一輪改革開放、“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也有重大意義。三是從整個亞太自貿區的角度看,RCEP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軌道,對于維護多邊貿易體制、深化區域經濟一體化乃至穩定全球經濟,都具有標志性意義。
《環球人物》:RCEP本來是16國框架,但印度幾次反復后還是決定不參與。印度為什么選擇退出?
張建平:印度擔心開放市場后,外國商品對其國內制造業有大的沖擊。印度的制造業水平目前還比較低,有大量小商戶、小作坊,會面臨難以承受的競爭壓力,而且印度失業率本來就高,貿易赤字也很嚴重。所以在RCEP談判中,難度最大的是印度,壓力最大的也是印度。
《環球人物》: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時也有同樣的擔憂。當時我們為什么能直面挑戰,最終獲得了融入全球化的發展機遇?
張建平:中國當時具備兩個條件:一是工業化水平,二是基礎設施建設。改革開放后,通過在自身產業體系上嫁接外資,中國在2000年左右已經成為“世界工廠”,工業化程度、規模都很大。在基礎設施方面,當時公路網、鐵路網已經比較發達,交通運輸的瓶頸基本上消除了。
印度的基建速度卻特別慢。它的法律規定,必須90%以上的農民簽字,政府才能征地,但印度人做事效率又不高,喜歡辯論,辯論完了就沒結果了,導致事情久拖不決。同樣的原因使得印度的工業發展也很緩慢,莫迪提出的“印度制造”一直搞不起來。
2019年,印度人均GDP約2100美元,與越南、柬埔寨、老撾屬一個梯隊。現在只能說印度是個潛在的市場,要真正成為有實際需求的市場,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被地緣政治影響,也影響地緣政治
《環球人物》:在RCEP成員國中,日本一直積極說服印度加入,在印度退出后,還要求保留讓其隨時加入的條件,這是出于什么考慮?
張建平:除了經濟因素外,還有政治因素的影響。日本的經濟規模雖然是世界第三,但論綜合實力,尤其是政治影響力,只能算二流國家。為了避免過度依賴中國市場,日本積極拉攏印度、澳大利亞、新西蘭,以平衡中國的影響力。加上美國近年來推動“印太戰略”,日本一直積極配合,所以更希望將印度留在RCEP中。
《環球人物》:RCEP的簽署對于推進中日韓自貿區有幫助嗎?
張建平:有很大幫助。中日韓自貿協定談判其實早于RCEP談判,但因為中日韓之間的歷史問題、領土爭端、安全問題,尤其是中日、日韓這兩個雙邊關系的疙疙瘩瘩很多,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形成自貿協定。
RCEP的簽署,給今后中日韓自貿協定談判打下了一個非常好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之上,中日韓可以再談一個標準更高、更有創新性的自貿協定,我覺得這個可能性越來越大了。
《環球人物》:東盟已經是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RCEP的簽署會讓雙方在哪些領域進一步合作?
張建平:未來雙方在各個行業、各個領域產業鏈的聯系都會更加緊密。現在已經有很多中國企業到東盟設廠,不僅覆蓋服裝、電子、機械等傳統投資項目,連鋼鐵、化工企業也在積極地去東盟投資。東盟已經成為中國企業最大的海外投資目的地。中國有14億人口,東盟有6億多,都是比較年輕的、成長中的市場,RCEP會使這兩個市場的分工更細、效率更高、供應鏈成本更低。
《環球人物》: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在RCEP中會發揮怎樣的作用?
張建平:這兩個國家人口少、發展水平高,人均GDP都在4萬—5萬美元,經濟以礦業、農業、服務業為主,工業非常少。澳大利亞幾乎沒有汽車產業,主要靠從發展中國家進口。
此外,澳新本身也是推崇自由貿易的國家,隨著亞太經濟合作的深入,它們對東亞、東南亞地區的經濟依賴性在提升,經濟互補性也在增強,特別是對中國市場的依賴度顯而易見。所以在RCEP談判中,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都是積極分子。這也是為什么我們說,RCEP的簽署是多邊主義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