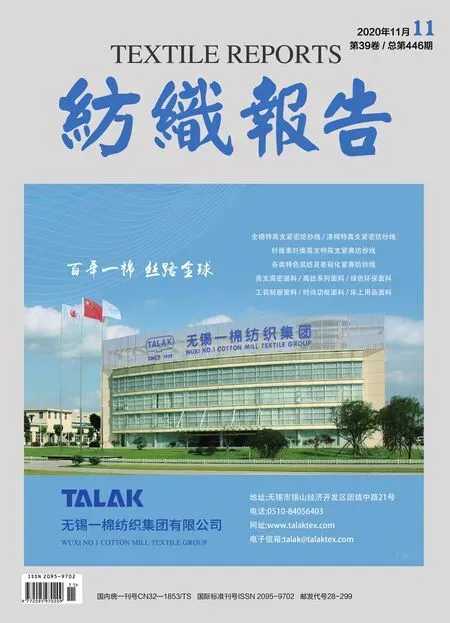民國初期北京女性服飾審美研究
關 悅
(北京服裝學院 服裝藝術與工程學院,北京 100029)
1 由“服飾之美”向“人體之美”的轉變
近代中國,女性服飾的審美觀念最明顯的變化是將審美觀的重心由服飾轉向人體本身,也是由服裝客體轉向以人為主體的表現。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內核始終是表達人與天地、人與自然的和諧之道,注重“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在“天人合一”為主導的女性服飾中,更注重人的精神、服飾的意象以及服飾的文化內涵,削弱了服裝的外在功能與形式。因此,具有東方傳統特點的服飾文化,以二維平面的裁剪方式構成了中國傳統服飾審美,體現了中國服飾審美文化所蘊含的美學思想和哲學觀念。
民國初期,女性開始重新審視服裝與人的關系,體現了服裝客體逐漸弱化、將女性置于主體位置的特點。以民國初期北京女性服飾為例,女性服飾被劃分為旗女、漢女兩式,滿族女性的服飾基本保持傳統造型,“齊腳寬松滿裝、絲質繡花馬甲、兩把頭、木質高底緞面繡花鞋”[1]。這一時期滿族女子的旗袍極為寬大,大襟、右衽,旗袍下擺長及腳面,袖口緣邊與下擺的裝飾極為精致繁縟。由于近代北京城市人口結構的變化,滿漢民族相互融合也體現在服飾上。滿族女性的服飾逐漸漢化,上衣下裙和上衣下褲成為這一時期女性的主要服飾,滿漢女子服飾的區別已不再明顯,“滿洲婦女近乃皆改漢裝。后此滿、漢、種族之不分”[2]。此時,女性穿著的襖裙是由漢族傳統的上衣下裳制演化而來的,襖服下擺的長度有逐漸縮短至腰線的趨勢,袖口和腰節的變化使服裝更加合體。
從服裝形制來說,北京滿族女子的旗袍平直、寬大,“削肩,細腰,平胸,薄而小的標準美女在這一層層衣衫的重壓下失蹤了,她本身是不存在的,不過是一個衣架子罷了”[3]。服飾掩蓋女性的身材特征,在煩瑣的服裝裝飾和嚴格的服飾制度中喪失了人的意義。
林語堂在《生活的藝術》中表達了中西服飾文化的差異:“中裝和西裝在哲學上不同之點就是,后者意在顯出人體的線形,而前者則意在遮蔽之。”[4]中西服飾文化的側重點體現了服飾審美觀念的差異性。西方文化歷來強調的是物質本身,注重物質的客觀屬性。西方服飾以立體剪裁的方式為主,利用服裝裁片的縫合轉折突出女性“人體美”的特征,是服裝“立體美”的表達。中國傳統服飾則以平面裁剪的方式塑造,更加看重服飾傳達的傳統文化意蘊。隨著西方文化的傳入,西方商品經濟極大地改變了本國的消費水平和人民的生活方式,大量舶來品的出現,使服飾表現出多樣性的特點。在北京,不少婦女開始模仿西人裝扮,“近年新式衣服,窄幾纏身,長能覆足,袖僅容臂,形不掩臂,偶然一蹲,動至綻裂,或謂是慕西服而為此者”[5]。中西方服飾文化的差異,實則是中西方美學思想和哲學思想的差異。
然而,民國初期女性對“人體之美”的探討還表現在對腳的解放上,放足是民國女性覺醒的開始,女性試圖擺脫封建禮教下傳統觀念的束縛,開始以平等、民主的社會觀念塑造新的女性形象。
從民國初期北京地區女性服飾的發展來看,服裝不再以主導人的思想、精神、觀念的形式而存在,而是形成一種從屬關系,以人為基礎服務于人這個主體。在女性服飾文化中,女性成為社會審美的中心,服裝首先需要傳達的是女性的需求和以女性為中心的審美意識。服飾審美附加于社會意識中,社會對于女性服飾的包容性是民國初期女性群體的表現,服飾審美并不是個人意識的傳遞,而是社會個人、群體和社會階層之間的整體趨向。
2 由“濃艷裝飾”向“樸素自然”的轉變
北京作為前朝舊都,在封建政治政權的主導下,傳統的寬袍大袖、圖案紋飾體現了服飾尊卑等級的象征意義,服飾上表現出的傳統禮教意義尤為突出。民國初期,北京女性服飾的變化反映了人們的審美觀念從傳統、繁縟轉向具有中國近代化意義的簡潔、自然的服飾風格。辛亥革命使新政權替代舊禮制,從社會變革與思想文化等方面重新建立具有現代意義的服飾制度。受外來文化的影響,傳統禮服的使用范圍具有局限性,無法滿足女性日常生活的要求。在北京,女性服飾除禮服保持漢族傳統的上衣下裳形制外,其余服飾“暫聽人民自由,不加限制”。因此,民國初期北京女性服飾中滿裝、漢裝、西裝相互影響、相互借鑒,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
同時,北京有一部分女性留學歐洲、日本,北京也成為這一時期女子教育的中心城市。受日本女裝的影響,女學生們開始模仿國外這種簡潔、樸素、自然的服飾風格:上穿高領衫,服裝以大襟右衽為主;上衣縮短變窄,長度及胯,服裝窄小適體,裝飾簡潔;下擺呈弧線、直線、圓角等,袖型寬大、長度及肘;下著黑色長裙,且均不以繡紋作裝飾,這樣的服裝被稱作“文明新裝”。時代更迭不僅表現在女性服飾形制的變遷中,還表現在傳統美學思想與具有進步意義的審美觀念的轉變中。民國初期,北京女性在服飾風貌的演變中還涉及服飾色彩觀念的變化,白色作為中國傳統封建觀念中的禁忌被打破了,女性紛紛效仿西方服飾文化中的尚白風俗,女學生等知識女性開始流行穿著白色或淺色的服裝。總體來看,女性服飾呈現樸素、淡雅之美,女性開始追求整齊簡潔的自然美,摒棄傳統禮教影響下的繁縟裝飾。
綜上所述,女性服飾在簡化服裝裝飾的同時,就是注重服裝功能性與實用性的開始。女學生穿著的“文明新裝”就是將服裝繁瑣的裝飾去掉,摒棄服裝除本質以外的其他附加含義。此后,民國中后期逐漸成為女性主流服飾的旗袍,也經歷了不斷簡化演變的過程。女性服飾追求簡化與功能,服裝作為女性意識和社會審美的標志,從側面反映了女性的民主與平等思想的進步以及女性心理成熟化的表現,使女性服飾回歸到服裝之本,女性服飾的簡化也是人作為主體的又一表現。
3 民國初期北京女性服飾審美變遷的原因
社會經濟的發展影響了北京女性服飾審美的變遷。西方商品經濟促進了近代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產生與發展,北京、天津、上海等地興辦工廠,服裝紡織品中出現了國產布料。然而,外貨輸入使國貨發展日漸停滯,此時,提出了振興實業、提倡國貨,應注重改良,在倡用國貨的同時,不宜排斥外貨。民國初年,北京設立國貨代銷局,舉辦國貨展覽會,各省市實施并提倡支持國貨的政策。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以及社會經濟與生產方式的相互影響,促進了服飾的變遷與發展。
城市結構的變化影響了北京女性服飾審美的變遷。由于工商業和交通運輸業的發展,北京城市人口逐漸增長,城市規模不斷擴大,社會結構發生了明顯變化。“北京較確切的人口統計是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民政部的調查,當時內外城共有761 106人,以后每年人口均有增長,至1927年達到878 811人”[5]。北京城市人口呈現逐年遞增的趨勢,以青壯年男性為主,知識女性、職業女性的比例大幅增加。
民主化思潮影響了北京女性服飾審美的變遷。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和約束人們思想、行為的尊卑等級制度。在五四運動“平等”“民主”思想的推動下,北京女學生樸素、簡潔的服飾風格也更新了對服飾的審美觀。隨著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女性逐漸走向社會并出現職業女性,追求男女平等和女性自由解放的風氣也影響了北京女性服飾的發展。知識女性從衛生、經濟、外觀等角度對女子剪發問題進行了討論。女子剪發是男女平權的又一表現。女性自身擺脫了封建禮教和傳統觀念的束縛,而民主化思潮使女性開始以獨立、平等的形象登上歷史舞臺。
4 結語
民國初期,北京女性服飾審美的變遷從社會的不同角度接收來自服飾形制、色彩、觀念上的轉變。北京女性服飾中固有的歷史延承性與在西方文化影響下的進步性并存,呈現出民國初期北京女性服飾特有的繁雜、矛盾的局面。民國初期,對于北京女性服飾審美觀念的進步意義是巨大的,女性服飾的審美觀念從“服飾美”轉向“人體美”,服飾作為客體,體現了人是主體、注重以人為核心的服飾文化。服裝打破了中國傳統的封建禮教意義,服裝裝飾的簡化與“文明新裝”的出現,都是西方文化影響下的產物。北京女性服飾就是在傳統與現代、滿族與漢族、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碰撞與融合中塑造出的具有中西結合特點的服飾風格,質樸、簡潔的風貌正是民國初期北京女性服飾變遷的進步表現,使得社會審美觀念朝著實用、功能、美觀的方向發展。通過對民國初期北京女性服飾的解讀,反映了民國女性審美觀念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