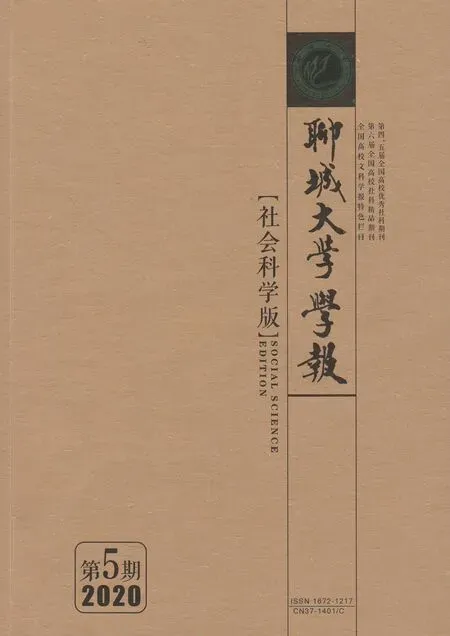論以媒介為中心的兒童教育與素養(yǎng)的提升
周海寧,程宗宇
(魯東大學 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山東 煙臺 264025)
2020年在中國教育體系中的兒童,至2030年便已經成為成人,并成為推動未來社會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生力軍,所以兒童教育事關中國的未來。經合組織(OECD)通過“未來教育和技能2030工程”①參考 OECD (2018), The Future of Education and Skills 2030 Project,http://www.oecd.org/education/2030/。提出了如下問題:如今的學生為了能夠茁壯成長并塑造他們自己的世界,需要怎樣的知識、技術、態(tài)度和價值?為此,應該建設怎樣的教育體制(instructional system)?當今兒童一代作為互聯網的原生代,與其他所謂的“互聯網移民一代”具有不同的特征呈現,因為當代兒童天然地與互聯網媒介環(huán)境交融在一起,即天然地生活在“媒介”之中,并需要形成數字化的生存能力。這與早期的媒介教育環(huán)境完全不同,早期媒介教育倡導“免疫與保護”②陸曄:《媒介素養(yǎng):理念、認知、參與》,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17頁。的保護主義媒介教育觀。它假設媒介與人之間可以維持必要的“壁壘(空間)”,認為這足以保護生活在其中的兒童免于媒介的侵害。但是在當今社會,我們無法想象將媒介從我們生活之中剝離以維持必要的距離。因為,對于當代的兒童來說,他們生來便與電子媒介為伍,并與電子媒介具有“天然”的契合感。他們通過媒介體驗生活、享受生活。“電子保姆”“媒介中毒”“網癮少年”等現象都從反面證明了媒介對于我們生活的滲透力度之大。所以對兒童教育來說,媒介教育應該成為兒童教育的一個重心。只有注重媒介教育,完善相關教育體制,才能提升兒童的媒介素養(yǎng),幫助兒童逐漸形成未來發(fā)展所需要的知識、技術、態(tài)度和價值,從而構建自己的世界。從當今社會媒介教育以及素養(yǎng)的內涵出發(fā),探討媒介教育之中存在的問題,并分析克服問題的可行性辦法或者理念便具有了重要性和緊迫性。
一、媒介教育與媒介素養(yǎng)的內涵再確認
媒介教育發(fā)展的推動力源自于媒介技術的不斷進步。未來學者凱文?凱利(Kevin Kelly)在其著作《Inevitable(必然)》①[美]凱文?凱利:《必然》,周峰、董理、金陽譯,北京:電子工業(yè)出版社,2016年,第20頁。之中指出,技術的發(fā)展方向是具有偏向性的,并提出了未來發(fā)展的12種趨勢:成為(Becoming)、認知(Cognifying)、互動(Interacting)、使用(Accessing)、共享(Sharing)、屏讀(Screening)、流動(Flowing)、重混(Remixing)、跟蹤(Tracking)、過濾(Filtering)、提問(Questioning)以及開始(Beginning)。由此便可以窺見未來社會的發(fā)展脈絡。特別是所謂第四次產業(yè)革命②周海寧:《“后人文時代”人類主體性研究的傳播學反思》,《視聽》2018年第9期。理念的提出,進一步推動社會向著上述的12種預測邁進。第四次產業(yè)革命以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為核心,以實現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材料技術、新能源技術的廣泛滲透與融合為目標。第四次產業(yè)革命是一次深度融合的革命,它將大幅度地改變人們對世界的認知,改變人們的思維方式,使人們的生活方式發(fā)生變化。
《必然》一書指出人類在未來社會將廣泛經歷如生物體人類一樣具有認知化(Cognifying)能力的人工智能(AI)。但是就目前,從實體的現象界出發(fā)去考察現實的媒介環(huán)境就可以發(fā)現,多樣化的人工智能技術體驗已經滲透到當代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了。例如:百度旗下的人工智能助手“小度”以及其衍生的多樣化產品——小度智能語音產品,已經讓兒童們一回到家的第一件事情可能就是呼喚“小度、小度”,從而“喚醒”小度智能助手為其服務。
另外,從文字閱讀到各種屏幕閱讀(Screening),從擁有到共享(Sharing)和使用(Accessing),以及日常利用的搜索引擎“百度(Baidu)”,并與之進行互動(Interacting),其互動的痕跡便成為可追蹤(Tracking)之物,在互聯網上進行流動(Flowing)。據此,廣告商家進行信息過濾(Filtering)行為,向潛在的用戶進行廣告信息推送,從而刺激電子媒介的使用者兒童發(fā)現更多“樂趣”,進而生成更多的購買訴求。
在如今的泛媒介化的環(huán)境之中,主體與他者(他人、媒介以及其他生命行為體、非生命行為體)之間的關系,已經從實體(reality)關系演化成更加多樣化的相互關系,即基于媒介的人際關系變得更為多元化和復雜化。所以“成為(Becoming)”這種理念在新媒介時代就凸顯其重要意義。“成為”這一概念點明了事物發(fā)展的動態(tài)過程以及可變性,是以德勒茲(Gilles Deleuze)和瓜塔里(Felix Guattari)的哲學為基準,在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的著作《后人類》(The Posthuman)之中描繪成了三種成為“他者”的形態(tài)——“成為動物”“成為地球”“成為機器”。③Rosi Braidotti. The Posthuman. Polity Press. 2013:55-104.其本質的訴求是呼吁人類不要再以“萬物的尺度”自居,而是需要超越“人類中心主義”的思想束縛,以“去人類中心”主義的新價值取向,去謀求人與媒介,人與他者的同發(fā)展、共進化。
于是,媒介教育與素養(yǎng)的重要性在互聯網時代強勢凸顯。因為“媒介教育這句話本身就具有重復性,媒介教育就是教育本身,教育就是幫助學生,使其能夠提出問題(Questioning),能夠教導他們使用(Access)信息的方法,教導他們既能分析和評價媒介信息,同時也能教育他們通過現代的傳播手段,學會表達自身信息的方法”。④Ahn Jungim. Media education as a cultural literature,Forum For Youth Culture 9(1), 2004.04.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在新媒介時代,媒介教育就等同于教育,對媒介教育的重要性如何強調亦是不會過分。
但是,這種認知雖然提高了媒介教育的段位,但是沒有強調媒介的可變性。因為在不同的時代,人們所使用的媒介是不同的,而媒介對人們認知的影響也是不同的。因為媒介不是價值中立的,例如我們每日使用的互聯網,其所提供的信息也是有偏向性的,因為這些信息所展現的世界并非世界本身而是世界的再現,即這些信息所建構的擬態(tài)環(huán)境與真實環(huán)境之間的差別是需要人們去質疑、評價、辨別的。那么這種對信息質疑、評價、辨別的能力就是媒介教育的內涵,同時也是媒介素養(yǎng)的內容。
并且,霍布斯①Hobbs, R. Media literacy, media activism. Telemedium. The Journal of Media Literacy. 42(3).1996.認為,媒介教育以及素養(yǎng)包含最基本的使用媒介、思考分析,以及利用媒介參與創(chuàng)造的過程。周葆華和陸曄認為媒介教育以及素養(yǎng)研究應包括兩部分:一是媒介信息處理(包括思考、質疑、拒絕和核實)②周葆華、陸曄:《從媒介使用到媒介參與:中國公眾媒介素養(yǎng)的基本現狀》,《新聞大學》2008年第4期。;二是媒介參與意向(受眾介入媒介信息生產的行為的“行為意向”③Fishbein, M., & Ajzen, I. Belief, Attitude, Intention, and Behavior: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Research. Reading.MA:Addison-Wesley.1975.)。
由此可見,媒介教育與媒介素養(yǎng)是“一體兩面”的關系。媒介教育是媒介素養(yǎng)形成的動因,而媒介素養(yǎng)的提升反過來又會推動媒介教育的反思與進一步升級。而按照凱文?凱利的12種趨勢的推測以及對照周邊媒介環(huán)境之中媒介技術的迭代升級便可以發(fā)現,“未來已經到來”,可是深處媒介文化之中的媒介使用者們卻依舊沒有準備充分。所以媒介素養(yǎng)教育應適應變化了的媒介環(huán)境,以及人機間同構作用的變化,除了包括基本的使用媒介,對媒介的內容(信息)進行處理(思考、質疑、拒絕與核實),以及主動的媒介參與之外,還應該具備一種新媒介價值觀,即將凱文?凱利的12種趨勢融合到媒介素養(yǎng)教育之中。
特別是對“成為(Becoming)”與“開始(Beginning)”兩大關鍵概念,必須進一步挖掘、理解。“成為”作為12種趨勢之首,表明人們應該放下“人類中心主義”的姿態(tài)而與媒介一起共存、共進。作為具有主體性的媒介使用者,生活在媒介所建構的社會化環(huán)境之中,其本身亦成為一種媒介性的存在,所以人與媒介之間的關系并非主體與對象之間涇渭分明的“二元對立”,而是一種具有“二而一”形式的整體性、合一性狀態(tài)。而“開始”作為最后一個趨勢的關鍵詞,表明媒介教育與素養(yǎng)是推進媒介文化進一步發(fā)展的動力,并且,隨著媒介技術的不斷更新,人類知識也需要不斷地去完善,所以保持一種不斷“開始”的態(tài)度,就是在新媒介環(huán)境之中媒介教育應該秉持的態(tài)度與價值觀。“成為”與“開始”這兩個概念象征的是一種動態(tài)的“變化”,并能夠形成一種周而復始的循環(huán)與自我更新。
所以文章將新媒介時代兒童媒介教育與媒介素養(yǎng)的內涵重新界定為:在泛媒介化的社會環(huán)境之中,基于互聯網媒介的人機關系以及人際關系是隨著媒介技術的迭代升級而同步發(fā)生相應變化,人與媒介、人與他者之間的關系不再是主客二元對立的支配與被支配的關系,而是在人類主體與數字化主體同發(fā)展、共進化下的主體間性平等關系,而作為未來媒介文化的締造者與主力軍——當代兒童的媒介教育與素養(yǎng),需要為其建構新的媒介價值觀,即為其建構超越人類中心主義的“去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助其認識與理解媒介,處理媒介內容(信息),參與媒介過程,提升數字化生存能力素養(yǎng),以期締造更加健康的媒介文化。
二、媒介教育與素養(yǎng)的必要性以及存在的問題
人機同構是基于人與媒介技術的同發(fā)展、共進化的理念而提出的,指出了人與媒介之間的關系并不是作為主體的人與作為對象的媒介之間的支配與被支配的關系,而是賦予人與媒介各自的主體性,從主體間性的角度出發(fā),認為人與媒介之間可以通過交互而相互作用,最終實現進化的同步性。那么,媒介技術的迅速迭代升級對應的便是媒介使用者知覺能力的相應提升,即媒介本體變化的同時,媒介使用者亦隨之同步演化。所以,不同的媒介時代需要具有不同的媒介教育與素養(yǎng),只有直面互聯網媒介時代兒童媒介教育存在的問題,才能克服可能發(fā)生的媒介文化危機偏向。
(一)不同的媒介時代需要不同的媒介教育與素養(yǎng)
以互聯網媒介為中心的媒介化的社會環(huán)境之中,媒介已經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線上生活和線下生活并舉,已經成為人們的生活常態(tài)。在“第一媒介時代”①[美]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時代》,范靜嘩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媒體的話語權掌握在少數的媒介組織之中,媒介組織以輿論形成為目標,對大眾進行無差別的、單方向話語傳播,受眾作為信息接收的一方,在相當程度上只能被動地接收信息,所以此時媒介教育理念在于“防御和免疫”,目的是將大眾從由媒體構建的“欺瞞”之中解放出來。而進入“第二媒介時代”,特別是互聯網技術的發(fā)展,使一般受眾得到的“賦權”,從而使雙向的“對話式傳播”成為可能,網民們自發(fā)形成的“輿論場”能夠有效地與傳統(tǒng)大眾媒介專業(yè)組織形成的“輿論場”進行博弈,最終實現了話語權向大眾的回歸。那么,此時針對變化了的媒介環(huán)境,媒介教育的教育目標也就發(fā)生了變化。即培養(yǎng)大眾信息處理的能力:構建有益信息得能力,培養(yǎng)信息責任感以及規(guī)范意識。從而實現媒介教育的轉型——從“釋放”到“賦權”的媒介教育以及素養(yǎng)理念。②閆方潔:《從“釋放”到“賦權”:自媒體語境下媒介素養(yǎng)教育理念的嬗變》,《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5年第7期。
在大眾傳媒繁榮的“第一媒介時代”,媒介教育的目的在于敦促大眾“啟蒙”,使大眾從大眾傳媒組織所營造的“文化產業(yè)”的“枷鎖”之中解放出來,所以媒介素養(yǎng)培養(yǎng)的中心在于培養(yǎng)大眾信息處理的能力,即:思考、分別、質疑、拒絕的能力。總而言之,這是一種自律的、主體性的批判素養(yǎng)能力的養(yǎng)成。但是由于當時媒介環(huán)境是自上而下的中心化、等級性傳播環(huán)境,單方向的話語傳播導致了“啟蒙”性的“釋放(解放)”不能夠有效地調動大眾營造一個合理的對話性氛圍。受眾的參與受到了“壓迫”,最終大眾信息處理能力的提高便有了局限性。因為傳統(tǒng)大眾媒介單一的“議程設定”以及重復的話語傳播,最終營造的“擬態(tài)環(huán)境(媒介環(huán)境)”遠比現實環(huán)境更為真實,所以鮑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提出了“超真實(super-reality)”這一術語來指稱大眾傳媒所營造的媒介現實。在這樣的環(huán)境之中,約翰?彌爾頓(John Milton)所謂的“真理的自由市場”以及“真理的自我修正”都將失去其效用,因為你無法親歷事實現場,你所看到的僅僅是大眾傳媒想讓你看到的。所以以“防御和免疫”為目的的“釋放性”媒介教育并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
而“第二媒介時代”,特別是2010年代之后互聯網時代,互聯網媒介的“無處不在”,移動終端的普及,以及自媒體交流平臺的繁榮,在“共享、自由、開放”理念的推動之下,受眾在媒介賦權的加持之下,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參與熱情”。互聯網媒介賦權是第一次不依賴權威的賦權——“參與式賦權”。在互聯網媒介所營造的新的媒介生態(tài)環(huán)境之下,中國媒介教育的研究范圍也從“保護主義范式”擴張到了“參與賦權范式”。③強月新、陳星:《我國媒介素養(yǎng)的研究視角及其現狀》,《新聞與寫作》2017年第6期。“參與式賦權”階段不同于大眾傳媒時代的“免疫保護式”媒介教育,并非僅僅注重“知識性的啟蒙”,所以媒介教育的目標不但要提升受眾對新時代媒介文化的認知力,同時重視提升受眾的“參與式”實踐行動力,通過建構并完善受眾的“數字化生存能力”而進一步促進受眾自律性主體意識以及行為的構建。
媒介環(huán)境的新變化推動媒介教育理念發(fā)生相應的改變,所以新的教育目標必須逐漸確立和完善,以此來應對未來可能發(fā)生的大變革。而決定未來發(fā)展的新生代兒童——“祖國的花朵們”其媒介素養(yǎng)教育的實施,及其數字化生存能力的提升便成為新媒介教育關注的頭等大事。因此前文提及OECD(2018)2030工程,便是呼吁各國都應該積極為此尋找解決以及應對的方案,探討當代兒童教育應該建設怎樣的教育體制,以及需要形成怎樣的知識、技術、態(tài)度以及價值。
(二)“媒介參與式賦權”時代,媒介教育與素養(yǎng)存在的問題
數字化媒介對兒童具有強大的吸引力。不同于紙媒,其單純的文字符號需要長久的學習才能夠掌握,數字化媒介以其多媒體融合技術,不僅有文字符號,同時還具有圖畫、顏色、聲音等符號,能夠多樣性地、充分地刺激兒童的五感。在這種多維度的媒介信息的刺激下,當今媒介社會中兒童的閱讀方式已經不同于紙媒時代的線性閱讀方式——“秉神凝息”的沉浸式閱讀,而是采用“分散性”的碎片化式閱讀方式。所以,“讀屏”取代了“讀書”,“讀片(短視頻)”取代了“讀圖”,“使用(access)”取代了“占有”,人機在相互作用的過程之中,強調的是“開放與分享”。然而,正是新媒介時代的新特征,導致了當代兒童媒介教育上出現了眾多的新問題——多維度的信息泛濫使兒童沉浸于娛樂傳播的情境之中,造成“媒介中毒”;“讀屏”取代了“讀書”,使深度思考以及批判性思維的養(yǎng)成變得困難,碎片化閱讀,帶來的碎片化思維,思維分散但是缺乏深度;“使用”取代了“占有”,一切“公開、共有”源自于互聯網的無處不在以及“隨時在線”,于是“連接一切”變成為了可能,隨時與他人建立聯系,建構“情感”,感性傳播易成但是感情卻難以深刻,因為隨時“斷線”成為可能,社交成本的降低帶來的卻是社交的脆弱。
1. 過度依賴電子媒介進行娛樂游戲,消解了童年
娛樂在一般意義上是指人們將自己從勞動之中“釋放”出來,通過游戲來充實自己的休閑時間,從而達到心情轉換或者元氣恢復的目的。①周海寧:《以互聯網媒介為中心的聽覺文化轉向以及構建》,《出版發(fā)行研究》2019年第7期。對兒童來說,游戲是其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德國教育家福祿貝爾(Friedrich Fr?bel)強調了游戲是“幼兒時期最純潔、最神圣的活動”②單中惠:《西方教育思想史》,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7年,第366頁。。兒童通過游戲來觀察世界,形成認知,從而激發(fā)創(chuàng)造力,促進智力的發(fā)展;意大利兒童教育家蒙臺梭利(Maria Montessori)認為兒童心理的發(fā)展具有敏感期,容易受到外界環(huán)境的刺激,而兒童心理發(fā)展的價值在于“兒童對一切事情都充滿了活力和激情,能夠容易地學會每件事物”。③[意]蒙臺梭利:《童年的秘密》,馬榮根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52頁。所以,這共同地說明游戲之于兒童的重要價值。但是隨著互聯網以及移動終端的普及,兒童游戲的手段卻逐漸變得“單一化”。即單純地依賴電子產品進行娛樂游戲。更有甚者,為了讓孩子安靜,父母將兒童完全交托于電子產品,并美其名曰“電子保姆”。然而電子產品的內容物與傳統(tǒng)紙媒不同。例如,在電視時代,尼爾波茲曼便感嘆電視媒介消解了兒童的純真能力。他認為基于文字的閱讀和書寫能力所營造的不透明性保護了兒童的天賦純真,并以此區(qū)分了成人世界和兒童世界。但是電視媒介卻“打破了兒童和成年之間的壁壘”④周海寧:《論從大眾傳媒時代到數字媒介時代的童年變化》,《新聞傳播》2018年第17期。。特別是進入了互聯網時代,由于智能終端的普及,兒童也能夠輕松占有媒介(電腦等智能終端),從而輕松地接觸到電子內容物進行娛樂游戲。并且兒童在使用智能終端在接收娛樂游戲內容上表現出了驚人的天分,正如蒙臺梭利所說“對一切充滿了活力和激情,能夠容易地學會每件事物”。因為影像內容能夠進行多維度的感官刺激,不同于線性文字的單一視覺刺激,消解了文字符號依賴識字教育所建立起來的“壁壘”。成人與兒童在某種程度上被消解了距離與差異。而最重要的是兒童在使用互聯網媒介與使用電視等大眾媒介上沒有典型的區(qū)別,沒有發(fā)揮互聯網媒介的雙向交流功能,而僅僅偏向于易于刺激感官的功能。并且,電子媒介的屏讀功能對兒童教育也帶來了影響。
2. 讀屏時代情感傳播為主的傳播方式造成兒童分散性認知習慣
互聯網媒介時代,屏讀擴展了傳統(tǒng)的紙媒閱讀,成為閱讀的主要方式。媒介使用方式的改變也造成人們認識方式的改變。正如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說的不同的時代都有各自的“新的知覺任務(new tasks of apperception)”。如果說傳統(tǒng)紙媒時代人們閱讀的方式為“沉浸式閱讀”,那么其認知方式則為“集中式認知”,而電子媒介時代人們的閱讀方式為“分散性、碎片化閱讀”,那么其認知方式則為“分散性、碎片化認知”。所以,本雅明認為對傳統(tǒng)繪畫作品的藝術鑒賞需要的是“凝神專注”的“觀照”,才能感受其氣韻(aura);而對電影等電子式藝術作品進行鑒賞的時候,由于其畫面的流動性,人們只能跟隨影片制作的蒙太奇手法,進行意識流動,所以其鑒賞方式則為“分散性專注”⑤周海寧:《從本雅明提出的aura(氣韻)媒介觀看對象與主體關系的演化》,《新聞傳播》2018年第21期。。那么,進入互聯網時代,兒童媒介教育理應順應媒介發(fā)展趨勢,培養(yǎng)兒童的“碎片化閱讀”“分散性專注”的知覺能力,使其能夠更好地駕馭新時代媒介。但是凡事過猶不及,以屏讀為基礎的碎片化“觀看”,容易造成兒童認知的過度分散。畫面的流動性使兒童難以長時間地關注于同一事物,而卻容易沉溺于流動性畫面對感官刺激所帶來的“沉溺性專注”,從而造成電子產品“中毒”現象。
由于互聯網媒介內容的碎片化特點,造成了使用者的碎片化閱讀偏向。而為了迎合受眾需要,媒介內容便越來越呈現出碎片化特點。于是,不同于紙媒時代,“凝神貫注”所對應的是深度思考能力,碎片化閱讀對應的是閱讀的快捷性和移動的便利性,而碎片化內容所對應的“淺閱讀”特點,容易造成受眾惰于思考,而極易引發(fā)情感響應。特別是互聯網媒介的內容具有多維度、多樣化的特點,所以互聯網媒介傳播具有傾向于感性傳播的特性。所以,對于兒童來說,互聯網媒介較之傳統(tǒng)媒介更具有吸引力,更能吸引兒童的參與意向。但是偏向于感性傳播,理性不足,必然造成思考力度不夠,而其強大的“參與性”吸引力的加持之下,勢必造成兒童極易沉溺其中、無法自拔。并且,網絡無處不在,具有“連接一切”的特性,這使人們的線上與線下生活并舉,但是線下的實體性生活與線上的虛擬性生活之間依舊存在較大的差異性,因為虛擬空間具有流動性以及不確定性的特征,相較于線下生活呈現出的人際關系更具有“脆弱性”。所以凱文?凱利指出了“以媒介技術為中心的連接與現實生活的情感連接之間存在著矛盾”①[美]雪莉?特克爾:《群體性孤獨》,周逵、劉菁荊譯, 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81頁。。因為線下的情感連接是建立在實體性情感以及諸多的社會約束的前提條件之下,人們在現實的關系之中更加容易地尋找到平衡,所以可以維持相對的穩(wěn)定,但是虛擬網絡空間的線上情感連接的形成,需要付出相對較少的社會成本,并具有虛擬性的非實體關系,即呈現出一種弱關系連接,所以虛擬關系的建構與瓦解相對于線下實體性關系來說更加具有容易性。
所以,兒童一旦沉迷于虛擬空間的弱關系連接,由于其相對較少的社會成本以及個人管理成本的付出,極有可能弱化兒童對線下實體交往的興趣,而從整體上對其虛擬的數字化生活和實體的現實生活的均衡產生影響。從互聯網時代虛擬傳播的感性化、情感化偏向來看,兒童過度依賴數字化的虛擬空間生活,形成分散性認知的認知慣性,最終將會降低其數字化的生存能力,這所帶來的問題則應該是媒介教育應該重點關注之所在。
三、互聯網時代建構兒童新媒介文化素養(yǎng)的路徑
互聯網時代以媒介為中心的兒童教育其中心乃是媒介教育。媒介技術的變化,使媒介教育也必須相應地發(fā)生變革。互聯網時代的兒童必須是可以進行雙向信息傳播,融信息生產、分配、消費于一體的能動性的信息主體。所以,互聯網時代的兒童不再是大眾傳媒時代的媒介附庸型存在,而是能夠積極地進行參與的能動性信息主體。這體現了在新時代人與媒介在共同建構的框架下同發(fā)展、共進化,媒介技術的迭代升級亦推動媒介使用者主體性的變化。所以兒童媒介教育必須順應新媒介時代人機、人際關系的新變化,提升兒童的新媒介素養(yǎng)能力,助其增強數字化生存能力。
(一)樹立媒介文化批判意識素養(yǎng)
英國學者萊恩?馬斯特曼(Len Masterman)指出,培養(yǎng)公眾對媒介負面功能的覺醒和反思能力,始終是媒介素養(yǎng)教育的首要任務。②閆方潔:《從“釋放”到“賦權”:自媒體語境下媒介素養(yǎng)教育理念的嬗變》,《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5年第7期,第147-150頁。這一觀點便是樹立媒介批判意識的體現。正如尼爾?波茲曼所認為的電子媒介由于其媒介屬性以及媒介所呈現的內容物(特指電視媒介)消解了童年,造成兒童與成年之間的“壁壘”崩潰。所以,媒介教育首先就是樹立對媒介屬性的批判性認知,從這一角度來提升兒童的批判性素養(yǎng)能力,正確認知媒介文化。例如:與互聯網的“碎片化信息”相對應的人的新的認知任務便是擁有“分散性認知”的能力,而“分散性認知能力”對應的是碎片化閱讀的能力,同時互聯網媒介還具有“普遍存在性”“連接一切”的特性,這些使信息時效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增強,使線上的各種連接(包括人際關系的連接)變得相對容易,而線上的連接與線下的連接之間是存在差異的。所以兒童媒介教育應有針對地將這些新出現的特性以及隱藏的可能性對兒童進行教育,使其形成相應的批判性媒介文化素養(yǎng)。
(二)平衡深度思考與碎片化思維能力
文字閱讀能夠培養(yǎng)兒童深度閱讀的能力,是維護兒童與成年之間差別的重要手段,能夠提升兒童智力,保護兒童的天真爛漫。而“屏讀”的對象主要是圖像,是一些“碎片化的內容”,訓練兒童“碎片化閱讀”的能力,能使兒童盡早適應新媒介時代信息的迅速性與復雜性,培養(yǎng)兒童在眾多信息中獲取有用信息的能力。這是新媒介時代兒童所應該具有的“新的知覺任務”。但是過度偏向于碎片化閱讀卻容易導致兒童思維的扁平化,不易于其進行深度思考。所以只有兼顧二者才能使兒童思維更加全面地發(fā)展,也不至于沉溺于電子媒介而造成“中毒”,如此才能以更加健全的數字化生存能力去建構更加健康的媒介文化。
(三)兼顧線上虛擬的數字化生活以及線下的實體化生活能力
互聯網媒介時代媒介教育應該同時兼顧線上與線下生活。互聯網媒介的特性便是“公開、分享、參與”。強參與性傾向是互聯網媒介媒介屬性所帶來的,而互聯網的“普遍存在性”以及“連接一切”的特性使兒童在參與線上生活變得更加簡易。可以說當代兒童天然地兼顧“線上與線下”雙重的混合式生活方式。但是線上生活偏向于感性傳播,而線下生活偏向于理性傳播,并且線上和線下的制約因素不同。線上的人際關系相對于線下要較為松散,線上身份的匿名性與眾多的不可知性使線上活動受到的制約要遠小于線下的實際的實體性生活。因此,線上生活就相對較少地肩負責任性,相應地,線上的關系也較之線下關系更為脆弱。如果一味沉溺線上關系勢必對兒童心理造成深遠的影響。所以媒介教育應該在注重媒介的參與性實踐的同時,更多地將線下的理性傳播融入其中,讓兒童從小就樹立堅定的責任意識和行為秩序意識,如此方能更好地適應未來的媒介化生存。
(四)在人機同構的理念下,建構同發(fā)展、共進化的價值觀
“未來已經到來”,人工智能已經充斥在我們的生活之中了。凱文?凱利所指出的12種趨勢,已經逐步現實化了。在媒介技術如此快速發(fā)展的今天,兒童媒介教育必須正確處理人與媒介的關系,人不再是媒介技術的附庸,而媒介也不再單純是人類征服世界的工具了。在“成為”“共享”“互動”等理念的加持作用下,兒童媒介教育與素養(yǎng)的內涵應該進一步完善:兒童媒介教育應該在新媒介文化時代,在人機同構理念下,超越傳統(tǒng)的“人類中心主義”發(fā)展模式,形成基于“去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以人與媒介“同發(fā)展、共進步”為手段的新發(fā)展模式。如此,新媒介文化時代的兒童才有可能逐步擁有較完善的知識、技術、態(tài)度,才能超越以及完善自己的世界。
四、結論
媒介所構建的世界是一種符號化的人為的世界,是區(qū)別于客觀存在的“第二自然”。不同時代的人們依靠媒介創(chuàng)造出不同的傳播文化,賦予生活以不同的意義以及關系。而生活在新媒介時代的兒童也會通過屬于自己時代的媒介來構建屬于自己的,與其他時代不同的,以媒介為中心的文化。而新媒介文化構建的關鍵在于如何使用媒介,具體來說就是應該掌握怎樣的媒介知識、技術、態(tài)度、價值。也就是說,不是單純地僅僅掌握媒介使用的知識,還應該了解媒介的技術本質,以及對待媒介所應持有的價值態(tài)度。所幸,在互聯網時代,隨著人們媒介參與度的不斷增強,媒介之于人類社會、文化的重要性已經被廣泛地認知并認可。因為互聯網媒介是第一次不依靠權威對民眾實施了賦權,這不但說明了媒介的重要性同時也說明了媒介的可變性。所以,新媒介文化時代,作為數字化存在的主體——兒童,其媒介教育不但要使其掌握基本的媒介知識,還需要具有對信息的思考、分別、質疑以及拒絕的能力,形成與媒介技術的迭代升級相適應的知覺意識。而具體來說,在以互聯網媒介技術為基礎構建的讀屏社會之中,分散性的認知能力是兒童順應媒介技術發(fā)展自然而然具有的能力,但是以文字閱讀為基礎的深度閱讀能力是兒童為了不成為媒介技術的附庸所必須培養(yǎng)以及習得的能力。特別是媒介化的生活能夠使兒童同時深度體驗兩種不同的生活:線下實體性生活與線上虛擬性生活。而新生代的兒童由于是互聯網的原住民,其對線上虛擬生活的貼合度要遠遠大于人們的想象,所以需要其能夠兼顧兩種生活而不過度偏于一隅。這是兒童對待媒介所應持有的態(tài)度。而理念(意識形態(tài))對實踐具有指導作用,所以兒童在建構以媒介為中心的新的傳播世界的同時,擁有“人機共存、共發(fā)展”的人機一體的“去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觀是關系到人與媒介關系朝著共贏方向發(fā)展的關鍵。這就是生活在以互聯網媒介為中心的當代兒童所需要具備的媒介知識、技術、態(tài)度以及理念價值。而媒介素養(yǎng)教育就應該據此綜合考慮來完善目前的教育體制,對當代媒介教育的偏向及時進行糾偏,讓中國的兒童在新媒介時代能夠接受到相對完善的媒介素養(yǎng)教育,助其建構屬于自己時代的媒介文化,同時推動整個中國的教育事業(yè)再上一個臺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