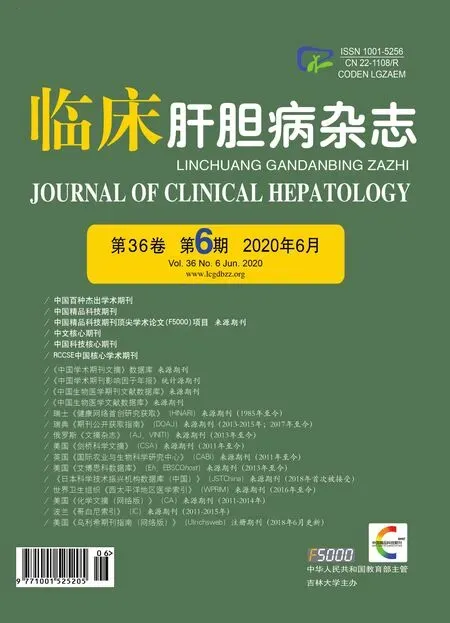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更名帶來的新思考
高 鑫
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 內分泌科, 上海 200032
自1980年Ludwig等采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這一術語用于描述沒有大量酒精攝入的情況下出現的脂肪性肝病以來,這一疾病的命名和診斷標準一直沿用至今[1]。按照目前的診斷定義,NAFLD已成為世界上大多數地區最常見的慢性肝病,全球患者數高達10億。根據最近我國學者[2]發表的數據顯示,全國NAFLD患病率為29.2%。NAFLD的危害不僅局限于肝病相關的高發病率和死亡率,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NAFLD是一種代謝紊亂相關的多系統疾病,在肥胖和2型糖尿病(T2DM)患者中更為常見,而且與這兩個共患疾病有著相似的不良結局。NAFLD患者死于心血管疾病的可能性是死于肝臟疾病的2倍[3]。然而,無論在公眾層面還是在專業領域,目前對NAFLD作為一種全身代謝性疾病的認識仍然不足,造成患者中對NAFLD知曉率、就診率、治療率低的局面。為了加強對這一疾病與代謝相關疾病的認識,筆者與《臨床肝膽病雜志》特別組織本期重點號,邀請全國該領域知名消化肝病和內分泌代謝專家分別對NAFLD涉及的代謝性疾病進行撰文,旨在從NAFLD的更改命名、糖尿病與NAFLD共患疾病的轉歸、防治、脂肪肝與腫瘤以及NAFLD發病機制最新進展進行系統論述,從而為消化肝病、內分泌代謝疾病、心血管疾病、腫瘤專業開展多學科合作達成共識。
1 NAFLD更名為代謝相關脂肪性肝病(metabolicassociatedfattyliverdisease, MAFLD)的重要意義
NAFLD這一命名已經沿用40多年。NAFLD定義為:除外過量飲酒和其他明確的損肝因素所致的肝細胞內脂肪沉積,包括從單純的肝脂肪變性到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以致一部分最終發展為肝硬化,甚至演變為肝細胞癌(HCC)的一組疾病。從病名字面可以看出其重點是集中在肝臟,而且以“排除性”的方式命名。這意味著其只在沒有明確病因所致脂肪肝的情況下才存在。然而,隨著我們對疾病認識的不斷深入,發現脂肪肝不僅可與病毒性肝炎、自身免疫性疾病和酒精性肝病等其他肝病并存,并對疾病的進展產生協同作用。而且大量證據顯示,NAFLD是一種代謝紊亂相關的多系統疾病,在肥胖和T2DM患者中更為常見。此外,其他內分泌代謝疾病也伴隨脂肪肝,譬如:多囊卵巢綜合征、甲狀腺功能減退、性腺功能減退、生長激素缺乏癥等。因此,NAFLD的命名不能滿足目前對這一疾病診斷和治療的需要,在定義中這些伴隨或共患疾病不應該被“排除”,而應該是“包括”,脂肪肝疾病的命名和診斷標準需要反映這一新認知。2020年2月,Gastroenterology發布了國際知名胃腸病、肝病、營養、病理學專家組共識[4],提出以“代謝相關脂肪性肝病(metabolic associated fatty liver disease,MAFLD)”取代現有命名。繼該共識發表之后,2020年4月在JournalofHepatology發表了國際專家組隊MAFLD的診斷定義共識[1]。這兩個共識的發表是NAFLD認識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非常可喜的是范建高教授親自參與了這兩個共識的制訂過程,本期重點號特邀范建高教授論述了兩個共識的重要內容和意義。
2 NAFLD/NASH可能成為T2DM并發癥
NAFLD使新發糖尿病風險增加2~3倍,在已診斷的T2DM患者更容易患脂肪性肝炎、肝纖維化和終末期肝病。胰島素抵抗是二者共同的發病機制。NAFLD和T2DM患者在肌肉、肝臟、脂肪組織均存在胰島素抵抗。胰島素抵抗引起脂肪組織的功能失調,脂肪分解率增加引起的游離脂肪酸(FFA)增高有助于肝脂肪沉積和其他組織異位脂肪的形成,進一步加重全身胰島素抵抗。過量的FFA是誘導肝臟炎癥、線粒體功能障礙、氧化應激的重要原因。在肝臟可激活肝星狀細胞的纖維化反應,從而促進進展為NASH和肝硬化。糖毒性和脂肪毒性是密切相關的,兩者均可導致T2DM中胰島素抵抗的惡化和胰島素分泌的受損。二者互為因果,形成惡性循環[5]。
內分泌科醫生日常工作中幾乎每天都會遇到肥胖以及肥胖相關的并發癥,因種族差異和檢測方法的不同,肥胖患者中NAFLD患病率存在很大差異,我國在肥胖患者中脂肪肝伴隨率可以高達70%~80%[6-7],已經診斷的T2DM患者中脂肪肝患病率在50%~80%[8]。與非糖尿病NAFLD患者相比,伴有T2DM的NAFLD患者肝臟病變更加嚴重,加速向 NASH進展,增加晚期纖維化和HCC的不良結局。因此,近年來有專家提出:應將NASH視為T2DM并發癥的概念。然而,目前NAFLD并未歸入糖尿病并發癥(如已經公認的有視網膜病變、神經病變和腎病),長期以來糖尿病患者的肝臟成為一個被忽視的器官,糖尿病伴隨脂肪肝的患者在臨床上常被內分泌科醫生和初級保健醫師忽視[9]。令人擔憂的是,相當多的T2DM患者,尤其是病程長、代謝控制不佳的患者,已經存在NASH或不同程度肝臟纖維化,然而,只有少數患者得到及時診斷。造成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包括:(1)患者和臨床醫生對NASH的潛在危害了解不足;(2)檢測設備和評估標準不統一;(3)由于肝活檢病理診斷十分有限,因此對糖尿病患者中脂肪肝肝炎、纖維化的患病率的研究相對較少;(4)患者和醫生不了解減輕體質量和某些藥物治療可能逆轉NASH[8,10-11]。在國內外有關脂肪性肝病相關診療指南和共識中已經提出推薦意見: 對于NAFLD患者,必須進行糖尿病篩查;由于T2DM患者有很高的肝病進展風險,因此應在T2DM患者中檢查是否存在NAFLD[10]。
最近,卞華教授團隊[12]根據肝活檢病理診斷結果,首次報道了我國糖尿病患者脂肪肝的嚴重程度分級,在糖尿病伴隨NAFLD患者中NASH和進展性纖維化的比例分別高達96.1%和56.5%。這一結果進一步支持T2DM患者中NAFLD是糖尿病并發癥的觀點。本期重點號特邀卞華教授詳細論述有關T2DM伴隨NAFLD的最新證據和治療進展。
3 降低肝脂肪含量可以逆轉糖尿病
NAFLD既是一個糖尿病發生的始動因素,也是一個加速糖尿病患者肝病進展的危險因素。NAFLD和T2DM既是惡性循環,又是互為因果,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將改善和治療T2DM的靶點集中在脂肪肝,則起到一石二鳥之功效。如果降低肝脂肪含量,是否既能逆轉脂肪肝,又能逆轉糖尿病呢?
雖然長期以來,糖尿病是“終身性疾病”的概念已經根深蒂固,但是近20年來發現T2DM臨床逆轉的證據越來越多。首次報道T2DM逆轉的證據來自減肥手術(代謝手術)的效果[13]。這一現象在限制熱卡飲食干預的前瞻性研究中不斷得到證實。英國一項糖尿病緩解臨床研究(DiRECT)[14]給與低熱卡飲食((825~853 kcal/d )干預12個月,約50%的糖尿病患者得到緩解。糖尿病緩解率因體質量減輕程度而不同,試驗過程中體質量增加的患者緩解率為零;體質量降低0~5 kg的受試者緩解率僅7%;體質量減輕5~10 kg緩解率為34%;體質量減輕10~15 kg緩解率57%;減輕15 kg或以上的緩解率高達86%。繼續干預12個月,在24個月內約超過1/3的T2DM患者得到緩解。持續緩解與持續減肥的程度有關[15]。
T2DM逆轉或緩解的現象,為T2DM的治療帶來新希望。對其機制的探索更是引起人們的極大興趣。Taylor 教授[16]提出了雙循環(the twin-cycle hypothesis)假設較好地解釋了這一現象的發生機制。肝臟作為第一個惡性循環是指長期攝入過量的熱量(正能量平衡)會導致肝脂肪沉積,進而導致肝臟胰島素的抵抗。肝臟胰島素抵抗對糖、脂代謝紊亂起著關鍵作用。脂肪肝促進肝臟糖異生,肝糖輸出增加,刺激胰島素分泌引起內源性胰島素分泌增加,加重肝脂肪沉積;脂肪肝促進肝脂肪酸和甘油三酯從頭合成,導致肝脂肪輸出率增加,使脂肪在全身其他組織中沉積(脂肪的異位沉積)。肝臟產生的甘油三酯以低密度脂蛋白的形式輸出后在胰腺沉積,則進入第2個惡性循環[17]。胰腺沉積過多脂肪引起β細胞受損。如果能量攝入過剩持續存在,這兩個惡性循環便持續進行,最終導致β細胞功能在數年后衰竭,致使T2DM發生與持續進展。雙循環假設是以脂肪肝為中心的肝-胰雙循環假設。限制飲食、代謝手術等方法使體質量下降,隨著能量過剩糾正,首先是肝臟胰島素抵抗改善,肝臟向胰腺輸出的甘油三酯減少,使第二個惡性循環恢復到正常,糖尿病可以緩解。肝脂肪過度沉積在雙循環理論中扮演了主動角色,以減輕和逆轉脂肪肝的策略是逆轉T2DM的關鍵。本期重點號特邀顏紅梅副教授詳細論述改善脂肪肝與逆轉T2DM問題。
4 NAFLD/NASH與肝癌關系密切機制同源
HCC是最常見的一種原發性肝癌,在全球范圍內是第二大實體瘤致死的癌癥。隨著肥胖和糖尿病的流行,NAFLD/NASH已經逐漸發展成為西方發達國家HCC的主要病因。來自美國的對比研究中,NASH相關肝硬化患者的HCC年累積發病率為2.6%,NAFLD或NASH成為肝癌最常見的潛在危險因素,NAFLD相關肝癌認為是美國肝移植的新指征。在韓國和日本均有類似報道[18-19]。肥胖、T2DM和NAFLD分別是肝癌的獨立危險因素。
代謝改變是所有癌細胞的特征之一。肥胖和T2DM的特點是脂肪組織、肝臟和腸道等多個器官的代謝失衡,脂肪組織-肝臟-腸肝軸的調節紊亂在NAFLD的病理生理學中發揮重要作用。慢性持續性能量攝入過剩、高脂肪或高果糖飲食引起的代謝應激可引起肝脂肪過度沉積、引起肝細胞代謝紊亂,肝細胞活性氧、內質網應激和氧化應激增加,引起細胞代謝重新編程。這些過程導致肝細胞凋亡和壞死,從而啟動肝臟炎癥反應。先天性免疫的啟動通過細胞因子進一步影響肝細胞代謝,導致肝細胞代謝紊亂加劇,進一步加重肝細胞損傷、細胞死亡、DNA損傷,代償性肝細胞增殖和免疫細胞活化進一步增強,激活了肝星狀細胞和纖維化,從而推動致癌過程。當抗腫瘤免疫監測無效時,癌前病變可能發展,最終導致HCC的發生[20]。隨著對NAFLD/NASH與HCC研究的深入,認識到由肥胖、胰島素抵抗、T2DM為背景的代謝紊亂對HCC的發病機制的關鍵作用,更加理解脂肪肝成為更廣義的代謝性疾病,以及NAFLD更名為MAFLD的合理性。本期重點號特邀施軍平教授系統論述從NASH到HCC流行現狀、臨床特征以及發病機制研究進展。
5 基礎研究
近年來對NAFLD/NASH發病機制的基礎研究十分活躍,涉及多重代謝通路調控異常[21]。基于目前尚沒有治療NASH的藥物上市,基礎研究的一個重要目的是研發治療NASH的藥物[22]。目前已經有針對不同代謝通路和靶點的治療NASH的新藥分別進入臨床前和臨床研究正在進行中[23-24]。已經看到ACC、ASK1、SCD1抑制劑和FXR激動劑治療NASH患者的臨床療效。這對治療NASH藥物尤其關注其對多代謝平衡的恢復,其目的是減少代謝底物向肝臟的傳遞或促進其安全處理。減輕NASH的代謝驅動因素應該是一種有效的治療方法。NASH的理想治療藥物不僅可以改善肝臟疾病,而且可以治療/預防與NASH相關的多發病(如T2DM或腦血管疾病)[24]。近年來在針對核受體作為代謝靶點的NASH藥物研發方面有更多的證據,尤其是Farnesoid X受體激動劑奧貝膽酸正在進行的Ⅲ期臨床試驗,顯示了良好的前景。
6 展望
NAFLD和T2DM是我國目前患病率高、患者數龐大的慢性代謝性疾病,從發病機制到疾病進展,二者有著共同的病理生理基礎,累及全身各個器官和多個代謝通路。肥胖、能量過剩、非肥胖患者的脂肪異位沉積(非肥胖患者NAFLD)是這兩個疾病的共同特征,糾正代謝異常成為預防和控制疾病發生和進展的關鍵。
然而,在實際工作中,NAFLD更名為MAFLD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長期以來NAFLD的重點強調肝臟病變和肝病相關結局,內分泌代謝醫生按照目前糖尿病臨床指南處理T2DM的同時往往忽視了對肝臟病變的篩查、診斷與處理。以降低肝脂肪含量為目標的防治T2DM的策略需要多學科臨床與基礎合作:消化肝病專業、內分泌代謝專業、營養、運動、心理、社區醫生共同學習和落實相關指南和共識,以用共同理念防治肥胖、脂肪肝、糖尿病,才能將最常見的慢病防治落到實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