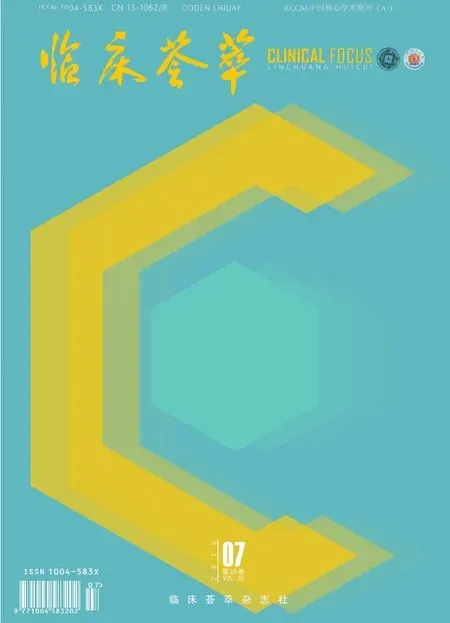冠狀動脈鈣化病變機制及治療相關的研究進展
畢 月,李擁軍
(1.河北醫科大學 研究生院, 河北 石家莊 050017; 2.河北醫科大學第二醫院 心內四科,河北 石家莊 050000)
冠狀動脈鈣化(coronary artery calcification, CAC)通常被認為是動脈粥樣硬化的自然進程,是一種血管退行性病變,主要是由于鈣鹽異常沉積于冠狀動脈壁,累及血管中膜和血管內膜從而導致血管壁硬化,使血管收縮反應降低,從而影響冠狀動脈血流。同時內膜損傷引起各種炎性反應促進斑塊的形成[1]。CAC病變通過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PCI)成功率低,術后并發癥較多,容易出現支架難以到位、膨脹不全、支架貼壁不良、支架內狹窄及支架內血栓形成等問題,是介入手術發展一大瓶頸。
藥物洗脫支架(drug-eluting stent, DES)是指在金屬裸支架(bare metal stent, BMS)上涂有抗內皮細胞及抗平滑肌細胞增殖的藥物,相對于BMS,DES可以降低支架內再狹窄及減少靶目標血運重建的發生率,但是,有可能增加晚期血栓發生率[2]。對于CAC病變,DES治療后的血管反應及其病理機制目前尚不明確。
1 CAC病變的發生機制
CAC通常分為中膜及內膜鈣化,兩者形成上不完全相同。內膜鈣化多是由于脂質蓄積和巨噬細胞滲出引發炎癥反應使鈣鹽沉積于血管壁。中膜鈣化通常是與鈣鹽代謝及糖代謝紊亂有關,發生于彈性蛋白和平滑肌纖維,與脂質沉積和巨噬細胞滲出無關[1]。動脈粥樣硬化斑塊始于富含脂質的泡沫巨噬細胞和血管平滑肌細胞的積累,導致內膜增厚。同時被巨噬細胞和T淋巴細胞浸潤,形成被纖維組織包裹的富含脂質的壞死核心,稱為纖維動脈瘤。在動脈粥樣硬化的早期階段,可以看到巨噬細胞浸潤到脂質池中,并且伴蛋白聚糖和膠原基質的灶性丟失。纖維狀動脈瘤的晚期,易損斑塊或薄帽纖維化動脈瘤由被薄纖維帽覆蓋的大壞死核組成。當纖維帽破裂時,發生斑塊破裂[11]。鈣化的初始形成與四種機制有關:即動脈粥樣硬化中炎癥細胞死亡釋放的凋亡小體和壞死碎片形成了磷酸鈣晶體形成的成核位點、壞死核心細胞外空間中的基質囊泡可作為鈣化的病灶、鈣化抑制劑的局部減少、周細胞和/或平滑肌細胞分化參與骨形成的誘導。影響血管鈣化的因素還包括內皮損傷、氧化應激、基因、遺傳、飲食、環境、感染、藥物等因素。盡管CAC是冠狀動脈粥樣硬化的標志,但密集的鈣化(通過CT測量鈣化積分,即鈣化面積×鈣化灶峰值>400 HU)通常與穩定的斑塊有關。相反,微鈣化(通常也稱為斑點鈣化)是由于巨噬細胞和平滑肌細胞凋亡,鈣化抑制劑減少,過多的鈣沉積所致,一般為鈣化的早期階段,被認為是易損斑塊的標志。同時有研究表明,纖維帽中的微鈣化可能會增加局部組織應力(取決于一個微鈣化位置與另一個微鈣化位置的接近程度,以及微鈣化相對于血流的方向),從而導致斑塊不穩定[4]。
2 CAC病變的治療
CAC病變治療上分為藥物治療、介入治療、手術治療等。對于介入治療及手術治療作為有創的治療方法應根據相關的治療指征,血運重建應具有充分的循證醫學證據,有研究發現,PCI治療穩定性心絞痛患者并不能改善患者預后[22],ACS相對于穩定性心絞痛的CAC患者更有血運重建的必要性。
2.1CAC病變藥物治療 CAC病變的形成是個長期過程,曾經多項研究試圖通過藥物來逆轉血管鈣化。有研究發現,他汀類藥物有抗炎作用,能使較晚期動脈粥樣硬化性疾病的患者受益[3]。也有研究發現,他汀類藥物可通過減少動脈粥樣硬化炎癥反應來阻滯血管鈣化的進展[5]。然而Healy[6]等研究發現他汀類藥物能夠通過抑制巨噬細胞Rac1-IL-1β信號軸來增加動脈粥樣硬化的鈣化。Rifai等[7]研究亦發現應用他汀類藥物并不改善CAC患者預后。因而他汀類藥物對CAC病變的作用目前來說仍不明確,需要更多的臨床研究進行證實。有相關研究發現鈣通道阻滯劑、血管鈣化抑制劑、磷酸鹽結合劑等藥物可以延緩 CAC病變的進程,但缺乏多中心大規模的前瞻性研究[8, 10]。
2.2CAC病變的介入治療
2.2.1DES植入后CAC病變處血管反應及雙抗時間 DES相對于BMS治療CAC血管病變,顯示出支架內再狹窄率低、靶血管重建發生率低等優勢[2]。Kereiakes等[15]研究發現,在10 026例受試者中,DES治療組支架血栓形成率低于BMS治療組(1.7%對2.6%;P=0.01)。為減少支架內血栓形成及不良心血管事件的發生,抗血小板藥物的應用起到重要的作用。2018歐洲心臟病學會在心肌血運重建指南中提出,穩定性冠心病患者行PCI術后,無論使用哪種支架,雙聯抗血小板(dual antiplatelet therapy, DAPT)時間推薦為6個月,(Ⅰ類推薦A級證據)[16]。但DES植入后支架內支撐桿新生內膜覆蓋不全,需要長時間的DAPT治療。DAPT應用時間長增加了患者出血的風險,應用時間短又使得支架內血栓形成,應用DAPT時間對于患者治療及預后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有研究發現在2 216例接受第二代DES植入治療的急性冠脈綜合征患者中,短期(≤6個月)和標準持續時間(>12個月)DAPT的主要事件終點(心源性死亡,心肌梗死,支架內血栓形成,中風和大出血)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66)[9]。由于應用雙抗藥物時間與新生內膜覆蓋支架速度、覆蓋率有關,為了更好的掌握雙抗時間的度,Lee等[12]教授曾對新一代DES的新生內膜覆蓋率對DAPT時間影響做了相關研究,894例患者分別隨機分為依維莫司洗脫支架(everolimus-eluting stent, EES)組和生物可降解聚合物涂層支架(biolimus-eluting stent, BES)組,并隨機分為光學相干斷層掃描(OCT)和血管造影術(CAG)組。結果顯示,患者植入EES與BES后3個月,EES和BES新生內膜覆蓋率在OCT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69),但是相對于CAG組,OCT組有更高的新生內膜覆蓋率(P=0.009)。兩組均根據血管內膜未覆蓋率決定DAPT時間,3個月后新生內膜未覆蓋率≤6%時,則停用氯吡格雷,使用阿司匹林單抗治療,新生內膜覆蓋率>6%則繼續應用DAPT至12個月,結果顯示3個月DAPT治療和12個月DAPT治療患者心源性死亡、心肌梗死、支架內血栓、大出血風險分別為為0.3%和0.2%。提示OCT指導支架植入,可以進一步更細致評判DAPT時間,減低心血管不良事件發生率,減少大出血的風險。
鈣化的血管對DES植入后的血管反應如何?Torii等[13]對CVPath尸檢登記處入選104例共134處DES植入進行了回顧性研究,通過放射影像學將其分為嚴重鈣化組(彌漫性鈣化,支架段占70%以上)和非嚴重鈣化組,通過進行形態計量學分析和組織學評估,研究DES植入30天后嚴重鈣化組和非嚴重鈣化組病變處的病理反應。結果發現嚴重鈣化組中支架內血栓形成率、再狹窄發生率、支架內新生內膜未覆蓋面積均明顯高于非嚴重鈣化組。并得出結論,支架小梁錯位和缺乏內膜撕裂是延遲支架覆蓋的獨立預測因子。由于嚴重鈣化組中DES新生內膜未覆蓋率相對于非嚴重鈣化組嚴重,因而DAPT治療可能需要更長時間,但目前對于冠脈嚴重鈣化患者DAPT時間時長研究較少,這項研究從病理及組織學角度分析,得出CAC是新一代DES植入后支架內膜未覆蓋及延遲動脈修復的獨立預測因子,但此項研究的對象是尸體,對于真實世界的患者來說,此項研究結論可能并不完全適用。張瑞巖等[14]對于97例共99處DES植入大于8個月的患者行血管內超聲(intravenous ultrasound, IVUS)檢查,根據檢查結果分為鈣化組及非鈣化組,比較兩者之間內膜增生程度。結果顯示DES治療鈣化病變支架擴張程度和對稱性均較差,鈣化組與非鈣化組相比,內膜增生明顯減少。因而推測,延長DAPT有可能會減少DES植入后的支架內血栓發生率。
2.2.2第一代DES與第二代DES在CAC患者中療效比較 隨著藥物及支架材料發展,第二代DES與第一代DES的主要不同點在于其藥物涂層采用可降解生物聚合物,避免了由此引發的血管炎癥等反應,從而減低了不良心血管事件發生率,可能降低晚期血栓發生率[17]。
然而,對于第一代和第二代DES在CAC患者中的療效是否存在差異,國內外對此研究較少。Nishida等[18]首先對第一代和第二代DES治療CAC患者的效果進行分析,將6090例入選人群分為鈣化組(≥1個中/重度鈣化病灶)和非鈣化組(無/輕度鈣化),并分別將第一代DES和第二代DES植入鈣化組和非鈣化組,主要事件終點是3年內的靶向病變血運重建(target lesion revascularization,TLR:定義為PCI或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治療靶病變的再狹窄或血栓,包括近端和遠端邊緣節段,以及側支的開口)。主要結果顯示第一代DES和第二代DES對TLR的影響并無顯著差異。次要結果顯示第二代DES的不良心血管事件(心臟性死亡、心肌梗死、臨床驅動的TLR)的3年累積發生率顯著低于第一代DES。但此項研究可能存在統計問題,同時存在兩個隨機對照試驗的時間、治療策略、病例選擇、病變形態學和治療方法不同的問題,故研究結果可能存在偏移。對于第一代和第二代DES對于CAC患者中的療效更缺乏多中心大規模臨床研究。
2.2.3DES植入前CAC病變處理方法 為解決CAC病變PCI中支架不到位及支架膨脹不全等問題,目前臨床上常在支架植入前對進行斑塊修飾,常用的方法包括:切割球囊(cutting balloon, CB)、冠脈旋磨術(rotational atherectomy,RA)、冠狀動脈軌道旋切術(orbital atherectomy,OA)、準分子激光冠狀動脈斑塊消融術(excimer laser coronary atherectomy, ELCA)。到底哪種方法處理CAC病變優勢更大,臨床上眾說紛紜,一方面要根據病變的位置,另一方面要根據鈣化的嚴重程度。比如,對于輕中度鈣化,適用于CB,而RA更適用于中度CAC患者,同時也適用于復雜的分叉病變。Redfors等[19]對ADAPT-DES研究進行事后分析,150例應用了RA和53例應用CB的CAC患者,在兩年的研究期間,前者的靶血管失敗(target-vessel failure, TVF:定義為死亡、心肌梗死和TLR)率20.8%,后者為24.1%,提示DES治療CAC病變,TVF發生率較高,與斑塊修飾技術無關。但此項結論存在局限性,病例數偏少。ORBIT I和ORBIT Ⅱ研究了OA在CAC患者中應用[21,28],結果發現在植入冠脈支架之前采用OA去除嚴重鈣化斑塊,患者在2年時間內主要心臟不良事件發生率明顯低于歷史對照組[8]。ELCA可適用于CAC病變、慢性完全閉塞病變、支架內再狹窄等復雜冠狀動脈病變,其最大的手術風險在于冠狀動脈穿孔,因而導管的直徑及激光的能量及脈沖頻率的選擇至關重要。有研究表明,對于球囊擴張失敗的血管病變,嚴重血管鈣化較非鈣化血管相比,應用ELCA治療成功率低,對于嚴重鈣化的血管病變,很多術者仍會首選RA,RA需要將專用0.009 in導絲送入冠脈遠端,但旋磨導絲難以通過嚴重狹窄病變,ELCA修飾病變后有助于旋磨導絲通過,兩者聯合應用對于處理嚴重鈣化能提高成功率[20]。
2.2.4DES植入后CAC患者預后 多個研究顯示BMS植入后CAC患者的存在并發癥多,尤其是支架內再狹窄風險高,DES治療CAC病變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研究偏少[24-25]。HORIZONS-AMI和ACUITY研究的合并分析中顯示,中度/重度靶病變鈣化與1年內支架血栓形成的發生率有關,同時與缺血性TLR發生也存在關聯性。隨著鈣化程度的加重,心源性死亡、支架血栓形成、局部缺血驅動的TLR和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發生率顯示出總體上升的趨勢。但CAC患者DES植入后的不良心血管事件的發生是否隨著時間增加而增加仍需要更長時間的隨訪[26]。ARRIVE研究觀察了紫杉醇洗脫支架植入2年后的心臟事件,結果仍提示中度/重度CAC組發生重大不良心臟事件和死亡的風險較高[27]。
2.3手術治療 嚴重的CAC病變或者冠狀動脈的復雜病變可以通過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 CABG)治療,即通過繞過病變部分的替代性結構來改變冠狀動脈的灌注。但CABG存在手術時間長,創傷大,同時由于CAC病變血管順應性下降,導致血管吻合效果差等問題,并且患者預后差。SYNTAX研究發現冠脈嚴重鈣化相對于冠脈輕中度鈣化患者CABG的患者死亡率增加,CABG可以減少心臟事件,但不能降低嚴重鈣化動脈患者的死亡率,考慮高死亡率可能與嚴重鈣化有關,同時可能也與其他動脈血管的鈣化引起相關并發癥有關,如腎衰竭、周圍動脈阻塞性疾病等[23]。
3 總結
CAC是動脈粥樣硬化的自然進程,由多個炎癥因子作用導致鈣磷結晶沉積在脂質壞死核心內并發展的過程。由于鈣化動脈順應性差,會導致支架貼壁不良、支架膨脹不全、支架內血栓等問題,通過支架植入前行球囊切割、旋磨術有可能降低并發癥的發生率。DES會導致鈣化血管新生內膜覆蓋率低及延遲動脈修復,因而應用DAPT具體時間仍值得進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