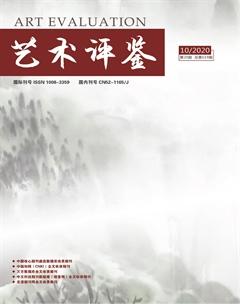突破·移情·對照
牛思凡
摘要:《少年的你》一改以往國產青春電影市場的頹靡狀況,上映之后斬獲15億票房,榮獲第39屆香港金像獎最佳影片獎,香港電影導演協會獎的最佳導演獎,2020年金雞百花電影節最佳女主角獎。電影以高中校園這一場所開始展開故事,校園是一個本應具有濃厚的學習氣氛以及庇護學子的場所,但其中發生了連鎖性的校園霸凌事件。從電影的外延來看,這一反常規青春題材設定,需要反思背后的人物價值觀、社會文化成因。從電影本質上看,以人物關系為主導的敘事推動,視聽語言相互配合的人物塑造串聯起完整的電影文本。
關鍵詞:《少年的你》? 題材突破? 人物塑造? 文化對照
中圖分類號:J905?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 ? ? ? 文章編號:1008-3359(2020)20-0158-03
一、國產青春電影的題材突破
國產青春電影的創作范疇和觀影群體以青年為主,但青年人物自身的特征多樣,年齡沒有標準的劃分依據,而且還存在心理等影響因素。所以國產青春電影的定義難以確定。陳墨教授把青年電影的發展按照導演代際進行梳理,如文革前的革命青春、文革后第四代導演個體的傷痕青春,第五代導演壓抑的青春,第六代導演殘酷的青春自述,以及新世紀后多元化、個性化的青春表達。戴錦華教授在針對日本青春電影《情書》的批評時總結出青春電影中帶有“打破美好“和“殘酷屬性”的元素。由此一來,對于青春電影的定義暫且以青年導演初期創作的以展現青年成長階段中的人物為主以及帶有“殘酷”屬性的電影作品。
這里并非一定要將青春和殘酷元素聯系在一起,而是根據現實中青年成長階段中極有可能出現的現象特征去劃分國產青春電影的主要內容。縱觀近十年以來的國產青春電影,無論是帶有勵志、愛情、甚至是懷舊色彩都具有明顯的“殘酷”特征。但是青春電影中展現“殘酷”的方式愈發流于表面,甚至出現了公式化的敘事模板,尤其是在趙薇導演的《致青春》之后的一系列青春電影《匆匆那年》《同桌的你》《左耳》等,聚焦于愛情或是對于逝去時光的追憶,人物所經歷的情感程序大多雷同,陷入了戴錦華教授所說的青春偶像劇的特征當中。這類走向虛無的愛情理念和故作呻吟的痛苦描寫“大都是青春神話的不斷復制再生產。它作為特定的世俗神話的功能,正在于以迷人、純情、間或矯情的白日夢,將年輕的觀眾帶離自己不無尷尬、挫敗的青春經驗,或者成功地以懷舊視野洗凈青春歲月的創痛”。于是乎,青春開始變成了一種神話,掩蓋了真正具有現實意義的殘酷屬性。而此次《少年的你》一開始就以具有時代和環境特征的校園場景為主,揭露當下語境中愈發明朗化的社會問題,對青年群體包括圍繞在青年周圍的“長者”人物的價值觀進行思考。而最為難得的是將成長傷痛和校園霸凌這一典型的社會事件進行結合。
曾國祥導演這部《少年的你》上映時最受人關注的就是校園霸凌這一題材。此前首次采用校園霸凌作為核心事件展開的國產青春電影是2018年上映,郭敬明導演的《悲傷逆流成河》。但霸凌事件早就已經成為一種現象在校園中層出不窮,校園霸凌最早叫作校園暴力,2009年公布的一項關于校園暴力的調查結果顯示,超過67%的受訪者表示身邊曾經發生過校園暴力事件,有26%的同學承認自己曾遭遇過校園暴力。在《少年的你》的豆瓣頁面中有“經歷過的人,不會釋懷,但能在電影里宣泄”這樣占據榜首的評論。因為此類傷害事件容易因為小事而引發,所以發生概論較大。2016年校園暴力與校園安全問題成為了當年兩會的熱點教育話題,2017年,教育部下發了《關于加強中小學生欺凌綜合治理方案》,針對這一現象做針對性的治理活動。現實中經過校園暴力事件的人群可能已經成年,但未成年人需要更多有關此類事件的指引。于是此類題材電影的出現就充當了釋情和指引或者是警示的藝術文本,這種警示不僅針對青少年本身,也更多的指向與之相對的“長者”身上。所以,《少年的你》在主題上的選擇獲得了大多數人的認可和贊同,關注曾有過類似傷痛的人,直擊觀影者本身最敏感的痛處,而非蒼白的用“愛的教育”去感化觀眾,屬于青春電影題材上一次大膽的突破。
二、人物塑造的移情作用
如果說題材的突破讓國產青春電影具有了“翻身”的機會,那么人物的移情作用是之所以讓觀眾有如此大感觸的原因。羅伯特·麥基說,“移情是觀眾和主人公之間的一根紐帶,移情是指“像我”,在主人公的內心深處,觀眾發現了某種共通的人性。通過移情,與一個虛構人物之間產生替代關系,考驗并擴展了我們的人性。人物塑造針對人物形象、人物關系和心理建構這幾方面。主人公陳念的人物形象變化代表著校園暴力事件的發展程度。在過程中觀眾不單單作為局外人產生觀看行為,而是將自身代入其中,切身感受到陳念的遭遇。
陳念最初是迫切想通過高考改變命運的學生。在影片開頭,一組特寫鏡頭展現學校的獎杯,學生晨練,以及鮮紅的紅色條幅塑造緊張的學習氛圍。換座位時,特寫景別切換展現成績單,陳念優異的成績快速閃過,證明她屬于這個環境。而她的衣著,樣貌極簡樸素,這也是典型的以學習為重的高考生特征。而伴隨暴力事件的展開,陳念的校服變得臟亂,被撕破,陳念的發型也從一開始的樸素整潔到最后被剪頭,這一點能夠直接被觀眾看到。
陳念的性格讓觀眾感知是從和胡小蝶的關系開始的。胡小蝶跳樓之后,導演多次變化機位,刻意避開了殘忍鏡頭的展現,而是選擇對陳念進行正面跟拍,觀眾跟隨陳念的視線看見了校園內的景觀,進入陳念當時無助和悲傷的狀態中。而接下來在校領導室內面對詢問時,閃回胡小蝶的特寫鏡頭,這是陳念的主觀鏡頭,胡小蝶的無助以及陳念的緊張憂郁和警惕隨之也進入了觀眾的情緒當中。之后在陳念回到教室,發現凳子上灑滿的紅墨水,繼續從陳念的主觀視角出發,環視教室內同學刻意回避的反應,接下來鏡頭轉向紅墨水,再次進入陳念對胡小蝶回憶的主觀閃回中,當時她和現在的周圍人一樣選擇了沉默。之后陳念在食堂面對魏萊用手機拍攝時又進入閃回。這幾次閃回將觀眾視線和陳念的主觀視線縫合,切身體會陳念的復雜心情,也預示陳念接下來的處境。但此時陳念的態度并不明晰,直到被推下樓后,再次出現對胡小蝶的主觀鏡頭閃回,這一次陳念直面了胡小蝶的質問“為什么你們不做點什么”,選擇了向警察說出實情,此時觀眾與主人公相通,陳念也徹底體會到胡小蝶當時的心情。如此一來,陳念的所作所為便具有了合理性,觀眾進入人物,體會所思所想。
在人物的心理建構上,電影無法像小說一樣用直白的文字表達,所以選用鏡頭、空間、聲音等展現人物心理。魏萊在階梯上給陳念道歉和陳念爆發這一分鐘之內就建構了陳念極度壓抑的內心。從魏萊追上來說自己要報考北大開始,鏡頭從兩人的中景直接切到了陳念的近景,聲音也開始變化,攝影機一直隨著陳念的步伐晃動,觀眾也開始進入不安的狀態中。之后兩人的交談鏡頭呈現的范圍具有了對比性,展現魏萊的部分速度減慢,背景色調單一;到陳念這里攝影機搖晃頻率加快,背景雜亂變換。最后魏萊說出有關陳念母親的話題時,沒有再出現在鏡頭里,而是陳念的扭曲面部特寫,鏡頭的搖晃,魏萊說話聲還在繼續,背景聲音持續催化,陳念的壓抑爆發,將魏萊推下樓梯。此時的空間得以展開,全景展示魏萊被推下階梯的過程,與當初展現胡小蝶跳樓的方式完全不同,這一次是陳念內心的釋放,但同時也將她自己的命運推了下去。樓梯這一空間意象一直代表陳念的心理狀態,影片開頭展現她上學的過程,仰拍陳念上階梯,表現她向上攀爬的艱難和決心,之后在學校樓梯被魏萊推下表示陳念“走出去”的希望被推下。所以此處陳念在和魏萊一起走上樓梯時,使用小的景別營造逼仄的空間,將陳念的心理凸顯出來,觀眾通過鏡頭的晃動,音效置身其中,在陳念的生存狀態里去體驗她的行為心理。
三、社會主流文化與亞文化的對照
主流文化是社會約定俗成的文化建構,規范著人們的言行舉止,從而形成社會群體中的每個個體都必須遵守和履行的普遍的行為模式。而亞文化是非主流的,反約定俗成,往往處于不被了解的邊緣,區別于常規認識中的文化現象。但亞文化脫胎于主流文化,是主流文化走向誤區的表征。在這部電影中表現出對制度的誤讀、技術濫用以及家庭結構失衡等社會主流文化癥狀的反思也在一定程度上對照著亞文化現象的發生。
對于制度的誤讀,是針對教育制度展開的,這種誤讀是身在體制中的人對人性和制度的失衡處理,其實也是“情”與“理”的失衡。教育制度中的兩任班主任老師屬于“長者”的身份,本應該對陳念進行指引拯救,但他們在對待看似與教育制度相沖突的事件時,多數的反應是“不能影響學習”,尤其是陳念的下一任班主任,只有不斷的學習口號,并沒有把學生當做主體去關懷。而陳念本身也刻意回避與其他人做朋友,這點也是她之所以不回應胡小蝶的原因。還有,電影中多次表現陳念英語的水平,開頭與結尾通過英語句式表達她對于曾經傷害的追憶,在胡小蝶出事之后陳念耳機里的英文聽力在描述野生動物的弱肉強食競爭,對應隨后的暴力事件,側面說明如今社會主流的競爭方式的偏頗。而電影雖然在表述主流教育制度的弊端,如“高考結束后漫天飛舞的考卷”,其實是在對教育和學習方式的思考,更多的是想要說明制度是理性的,而作為主體的人是具有情感的,如果高考只是單純的為了培養高分的人,那么人就等同于被機械化、被制度化了。所以與其說是體制或者制度的弊端,不如說是在這個制度下,人走向了極端,走向了忽略人性的一面,在“情”和“理”的協調上失衡。
技術的濫用是通過手機展開的。2013年中國全面進入4G時代,智能手機發展迅猛,信息交流全面實現遠距離無間斷傳播。但電影的幾處展現手機的鏡頭卻表現出技術發達的負面影響。在胡小蝶跳樓之后,特寫鏡頭展現手機屏幕,以往魯迅所認為的“看客”如今變成在網絡里事不關己,躲在屏幕背后熱烈討論的網民。陳念媽媽賣三無產品的丑聞被曝光,通過手機的群發功能將信息傳遞給陳念的所有同學,導致了陳念被嘲笑和孤立。胡小蝶被欺凌、陳念最后被剪頭發、扒衣服都被魏萊等人通過手機錄下了全過程。而一旦此類視頻傳播到網絡上,又會引發新一輪的網絡暴力。在高度發達的現代社會智能手機將人們連接成為網狀關系,言語和輿論攻擊不再是“一對一”或“一傳十,十傳百”需要時間和記憶成本的小范圍傷害,而是降低暴力成本的集群式表現。所以技術的濫用,其實也是主流文化催生的技術下人的異化。《啟蒙辯證法》中提到啟蒙思想讓科技帶領人類社會進步,但科技使人類社會面臨更大的危機。校園暴力與網絡暴力相結合,促使處于輿論漩渦內的人被迫逃離學校,同時也逃離了主流社會,如陳念在小北家將手機關機,給鄭義打電話沒有接通后隨即也放棄了向警方繼續求助,轉向了小北,進而組成了青年亞文化下的共生關系。
最后是主流社會中的家庭結構失衡。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模式通常讓子女在家中更多的時間是和母親接觸,如今大多數的家庭可能父親由于工作或者不可控因素而缺席子女的成長。在《少年的你》中沒有出現陳念和徐渺的父親,魏萊和羅婷的父親屬于“暴力”式的“在場的缺席”,小北的父親從小就是個“迷”。近年國產青春電影《過春天》《陽臺上》《大象席地而坐》中人物都存在父親缺失現象。《黑處有什么》當中直接解釋了這個現象“爸爸其實并不重要,在自然界里,小獸總是跟著母獸成長”。這樣的設置必然會讓家庭中母親的角色成為子女的生活重心。在這幾部電影中的母親形象也正在走向失責的一面,而且她們大多都是“單親”母親。《過春天》里的母親形象化著濃妝、不擅于家務,無法與女兒溝通;《大象席地而坐》里女同學的母親形象是暴躁不安的;《少年的你》中羅婷沒有出現母親,徐渺的母親懦弱,魏萊的母親溺愛,小北的母親在他小時候就改嫁了。陳念的母親為了積攢學費,以犧牲陪伴陳念或者無法保護她為代價。雖然每一次在和陳念的交談中都能看出作為母親的關心,但也都是空洞的言語表達,無法付諸行動。從陳念人際關系的單薄,小北的反社會價值觀“挨打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一定會打回去”,魏萊無視生命卻畏懼父親,羅婷的暴力傾向,以及徐渺的沒有主見都能看出主流的家庭結構的自我失衡,以至迫使青少年群體中出現犯罪、極端行為等亞文化現象。
四、結語
由此可見,《少年的你》不僅僅是作為商業類型片在題材上立新突圍,更深層度的開始轉向對于青年亞文化群體的關注,借用發揮移情作用的人物塑造方式,讓觀眾切身的進入到核心事件的人物內心,體會這類群體的極端行為之后,反思引發這類現象的原因,給予國產青春電影新的立意和高度。
參考文獻:
[1]陳墨.當代中國青年電影發展初探[J].當代電影,2006(03):81-84.
[2]戴錦華.電影批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164.
[3]許諾.《南方周末》校園暴力事件報道研究(2000-2009)[D].上海:復旦大學,2010年.
[4]王寧.《中國青年報》校園暴力事件報道研究[D].大連:大連理工大學,2019年.
[5]羅伯特·麥基[美].故事:材質、結構、風格和銀幕劇作的原理[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1:165.
[6]陳剛.《少年的你》的社會學意義[J].當代電影,2019(12):2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