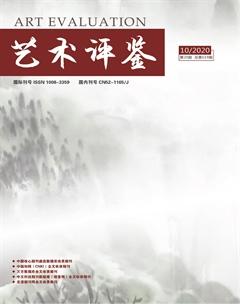瑪緹·迪歐普的電影美學(xué)風(fēng)格:以《大西洋》為例
張承昊
摘要:獲得戛納電影節(jié)評審團(tuán)獎(jiǎng)的瑪緹·迪歐普,通過獨(dú)特的風(fēng)格化造型、敘事以及紀(jì)錄美學(xué)與作者身份表達(dá)的融合,創(chuàng)作出一種具有作者化美學(xué)風(fēng)格的體驗(yàn)性、身體性與文化性的電影。
關(guān)鍵詞:非洲電影? 瑪緹·迪歐普? 紀(jì)錄美學(xué)? 作者性
中圖分類號:J905? ? ? ? ? ? ? ? ?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 ? ? ? ? ? ? ? ? 文章編號:1008-3359(2020)20-0164-03
一、瑪緹·迪歐普的創(chuàng)作
擁有法國與塞內(nèi)加爾血統(tǒng)的瑪緹·迪歐普(Mati Diop)在她的電影中表現(xiàn)著身份與社會(huì)的張力。身兼導(dǎo)演與演員兩種職業(yè),具有跨文化背景的她通過導(dǎo)演、表演與攝影創(chuàng)作,以性別視角關(guān)注移民與身份問題,聚焦青年人的生活、抉擇、命運(yùn)與不斷追求的勇氣。2019年,她創(chuàng)作了首部長片《大西洋》(Atlantique,2019),獲得第72屆戛納國際電影節(jié)金棕櫚獎(jiǎng)提名,奪得評審團(tuán)獎(jiǎng)。從她的短片《大西洋》(Atlantiques,2009)、《雪炮》(Snow Canon,2011)、《在越南》(Big In Vietnam)到紀(jì)錄片《千陽》(Mille Soleils),瑪緹·迪歐普持續(xù)表現(xiàn)出一種獨(dú)特的美學(xué)風(fēng)格。她最新的作品是短片《在我的房間》(In My Room,2020)。此外,她早期還有數(shù)部短片作品:《人造之島》(Ile artificielle-Expédition,2006)《奧林匹斯》(Olympus,2017)等。
在迪歐普的影像中,寫實(shí)主義美學(xué)與獨(dú)具一格的作者風(fēng)格共存,在同一個(gè)邊緣性的空間里肆意流動(dòng)。她通過攝影機(jī)的捕捉,以獨(dú)特的視角抓取身份困境之間的人與文化的張力。
二、紀(jì)錄與體驗(yàn):迪歐普電影的美學(xué)共性
瑪緹·迪歐普冷靜的紀(jì)實(shí)化影像中隱藏著神秘與文化的痕跡。日常世界不可思議地異變,與夢境般的泛靈現(xiàn)實(shí)連通。迪歐普紀(jì)錄的空間仿佛是亨利·阿杰爾“disposition of cinema”的影像實(shí)例。阿杰爾作為現(xiàn)象學(xué)家,引述巴贊的“熱情地隨著音樂旋律的邀請,翩然起舞……我們能感受到某種意義,就好像隨著感性的顯現(xiàn),覆蓋世界的神秘面紗被掀開了”這一觀點(diǎn),來論述自己的藝術(shù)是“從體驗(yàn)出發(fā)”以及藝術(shù)具有人類身體性質(zhì)的觀念。迪歐普的紀(jì)錄美學(xué)通過對感性體驗(yàn)的抒發(fā),試圖揭開覆蓋在塞內(nèi)加爾以及西非人身份上的“面紗”,而這種神秘的體驗(yàn)來源于迪歐普對時(shí)間、歷史性之中潛藏的文化的挖掘,在后殖民主義的地域世界之間,迪歐普在西非的城市之間運(yùn)用攝影機(jī)運(yùn)動(dòng)與精妙的畫面構(gòu)圖,去發(fā)現(xiàn)如空氣一般充斥于現(xiàn)代化城市之間的歷史與文化物質(zhì)所偶現(xiàn)的某些不透明的瞬間。
短片《大西洋》中,迪歐普以寫實(shí)兼具抒情的鏡頭,拍攝蔚藍(lán)的大西洋與熊熊燃燒的篝火。海水作為意象,填充著人物群像之間的情感間隙;特寫在手持鏡頭的表現(xiàn)下呈現(xiàn)出動(dòng)人的力量。迪歐普記錄西非的宗教文化:充滿力量的手在刻著經(jīng)文的小石碑前方環(huán)繞,一只黑人的手撒下三圈土。身體處于儀式之間:攝影機(jī)的平實(shí)紀(jì)錄手法將神秘與靈性包裹在數(shù)字的場域之間,使得觀眾如同直接在場,儀式的神秘在最顯真實(shí)的影像中莊嚴(yán)且自然地流動(dòng)。
迪歐普同時(shí)也聚焦屬于殖民地身份范疇的問題。在她的作品中,對音樂的使用十分克制;潮濕的前殖民地的影像以手持拍攝、自然光外景以及她對特寫與群像的偏愛而構(gòu)建。她善于利用建筑本身的結(jié)構(gòu)來構(gòu)圖,將人物閉鎖于其間,或使角色在這種布局之間穿行。物體與身體的聯(lián)系在這種鏡頭內(nèi)部關(guān)系中愈顯強(qiáng)烈,不斷強(qiáng)化著人與后殖民的環(huán)境中交互所顯現(xiàn)的身份。《大西洋》的開頭,工地上的男孩坐在鋼結(jié)構(gòu)之下,穩(wěn)定的幾何線條將人物框在內(nèi)部。建筑作為隱喻,通過她的調(diào)度在寫實(shí)主義的影像中變異,成為通道或牢籠。例如,通過取景,街道與樓房、路邊車群與電線桿構(gòu)成線條整齊的隧道,人物從遠(yuǎn)處的透視點(diǎn)緩緩走來。在浸染著泛靈論的影像中,人物自然地穿行于由物連接的不同時(shí)空:身體處于城市實(shí)景,或漸漸走入繁盛的樹影。包括在《千陽》中,迪歐普在影片開頭就將穿過現(xiàn)代化公路的牲畜群與川流不息的轎車并置,牲畜的后面,人類跟隨著。在這日光下的實(shí)景鏡頭里,整齊的樓房、行駛的車輛與最本質(zhì)的地理環(huán)境搭建出一種強(qiáng)力的包容性,現(xiàn)代化與傳統(tǒng)的視覺元素在空間內(nèi)被迪歐普并置,人的存在以某種混合的文化下的狀態(tài)表現(xiàn)出來。也就是說,那些偶然的瞬間,通過迪歐普對儀式、身體與空間的紀(jì)錄式再現(xiàn)而現(xiàn)身。
三、光:一種迪歐普的作者標(biāo)志
迪歐普的電影總是在運(yùn)用光作為表現(xiàn)手段。運(yùn)用具有鮮明霓虹色調(diào)的人造光以及表現(xiàn)城市與自然的光源,實(shí)現(xiàn)了兩種目的:其一,與敘事構(gòu)成關(guān)系;其二,作為場面調(diào)度中的風(fēng)格化視覺元素。
在《大西洋》電影中,前往西班牙遭遇海難的男孩們重回故土,與女孩們在當(dāng)?shù)氐木瓢上鄷?huì),這一場戲是用光最為典型的地方。迪歐普在其中安排的酒吧射燈燈光,采用綠色為基調(diào),且有多種表現(xiàn)形式:或直射,來回聚光于不同的物體,并暈染周圍的空氣環(huán)境;或形成具有動(dòng)感的光斑。直射的綠光使人物浸泡在一個(gè)如同彌漫著綠霧的海邊潮濕酒吧的環(huán)境里,在鏡中才能顯影男孩們的靈魂,通過綠光營造的氛圍,直接與女孩們在一個(gè)物質(zhì)性的場所中達(dá)成了接觸;夜色中的酒吧儼然成了合情合理的異空間,綠光使得《大西洋》中的紀(jì)錄美學(xué)的場景與神秘的空間明顯區(qū)隔;女孩們穿梭于白日的現(xiàn)實(shí)與夜晚的“著魔”間,她們成為毫無疑問的能動(dòng)性的主體。在相聚這一場戲之前的段落里,女主角艾達(dá)曾坐在酒吧綠色的光影中,螢火般的光斑環(huán)繞在她的周身,她成了一種被投射的對象:某種來自“遠(yuǎn)方”的想念。綠色的光不但實(shí)現(xiàn)了布光的效用,還可作為表現(xiàn)式手法塑造人物。這種表達(dá)方式在迪歐普的電影中隨處可見。
作為風(fēng)格化的構(gòu)成,城市光與自然光也被誠實(shí)地捕捉,構(gòu)成一種不脫離紀(jì)實(shí)美學(xué)的范疇,又具有強(qiáng)烈作者性的表現(xiàn)元素。達(dá)喀爾市中心與其海邊現(xiàn)代化高聳入云的建筑,被迪歐普納入一個(gè)個(gè)鏡頭構(gòu)圖中:白天,偏黃色的街景中,后現(xiàn)代風(fēng)格的建筑在海邊矗立,在同一個(gè)鏡頭內(nèi)與略顯破敗的居民樓群構(gòu)成縱深關(guān)系;夜晚,路燈與一切城市光源又將貧困與對立隱沒在冰冷、現(xiàn)代的氛圍之中,大遠(yuǎn)景鏡頭中的海洋、高樓與低矮建筑群之間的經(jīng)濟(jì)、文化差異與象征,已然化為電氣時(shí)代光芒渲染下同質(zhì)性的都市空間。
《大西洋》表明,不論哪一種光的迪歐普式運(yùn)用,都使得她影像中最本質(zhì)的紀(jì)錄美學(xué)與個(gè)人風(fēng)格間構(gòu)成一種張力。作者化的風(fēng)格能夠延續(xù)標(biāo)記在她家庭錄像帶式的影像中:居家一日從白天到黑夜的轉(zhuǎn)換,也被放置在自然光、紫色人造光、電腦的屏幕光,甚至都市玻璃外墻的光污染——仿佛能構(gòu)成一種靈光乍現(xiàn)的時(shí)刻之中。
四、水與空間:海洋意象作為空間的通道
海洋也是迪歐普電影中不可或缺的意象。大海在她的作品中隨處可見。在她的世界里,水作為一種物質(zhì)性的存在,連通著陸地間的文化裂隙,成為一座柔軟的橋梁。航海時(shí)代的隱喻已然穿行至迪歐普關(guān)于痛苦、選擇、改變與青年一代的影像中。海洋流淌在敘境中的每一個(gè)角落,不論是《大西洋》中的男孩通過海洋前往西班牙,或是這些男孩被機(jī)遇的海洋所吞沒,敘事中的海洋無一例外成為后殖民主義現(xiàn)代性的場域。
海洋不但是迪歐普影像中溝通落后與發(fā)展、殖民與后殖民以及文化界面交融的重要意象與媒介,它同時(shí)也成為主觀視角下勾連敘事的作用于劇作文本的意象。這樣一來,海洋成為了它在迪歐普電影中的一個(gè)重要的能指:空間的通道。水的意象在迪歐普的電影中隨處可見,海洋具有各種顏色與質(zhì)感,已然成了迪歐普電影中最具深度的形象:當(dāng)海洋占據(jù)整個(gè)鏡頭,就像伯特·艾克斯(Birt Acres)在19世紀(jì)末英國東南部的港口城市多佛捕捉到的狂暴、洶涌的大海那樣,物自身便開始與觀眾對話。
在《大西洋》中,海水本身就像是一塊巨大的畫布,接受著達(dá)喀爾年輕人各種情感、焦慮與希望的投射。在她標(biāo)志性的大遠(yuǎn)景鏡頭中,迪歐普捕捉到不同光線下、夜色中以及城市燈光里的大西洋:蔚藍(lán)的、灰暗的,甚至被落日染出大片翻滾著的橘紅——不同天氣條件下,海洋表現(xiàn)出不同的形態(tài),經(jīng)由迪歐普的調(diào)度,暗示著人物選擇與海洋地理環(huán)境引發(fā)的敘事走向與命運(yùn)發(fā)展。海洋的色彩暗示著主觀鏡頭與客觀鏡頭的切換,男主蘇雷曼眼中的海洋是泛著灰色海霧與白光的;當(dāng)蘇雷曼與艾達(dá)在海邊共處,攝影機(jī)從蘇雷曼的身體出離成為客觀視角時(shí),海洋變成了湛藍(lán)色。同樣,這也暗示著調(diào)查艾達(dá)未婚夫家縱火案的警察在哪些關(guān)鍵時(shí)刻被蘇雷曼的亡魂附身。由此,大西洋成為了身體空間、經(jīng)濟(jì)地理空間與文化空間之間的通道,西非本土宗教文化在通道之中穿行,確立著塞內(nèi)加爾人的批判著殖民主義的民族性。
五、特寫與凝視:目光的變異
莫里斯·梅洛-龐蒂通過對幻肢現(xiàn)象的論述引出了“身體—主體”的概念:“擁有一個(gè)身體,就等于擁有一個(gè)實(shí)踐場,介入一個(gè)生存環(huán)境”。在梅洛-龐蒂這里,意識主體轉(zhuǎn)換為知覺主體,身體獲得了與意識相連的主體地位,并且身體并未成為意識化的身體,存在著一種前反思的身體活動(dòng),意味著身體本身就具有進(jìn)行前反思的身體活動(dòng)的能力。梅洛-龐蒂的電影美學(xué)是具身性的,他提出,“他人的心理活動(dòng)便不是外在于我的存在的心理事實(shí),而是“自外可見的行為類型或舉止風(fēng)格。它們就在那張面孔上或那些姿態(tài)里,而非隱藏于它們背后……電影則特別適合讓心靈與身體、心靈與世界的統(tǒng)一性以及雙方的相互表達(dá)呈現(xiàn)出來”。與此同時(shí),一種從身體出發(fā)的觀影可能,強(qiáng)調(diào)了身體主體成為了接受的主體:梅洛-龐蒂的“電影作為視聽格式塔”的美學(xué)建構(gòu)使觀眾得到了又一個(gè)通過身體感知銀幕形象的合法性的理論依據(jù),因?yàn)閺拿仿?龐蒂的“知覺”出發(fā),“電影會(huì)像其他藝術(shù)一樣也成為我們所感知的東西”。
迪歐普對身體的表現(xiàn),不但是當(dāng)代法國文化界對哲學(xué)轉(zhuǎn)向的一種繼續(xù)反映,也是對于電影紀(jì)錄美學(xué)與阿梅代·艾弗爾與阿杰爾的現(xiàn)象學(xué)電影學(xué)之關(guān)系論述的一種印證。前反思、心靈與身體及世界的統(tǒng)一性以及知覺所決定的“電影作為感知”都在迪歐普的電影中。她脫離邏各斯中心主義的平實(shí)紀(jì)錄、超驗(yàn)的文化與儀式表現(xiàn),通過運(yùn)用特寫鏡頭與塑造身體造型,達(dá)成被感知的影像現(xiàn)實(shí)的成功構(gòu)造。《千陽》中已經(jīng)通過面部特寫,使得身體與心靈(由面部表情的表意所暗示)合為一體。這種特寫也許也如往常一般,不免會(huì)造成打破線性時(shí)間的結(jié)果;但她前反思的電影特質(zhì)已經(jīng)使得敘事不再成為占據(jù)影片主導(dǎo)的局面形成,且早已從制作的肇始打破了性別主義的視線可能性。《大西洋》電影中,艾達(dá)最后面對鏡子注視著自己的鏡像,繼而確認(rèn)自己的獨(dú)立性。這一舉動(dòng)不但是她看到自己,再度確認(rèn)自己的主體性的過程,還打破了第四堵墻。一方面,看到鏡像,即看到自己追求自由、欲脫離二重身份的束縛的過程;同時(shí),另一方面,艾達(dá)也與銀幕前的觀影者四目交接:穆爾維式的憤怒指控被迪歐普的個(gè)體表達(dá)所安撫、平息,艾達(dá)突破層層被看的地位,最終使得反叛的凝視力量超越了銀幕的物質(zhì)阻隔,使得觀眾完全感知到了一種當(dāng)代的、具有力量的目光。
當(dāng)出海的男孩們附著在女孩的身體上,前往高檔的住宅區(qū)討薪之時(shí),女孩們的眼球結(jié)構(gòu)皆發(fā)生變異,眼白充斥整個(gè)眼球,目光變成了無限的渙散:這種恐怖片類型化的白色眼球的造型,迎合了女孩們身體內(nèi)部的空間,卻撕開了關(guān)于身體的含混性問題的一道裂隙:在西非文化的語境下,在意識基本成為了靈魂的同義詞的時(shí)刻,人的意識最終還是與身體分隔開來了嗎?身體仍然屈居于意識之下嗎?迪歐普在復(fù)現(xiàn)傳統(tǒng)文化的同時(shí),給出了自己的答案:身體在當(dāng)下仍然不能屈居于意識的下層。女孩們眼球的變化,一方面表明她們成為男孩靈魂的容器,另一方面更加凸顯了身體的物質(zhì)性存在。西非人相信靈魂與物質(zhì)世界并不完全分離,如同“祖先力量”,會(huì)形成一種力量,但這種力量并非完全處在自由的境地之間,因?yàn)椤吧鐓^(qū)長者是人們和他們祖先們的靈魂取得聯(lián)系的主要紐帶”。這樣說來,身體與靈魂的關(guān)系仍然不是自由的,仍是被分隔的;在世的肉身需要一個(gè)高等級的連通,才可以接觸到“祖先”般的靈魂。這里依然體現(xiàn)著一種靈魂需要中介才能與肉體發(fā)生聯(lián)系的觀念。而在《大西洋》中,靈魂卻直接借由女孩的身體,身體與靈魂的融合非常容易,非常自然——只需要女孩們付出一點(diǎn)發(fā)熱與不適的代價(jià)。因此,在夜色中,女孩們白色眼球的目光實(shí)際上也是男孩視線,女孩的身體成為了某種雙性同體。身體與靈魂之間去中介的自由,實(shí)際上也體現(xiàn)出一定的梅洛-龐蒂式的含混性;而當(dāng)身體具有這種含混性,影像當(dāng)中的女孩子們徹底占據(jù)了重要的主體位置:沒有她們,就不可能有還魂的情節(jié)。迪歐普風(fēng)格化與紀(jì)實(shí)性相切合的影像中,男孩們的憤怒通過女孩們的四肢、女孩們的肌肉與骨骼的力量,通過女孩眼球異變的凝視而從容地爆發(fā),一種迪歐普理想中的身份主體力量形成了:既是性別的、又是種族的。這一溝通著民族現(xiàn)代性與民族傳統(tǒng)的身體力量,也許會(huì)使得殖民主義殘存在影像空間內(nèi)達(dá)到崩潰的臨界。
六、結(jié)語
瑪緹·迪歐普的《大西洋》延續(xù)了她獨(dú)特的作者的美學(xué)。紀(jì)實(shí)性的影像與風(fēng)格化的表達(dá),使得她從容地運(yùn)用攝影機(jī),搭建起一個(gè)個(gè)身份與文化的通道。塞內(nèi)加爾與法國血統(tǒng)使她思考第三世界與人的存在,性別使她思考多元因素的糾纏。在平實(shí)紀(jì)錄風(fēng)格與表現(xiàn)性手法之間,她的創(chuàng)作顯得靈光閃爍。
參考文獻(xiàn):
[1][美]達(dá)德利·安德魯.經(jīng)典電影理論導(dǎo)論[M].李偉峰譯.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司,2012.
[2]張穎.意義與視覺:梅洛-龐蒂美學(xué)及其他[M].北京:北京時(shí)代華文書局,2017.
[3]楊大亮,白瑋瑋.再論非洲傳統(tǒng)元素在托尼莫里森小說《寵兒》中的體現(xiàn)[J].時(shí)代文學(xué)(下半月),201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