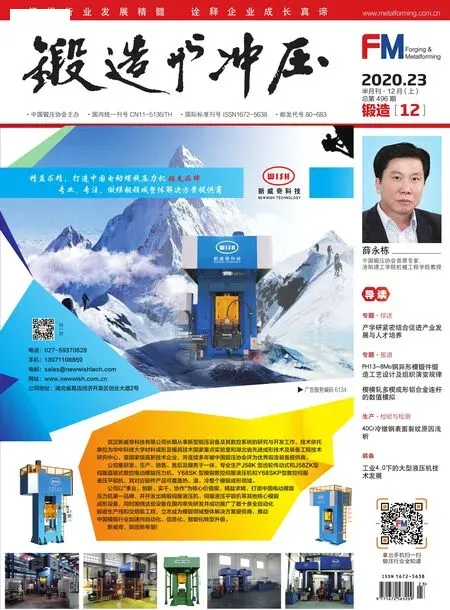潛心熱加工技術, 做理論和實踐的踐行者
文/方婷·FM 記者
薛永棟
工學博士,教授級高級工程師,中國鍛壓協會(自由鍛組)首席專家,洛陽市第二屆優秀科技領軍人才,河南科技大學、河南理工大學碩士生校外導師。
學習經歷
1993 年~1997 年,東北重型機械學院,鍛壓工藝及設備專業,獲學士學位;
2000 年~2003 年,燕山大學,壓力加工專業,獲碩士學位;
2003 年~2007 年,北京科技大學,壓力加工工程專業,獲博士學位。
工作經歷
2008 年~2019 年,中信重型機械股份有限公司,先后任重型鑄鍛廠技術副廠長、公司技術部副主任;
2019 年~至今,在洛陽理工學院任教。
“千年帝都,牡丹花城”,洛陽,因地處洛水之陽而得名,是華夏文明和中華民族的發源地之一。今天的洛陽,更是我國重要的工業基地,眾多知名大型企業在這里長足發展,中國一拖、中信重工這些“共和國長子”,如今更是在轉型發展中煥發出時代的生機和光彩。本期《鍛造與沖壓》雜志記者有幸采訪到的中國鍛壓協會首席專家、洛陽理工學院機械工程學院(以下簡稱“洛陽理工”)教授薛永棟先生,就曾在中信重工工作多年。今天,就請他為我們談談由企業轉入高校,將企業的實戰經驗和高校的研究工作結合在一起的心得體會。
潛心鉆研,見解獨到
談及鍛件技術的研究工作,薛永棟介紹說:“我本人從本科到博士,一直學習、研究鍛造技術。從2008 年進入中信重工,有企業多年的鍛造技術研發、現場生產技術經驗,到現在的,進入洛陽理工學院任教,就是為了能更好的潛心研究鍛造行業尚存的一些技術問題,培養后續人才。
“很多人在涉及到鍛件時,常常只關注鍛造這一個工序,甚至只關注壓力加工環節。比如鍛件內部非連續性缺陷、鍛件探傷草狀波缺陷等問題的分析,習慣將原因歸于鍛造環節,認為是壓力加工工藝不到位或變形量不夠所致,而不是從系統上綜合相關專業環節進行全面分析。
“如20#鋼這類鋼種的鍛件,隨著冶煉技術的不斷進步,鋼的純凈度達到很高的程度,那些原來在鋼中起著阻礙晶粒長大作用的雜質大量減少,完全沿襲傳統工藝就容易造成晶粒粗大,原來生產起來很容易、性價比很高的鋼種,現在卻問題頻頻發生,然而梳理生產流程也似乎沒有任何異常,個中原因實際是冶煉技術的提升,帶來鋼水潔凈度提高的同時也附帶了‘消極作用’的發生。當然,如果從材料上略微加以改造,也是能繼續保證鋼種原有特性的。可見對鍛件制造的相關技術有一個全面認識,在其實際生產中進行系統的把控,對保證和提高鍛件生產一次合格品率,重要性是顯而易見。
“鍛件技術是涉及材料、冶煉、凝固、鍛造、加熱與冷卻(含熱處理)、金相組織學、金屬性能學等相關方面的一門綜合技術,其制造過程需堅持系統觀,講究各專業的統籌兼顧,各工序的緊密配合,同時也要對各環節嚴格控制,強化工藝紀律,最終實現質量和成本的有效控制。這種系統性把控鍛件制造過程理念的推廣,將極大地推動我國鍛件制造技術水平的顯著提高。”
工藝要靈活,認識需深刻
對于鍛造企業,制造成本管控也是很重要的研究方向,對于這塊的研究,薛永棟也談到他的想法:“為了降低鍛件的制造成本,工藝制定要做到因地制宜,靈活調整。舉例來說,白點是鍛件生產中一種致命性缺陷,其本質是一種發裂,一種很細小的特定裂紋,鍛件中一旦出現基本上是報廢,鋼中的H 元素含量低于2ppm 時,基本可以控制住鋼中不出現白點,這是從大量生產實踐中總結出來的,當然通過實踐證明也是有效的。隨著爐外精煉技術的進步,鋼水經過真空脫氣處理,成品鋼水的H 含量取樣測量已在2ppm 左右,后續澆鑄雖存在一定回吸,但經過真空澆鑄后最終鋼錠H 含量相對過去大幅下降,通常達到2ppm 以下,擴氫工藝的制定應當與時俱進,擴氫時間相對于傳統標準進行大幅減少,實現成本降低、節奏加快。
“再比如,很多鍛件,由于材料、形狀、裝備條件或操作技能等原因,僅通過壓力加工環節不能成功對晶粒度實現有效控制,對于這些鍛件,鍛后一定的預備熱處理是必要的。而有一些鍛件,能在末火次對其通體實現較大變形量,且其鋼種有一定的合金含量,尤其含有C、N化合物穩定的合金元素,如Ti、Nb、V等,這些鍛件,可以繞開傳統工藝守則,制定針對性的工藝,相對傳統工藝進行優化、簡化,甚至省去某些工藝環節。“
理論與實踐,相輔相成
鍛件相關技術的實踐性都很強,將理論靈活地應用到鍛件生產制造的實踐中,并進行跟蹤驗證,結合反饋再進行思考,從而加深對理論的認知,當談及后續如何帶領學生做研究課題時,薛永棟介紹說:“我們會根據企業各個案例分析,應用理論解釋現場出現的各種問題和現象,尤其是對一些司空見慣的工藝過程進行深入思考和解釋,讓學生更快速的提高對理論的認識深度。如擴環形鍛件,錘下金屬沿切向流動延展,環的其余部分在牽制這個延展的同時,也被延展進行著‘掰’的反作用,從而實現‘擴’大環形鍛件直徑的效果。大型軸類鍛件的拔長,小徑段在錘下直徑變小,緊鄰端在阻礙這種變化的同時,也被影響,形成斜坡,而不是形成臺階。通過脹形法制造膨脹節則與拔長的材料流動相反。
“再比如,生產單側帶凸臺的厚板時,兩面不是對稱變形,成形時先將凸臺背面通過一面受力達到材料流動極限,另一面整體保持受力但未達到材料流動極限,如此形成凸臺背面的凹坑后再對板坯兩面進行對稱壓制變形。有了以上這些案例的觀察和思考,對金屬在受壓時的流動達到一定認識深度,對核電主管道、錐形筒節等難度較高異形鍛件的成形方案的制定和把控,就必然舉重若輕了。在生產實踐中,積極應用理論對實際進行解釋,在加深了對實際認識的同時,也促進了對理論的認識和對理論的進一步靈活應用。”
行業現狀,任重道遠
對于鍛造行業的看法,薛永棟接著說:“鍛造這個行業無疑是重要的,特點也很鮮明,屬于資金密集、勞動密集、技術密集、能源密集的產業,加工周期長、影響因素多、工藝過程復雜、技術含量高、成本風險大,看似‘粗活’,傻大笨粗,實屬細活,如同繡花一般,來不得半點馬虎。
“我國大鍛件行業,在‘十二五’前后經歷了一輪爆發式的發展,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我國已投產的萬噸壓機數量總和已超過20 臺。伴隨著多臺大壓機的投產,我國大鍛件的產能在世界已穩居第一。近幾年,由于傳統大鍛件需求持續萎縮,新建和技改項目同步減少,行業主導產品價格大幅下降的趨勢仍未改變。同時,能源、人工、資金、環境等要素成本不斷上升,嚴重加大了大鍛件制造企業的生存壓力。產能嚴重過剩,產品高度重合,同質化競爭激烈,短期內難以得到化解。另外,部分國內企業在采購時對國外鍛件產品的偏愛,更使我國大鍛件企業境況雪上加霜。
“當然,我國大鍛件行業近年來取得了巨大進步。隨著大壓機大量上馬,我國在大鍛件的很多方面實現了突破,成功制造出了500 ~700t 級鋼錠,攻克了超大型鋼錠鍛造壓實和晶粒控制及性能熱處理關鍵技術,以AP1000、CAP1400 為代表的核島大鍛件也已研制成功并實現量產,研制出了核電常規島發電機轉子和汽輪機轉子鍛件,難度極高的低碳控氮不銹鋼主管道在當前核電發展水平上也實現了自給自足,等等。
“在取得大步進展的同時,我們應該保持清醒,應該說我國大鍛件行業還處于大而不強的階段,制造能力處于‘過剩’和‘短缺’的雙重壓力。一般性大鍛件供大于求,對技術含量和質量要求高的大鍛件,如百萬千瓦級火電和核電用(超臨界、超超臨界)汽輪機轉子、特大型支承輥和熱軋工作輥、大馬力低速柴油機組合曲軸鍛件等,生產能力低、質量不穩定或基本不能生產,很多都尚依賴進口。就拿超超臨界高中壓轉子來說,無論是用于600℃左右的COST E、COST F 高中壓轉子,還是用于625℃左右的FB2 高中壓轉子,我國目前基本尚不具備穩定供貨能力,有企業對COST E 轉子進行了試制,情況也不太樂觀。國外部分先進企業,如德國Saar 和日本JSW,多年前就已達到COST E、COST F 轉子的穩定量產。2000 ~2007 年德國Saar共交付55 根COST E 轉子和11 根COST F 轉子;FB2轉子在國外也已投入商業運營,比如日本的新磯子電廠2 號機組,德國的Walsum 電廠10 號機組。總體來說,我國大鍛件技術水平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還有一點差距。
“長期以來,整個行業重視硬件(設備、廠房和圈地)投資,對軟件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比如管理,國有企業在這方面多年來沒有做出任何新的重大的提升,致使包括人才在內的諸多資源存在極大低效現象,各個企業也呈現效率和效益雙重低下的水平;對于民營企業而言,由于市場人員流動的不規范性,企業培養人的積極性低,管理創新和技術創新的積極性弱,滿腦子充斥從國有企業挖人的思想,這也是我國大鍛件行業重復低檔次建設的根本原因之一。各大鍛件企業,作為肩負行業發展的主體,必須深入認識本行業的特性和難度,務須堅持在硬件和軟件兩個方面協調發展,‘軟硬兼施’,方為長遠之道。“
初心為楫,未來可期
行業發展亟需大量的應用型人才,作為培養人才的主體,高校承擔著為社會發展輸送大批高素質應用型人才的重任,努力做好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教學模式,為企業培養更多的實用型人才。在這里我們也希望未來有更多的像薛永棟先生一樣的技術專家能夠進入高校,將自己的專業技術經驗傳授給更多的學生,為做強我國鍛造行業培養更多的后備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