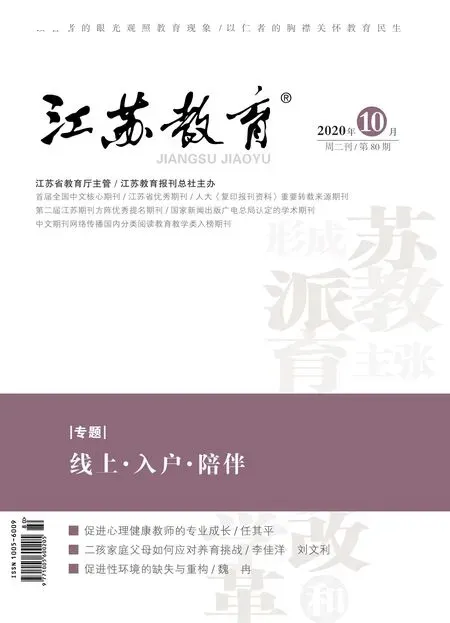促進性環境的缺失與重構
魏 冉
精神分析學家唐納德·梅澤爾將青少年形容為“處于潛伏期的‘不安’和成年生活的‘安定’之間,是一群快樂又不快樂的人”。相較于其他人生階段,青少年的身體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劇變,他們的身高、體重快速增長,性器官日益成熟,第二性征愈發凸顯。望著鏡子里熟悉又陌生的自己,青少年滿懷好奇與疑惑,踏上了危機與契機并存的自我覺醒之路。
一、青少年心理問題與促進性環境的缺失
青少年階段,個體要向童年、家庭告別,獨立地探索新世界,建立起協調和穩定的自我認同,尤其是性認同,這極具挑戰的發展任務會引發青少年的焦慮不安。雖然自我同一性混亂是青少年普遍存在的心理狀態,但有部分青少年承受著過度的焦慮、孤獨、困惑等情緒,表現出心理癥狀及行為障礙。
精神分析學家唐納德·溫尼科特提出了重要的精神分析概念——促進性環境,強調環境對個體的心理發展和人格形成的影響。促進性環境,指父母或主要照料者以及生存環境可以充分覺察并滿足孩子的需要,尊重孩子的邊界,給予他們自由活動的心理和生存空間,從而促進其自發性和創造性的發展,形成穩定且獨立的人格。反之,若孩子持續感到自己的發展性需要被忽視、否認或剝奪,不安全感會隨之而來。為了避免這種痛苦,他們會將大量精力投入到對外在世界的適應中,失去了探索和呈現真實自體的機會,他們得依靠虛假自體保持與重要他人及環境的良好關系。值得一提的是,虛假自體雖然不夠真實和自然,但它在某種程度上為個體提供了環境所不具備的照顧功能,幫助他們通過“好孩子”“乖乖女”“優等生”等符合外在期待的形象渡過潛伏期。如果過分仰賴虛假自體生存,當他們進入青少年期時,新的發展任務會讓他們陷入自體崩潰的危機之中。同時,由于不具備彈性的心理空間,他們只能通過行動化的方式來擺脫內心極度的混亂和無力,但結果往往事與愿違。
二、青少年心理咨詢與促進性環境的重構
三例個案生動地呈現了上述內容。八年級的小帥竭盡所能地模仿著偶像的外表,高一的小媛在課堂上展露夸張的笑容,高三的小A執著于英語成績的提高。他們模仿、夸張和執拗的行為表現,實則是為擺脫內心沖突、重塑自體所進行的嘗試。這些嘗試是勇敢的,但結果卻不盡如人意。
回溯他們的成長經歷可以看到,小A 自幼與祖父母一起生活,小學時因成績優秀與父母重聚,但關系疏離。小帥與母親關系密切,但常被念叨成績,感覺父母“不能理解自己”。小媛的成長經歷在案例報告中著墨甚少,但從她對咨詢師的積極反饋中可以看出,她自小被孤獨感裹挾。由此,我們不難假設,生命早期的留守經歷,照料者過分關注學業、忽視情感等養育方式,使得三位青少年在不同程度上經歷了促進性環境的缺失,阻礙了他們發展性需要的滿足,如今,在繁重的課業和自我同一性的發展任務面前,一度被隱藏的問題凸顯出來。令人欣喜的是,他們主動尋求心理咨詢的勇敢舉動,為促進性環境的重構以及舊傷新患的解決創造了機會。
溫尼科特認為,“足夠好的母親”是最早且最重要的促進性環境。“足夠好的母親”(父母或主要照料者)可以鏡映、抱持孩子的發展性需要。通過這種持續性的養育,孩子會逐漸感受到自己真實的存在,獲得耐受情感和思考的能力,依靠自發性和創造性克服困難,獲得成長。因此,面對來訪者促進性環境的缺失,心理咨詢師提供一種類似“足夠好的母親”的咨詢空間,就可以彌補這一缺失,讓來訪者的真實自體得以呈現,并且獲得發展。
首先,三位咨詢師都有著強烈的助人愿望,能夠“看到”來訪者。小A的咨詢師將她的模樣印刻在腦海里,渴望幫助她“撥開云霧,重獲陽光”;小媛的咨詢師敏銳地覺察到她“由晴轉陰”的情緒變化;小帥的咨詢師持續關注他的“言語和非言語信息”。其次,他們將來訪者的困境視為青少年自我同一性的發展需要,不把“現象問題化”。咨詢中,他們鼓勵來訪者“慢慢講”,專注傾聽,接納來訪者的情緒,并在內心構建心理學假設。再次,無論是探尋行為背后的原因,將“認知調整”作為咨詢目標,還是使用“認知循環模型”的咨詢技術,他們都給予來訪者安全和開放的思考空間,引導來訪者進行反思。最后,他們尊重并且信任來訪者,根據來訪者的需要具體化咨詢目標,相信他們是“解決問題的專家”,鼓勵和支持他們創造性地解決自己的問題。
三、青少年期的心理修復與成長
隨著工作的開展,三位青少年在不同程度上表現出對心理咨詢師的依賴,這也就是某種程度的退行。溫尼科特認為,在退行狀態下,早年失敗的環境因素通過移情的方式進入到咨詢情境中,而此時,抱持性的環境替代了失敗的環境,來訪者真實的自體被鼓舞和認可,他們由此感受到一種真實的存在感。所以,雖然咨詢時間不長,自我同一性的發展任務尚未完成,但三位來訪者都在咨詢結束階段表現出了滿足和自信。
值得一提的是,為了使青少年來訪者獲得持續發展,在初步建立咨詢關系之后,咨詢師可以放慢腳步,將工作拓展到更深、更廣的領域,給予來訪者更多的時間去修復和成長。同時,性認同是青少年階段自我同一性建立不容忽視的方面,在工作中應當有意識地加以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