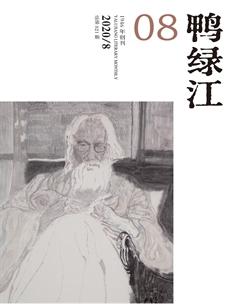牧歌與頌歌
邵部
浩然雖以短篇小說《喜鵲登枝》(《北京文藝》1956年11月號)登上文壇,但內心實則有著為中國農村的集體化道路寫史立傳的史傳意識和長篇情結。因此,他嶄露頭角之后一度急于求成,嘗試寫出并不成功的長篇《狂濤巨浪》。中國青年出版社的編輯蕭也牧做了退稿處理,并建議他先從短篇小說入門,像畫家先要打好素描底子一樣,練好基本功后再做長篇。此后,浩然進入短篇小說創作的自覺期,集中精力專攻短篇,至1962年動筆寫作《艷陽天》前,已經寫出了百余個作品,出版了多部小說集。
這些小說多寫農村的新人新事,反映波瀾壯闊的當代變革中舊觀念的改造以及新道德的養成。語言樸素自然,不用浮辭卻也聲口畢肖。摹形狀物、章法結構上多有璞玉天成之感,稚拙中透露著作者的才情。格調明亮輕快,宛如鄉野的牧歌,而又全然出乎廢名、沈從文一脈的文學傳統,有獨屬于當代的氣息和個人的創造。總的來說,對于生活的樂天態度充溢在小說內外,呼應著新生政權的活潑氣象,集中展現了50年代生活中欣欣向榮的一面。這些創作記錄了一位“工農兵作家”的成長過程,確立了浩然的文學風格。這一段是浩然文學道路上的第一個活躍期,也是一個可以單獨取出的創作單元。
這時期的作品中,發表在《鴨綠江》(曾更名為《處女地》《文藝紅旗》等)上的計有《風雨》《滿堂光輝》《箭稈河邊》《朝霞紅似火》《炊煙》等篇目,較為集中地反映了浩然的創作面貌。本文即準備以這些作品為中心,輻射此期的其他創作,談一談浩然早期小說的藝術風格。
1
浩然1932年出生于河北開灤趙各莊礦區的一個底層家庭。囿于出身以及家庭變故,他的教育經歷限于三年平民小學以及半年傳統私塾。少年時代的浩然酷愛讀書,但所能接觸的書籍極少。對浩然產生影響的主要是民間文化與文學。以評劇、河北梆子為主體的地方戲曲,母親講述的民間故事和民間傳說以及通過鄉間婦女夾存花樣、絲線的“樣冊子”接觸到的說唱故事、古典小說等,構成了浩然閱讀的主線。直到單門獨戶過日子后,浩然才輾轉借閱到《東周列國志》《三國演義》《鏡花緣》之類的古典小說。其外還有張恨水的《啼笑因緣》和兩本敘述城市里的有錢人家男男女女、勾勾搭搭的故事。實在無書可讀,就找幾本醫藥丹方之類的藥書翻看。《浩然口述自述》中提到的唯一一次買書經歷,是到鎮上置辦年貨時被擺著各種唱本和舊書的書攤吸引,用過年買肉的錢,買了一套《繡像水滸全傳》和一本《六言雜字》。
以上閱讀經歷可見,浩然沒有系統的古典文學的修養,也未曾感知過五四新文學的趣味,遑論遙遠的域外文學——他的一方小天地完全浸潤在舊文學的環境中,并在這種貧瘠的文學土壤里接受了最初的文學訓練。這種限制無疑不利于作家成長,但在某些方面卻滋養出了浩然獨特的文學風格。浩然早期創作整體上不注重以矛盾沖突結構小說,勝在樸素的文風、清新的語言和準確的對話。比如《滿堂光輝》趙大娘第一次接聽電話時的情景:
突然,從聽筒里傳出沙沙的聲管:“你是誰呀?”天哪,這不是春先他爸爸的聲音嗎?她滿屋地搜尋著,不見人,更使勁抓著聽那筒,唯恐說話的人跑了似的:“我,我,是你嗎?你在那兒呀?”
聽到電話里的聲音,首先滿屋子里尋人,緊接著握緊護筒,然后再是慌亂地問話,“陌生化”地表現了鄉村女性第一次接觸新奇事物時的不知所措。
《滿堂光輝》結構簡單,是一曲新生活的頌歌。小說里沒有觀念守舊需要改造的落后人物,也沒有兩條路線的斗爭,有的只是“社里的喜事一個跟著一個來”。問題的提出與問題的解決在文本上連接得如此緊密,以至于給人一種因為格調過于亮麗而在敘事上少于波瀾的印象。因而,敘事對于推動情節、塑造人物的作用被淡化,這一任務主要交由對話來完成。小說開篇是家庭會議的場景,趙大伯主持,兒子、兒媳、女兒你一言我一語,對話各有特色,唯有趙大娘沒能發表意見。一方面既表明了集體的事業如何滲透到家庭的生活中,另一方面通過趙大娘在話語權上的慢了半步,反映出她沒能跟上家人融入集體生活的節奏。小說中最大的難題,供應改造沙荒地所需的肥料,也是在趙大娘母女的對話中解決。先是趙大娘依靠生活經驗,對突擊清底的安排提出質疑:“傻孩子,豬圈、茅房、牲口棚,春來都清了一回底,再清一回也沒有多少油水了,就算硬著脖子把它挖出來,土里邊能有大勁?”接著是她受到女兒講解的書本知識的啟發,設想出火溫漚肥的做法,忽然說:“這回我明白了,高溫積肥就是石灰跟人尿的熱勁兒把柴草搞霉,對嗎?喔,我想起來了,要是把窯裝好,把窯底下掏個灶,給它加把火,不就發熱發霉的快了嗎?”趙大娘智慧的解放,解決了生產上的大問題。她由開篇時被家人無意識地忽視到末尾被請去工地做火溫漚肥的“顧問”,火熱的生活感召著她投入集體的事業,并在這一過程中實現個人的價值。她的形象也就在對話中得以塑造。
浩然的文字有著農民式的樸質和鮮活,如《新媳婦》中的這一段描寫:
話說到了辦喜事這天,梁家院子里可熱鬧哩!等洞房里的燈一亮,院內活動著的人都停住了,一齊擁到洞房來。前邊那幾個楞小伙子,向著新媳婦搖頭晃腦出洋相。一個叫黃全寶的中年漢子,是全村有名兒的“刺頭”,那家娶媳婦鬧洞房也離不開他。這次又被大伙選上代表先向新媳婦談判。他向眾人做個鬼臉,然后坐在新媳婦身邊,尖聲噶氣的說:“喂,你先出個條件吧,是要文的,還是要武的?”
用“話說”開頭,讀來頗有說書人的感覺。三言兩語之間,鄉村鬧洞房的民俗、刺頭黃全寶的形象便呼之欲出。
浩然初登文壇,葉圣陶即注意到他的語言天賦,在《新農村的新面貌》一文中評價道:“寫對話,寫景物,集中在表現人物的需要上,不肯隨便浪費筆墨。所用語言樸素、干凈,有自然之美。是可以上口念的作品,念起來比僅僅用眼睛看更有意思。”浩然的兒子梁秋川也在《曾經的艷陽天》一書中談道:“父親在多篇談創作的文章中推薦過這種方式,認為通過朗讀,可以使作者和聽者更直覺得體會到作品是否寫得通順上口,對修改稿件能起到許多無聲默讀所起不到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上口念”正是趙樹理的文學追求。趙樹理試圖通過民族化、大眾化的文學實踐,讓小說通過“聽讀”進入到更廣泛的農民群眾中。這里所設定的讀者正是浩然這類農民:有精神生活的需要,卻由于農村文藝陣地被封建文化占領,只能接受被否定的舊文學。為此,趙樹理立下一個做“文攤文學家”的志向。不同的是,趙樹理有一個“新文學”創作的前史,以知識分子氣質的文學創作起步。走向民間的語言實驗是在經受過啟蒙思想和五四新文學熏陶,自覺思考農村文藝方向后的主動選擇。浩然的文學創作卻是從無到有,唯有來自于民間生活的經驗可資調用,全憑了一股向上的韌勁以及超出一般工農兵作者的生活感受能力和語言表達能力,便不自覺地走上了趙樹理開辟的道路。在這種情況下,浩然與趙樹理的寫作分別指向了工農兵文學的不同話語層面:如果說趙樹理面對的是如何為工農兵的問題,那么浩然所面對的便是工農兵能不能寫、怎么寫的問題。這一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賦予民間經驗當代性,進而使這種創作成為當代文學的有機組成部分。
問題得以解決的契機,源自1952年前后浩然第一次接觸到《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當時他正在河北省團校學習,得到了一冊解放區鉛印的《講話》,一口氣讀了兩遍,繼而受到長久的震撼。在《講話》的啟示下,浩然意識到自己是當然的寫作者,他的民間經驗因此被激活,轉換為創作的有效資源。這里所講的“民間”,并非陳思和先生提出的“一個與國家相對的概念”,而趨向于被《講話》賦予合法性的“人民生活”:“人民生活中本來存在著文學藝術原料的礦藏,這是自然形態的東西,是粗糙的東西,但也是最生動、最豐富、最基本的東西;在這點上說,它們使一切文學藝術相形見絀,它們是一切文學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人民生活”被設定為構建“人民文藝”的主要路向。與此同時,生活的經驗者也被寄予成為“言說者”的期望。毛澤東在《講話》中提到文藝工作者“不熟,不懂,英雄無用武之地的問題”。“不熟”,即人不熟,對文藝工作的對象——工農兵及其干部不熟。“不懂”,即語言不懂,對于人民群眾的豐富的生動的語言缺乏充分的知識。這些對于知識分子型的作家是需要加以改造的地方,于浩然這類工農兵作家卻是天然的優勢。在《講話》開辟的文學空間中,浩然生活和文學上的原初狀態最終以工農兵文藝的名義進入主流文學的脈絡。
2
浩然在小說集《珍珠》(百花文藝出版社1962年版)的前言中寫道:“這一時期的作品,所描所繪,都是我最感興趣和有所理解的事物。可能因為我自己是青年人的緣故,平時下鄉和下訪期間,接觸最多、談得也最投機的是青年,所以這個集子里描寫青年男女的篇章占了大多數,其他方面就比較少。”可以說,青年男女形象構成了浩然早期小說的核心人物序列。而刻畫這一形象,最容易出彩也最容易墜入窠臼的部分,莫過于描寫青年男女的愛情。
浩然早期小說中,青年男女的愛情故事常常放置在某一政策或運動的背景之下,政策的落實或運動的推進與愛情的發展呈現出結構上的對應關系,力求在兒女情與風云氣之間求得平衡。
《朝霞紅似火》是在這一點上處理得較為成功的作品。小說的主線索是大煉鋼鐵背景下一對農村新人的戀愛故事。丁大川“身材魁梧,相貌英俊,性子剛強”,金華珍“是一個漂亮姑娘,中溜個子,烏黑的頭發,明亮的眼睛”。然而,古典小說中的才子佳人模式已經被浩然自覺拋棄。他將二人的結識放置在先進生產者代表會議的情境中,以“英雄愛英雄”的方式解釋丁大川對金華珍的愛慕之心,由此證明戀愛的正當性不是來自外貌,而是源于追隨集體事業的內心。
會議結束后,金華珍掛念煉鐵試驗的成果,在城關著急地等待回村汽車。路過的丁大川主動請纓,硬要用新自行車送她回家。因為二人的身份被設定為“新人”,單就施助行為來看,如果處理不當很容易將情感描寫止步于同志之間的“革命情誼”。如何既寫出新人的“泛愛”,又能在其中分別出具體的男女之愛,對于寫作者其實是一個不小的挑戰。浩然通過對丁大川的動作描寫巧妙地化解了這一難題:“他伸手奪過金華珍的包裹,跟自己的行李分拴在后架子上,又把自己的大棉襖墊在上邊,然后,硬拉金華珍上了車。”“奪”“拴”“硬拉”,動作一氣呵成,極有畫面感,顯示出農村青年男女交往中純然的毫不忸怩作態的一面。而在這些極快的動作中間,“墊”在后座上的棉襖,則透露出丁大川對“同志”的誠摯幫助之中,也有對意中人的周到與細膩。這是粗中有細、公中有私的一面,同志之情夾雜著男女之愛。
遇到路況不好的地方,兩人停下車來,并肩步行在洋溢著春天氣息的小路上。這時,浩然用如詩如畫的筆墨描寫沿途的風景:
太陽已經西沉,盤山前的大平原,顯得遼闊、寧靜。剛剛開放雪白花團的梨樹,點綴著綠得象翡翠一樣的麥田。水車叮當叮當地響著,間或傳來澆麥人的歡樂小曲。
這段描寫并沒有怎樣巧妙的藝術手法。唯一一處修辭,用翡翠比喻麥田,不僅談不上高級,反而顯得很通俗。然而,這些詞句組合到一起,卻給讀者一種很調和的感覺,仿佛眼前出現了一幅鄉土氣息濃厚的風景畫:夕陽、遼闊寧靜的平原、梨樹與麥田、一對萌生了愛意而又未確定關系的戀人。畫外是水車的響聲與澆麥人的歌聲。農業生產不僅沒有破壞這一靜謐的瞬間,反而將勞作的美引入詩境。浩然的小說中,有許多這種看似普通卻經得起品味的描寫。
因為“階級斗爭”還沒有成為作家觀察農村生活的主導視角,浩然早期小說著意表現的是正向的情感和積極的人生態度,多寫人間的歡樂與喜愛,仇恨與怨懟相對來說虛無縹緲的事情。作為與這種情感結構對應的文本結構,小說以正劇的雅正為主調,雜有喜劇的詼諧。丁大川到紅棗村學習煉鐵經驗,連著三天沒有見到金華珍,臨走前按捺不住對心上人的想念,決意去村里尋訪。向村頭一位搖轆轱打水的老大娘問路,那人卻正好是金華珍的母親。丁大川臉一紅,不由分說便彎腰拾起扁擔挑水,連著挑了三趟。老大娘不肯讓他再挑,卻也對他產生了好感:“就這么一會兒,老人覺得這個年輕人很討人喜歡。”不得不說,這是一個講究策略,有著戀愛頭腦的青年人。這一段尋而未得的小插曲,既為丁金的交往做了鋪墊,感情升溫變得順理成章;另一方面又頗具喜劇效果,在戲劇性的情景中刻畫丁大川的羞澀與殷勤,讓讀者看到,他的身上不僅有高于普通人的“新人”品質,也有“青年”可感可觸的一面。
再如《箭桿河邊》。公社成立后的第一個年頭,暴雨突降,箭桿河凌汛來襲。精壯勞力在外支援水庫建設,社里只有老弱病殘和婦女可供調用。徐廣泰不相信婦女的力量,緊急向上級求援。等到支援隊趕來,馬燈一照,清一色婦女。更關鍵的是,帶頭的不是別人,正是范新春。徐廣泰貧雇農出身,災荒年月妻離母死,直到土地改革才算翻身過上安穩日子。經人撮合結識了已有三個孩子的寡婦范新春。徐廣泰自覺無力承擔重組家庭后的負擔,因而痛心拒絕了她。時隔兩年再見,徐廣泰還是那樣的舊觀念,而范新春卻煥然一新:
這個女人象從天上掉下來的一樣,站在徐廣泰的面前。她腦后那只小發髻不見了,剪短的頭發披在肩上;穿的不是那身毛藍粗布打補釘的衣服,是花格洋布小褂,青斜紋布褲,還穿著一雙時興的球鞋。這還不算,她不再是擰皺著眉頭、腫著眼泡、在人們面前垂頭低語的小寡婦,而是喜眉笑臉、豁豁朗朗的帶隊的女干部,并且在生人面前象個走南闖北的男子大漢那樣,通名報姓:我叫范新春!……
面對改頭換面的范新春,浩然用諧趣的筆調表現徐廣泰的心理活動:“一股說不出來的、酸溜溜的情緒頂到他的嗓子眼兒,不覺中,手里的餅子被他攥的粉碎。”他一度懷疑“莫不是她已經改嫁了?嫁了個有本事的男人?”
經過防汛一事,他終于認清范新春的新生不是出自男性的拯救,而全然是她個人的解放。范新春的改變讓徐廣泰重又動了重組家庭的念頭。他紅著臉說服范新春留下,理由是他們是兩邊的帶隊人,應該把這幾天的工作總結總結,打個報告給公社黨委。對于范新春來講,這是一個無法拒絕的提議。待到兩邊人馬回去,兩人終于有了獨處的機會。徐廣泰卻閉口不提總結的事,臉紅了半天,只是說“你們婦女真叫棒呵!”頭一句已是突兀,第二句話更是沒頭沒腦:“過去是我錯了,對不起你,原諒我吧!”作品中的主人公臉紅心跳的時候,讀者也隨著會心一笑。直到最后我們也沒看到徐廣泰的總結,但范新春的新生與徐廣泰的轉變,顯然已經透過兒女情傳達出了風云氣——“新農村的新面貌”。
3
兒女情與風云氣,歸根結底還是一個文學與政治的關系的問題。時至今日,將浩然認定為“政治化寫作”依然是一種具有話語權的解讀方式。這種闡釋模式將文本割裂為政治與文學兩個互不相融的部分,認為政治因素壓抑了文學因素,浩然作為寫作者,完全淪為了意識形態的工具。他的作品缺乏起碼的文藝價值,有的只是對政治的阿諛。這種對浩然的理解其實并沒有走出1978年重評浩然的“新時期”歷史視野。
筆者以為,評價浩然作品以及以他為代表的當代農村題材小說,需要注意的一點是大政治與小政治的分疏。所謂小政治,指的是具有特定對象的政策法令、一時一地的政治意圖以及上級單位、組織、人物的影響等層面,它制造了作家周邊的政治氛圍、社會風向以及創作壓力,是長遠看并不穩定卻又對置身其中的作家產生實在影響的小氣候。迎合小政治的創作,反映的是文學的政治功利主義傾向。如同命題作文一般,首先設定“主題”,然后在現實生活中尋找與之呼應的故事,創造力自然受到束縛。浩然創作上的這一問題,在早期小說中已初露端倪。短篇小說《送菜籽》刊發于1960年8月26日的《人民日報》,是一篇為了配合社論而創作“時令性”小說。這篇小說的“生產”過程具有癥候性的意味。在整風運動中,有人就浩然創作跟著《人民日報》社論跑的現象提意見,認為他的小說“只能算是《人民日報》社論的注釋”,并稱他為“人民日報社論解說員”。這本是批評意見,浩然卻將之視為光榮稱號,并向身邊的朋友半玩笑半認真地說:“《送菜籽》就是《人民日報》‘大種秋菜社論的注解,難道不好嗎?”于是,“幾千字的小說,連構思、帶起草稿、修改、抄清、封好、寄出,只是半個下午和一個晚上的時間”,而從寄出到發表,僅用了七天時間。這種寫作方式將短篇小說“短平快”的特點發揮到極致,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人物、結構、情節上的平面化,不可能創造出與時間抗衡的文學經典。我以為政治對于浩然文學創作的抑制,主要是就這一方面而言。
另一方面,從大政治的角度講,對于浩然這類工農兵作家而言,政治上的進步,不僅無害于文學,反而有助于提升作家的視野與境界。這里的大政治,是錢穆先生所講的一項制度之創建與推行背后的意識與精神。具體到“十七年”農村的改造與建制而言,是在這一過程中發揮了理論導向和動員能力的社會主義理想。浩然少年失恃失怙,是新生的民主政權拯救他于親族的侵奪。參加革命工作之后,地方黨校培訓班的課程又系統地提升了他的理論認識。個人的親身經歷以及后天的社會主義教育,使浩然對于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生發出由衷的認同。人民翻身做主,成為自己的主人也成為歷史的主人。翻身的工農兵不是被動地參與歷史的建設,而是通過主體意識的確立完成心靈的重建,并被賦予表述這一過程的話語權。浩然的寫作本身即是這一歷史實踐的產物。可以說,如果沒有廢除土地私有制的農村集體化進程,如果沒有蕭長春、高大泉式的農村新人的涌現,如果浩然沒有成長為一個具有社會主義理想的農民寫作者,僅憑他淺薄的民間文學修養,很難在文學上有所作為。
《風雨》中,尤家男戶主去世、女戶主病倒,小家庭風雨飄搖,有解體之危。在這危機時刻,同姓尤會計想的是如何侵占房屋,而素有仇怨的喬家以及更廣大的社員卻無私地幫他們渡過難關。小說是一個結怨與和解的故事。結怨的一面是歷史敘事,揭示了土地私有制如何造成了底層農民的互相剝削與仇恨。和解的一面則指向農業社的現實與未來。在這一時空維度上,傳統鄉村社會中的姓氏——宗族結構解體,“眼下我們是一個船上的人”的樸素認識打破了這一“差序格局”,導向一種新的鄉村共同體的形成。
《箭桿河邊》的“政治”是婦女解放的話題。農業社的成立將范新春從舊觀念與家務事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她從家庭范圍內的“第二性”,成長為社會勞動的參與者。這篇小說可貴之處,在于浩然沒有把婦女解放停留在沒有性別差異的“勞動力”層面上,而是更進一步,書寫了范新春對于女性特質的重新發現。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浩然總是在范新春成長的關鍵節點安排一個“照鏡子”的情節。她領到農業社的工資,第一件事便是去供銷社扯了一塊“喜歡許久沒有摸到手的花格洋布”,縫了一件合身的褂子,“走在小塘邊照一照,她發覺自己是那么年輕、那么漂亮”。防汛結束,范新春“解下頭上的毛巾,撣撣身上的土,往堤下走幾步,伏下身去,兩手捧著水,洗去臉上的泥污。緩緩流動的河水,象一面鏡子,映起她那俊俏的面影。幾日風吹雨淋日光曬,皮膚好象黑了一些,但是更好看了。”范新春的第一重解放,是由“傳統女性”到“勞動力”的蛻變。面對徐廣泰“為什么不來勞動力呢”的不解,她自信地回應“我們不是勞動力嗎?”她的第二重解放,是在“勞動力”概念范疇中,重新發現了自己作為女性的魅力和性別特征,由此成長為“農村新女性”。她在水中的鏡像,表明當代中國的婦女解放不是對性別差異的抹殺,而是在確認主體性之后性別意識的重建。不論是晚清以來的“興女學”,還是世界性的女權運動,這種理念都堪稱新潮。婦女解放本身是中國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亦即當代中國政治的一部分。浩然秉持此種理念建構女性形象,不僅沒有損害文學,反而顯露出獨特的魅力。
古典文學學者葉嘉瑩先生在《我看<艷陽天>》中說:“如果一位作者的生活體驗和思想及感情,都是與他所要表達的政治目的合一的話,那么政治目的對于他的創作生命便不僅是一種遏抑,且有時還會成為一種滋養,因此他自然便可以寫出一部雖然含有強烈的政治目的,也同樣具有強烈的創作生命的文學作品來。”對于浩然尤其是他的早期小說來講,感發的生命與現實政治的融合,于他的文學品格更多的是一種助益。浩然的語言、情感與政治在我們今天看來或許可以彼此剝離,在浩然那里卻是混溶合一的整體。相對于從一個方面否定另一個方面,建構一種對于浩然的整體性認識或許是更有意義的研究路徑。
【責任編輯】? 陳昌平
作者簡介:
邵部,山東濟寧人,中國人民大學文學博士,現為山東大學文學院助理研究員,主要從事當代文學史研究與文學批評。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當代作家評論》《文藝爭鳴》《南方文壇》等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十余篇,部分文章被人大復印資料全文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