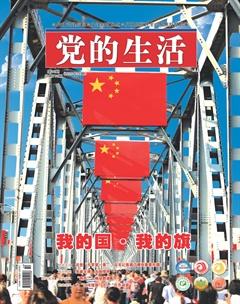“哨聲”一響動鶴城
楊明 張銘 許樂


“鄰居們自掏腰包買來樹苗,各家認領(lǐng)各家的樹,栽種、施肥、澆水……茶余飯后,老哥兒幾個坐在果園里喝喝茶、嘮嘮嗑兒,挺美!”吃過午飯,74歲的齊齊哈爾市富拉爾基區(qū)北興街道二十五社區(qū)網(wǎng)格長黃繼軍就想著到社區(qū)的“紅色果園”逛逛。
兩道彎剛過,歡聲笑語便已入耳,黃繼軍不禁感慨——曾經(jīng)人人都繞著走的垃圾場,短短數(shù)月便成了聚集人氣的社區(qū)“地標”。“大伙兒利用廢棄樹根做成桌椅板凳,上面還用炭燒法畫上山水圖……每個創(chuàng)意都飽含真情。”身為“紅色果園”建設(shè)的親歷者,黃繼軍漸漸明白了一個道理——只要在黨建引領(lǐng)上下功夫,基層治理便大有可為。
事實上,在齊齊哈爾已有4621個網(wǎng)格在全市鋪開,類似“紅色果園”的眾多變化正悄然出現(xiàn)。為把黨的力量和主張傳遞到“神經(jīng)末梢”,使基層治理有“魂”、有序、有力、有效,齊齊哈爾交出了一份獨具特色的“鶴城答卷”。
打通聯(lián)系群眾“最后一米”
“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一段時間以來,街鄉(xiāng)的職能定位不清、權(quán)責邊界不明,阻礙著基層政府職能轉(zhuǎn)變和治理水平的提升。尤其在社區(qū)一級,很多地方暴露出基層組織體系不健全、組織神經(jīng)末梢麻痹、聯(lián)系群眾斷層缺位等問題。
啃下硬骨頭,要有新辦法。總結(jié)以往經(jīng)驗,齊齊哈爾市委提出以“吹哨報到”為代表的一系列工作機制改革,并相繼出臺《關(guān)于深化“吹哨報到”工作的通知》等系列文件,推動一時一地的基層鮮活實踐躍變?yōu)橹贫然⒖茖W化、系統(tǒng)化的體制機制改革。
“基層治理,關(guān)鍵看黨員與群眾之間的聯(lián)系。要做到哪里有黨員,哪里就有黨的組織;哪里有群眾,哪里就有黨員聯(lián)系。”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齊齊哈爾市委書記孫珅在工作推進會上提出,“要打通聯(lián)系群眾‘最后一米。”
在龍沙區(qū)彩虹街道太陽社區(qū),對55歲的低保戶鄭廣東而言,“最后一米”意味著直抵內(nèi)心的溫度。
鄭廣東早年下崗,因患強直性脊柱炎行走困難、不能自理,離婚后一直由60多歲的哥哥姐姐照顧。2019年,鄭廣東因病情加重,連正常站立都成了難事,這對他無疑又是一記重創(chuàng)。在做網(wǎng)格調(diào)查的過程中,太陽社區(qū)黨委書記曾繁榮了解到鄭廣東的情況,立刻上報街道。沒幾天,社區(qū)工作人員就為鄭廣東送來一輛嶄新的輪椅。坐在輪椅上,鄭廣東激動得幾近哽咽:“社區(qū)把工作做到了老百姓的心坎兒上!”
網(wǎng)格雖小,作用卻大。齊齊哈爾市委將城管、綜治等職能部門在社區(qū)設(shè)置的多個網(wǎng)格整合為一個綜合網(wǎng)格,每個網(wǎng)格居民戶數(shù)由100~700戶調(diào)減為100~300戶,著力劃細劃小。各網(wǎng)格通過公布熱線電話、發(fā)布二維碼、開通微信公眾號、入戶走訪等形式,人人皆可實時反映問題。
泰來縣的農(nóng)行小區(qū)已有25年歷史,由于年久失修,曾是全縣最破舊的小區(qū)之一。“像這樣的小區(qū)太多了,僅靠社區(qū)力量顯然不夠。”泰來縣委常委、組織部部長趙志新認為,“只有依托網(wǎng)格,利用居民自治,基層治理才能扎實落地。”
改革實行后,為進一步織密基層組織網(wǎng)絡(luò),農(nóng)行小區(qū)每棟樓由黨員中心戶組織建立業(yè)主微信群,構(gòu)建“小區(qū)黨組織+網(wǎng)格黨支部+樓棟(單元)黨員中心戶”的組織體系,78歲的楊永奎被推舉為小區(qū)黨組織書記、業(yè)委會黨支部書記、業(yè)委會主任。
“一肩三挑”帶來的是壓力,更是動力。盡管整天樓上樓下跑,楊永奎沒少挨累,但以身邊人說身邊事,在群眾中具有天然的信任度和配合度。很快,物業(yè)維修基金收上來了,違規(guī)設(shè)施順利拆除了,舊樓改造工程轟轟烈烈地開始了。
“注意到我家門口掛的‘黨員模范之家的小牌子沒有?”楊永奎指了指自家門右上角,認真介紹,“每棟樓的黨員家門口都會掛上這樣的牌子,現(xiàn)在,‘黨員帶頭已經(jīng)成了大家的共識。”
成千上萬黨員紛紛到自己居住的社區(qū)“報到”,把機關(guān)黨組織的服務(wù)范圍延伸到一線,把在職黨員的活動“觸角”延伸至“八小時以外”。這支龐大的力量,投身形式多樣的志愿服務(wù)活動,在環(huán)境整治、教育培訓、政策咨詢、服務(wù)群眾等方面發(fā)揮著重要作用。
短短幾個月的時間,昔日雜亂的院子找回了盛時風貌,被雜物遮蔽多年的影壁也得以重見陽光,小區(qū)里有了綠蔭,有了花香,也有了燕巢和鴿哨。
“一根針”拉動“千條線”
2020年5月21日下午,甘南縣黨群服務(wù)中心主任張偉志正埋頭工作,手機彈出這樣一條消息:“城建部門行動迅速、處理及時,損壞道路在一小時內(nèi)得到修復(fù),給你們點贊!”看著簡簡單單的兩行字,張偉志會心地笑了。自打“甘南縣黨群服務(wù)中心”APP上線以來,他比以前忙了,收到類似的好評也多了。
若時間倒退三個月,盡管彼時手里也攥著“哨子”,但張偉志心里一直在打鼓:“‘哨聲響了,各單位能不能聽得見、叫得來?”
這樣的擔心并非沒有道理。面對這么多行政級別高、社會資源豐富的機關(guān)單位,處于行政序列末梢的黨群服務(wù)中心,究竟能不能叫得動他們?黨建引領(lǐng)“吹哨報到”,解決了張偉志心中的困惑。
一聲哨響,四方來應(yīng)。甘南縣委組織部副部長曲國生介紹:“縣里成立了縣、街(鄉(xiāng))、社區(qū)(村)三級黨建工作協(xié)調(diào)委員會。只要‘哨聲響了,不論是政府職能部門、街道、社區(qū),還是駐區(qū)單位、非公組織,所在黨委都要立即響應(yīng),共同參與社會治理。”
“以前我們發(fā)現(xiàn)問題,要先上社區(qū)向書記匯報,書記再向鎮(zhèn)里匯報……層層匯報,耗費時間。”繁榮社區(qū)的網(wǎng)格員李淑霞不由得感慨,“現(xiàn)在工作效率上來了,大伙兒干事的熱情也高了。”
實際上,早在今年年初,齊齊哈爾市委便整合“12345”、數(shù)字城管等信息系統(tǒng),建立市、縣(區(qū))、街道三級指揮調(diào)度平臺,按層級受理、篩選、轉(zhuǎn)交、督辦,分層級受理、篩選基層單位和群眾反映的各類問題,按層級分別向市、縣(區(qū))職能部門轉(zhuǎn)單交辦。
“群眾可以通過微信公眾號直接向相關(guān)責任主體吹哨,通過遞交訴求、等待解決、效果評價三個步驟,使‘群眾跑腿變?yōu)椤當?shù)據(jù)跑路。”曲國生介紹,“這項改革直接推動了行政效率的提升。”
“為推動及時辦哨,我們通過三種方式,對接哨處理情況進行監(jiān)督。一是縣領(lǐng)導通過APP隨時關(guān)注,查看分管戰(zhàn)線及包扶鄉(xiāng)鎮(zhèn)接哨辦理情況;二是黨群服務(wù)平臺每周匯總并通報接哨單位辦理情況;三是啟動問責機制,對于接哨慢、辦理不到位的,縣委對黨政‘一把手問責。”如今,張偉志對工作信心滿滿。
甘南縣的變化在齊齊哈爾絕非個例。在富拉爾基區(qū),“大美紅岸”指揮平臺將各部門職責厘清為6大類54小類,通過實施“以哨為令”五步解難題群眾工作法,大量問題和隱患被消除在萌芽狀態(tài),解決了“看得見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見”的問題;在龍沙區(qū),“黨建引領(lǐng)+智慧社區(qū)”平臺通過“線上聯(lián)系,線下服務(wù)”的方式,涵蓋物業(yè)、家政、網(wǎng)上商城等八項便民服務(wù),進而創(chuàng)建了“積分兌換物業(yè)費”模式,用“小積分”激發(fā)“大能量”,實現(xiàn)了自內(nèi)而外的品牌效應(yīng)。
召喚的“哨聲”隨時出現(xiàn),落實的“報到”聞聲而動。有權(quán)管事、有人干事、有錢做事,基層有了力量,“哨子”也自然吹得響亮、吹出實效。
讓干部“暖心”更“安心”
經(jīng)過持續(xù)推進,齊齊哈爾全市上下黨建引領(lǐng)基層治理的氛圍日益濃厚。
為配強落實各項工作的基層力量,龍江縣優(yōu)化村級代辦員設(shè)置,把代辦員崗位升級為民事代辦員、黨建助理員、網(wǎng)格管理員、人民調(diào)解員、信訪信息員“五員一體”,具體負責村級網(wǎng)格服務(wù)站工作。通過嚴格掌握選人標準,全縣共選拔“五大員”178名,作為村級后備人才進行儲備、培養(yǎng)和管理。
前不久的一天,龍江縣魯河鄉(xiāng)四撮房村村民顧喜貴急匆匆地來到村網(wǎng)格化服務(wù)站,直接找“五大員”反映情況:“鄭德良家把地邊路開起一壟,我家的農(nóng)用車沒法用了!”
詳細了解情況后,“五大員”立即向網(wǎng)格長進行匯報,并將鄭德良找到村里協(xié)商,但雙方仍爭吵不休、各說各理。眼見調(diào)解不成,“五大員”向鄉(xiāng)網(wǎng)格化服務(wù)中心吹了“需求哨”。半小時后,司法所的工作人員來到村調(diào)解室。
“經(jīng)過鄉(xiāng)司法所和村里的共同調(diào)解,我們情緒緩和了很多,也意識到了自己的問題。”顧喜貴撓了撓頭,有點兒不好意思。最終,兩家都同意往后各退半米,把道路恢復(fù)原樣,糾紛得以順利解決。
“‘五大員會干事、腦子活,給全村工作注入一股活力。”跟村里“五大員”共事一段時間之后,杏山鎮(zhèn)后六九村黨支部書記馬長信直言,“我肩上的擔子輕了不少。”
龍江縣的例子很有代表性,但配齊配強干部隊伍,不只是選人用人那么簡單。這背后,有著無數(shù)基層干部的辛苦付出。
“基層工作任務(wù)繁重,責任和權(quán)益不對等,報酬待遇跟不上。”龍江縣委常委、組織部部長范福友坦言,“長此以往,崗位吸引力、干部活力都成問題。” 對此,齊齊哈爾市委以選聘優(yōu)秀村、社區(qū)書記進入事業(yè)編制為重點,著力健全激勵保障機制。
捅破“天花板”,才能“干有所盼”。對符合選聘進編條件的優(yōu)秀村、社區(qū)黨組織書記,市委采取考核和面試相結(jié)合的辦法,選聘街道(鄉(xiāng)鎮(zhèn))事業(yè)單位人員,每年一次,常態(tài)激勵。
2020年8月末,鐵鋒區(qū)龍華街道中東社區(qū)的老舊小區(qū)改造進入關(guān)鍵階段,社區(qū)黨委書記張志新每天早起晚歸,遇到關(guān)鍵事宜更是連軸轉(zhuǎn)。“以往,工作干得再好,政治待遇上總有道邁不過去的‘坎。”作為齊齊哈爾市第一批進編社區(qū)干部,現(xiàn)在張立新覺得工作更有“奔頭”,“這讓干部們看到了希望!”
但選聘進編不等于端上了“鐵飯碗”。齊齊哈爾市委對納入事業(yè)編和公職化管理的優(yōu)秀村、社區(qū)黨組織書記,簽訂聘任合同,并根據(jù)工作需要,明確解聘退出的附加條款和具體情形,建立分級分類精準培訓制度,促進素質(zhì)的全面提升。在鐵鋒區(qū)打造的評估激勵體系中,街道黨工委、社區(qū)黨委對網(wǎng)格黨建工作開展情況進行定期評估和量化考核,并對網(wǎng)格黨支部和樓棟黨員中心戶實行星級化管理,發(fā)放統(tǒng)一標識,及時公開公示。
千帆競進,百舸爭流。近一年來,齊齊哈爾市各級黨組織在工作實踐中的創(chuàng)新舉措不斷涌現(xiàn),黨建引領(lǐng)基層治理工作機制在鶴鄉(xiāng)大地落地開花。在探索基層治理的征程上,齊齊哈爾正在畫出最大同心圓,走出新時代的群眾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