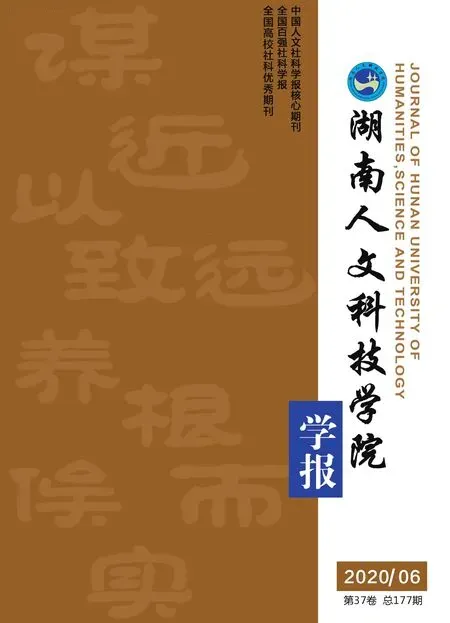再論曾國藩道德領導
周海生
(中共淮安市委黨校 市情研究中心,江蘇 淮安 223005)
學史可以看成敗、鑒得失、知興替;學倫理可以知廉恥、懂榮辱、辨是非[1]。論者曾在《湖南人文科技學院學報》2017年第1期刊文指出過,近代重要歷史人物曾國藩治術中蘊含道德領導力因素。其具體體現在,注重以“仁”“禮”等價值觀統(tǒng)領軍隊;以“樸實有農夫土氣”“忠義血性”為標準,遴選湘軍成員;營造道德基礎上以“彼此相顧”為目標的運轉機制和以質樸為特征的軍隊風格;以道德判斷為依據辨是非、“興舉劾”。用倫理學概念譜系觀照晚清政治人物曾國藩“思維世界”中的道德理性和“歷史世界”中的領導實踐,還可以看到理性和實踐相互作用的運動過程。這一運動過程呈現出道德理論知識與道德實踐行動合一、個人道德記憶與家庭道德記憶合一、道德軟性約束與道德硬性約束合一的特征。危機時期,人們比平常歲月更不能容忍從政人員的道德缺失,也不能容忍用道德理由當做怠政、亂政的借口。再論曾國藩的道德領導,從中尋求倫理鑒示,將有助于了解危機中從政者的倫理軌跡,進而提升從政者應對危機的能力。
一、曾國藩道德領導是道德理論知識與道德實踐行動合一的過程
(一)曾國藩開展道德認知
價值體系建立的前提和基礎是進行道德認知,獲得道德知識。曾國藩道德知識從哪里來?不言而喻,成長經歷中的生活環(huán)境、質樸鄉(xiāng)風、艱難生活、長輩的言傳身教是道德認知的基礎和來源,自然給曾國藩的價值觀打上烙印,使其獲得初步的、尚未系統(tǒng)化的道德知識。求學和交游經歷也增進了曾國藩的道德認知。曾國藩幼年受教于父親曾麟書,后來曾就讀于家鄉(xiāng)的漣濱書院和省城的岳麓書院。湖南經世致用學風通過書院,特別是岳麓書院厚植于曾國藩思想之中。青年時期曾國藩還先后結識劉蓉、郭嵩燾、陳源袞、何桂珍、何紹基、吳嘉賓、吳廷棟、竇垿、馮樹堂、邵懿辰、劉傳瑩等人。有志好友相互間的箴勸讓曾國藩頗為受益。
尤為重要的是,科舉經歷是曾國藩獲得和儲備道德知識的通道和過程,促成其道德知識的體系化。
始于隋唐時期的以進士科為核心的科舉制度,到了清代已經相當完備,這一體現就是信度的不斷提高。“中國的文官選拔史,就是信度(不同考試條件下考試結果的一致性)、公平性和效度(考試結果、分析、應用與考試初衷的一致性)之間互相爭斗的歷史。在這一斗爭中,信度和公平性漸漸占據上風。選拔的方法、過程、結果越來越可靠,越來越準確,越來越公平”,但在效度上,即通過考試為王朝治理選賢任能上來說,“選拔出來的文官也越來越與賢能脫節(jié)”的問題始終存在[2]。清代科舉體制是一金字塔結構,大致可分初、中、高三級。初級主要是“秀才”試;中級是鄉(xiāng)試,三年一比,考取后成為舉人;高級是會試,在鄉(xiāng)試次年舉行,中式為進士,之后還有殿試、朝考,優(yōu)異者選入翰林院。明清朝政治慣例,非進士不得為翰林,非翰林不得入內閣。且明清政體中無宰相,入閣成大學士即被世人視為宰相,因而翰林的社會聲望和期望值都極高。曾國藩是“兩榜”正途出身,從秀才到登鄉(xiāng)試桂榜、會試杏榜,進而為翰林。科考過程也是其道德內化過程。為什么這么說呢?這和清代科舉考試內容和形式有關。
就內容而言,清代科舉總體沿襲前朝,并在相當長時期內都穩(wěn)定實行。這一期間,鄉(xiāng)試、會試均進行三場考試,且內容一致,即:首場為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八股文3道與試帖詩1道,次場五經(《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春秋》)八股文5道,末場策論5道[3]。自元代后,四書在科舉考試中地位超過五經,四書只用南宋大思想家朱熹的經義注解,五經也主要采用朱熹等人的解釋。朱熹是儒家思想發(fā)展到宋代之集大成者,由朱熹為主建構的程朱理學通過科舉制度成為明清官方主流意識形態(tài)。官方也刻意用理學學說進行社會控制和整合。任何一個投身科舉的人,從最初受學到獲取功名,長年累月要不斷背誦四書五經等經典,更要不斷理解領會朱熹等所做的權威性、排他性經義解釋。這是幾乎每個士子的知識來源和知識結構。“鄉(xiāng)會試所考察的知識內容對于清代讀書人群體最為重要,故尤其能夠影響到讀書人群體的閱讀世界與知識儲備”[4]。眾所周知,儒家思想是倫理道德本位的,程朱學說更是道德至上的哲學體系。因此,這樣的“閱讀世界”和“知識儲備”必然包括道德知識的閱讀和儲備。
就形式而言,前文所說的科舉制度信度不斷提高,體現在以八股程式對取士的唯一性和決定性上。明清時代以八股文應試已發(fā)展成文化形態(tài),其要點有兩大端:體裁用排偶句式,視角仿古圣先賢。任何學子在長期應考訓練和考試中,都要以先哲語氣立言,要用皇家認定的權威經義立論,要用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的機械格套行文。這不啻是一種角色扮演,即以道德先賢視角和儒家學說來看待世界和分析問題。這種考試形式顯然預設,掌握大量道德知識便能成為有道德的人,且不說這種預設在明清兩代演生出多少出科舉中人悲喜劇,但經過經年累月的背誦、練習,道德知識、價值觀念終究可以內化到士子的主觀世界中,儒家理念滋潤心靈的作用是無可否認的。
曾國藩也是在科考一般性規(guī)律下成長的。曾國藩9歲“讀《五經》畢,始為時文帖括之學”[5]10。 15歲在父親私塾中“受讀《周禮》《儀禮》成誦,兼及《史記》《文選》”[5]14。三度參加會試,最后一次會試中式,殿試和朝考順利,得中翰林。朝考中曾國藩所作策文題為《順性命之理論》。從文本看,28歲的曾國藩完全是以宋明理學的價值框架和概念觀點,如“性”“命”“理”“氣”“仁”“義”“禮”“智”等看待和分析世界了[5]26。由于前述諸種原因,特別是科考的漫長準備,曾國藩初步建構起儒家化的價值體系。這也是曾國藩能夠進行道德領導的基礎條件。
(二)曾國藩力行道德稽核
擁有體系化的道德知識、建構起價值體系,只表明是主觀世界里的擁有,只是過有道德的生活的必要條件,并不必然保證就能正確地踐行道德,或踐行正確的道德。儒家成圣成賢學說是完整價值鏈,既要有格物致知、誠意正心,還要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在倫理學話語中,道德稽核意指道德主體主動用道德理念、道德標準驗證、稱量行為,屬于理論指導實踐范疇。
曾國藩道德稽核的起點是接受理學修身方法,標志是立志做圣賢。1840年,曾國藩成為翰林官之后,有數年處于人生坐標調適期。考察曾氏這一時期日記,基本是酬答、交游之類活動。但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人,路徑在哪里,一直縈繞心頭。最初他定位在成為一名皇家文學侍從。進京為翰林初期,他曾內心獨白,要抖擻精神,為家庭惜福,“可以無愧詞臣,尚能以文章報國”[6] 41。“時方詳覽前史,求經世之學,兼治詩古文詞,分門記錄”[7]47,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治學的廣博。1841和1842年,他先后拜訪以修習理學而著名的唐鑒和倭仁。前者向曾國藩開示“檢身之要,讀書之法”,教其以《朱子全書》為宗,從事義理之學等。此番受教對曾國藩大概有醍醐灌頂、茅塞頓開的作用,“聽之,昭然若發(fā)蒙也”[6]92。次年,他繼續(xù)行走在追求理學的道路上。 “拜倭艮峰前輩,先生言‘研幾’工夫最要緊……又教余寫日課,當即寫,不宜再因循”[6]113。理學家倭仁向曾國藩授以理學“研幾”獨家心得,強調“內省”,講求時刻對照朱熹等先賢確定的義理道德標準,檢查、審視主觀念頭和客觀行跡,且將之與修齊治平聯系起來。倭仁還要求曾氏以類似“狠斗私字一閃念”的方法寫心靈日記,并交其本人批改。此后數年內,曾國藩以虔誠心態(tài)、機械方法、嚴厲態(tài)度游于理學修身門徑。每日里將幾乎近于瑣碎的行為、近乎瞬間的念頭放在道德標準的探照燈、顯微鏡之下,以此來稽核道德。多半因初習理學修身之法,曾國藩道德稽核有時甚至到了荒唐、苛求的地步,此時期他的狀態(tài),要不就進退失據,要不就坐立不安,要不就患得患失。“其為日記,力求改過,多痛自刻責之語。”[7]47自此,曾國藩終身未輟體察反省、拷問道德的習慣。人生定位在此時也得到清晰確認,就是立志做圣賢。其“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圣外王之業(yè),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一語[8]34,顯示人生新坐標已定、大格局已展。
(三)曾國藩踐履道德反思
隨著曾國藩領導實踐的逐漸展開,其道德理性活動場景拓展到治事、治軍、求才等方面。要使領導活動順利推展,原來只適應處理個人內心關系的道德稽核逐漸被更多實踐面向和基于情境思考的道德反思取代。道德反思對道德稽核不是否定,而是包涵和覆蓋;從認識論而言,是在道德稽核基礎上不斷調較、豐富并修正道德理念、再指導實踐的運動過程,是整改落實,是再認識、再實踐,是既成就自己也成就他人;就發(fā)生學而論,是由道德知識、道德稽核、領導實踐、人生志向共同作用催生的一個過程。
放在長時段歷史文化視野里,與其他著名歷史人物相比,曾國藩道德反思呈現的特點在于經歷過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
1857年3月,曾國藩接到父親去世噩耗,未等朝廷指示發(fā)回,便將軍務交托他人,趕回家鄉(xiāng)奔喪。此后備受“守制”與“奪情”道德兩難的煎熬[9]。鄉(xiāng)居守禮歲月,村里面也發(fā)生過許多許多的事。這一年家鄉(xiāng)畫風是這樣的:他的大兒媳在黃金堂難產去世;大兒媳的母親也在此辭世。他的弟媳婦、曾國荃夫人正處懷孕期間,難免覺得宅子不潔,便請巫師上門“禳祓”。在家守制的曾國藩,本來情緒、身體均一直不佳,偶而有一次白天睡覺,正趕上巫師開展工作,便怒不可遏大發(fā)脾氣,大概是連巫師帶弟媳一同訓斥了。一同從江西回家守孝的曾國荃估計臉上掛不住,便從黃金堂遷居他處[10]。傷心事、糟心事如此之多,更迫使曾國藩不斷反思,特別聚焦在“我為什么會在領導過程中如此失敗”問題上。“每念數年在外,愆尤叢集。官事私事,不乏未了之局,死者生者,猶多愧負之言。”[11]592結論也有了。“余生平不講文飾,到處行不動,近來大悟前非。”[8]326備經煎熬的時期也是砥礪的時期,再次復出的曾國藩在道德反思上遂實現質變。其好友歐陽兆熊評論,曾國藩治術歷經“程朱”到“申韓”再到“黃老”的轉變,故“此次出山后,—以柔道行之,以至成此巨功”[12]。
此質變有二個體現,道德不斷升華和體系日臻完備。
道德升華,是道德認識和思考達到的層次和境界,是高度。1862年5月,曾國藩“靜中細思”,時間、空間、知識、世事相對于人生的有限來說是無限的,因此,“知天之長而吾所歷者短,則遇憂患橫逆之來,當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則遇榮利爭奪之境,當退讓以守其雌;知書籍之多而吾所見者寡,則不敢以一得自喜,而當思擇善而約守之;知事變之多而吾所辦之者少,則不敢以功名自矜,而當思舉賢而共圖之。夫如是則自私自滿之見,可漸漸蠲除矣。”[13]280當時的曾國藩領導情境,大端有:清廷以東南半壁與太平軍交戰(zhàn)的軍務盡委之于曾國藩,其弟曾國荃和曾國葆已是湘軍重要將領并將進軍金陵城下,其部下、同鄉(xiāng)左宗棠領一支湘軍進攻浙江,淮軍已成并由其部下兼年家子李鴻章率至上海,以兩江總督身份開始與西方諸強交涉事務,一紙奏折可以決定軍務省份封疆大員去留榮辱,要為直接和間接指揮的數十萬軍隊籌糧、籌餉、籌戰(zhàn)爭物資。反思的重點是什么呢?道德方面,自身堅持用堅韌、退讓、謙虛、舉賢來克服品德缺陷、成就更高的道德。
1863年3月,“在轎中,思古圣人之道莫大乎與人為善。以言誨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熏人,是以善養(yǎng)人也;此與人為善之事也。然徒與人則我之善有限,故又貴取諸人以為善。……巨寇方張,大難莫平,惟有就吾之所見多教數人,因取人之所長還攻吾短,或者鼓蕩斯世之善機,因以挽回天地之生機乎!”[13]389直接在道德和領導中踱步思量,將領悟出的圣人之道與事功相聯,大體展示出其道德反思已走向對標圣賢、追尋圣境之路。
道德體系日臻完備,指的是道德認識和思考的整體性和系統(tǒng)性,是深度。曾國藩曾先后提出“八德”體系,先是“勤儉剛明孝信謙渾”[14];后改成“勤儉剛明忠恕謙渾”,指出此為人生八種品德,前四者對己,后四者對人[15]415。還在不同場合對“八德”內容予以闡釋,并以“八德”當做行動指南。
道德認知對應道德有無,道德稽核對應道德對錯,道德反思對應道德損益。還原到具體生活場景中,肯定不是由此及彼的線形過程,但在抽象層次上,則體現為思維和實踐的辯證運動過程,首先是對知識化道德的肯定,然后是主觀見之于客觀過程中對道德知識和價值觀念的稽核、批判和否定,在此基礎上道德理念更加理性化了,然后再施諸于客觀活動,這時候已經是否定之否定了。“在經過了形而上學思維之后,人類對經驗現實的回歸絕對不是簡單地回到‘原點’而是帶著批判性的回歸”[16]。
二、個人道德記憶與家庭道德記憶的合一
在倫理學看來,“家”和“家庭”都是倫理實體,各自承載著倫理精神。前者折射的主要是人與物的倫理關系,倫理意義在于它的工具價值,即在提供生存空間的同時提供人之所以為人應有的安全感、尊嚴感和高貴感,倫理精神是“愛物”。后者反映的主要是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系,倫理意義在于家庭成員之間的和諧,并由此生發(fā)人類社會其他倫理價值,倫理精神是“愛親人”[17]。家和家庭的持續(xù)發(fā)展是人類不言而喻的價值。家庭倫理建構之后,家庭道德也相應產生。隨著家庭倫理和道德的發(fā)展,精神文化形態(tài)的家訓家風也發(fā)展起來。家庭倫理道德是家訓家風的價值基礎和生成空間,家訓家風是家庭倫理道德的表達方式和體現形式。就社會一般性而言,家訓家風一旦形成,就會成為一種文化傳統(tǒng)和精神,進行歷史傳承。就家庭特殊性而言,那些為家庭興旺、家遠綿長奮斗的人們,會將家訓家風當作精神財富進行歷史傳遞。家訓家風就是家庭道德記憶的具象存在形式,其實質是可以在家庭里傳播和傳承的家庭道德記憶。按倫理學,道德記憶是人類記憶活動的一種重要表現形式,是人類道德生活經歷在其腦海中留下的印記或印象;主要包括道德風俗和習慣、道德原則和規(guī)范、道德思想和精神、道德實踐和行為等。個體道德記憶是關于個人道德生活經歷的記憶,家庭道德記憶是關于家庭道德生活經歷的記憶[18]。
曾國藩的家訓家風一向為后人稱道。隨著曾國藩科舉的成功,特別是后期創(chuàng)建湘軍、恢復東南社會秩序、主導自強運動等領導活動的展開,曾國藩對家訓家風家運日益重視,主要是在其創(chuàng)造和努力下,曾氏家族成員也參與進來,共同維系和推動曾氏家訓家風,從而體現為個人道德記憶和集體道德記憶密切互動的運動過程,其中曾國藩個人道德記憶是主要的決定方面。從領導力就是影響力角度說,曾國藩營造家風,實質上是以個人道德記憶去建構家庭道德記憶,也是一種領導活動。
(一)曾國藩勾勒先輩家風,回溯早期家庭道德記憶
先人們的家庭道德生活深刻地影響著曾國藩。曾國藩先祖輩務農為生,他們并沒有形成體系化的家訓家規(guī),但并不意味沒有道德生活。其先輩,特別是其祖父治家實踐對曾國藩個人道德記憶影響很大。“(我家)累世力農,至我王考星岡府君(祖父)乃大以不學為恥,講求禮制,賓接文士。……其責府君(父)也尤峻……府君則起敬起孝,屏氣負墻,踧踖徐進,愉色如初”[19]。這已是曾國藩晚年的記述,依然側重敘寫先輩生活的道德意蘊,可知對曾國藩道德刻寫之作用深遠。曾國藩道德領導行為上也有先輩留下的印跡,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曾國藩晚年曾與密友交談稱:家里向來貧窮,在祖父操持下才有勉強能維持生計的微薄產業(yè);即使中翰林做京官后,祖父仍然告訴父親,家中照舊生活,不要他資助家中財物,所以“吾聞訊感動,誓守清素,以迄于今,皆服此一言也”[20]1107。
曾國藩也注重將對先輩的記憶向家庭成員傳遞。如關于祖父的道德教誨,他向弟弟們回憶:他至今都記得,進京為官前請祖父訓話,祖父教育他不要驕傲;如今,弟弟們也要遵守祖父昔日教誨[8]256。關于母親,他也多從品格特征處回憶,“吾兄弟皆稟母德居多,其好處亦正在倔強”[15]115。
曾國藩總結提煉早期家庭道德生活。曾家先人的道德生活是自在自為狀態(tài)的,但還不是一種理論自覺。將先輩們分散的有道德意含的語言和行為提煉成體系的工作是由曾國藩完成的。曾國藩祖父對整個曾氏家族貢獻比較大,曾國藩對家庭早期道德生活的思考就聚焦在祖父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上,提煉成“八寶三不信”家規(guī)體系。“吾祖星岡公之教人,則有八字,三不信。八者曰:考、寶、早、掃、書、蔬、魚、豬。三者,曰僧巫,曰地仙,曰醫(yī)藥,皆不信也”[8]594。祖父的風范影響如此之深,以至于他對自己的概括仍覺得不完善,后來還提出升級版“八好六惱”。“吾家代代皆有世德明訓,惟星岡公之教尤應謹守牢記。吾近將星岡公之家規(guī)編成八句,云:‘書、蔬、魚、豬、考、早、掃、寶,常說常行,八者都好;地、命、醫(yī)理、僧巫、祈禱、留客久住,六者俱惱。’……此八好六惱,我家世世守之,永為家訓,子孫雖愚,亦必略有范圍也”[15]468。
(二)曾國藩營造家風,建構家庭道德記憶
2012版《曾國藩全集》收錄曾國藩于1840年入京為官至1871年所寫共1485封家書。在主要寫給弟、子的信中,關于治家、興家、做事、做人的思考和要求隨處可見。曾國藩領導過程與治家過程相始終,其特點在于理論自覺和實踐自覺,即注重從理論層次探討家庭道德記憶,豐富家風思想內涵;個人以身作則,注重提出切實可行的、有針對性的推進舉措,并有嚴格的過程管理和績效考核。
他重點幫扶對象是四個弟弟中的四弟國潢和九弟國荃,因為另外兩個弟弟均過早在戰(zhàn)場去世。除了平常書信交流反復叮囑為人治家之道,兄弟見面時也會深度探討家庭道德記憶內涵。在軍務倥傯之際,仍“夜與沅弟(曾國荃)論為人之道有四知,天道有三惡。三惡之目曰天道惡巧,天道惡盈,天道惡貳。貳者,多猜忌也,不忠誠也,無恒心也。四知之目,即《論語》末章之‘知命’、‘知禮’、‘知言’,而吾更加以‘知仁’。……愿與沅弟共勉。沅弟亦深領此言。謂欲培植家遠,須從此七者致力也”[6]435。1868年,曾國潢千里迢迢從鄉(xiāng)間趕至金陵,兄弟十年未見,既享喜悅之情,更多深度交談。“酉初與澄弟(曾國潢)談,直至二更三點,說話極多,疲甚。中講《孟子》中也養(yǎng)不中一章,弟深能領會,殊有和樂且湛之趣。”[21]102行將北上任直隸總督之際,曾國藩懷著未知今生能否再相見的傷感,提筆對四弟作近千字臨別贈言,勸其保持“清、儉、明、慎、恕、靜”[19]472-474。盡管數日前還“聞有狎邪之游,心實憂之。老年昆弟,不欲遽責之”[21]104。
全面管理對象則是自己的兩子五女,其中重點是兒子。比之現代父母,曾國藩也不遑多讓,動輒以“別人家的孩子如何如何”進行對比式教育。長子曾紀澤第一次婚姻娶曾任云貴總督的賀長齡之女。曾國藩信中稱:你看陳伯伯家兒子多優(yōu)秀,可你卻貪圖安逸;正值你成家的時候,全家要努力做到以下幾點:“新婦初來,宜教之入廚作羹,勤于紡織,不宜因其為富貴子女不事操作。大、二、三諸女,已能做大鞋否?三姑一嫂,每年做鞋一雙寄余,各表孝敬之忱,各爭針黹之工;所織之布,做成衣襪寄來,余亦得察閨門以內之勤惰也。”[8]291另外,“爾每次安稟,詳陳一切,不可草率,祖父大人之起居,合家之瑣事,學堂之功課,均須詳載,切切此諭。”[8]291數年后,賀氏去世,曾紀澤第二次婚姻娶后來曾任陜西巡撫的劉蓉之女。曾國藩為其梳理家庭道德記憶,“我家高曾祖考相傳早起,吾得見竟希公、星岡公皆未明即起……吾父竹亭公亦甫黎明即起…余近亦黎明即起,思有以紹先人之家風。”因此,“爾即冠授室,當以早起為第一先務。自力行之,亦率新婦力行之。”“余生平坐無恒之弊……用為內恥。……星岡公儀表絕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頗重厚,蓋取法于星岡公。爾之容止甚輕,是一大弊病……早起也,有恒也,重也,三者皆爾最要之務。早起是先人之家法,無恒是吾身之大恥,不重是爾身之短處”[8]453-454。這封長信中從曾家祖輩一路說下來,著重指明祖先的道德生活及對自己的影響,再闡明父子各自的優(yōu)缺點,明確曾紀澤成立新家庭后的努力方向。不啻是家庭道德記憶的路線圖。
(三)曾氏家族共鑄家庭道德記憶、維系家風
僅有曾國藩個人的努力,道德記憶只能在個人框架內生長。經過曾國藩經歷累月不懈努力,曾氏族人或主動、或被動也致力于營造家風,鑄成家庭道德記憶。兄弟和衷共濟、妯娌相互關心、晚輩抵足而眠的畫面屢見曾氏家人筆端。
家庭道德記憶要靠族中人共同參與,但不是所有人對家風的理解、參與的態(tài)度、所起的作用都是相同的。其中以曾國荃變化最為典型。曾國荃在41歲時就已任浙江巡撫,統(tǒng)領五萬湘軍奪取太平天國都城金陵。正躊躇滿志之時,曾國藩勸其激流勇退。曾國荃雖長期受曾國藩的教誨熏陶,但對他“花未全開月未圓”“上場當念下場時”之類對立統(tǒng)一的哲學和盈科后進的智慧并不能完全理解和接受,對其兄建議更嘖有煩言。“三年秋,吾進此城行署之日,舍弟甫解浙撫任,不平見之辭色。時會者盈庭,吾直無地置面目”[20]1110。經過回鄉(xiāng)年月的積淀、思考,國荃再出任湖北巡撫,但在領導實踐過程中卻連遭重大挫敗。曾國藩為幫助其弟度過難關,提升道德韌勁,遂將自己專屬的個人道德記憶拿出來分享,說起生平遭逢的“四塹”:科考時曾被掛牌批評,做京官時被眾多高官排斥,初領湘軍時被湖南官場排擠,在江西征戰(zhàn)時被官紳嘲弄戲弄。“吃此四塹,無地自容。故近雖忝竊大名,而不敢自詡為有本領,不敢自以為是。俯畏人言,仰畏天命,皆從磨煉后得來。……弟力守悔字硬字兩訣,以求挽回……”[15]488。曾國荃逐漸感悟到其兄促進家庭道德記憶的見識高遠,向其兄表示,“(以前)以為(自己)本領甚足,今乃知全是運氣,毫無本事。……又以一家而論,亦已近炎炎之勢,趁此時弟尚可稍冷一步,冀以久延世澤”[22]。日后,曾國荃從負有饕餮之名,真正進入到與其兄共同維系家風、構筑家庭道德記憶之中。
曾國藩的子女是其刻寫道德記憶的主要對象,自然是恪守家訓、延續(xù)家風的主力軍,傳承家庭道德記憶的主體。他們也用行為證明了這一點。曾國藩對兒子曾如此期待,“余生平有三恥:學問各涂,皆略涉其涯矣,獨天文、算學,毫無所知,雖恒星五緯亦不識認,一恥也;每作一事,治一業(yè),輒有始無終,二恥也;少時作字,不能臨摹一家之體,遂致屢變而無所成,鈍而不適于用,近歲在軍,因作字太鈍,廢閣殊多,三恥也。爾若為克家之子,當思雪此三恥”[8]373。前文也提到,曾國藩對曾紀澤有“早起、有恒、持重”的要求。后來長子曾紀澤成長為晚清外交家,憑借持重、穩(wěn)慎、周密的特點,與西方諸強周旋,并爭回部分領土權益。次子曾紀鴻投身數學且有精深造詣。當可視作是對曾國藩教誨與期許的恪守和實現,對家族道德記憶的參與。
曾氏后人身處繁華,仍舊躬行勤儉謙慎的道德生活。多年后,曾國藩五女曾紀芬回憶起曾家兒女當年在兩江總督府,按照父親所定作息時間表和課程表,一起生活的情景,曾家后人共同促成家庭道德記憶的畫面躍然而出。
早飯后 做小菜點心酒醬之類 食事
己午刻 紡花或績麻 衣事
中飯后 做針黹刺繡之類 細工
酉刻(過二更后) 做男鞋女鞋或縫衣 粗工
吾家男子于看讀寫作四字缺一不可,婦女于衣食粗細四字缺一不可。吾已教訓數年,總未做出一定規(guī)矩。自后每日立定功課,吾親自驗功。食事則每日驗一次,衣事則三日驗一次,紡者驗線子,績者驗鵝蛋,細工則五日驗一次,粗工則每月驗一次。每月須做成男鞋一雙,女鞋不驗。
上右驗功課單諭兒婦、侄婦、滿女知之,甥婦到日亦照此遵行。[8]107
曾國藩后來還在此單后添上四句話。“家勤則興,人勤則健;能勤能儉,永不貧賤。”[21]60就像為家庭道德記憶篆刻一枚印章。
三、道德軟性約束與道德硬性約束的合一
曾國藩領導實踐過程中,有一個總的指導原則,“帶勇之法: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禮。”[6]442按其領導經歷,“帶勇”不僅指率領湘軍士兵,也當指與人打交道、帶隊伍、培育人才等。“仁”及“禮”都是儒家核心道德理念,“用恩”及“用威”意指領導方法上的柔性和剛性。基于道德具有規(guī)范人行為的性質及功能,“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禮”即是道德的軟約束和硬約束。硬性約束是對軟性約束的保障和補充,是“高壓線”;軟性約束是硬性約束的道義屏障和精神牽引,是“沖刺線”。沒有硬性約束,軟性約束就可能流于“義理”之學的空談和玄學的“鑿空”;沒有軟性約束,硬性約束就可能墜向法家的酷烈。在曾國藩的領導實踐中,這二者也是合一的。
(一)道德軟性約束
“用恩莫如仁”意味著“仁”是“用恩”的主要途徑方法,即稱“恩”就主要是教誨、激勵、給與等隱性和柔性手段來引導人的行為,道德軟性約束即由此生發(fā)。
“仁”字一詞,在曾國藩語境里,當指自己的道德發(fā)展與別人的道德發(fā)展、自己的事業(yè)發(fā)展與別人的事業(yè)發(fā)展相互促進的問題。其核心要義是“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外在特征是“恕”[6]442。 “求仁”極其重要,既與儒家宇宙觀、本體論相聯,又是儒家“成已”“成物”“成人”的根本路徑。曾國藩晚年作“日課四條”專論“求仁則人悅”。“我與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愛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孔門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數語。……必如此,乃可謂之人,不如此,則曰悖德,曰賊。”[15]546-548“用恩求仁”理念下,是家庭關系、家庭結構向人際關系、組織結構的延伸和復制,家長就是軍官、長官、師長,子弟就是士兵、員工、學生,領導的追隨者就是子弟學生。如此則每一層級的領導者都負有讓追隨者獲得發(fā)展的義務。
曾國藩用“仁”突出體現之一,是對撫恤、封典賞賜和保舉等事務極為重視和謹慎,盡量做到公平。
撫恤是對傷者、逝者的補償和慰藉,封典賞賜是封建君主給予的榮譽,保舉則是請求君主予以官銜和官職。其實質是兌現“仁”。湘軍每野戰(zhàn)勝,或奪回城市,幾乎必定即刻奏請保舉、請求撫恤、申請封賞[23]。曾國藩曾思考過保舉的人數比例問題,稱“各營請獎,此間批定之案,每百人中,多者準保十四人遞減至八人不等,然終嫌其太濫。……近年每百人保二十人者,幾成常套。弟去年思挽回一二,批定極多不準過十四人。”[24]必定保舉,是為了讓沖鋒陷陣的將士得到回報,是體現“仁”。確定額度,是為了讓“仁”的物質化和精神化顯得稀缺而有價值。即刻奏請,是彰顯領導者對在一線辛勞的重視;拖沓意味著對基層工作的輕視。必定、即刻和限額,在曾國藩處也就有了倫理意味。
曾國藩用“仁”突出體現之二,是不斷在領導活動中對部下進行道德灌輸和熏陶。
為什么要灌輸道德?曾國藩治軍之初,官民矛盾、軍民矛盾早已非常尖銳。在此領導情境下,“誓欲練成一旅,秋毫無犯,以挽民心而塞民口。每逢三八操演,集諸勇而教之,反復開說至千百語,但令其無擾百姓。……雖不敢云說法點頑石之頭,亦誠欲以苦口滴杜鵑之血。……國藩之為此,蓋欲感動一二,冀其不擾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賊匪之恥,而稍變武弁漫無紀律之態(tài)。”[11]200
無論是指揮湘軍、領導淮軍,還是總督兩江,曾國藩總把與部下談心談話、書信交流、批閱稟件當作主要的領導方法。其內容除了部署工作、學術切磋外,更多的是道德上的勉勵勸誡。其日記、批牘、作品包括他人的回憶,盡多如此之語,茲舉代表性數例。
1861年,湘軍攻下一直在太平軍掌握之中的安徽省城安慶,任兩江總督一年多的曾國藩總算有了穩(wěn)定且相對安全的辦公場所。駐節(jié)安慶伊始,曾國藩即定章程:地方官員,要做到治署內以端本、明刑法以清訟、重農事以厚生、崇儉樸以養(yǎng)廉;軍隊官員,要做到禁騷擾以安民、戒煙賭以儆惰、勤訓練以御寇、尚廉儉以服從;辦事人員,要做到習勤勞以盡職、崇儉約以養(yǎng)廉、勤學問以廣才、戒傲惰以正俗;地方士紳,要做到保愚懦以庇鄉(xiāng)、崇廉讓以奉公、禁大言以務實、擴才識以待用[19]444-449。對于領導過程中主要涉及的各類官員,提出分門別類的要求,這些要求包含的主要是品德、作風因素。1864年,湘軍攻占金陵,曾國藩駐進兩江總督官署,即作官箴,并懸掛于駐節(jié)地。“雖賢哲難免過差,愿諸君讜論忠言,常攻吾短;凡堂屬略同師弟,使僚友行修名立,乃盡我心”[19]100。1869年任直隸總督后,再對同僚作道德勸勉。“長吏多從耕田鑿井而來,視民事須如家事;吾曹同講補過盡忠之道,凜心箴即是官箴”[19]102。從事科舉時受過的排偶詩賦訓練也有了用武之地。
(二)道德硬性約束
“用威莫如禮”意味著“禮”是“用威”的主要途徑方法。即稱“威”就要有暴力、懲戒等做后盾制約人的行為,是一種硬性約束。
曾國藩曾論述何謂“禮”“古之君子……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則一秉乎禮。自內焉者言之,舍禮無所謂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禮無所謂政事”[19]410。“禮者,即所謂無眾寡,無大小,無敢慢,泰而不驕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6]442。一般而論,曾國藩認為“禮”有兩層內涵,“道 ”層次上的道德精神和“器”層次上的制度理性。在曾國藩開展領導實踐角度上,“禮”是具有“辨等明威”功能的規(guī)矩、禮儀、規(guī)范等實體性制度,故是一種“禮”制,其有若干特征。
其一,道德標準和要求融入選人用人機制。
對于士兵,“募格,須擇技藝嫻熟、年輕力壯、樸實而有農夫土氣者為上。其油頭滑面,有市井氣者,有衙門氣者,概不收用。”[19]406對于軍官,曾國藩也有品格要求。“將領之浮滑者,一遇危險之際,其神情之飛動,足以搖惑軍心;其言語之圓滑,足以淆亂是非,故楚軍歷不喜用善說話之將”[25]。 “帶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大抵有忠義血性,則四者相從以俱至;無忠義血性,則貌似四者,終不可恃。”[11]215-216湘軍早期名將羅澤南就是在這種選人機制中脫穎而出的。其“以宋儒之理學治兵,以兵衛(wèi)民,皎然不欺其志”[26]。
其二,道德價值意蘊貫穿指揮運轉機制。
選士兵和軍官解決的是選什么人的問題,還要解決怎么選、怎么組織的問題。“營官由統(tǒng)領挑選,哨弁由營官挑選,什長由哨弁挑選,勇丁由什長挑選。……是以口糧雖出自公款,而勇丁感營官挑選之恩,皆若受其私惠”[27]。此外還有取保制度、軍餉發(fā)放制度、后勤保障制度等。有逐級挑選,指揮命令可以一以貫之;有“口糧”發(fā)放,就有凝聚和服從。再加以另外一條特別緊要的規(guī)定:如統(tǒng)帶營官傷亡,或士兵潰逃過多,則取消番號。幾者相合,組織內成員甚至組織間的情義也產生了。這也是湘軍“敗必相救”的倫理底色。
其三,包涵道德內容的訓練機制。人員選好,架構搭好,還要解決能不能打、能不能長期打贏的問題。訓練機制是湘軍戰(zhàn)斗力的獨到之處。曾國藩創(chuàng)湘軍之初就重視訓練。合成建制后必須訓練數月方能上戰(zhàn)場成為湘軍成例。獨到之處體現在“訓”有倫理道德指向。 “訓有二端:一曰訓營規(guī),二曰訓家規(guī)。……點名、演操、巡更、放哨,此營官教兵勇之營規(guī)也;禁嫖賭、戒游惰、慎語言、敬尊長,此父兄教子弟之家規(guī)也。為營官者,待兵勇如子弟,使人人學好,個個成名,則眾勇感之矣”[19]446。家庭成員間的道德義務和關系模式幾乎原樣復制到組織中,并且更制度化了,從而約束性也更強。
民國年代,曾國藩外孫聶云臺發(fā)出如許感慨:相比之下,后世湘軍名門家運要好過淮軍名門,重視讀書的軍功世家子弟要比只知積聚財富的軍功世家子弟優(yōu)秀,“當時不肯發(fā)財,不為子孫積錢的幾家,他們的子孫反而卻多優(yōu)秀。最顯明的,是曾文正公”[28]。曾國藩構建家庭道德記憶、孜孜不倦用道德教誨湘軍將士,多年后在湘軍、淮軍各名門家族命運盛衰比較中顯出了效果。
曾國藩道德領導有其歷史局限性,不能脫離其身處的“歷史世界”而拔高其“思維世界”。在倫理學理論視野下,曾國藩道德之領導和領導之道德有著求“真”求“善”的因素,更包括對傳統(tǒng)文化精神的汲取,因而也有價值合理性。基于此,上述諸論在以下方面給現代人以啟示:沒有道德和倫理的領導實踐,是道德虛無主義;不顧實踐和沒有立場的道德,是唯道德論和道德至上主義;動輒強調領導情境決定領導行為,是道德機會主義;不在現實世界和實踐中尋求解決問題答案、一味向歷史回歸是道德復古主義和封閉主義;離開家庭家風而談道德領導,是道德空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