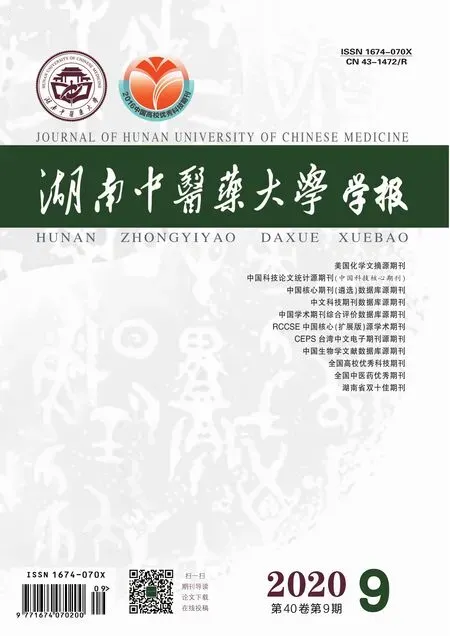針刺與艾灸療法的共性分析
歐陽里知,胡舒寧,劉 密,劉邁蘭,鐘 歡,常小榮*,謝 輝*
(1.湖南中醫藥大學,湖南 長沙410208;2.瀏陽市中醫醫院,湖南 瀏陽410300;3.郴州市第一人民醫院西院,湖南 郴州423000)
針法和灸法是在中醫理論指導下,用于防治疾病的兩種外治方法,常并稱為針灸。歷經沿襲發展,現代臨床的針法以毫針刺法為主,灸法則以艾灸為主。毫針刺法(以下簡稱針刺)是將毫針刺入腧穴,通過針刺補瀉手法,激發經氣,達到防治疾病的目的;而艾灸則通過將艾草制成的艾絨或艾炷在體表腧穴燒灼、熏熨,結合艾灸手法,以溫熱(艾草藥理作用)刺激經絡,達到防治疾病的目的。進行針刺和艾灸療法的共性研究,從中發掘普遍規律,對于針灸臨床應用具有指導意義。
1 同以體表刺激為特點
《素問·湯液醪醴論》曰:“當今之世,必齊毒藥攻其中,鑱石、針艾治其外也。”針刺的器具材質從砭石到各類材質,再到金屬針(不銹鋼針),常用種類從九針到毫針為主;灸療從熱石燙熨到燃材灸熨,再到艾葉灸治,都經歷了以實用、療效為核心的變化發展過程。 雖然針刺和艾灸的器具、施術手法存在差異,但是兩者都以體表刺激為特點,作用于腧穴、經絡,不存在由外向內的物質輸送,有異于中藥方劑、西醫藥劑的外源性物質輸入。針刺與艾灸對機體的體表刺激,同以造成局部刺激為特點,針刺以針具刺入穴位,產生皮膚、肌肉刺激為特點;艾灸法以艾火熏灼腧穴,對皮膚、肌肉產生熱力、艾草藥理作用,其中直接灸以產生皮膚、肌肉化膿、形成灸瘡為特點;針刺和艾灸形成的局部刺激都通過作用于腧穴、經絡,達到調節機體、防治疾病的療效。而腧穴既反應病候又接受刺激的診治特點為針刺與艾灸防治疾病提供了共同作用載體,是兩者同以體表刺激為特點的基礎。
2 同以病理狀態為條件
中醫診治疾病注重三因制宜——因人、因地、因時。其中因人制宜尤其注重患者的體質,而正邪盛虛能一定程度上表現于患者所處的病理狀態;相同的療法,對于不同的病理狀態會呈現療效差異,古籍中關于針刺和艾灸療法的運用,有不少強調根據病理狀態而施術,針刺和艾灸的效應產生都以病理狀態為條件。《難經·七十難》對于《黃帝內經》中“春夏刺淺、秋冬刺深”的論述進行了深入解釋:“春夏者,陽氣在上,人氣變在上,故當淺取之;秋冬者,陽氣在下,人氣變在下,故當深取之。”不僅體現人體與自然界四季相通應的天人觀,還強調人體生理病理狀態的差異對針刺深淺的影響,揭示以病理狀態為條件的療法施用原則。
《素問·繆刺論》闡述巨刺與繆刺之別時,記載:“夫邪客大絡者,左注右,右注左,上下左右與經相干,而布于四末,其氣無常處,不入于經俞,命曰繆刺……邪客于經,左盛則右病,右盛則左病,亦有移易者,左痛未已而右脈先病,如此者,必巨刺之,必中其經,非絡脈也。故絡病者,其痛與經脈繆處,故命曰繆刺。”歧伯解釋了兩者雖然都是左病治右、 右病治左,卻是根據兩類人群不同的病理狀態而施針——病在經,針用巨刺;病在絡,針用繆刺。
在針刺和艾灸過程中,患者病理狀態的轉變還可影響后續療效,故而受到歷代醫家的重視,其中“氣至而有效”理論較好地反應了病理狀態下,患者對針灸治療的生理反饋,也成為針灸療效的預判標準之一。《衛生寶鑒·卷二·灸之不發》曰:“用針者,氣不至而不效,灸之亦不發,大抵本氣空虛,不能作膿,失其所養故也,更加不慎,邪氣加之,病必不退。”《針灸大成·標幽賦》也指出:“氣速至而速效,氣遲至而不治。”針灸治療過程中強調“氣至”包含了患者和醫生雙方的狀態,就患者而言,“氣至”的反饋體現了針灸治療過程中機體病理狀態的調整征兆。
《針灸問對》則詳細闡述了不同病理狀態下灸法的作用:“虛者灸之使火氣以助元氣也;實者灸之使實邪隨火氣而發散也;寒者灸之使其氣復溫也;熱者灸之引郁熱外發。”有寒熱虛實病理改變時,灸法起到對癥(證)治療的效果,若正常之人,灸療可能就難見上述針對性功用;這與方劑運用中有是證、用是藥,以病理狀態為條件相似。也可以說是,當實證已具備瀉的條件和要求,虛證有待補的措施與作用,針和灸的刺激作用于身體的病理狀態,自可順水行舟,因勢利導,產生機體的自我調節功能;反之,不虛不實的平人,施以針灸通常不會出現特異性的改變。
3 同以明證審穴為指導
辨證論治是中醫認識和治療疾病的基本原則,在疾病的診治過程中,中醫通過四診合參辨析疾病的病因病機、病理階段,有的放矢地針對性治療。清代吳亦鼎的《神灸經綸》指出“癥不明則無以知其病之在陽在陰,穴不審則多有誤于傷氣傷血”;李學川在《針灸逢源》中也主張“因證以考穴,按穴以施治”。這些記載都體現了古代醫者在運用針刺和艾灸療法時謹慎辨證、審慎用穴[1]的思辨。竇漢卿所著《針經指南·標幽賦》云:“察歲時于天道,定形氣于余心”“大患危疾,色脈不順而莫針;寒熱風陰,饑飽醉勞而切忌。 望不補而晦不瀉,弦不奪而朔不濟;精其心而窮其法,無灸艾而壞其皮;正其理而求其源,免投針而失其位。”通過指出禁用針刺和艾灸的特殊癥狀(證候)[2],側面指出需在明確癥狀(證候)后方能施用針刺或灸法,避免施用不當造成不良后果。 《史記》關于針灸的記載:“當論俞所居,及氣當上下出入,邪正逆順,以宜镵石,定砭灸處”,強調了審穴后施用針刺和艾灸[3]。
明代楊繼洲強調針灸藥并用[4]。 《針灸大成·諸家得失策》中記載:“疾在腸胃,非藥餌不能以濟;在血脈,非針刺不能以及;在腠理,非熨焫不能以達,是針灸藥者,醫家之不可缺一者也。”指出針刺和艾灸雖然是外治法,也必須以明確疾病(證)為施治前提。 《針灸逢源·卷五·癰疽門》在治療瘡瘍時也強調明證審穴方能指導針刺或艾灸的具體操作:“凡瘡瘍可灸刺者,須分經絡部分、血氣多少、俞穴遠近,或刺或灸,泄其邪氣……。”
中醫藥辨證論治的關鍵在于辨明疾病所處的證候階段,針對疾病的病因和本質施以對應療法,在方劑的運用中,可以出現同一種疾病由于所處疾病階段(證候)的差異而選取不同的方藥,即“同病異治”,而有時不同的兩種疾病由于所處疾病階段相同而選取同樣的方藥,即“異病同治”;在施以針刺和艾灸治療時,除了治療手法的辨證使用,由于腧穴既能反應病候,又能反饋刺激、調治疾病(即腧穴具備的診治雙重性)的特性,往往還需審慎取穴,也正是針刺與艾灸同以明證審穴為指導的根本原因所在。此外,針刺和艾灸治病,區別于方劑湯藥等其他中醫藥治法,還強調“治神”,需“氣至病所”,實際上是對兩者治療定向性的強調,正是追求這種定向反應,使針刺與艾灸起到防治疾病的作用,兩者緊密聯系,常并稱“針灸”。
4 同以標本兼顧為原則
針刺和艾灸都以中醫理論為基礎,在辨證明確的前提下,遵循標本兼治的原則,以中醫整體觀為基石而防治疾病。例如,《針灸逢源》沿用了《黃帝內經》治療瘧疾“瘧脈小實急,灸脛少陰,刺諸井”的方法,并進一步闡釋“脈小實急,陰邪勝也。陰勝者生內寒,故當灸足少陰復溜以散寒,又刺足太陽至陰以補陽也”。 針對陰盛而寒的病機,既散寒祛邪治標,又補陽氣以治本,標本兼顧。中醫治病,有“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的權宜之策,又有“治病求本,標本兼顧”的全局之策,誠如《素問·標本病傳論》所言:“有其在標而求之于標,有其在本而求之于本,有其在本而求之于標,有其在標而求之于本”。 針刺與艾灸作為中醫防治疾病的重要外治療法,古籍中關于兩者的運用都體現了古代醫家標本兼顧的學術思想。
中醫的標本學說對于病和癥的闡述,以疾病為本,癥候為標,病是本質,癥為現象。醫家在診治疾病時,既有對癥下藥,又有分析病因、探尋病之本質再處方,往往可獲成效。對癥下藥的癥狀緩解,卻由于病本未消,容易復發;析因尋本地治療疾病,但癥狀的消除需時間的積累。由此觀之,治標與治本同樣重要,都是診治的最終目的,所以治癥和治病不可偏廢。方劑湯藥強調各藥物的四氣五味特性及相互配伍,達到標本兼治目的。針刺和艾灸治病具備雙相性特點,具體表現在主穴與配穴的選取。例如肝陽上亢頭痛劇烈,取太陽、風池止痛是治標(有其在標而求之于標),取肝俞以疏肝,陽陵泉、絕骨以下氣是治本(其在本而求之于本)。這種標本兼顧的思想體系,是針刺和艾灸的共同原則,也是針與灸互相聯系的主要基礎。
5 同以攻補兼施為手段
雖然沒有中藥方劑君臣佐使的配伍運用,針刺和艾灸有辨病選穴、辨經選穴,兩者操作各有多種手法,且分補瀉,以補正氣、攻邪氣。《針經指南》云:“虛羸氣弱癢麻者補之、豐肥堅硬疼痛者瀉之。”《太平圣惠方·針經序》記載了針刺補瀉手法的要點:“虛者徐而疾,實者疾而徐。 徐即是瀉,疾即是補。補瀉之法,一依此也。”《靈樞·背腧》則記載了艾灸補瀉[5]的具體操作細節:“氣盛則瀉之,虛則補之。以火補者,毋吹其火,須自滅也;以火瀉者,疾吹其火,傳其艾,須其火滅也。”《標幽賦》則是將“春夏刺淺、秋冬刺深、呼吸補瀉、手指補瀉”等針刺補瀉手法進行了綜合運用[6]。
《素問·氣穴論》將孔穴(腧穴)的作用描述為“以溢奇邪,以行營衛”。 溢奇邪就是宣泄病理產物,通營衛就是發揮生理機能。人體各經穴本身,就具備扶正祛邪的雙重作用,針刺與艾灸同屬作用于經絡腧穴的療法,在選穴處方都遵循對正氣的扶助和對邪氣的驅逐,因此,針與灸都是一種攻補兼行,祛邪與扶正并存的治療方法。
6 同以疏通經脈為根本
經絡腧穴理論認為:人體是由直行的經脈與橫行的絡脈網羅交織的經絡系統,溝通體表與內臟,聯系四肢百骸而形成的有機整體。人體正是有經絡體系的存在,維持各器官組織間的聯系,不論是人體生理機能的發揮,還是病理變化的出現,都與經絡息息相關。 《素問·調經論》言:“五藏之道皆出于經隧,以行血氣,血氣不和,百病乃變化而生,是故守經隧焉。”其中經隧即指經絡,指出了疏通經脈為疾病治療的根本。 《靈樞·經別》形容經脈是“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對經脈作用進行了高度概括。
針刺與艾灸治療作用的產生,不論是古人所說的“氣至病所”,還是今人所重視的感傳作用,都是通過經脈作用實現的;而經氣流行的循經現象,正是經脈得以疏通的表現形式,經脈通暢,血氣暢行,陰陽平衡,生理機能可充分發揮,病理狀態也能得以調整。清·吳亦鼎提出:“氣流通即是補,非必以參芪為補也。同此,氣流通即是瀉,非必以硝黃為瀉也。”所以針刺與艾灸同以疏通經脈為根本,發揮生理機能和調治病理狀態,達到防治疾病目的。
7 同以調和氣血為關鍵
氣血是中醫陰陽學說的具象之一,不同語境下,氣血的含義有所差異。氣血可合稱代表行于脈內的物質,此時氣與血是一體的,脈為氣血之府,氣血為脈之用,《黃帝內經》以氣血的功用含義指代脈。 氣血又可各自獨立,稱為氣和血,其中“氣”代表周身之正氣,包括了元氣、衛氣、宗氣、營氣等,“血”代表榮養周身之血,即營血(榮血)。 病理學研究表明[7]:各種疾病的發生,都是由組織/器官的基本病理改變引起的,這些病理改變包括了代謝、機能和形態結構的改變。其中,代謝和機能的改變對應中醫氣的功能性改變,且與中醫的情志相關,而形態結構的改變表明組織、器官的血液流通和供應隨之改變,對應中醫血的功能性改變。因此,《素問·調經論》云:“氣血不和,百病乃變化而生。”《千金翼方》云:“凡病皆因氣血壅滯,不得宣通。 ”
針刺和艾灸的治療作用,同以調和氣血為關鍵,表現為針與灸不僅激發經氣,調節機體,還可治神調神,調節情志,身心同治則氣血和暢,疾病自除。盡管病理變化多樣,人體生理機能的提高與血流供應的改善是治愈疾病的關鍵環節,抓住這兩個環節,就是抓住治療學上具有普遍意義的客觀規律。中醫對于氣血不和的病理認識,實際上高度概括了疾病發生的普遍規律,所以,糾正氣血不和,同為針與灸達到治病療效的關鍵。
8 同以平衡陰陽為目的
人體是陰陽對立的統一整體,不論是生理作用的發揮,還是病理過程的衍變,都是陰陽轉化和矛盾對立的運動過程,故中醫認為疾病的發生是陰陽失調的結果。《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中對陰陽的定義有“天地之道,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等描述,然后強調“治病必求于本”,根據前后文意,此處的“本”即指陰陽,指出治病需探尋疾病的本源;歧伯描述陰陽偏勝:“陽勝則身熱,腠理閉……陰勝則身寒,汗出……此陰陽更勝之變,病之形能(態)也。”闡明疾病的本質是陰陽的失衡,據此理論基礎,中醫藥治病的最終目的都在于使失衡的陰陽重歸平衡,即古籍所謂“陰平陽秘”。《靈樞·根結》言:“用針之要在于知調陰與陽。”說明針刺的關鍵是調和陰陽,以平衡陰陽為目的。
瀉有余,補不足,是中醫臨床的基本原則,有余為亢盛屬陽,不足為衰竭屬陰,亢盛的機能得到抑制,衰竭的機能得到興奮,陰陽平衡,健康自可恢復。在針灸臨床上,常有左右互取,以及前后上下的顛倒取穴法,這是基于中醫從陽引陰、從陰引陽的理論,在此原則的指引下,衍生靈活多變的配穴與取穴法。中醫的陰陽互引法基于陰陽互根的原則,現代醫學的神經解剖發現中樞對外周神經的交叉支配,用以解釋一些腦中風事件,病灶在左腦,病癥卻表現為右側肢體癱瘓;此類病證的針灸治療,辨證取穴常體現在重點調治患側肢體及對側腦區,又在患側肢體的針灸治療上,區分陰陽經脈的痙攣與遲緩,有針對性地選穴針灸,使痙攣的一側放松,增加遲緩一側的肌力,達到平衡陰陽目的。
9 結語
針刺和艾灸作為中醫學不可或缺的兩種外治療法,對疾病防治具備重要作用。針刺和艾灸在用具、施術手法、優勢病種、治病機制等方面存在諸多差異[8-9],但是兩者的相同點溝通著理論與實踐,對于針刺和艾灸療法的臨床應用具有較好的思辨指導。針刺與艾灸同基于中醫理論,在發揮防治疾病作用時,存在眾多公理性統一,兩者的基礎相同點可概括為理論同宗,治則同源。
針刺和艾灸在施術方面,包括了工具、手法和原則,雖然施術的基礎工具有針具和艾葉的差異,但兩種療法的刺激部位都局限于體表,主要以腧穴、經絡部皮膚、肌肉為主,并未由器具直接刺激或接觸內臟;盡管針與灸的施術手法有所差異,但是針刺和艾灸的手法同樣都區分補和瀉,基于正邪的偏勝偏衰,辨虛實、施補瀉;針刺與艾灸的施術原則共同根源于中醫基礎理論的相關公理,其中最重要的公理是經絡腧穴理論指導下的人體認知,涉及中醫從經絡視角對人體生理病理的認識。 中醫認為:經絡是內連臟腑、外絡肢節的人體溝通系統。 古代醫家積累了大量針灸臨床經驗,根據體表各刺激點(腧穴、孔穴)對臟腑病癥的治療作用,歸納推理,形成經絡的體表循行和內在屬絡關系,總結出針灸臨床的取穴配穴原則。 針刺和艾灸發揮防治作用,都需以辨證論治為施術前提,明確證(癥)以后,辨明標本虛實,選經取穴配穴,標本兼顧,配合補瀉手法,攻補兼施,通過刺激作用于腧穴,疏通經絡,調整臟腑功能[10],調和氣血,達到平衡陰陽的目的,陰平陽秘則疾病自消。
綜上所述,針刺和艾灸,在理論基礎上具備以下共同點:以疏通經脈為根本,以調和氣血為關鍵,以平衡陰陽為目的。 兩者的理論基礎共同源于腧穴-經絡-臟腑相關的理論,深受氣血、陰陽學說等中醫理論的影響。在治療特性上,針刺和艾灸具備以下共同點:以體表刺激為特點,以病理狀態為條件,以明證審穴為指導,以標本兼顧為原則,以攻補兼施為手段。兩者共同的理論來源為治療特性奠定基礎,指導施術法則的設立和補瀉手法、刺灸處、刺灸法的選擇,且共同基于中醫整體觀念和辨證論治。研習古籍,能從中感悟古代醫家運用針刺和艾灸療法的臨證思維,為現代臨床提供重要理論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