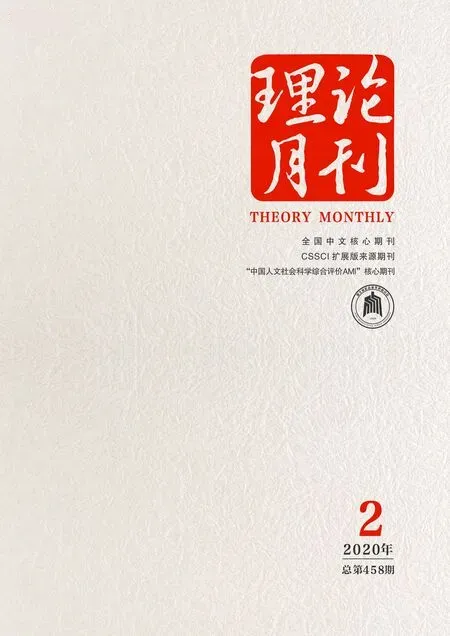道可得學邪
——以《莊子》為中心
□黃 河
(華東師范大學 哲學系,上海 200241)
“美德”是西方哲學討論的核心議題。蘇格拉底在很早的時候就提出了“美德是否可教”問題。而亞里士多德站在批判柏拉圖“理念論”的基礎上,強調教育對德性的培養作用。叔本華在《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繼承了蘇格拉底的觀點,但該觀點遭到包爾生的反駁:“德性是可以靠教育獲得的嗎?”[1](p407)他認為只有通過實踐的方式來培養道德能力。特雷安塔費勒斯在《美德可教嗎:政治哲學的悖論》中做了總結,認為:“美德不可思議地可學(learnable),卻并非必然明顯地可教。”[2](p13)圍繞“美德是否可教”這一經典哲學命題的不斷爭鳴和積極探討,構成了西方哲學史發展主線之一,成為理解、梳理西方哲學的關鍵鑰匙。
“德性”在中國哲學視域里固然重要,但在先秦道家那里,“道”似乎更能反映其理論旨趣,并使之成為中國哲學史上的重要范疇之一。那么,在中國哲學語境下,作為形而上學的“道”是否可教或可學呢?事實上,莊子在《大宗師》中討論完道內存于各種神化人物以及與之相應的活動之后,通過南伯子葵與女偊的對話,提出了“道可得學邪”的問題。依此,可明顯地看出莊子已意識到這一問題的重要性。那么,關于“道可得學邪”這一問題,莊子是如何回應的?以及,他回應的內在理路是什么?進而,后來的學者沿著這一理路,又做了怎樣的探討?而這樣的討論,能否作為理解中國哲學史的又一線索呢?以《莊子》文本為中心,本文力圖對以上諸問題做出相應的回應。
一、“道可得學邪”問題的提出
與“道可得學邪”問題涉及的,首先是“何為道”的問題。而在中國哲學史上最早關注“道”,并把“道”作為形而上學最高規定的是老子。在老子之前,人們都是以天、自然作為萬物之主宰,而老子則觀變思常,明確將“道”界定為超越經驗的本源存在,視作為萬物變化之母,亦即“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德經·二十五章》)。具有本體性意義的“道”雖超越經驗而存在,并“大道氾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道德經·三十四章》),先于天地而生,以“寂寥獨立”為其存在狀態,但不能離開經驗世界,所以“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道”周遍于萬事萬物而無終止。在價值論意義上,“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道德經·四十二章》),“道”既體現為萬物發生之泉源,又衍化為世間萬物演化之過程。所以“道”在創生萬物之后,總以“德畜之”而成為萬物之內在本性,亦即“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道德經·五十一章》),并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邏輯秩序(《道德經·二十五章》),成為經驗世界中決定“變”與“常”的規律或法則。由此觀之,老子思想中的“道”,不但涉及對終極本體、萬物本源等終極問題的思考,而且還關乎對存在的依循秩序、演化法則等普遍規律的確認,在中國哲學史上具有形而上學價值。而正是這樣深邃的思想關切,讓張岱年認為“老子是第一個提起本根問題的人”[3](p79)。
莊子繼承了老子關于“道”的理解和認識,但又不局限于老子本體論和價值論上的討論,而將其與“物”“死生”等相溝通,使之能夠顯現于多樣的變化和現實的活動之中,并成為世界變化和人之活動的內在根據,“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辨之”(《莊子·天下》)。因而在形成的“道物關系”中,“道”始終作為第一原理,是本體論意義上的本根和宇宙論意義上的始源,正所謂“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莊子·大宗師》),在終極的“可能世界”里只有“道”,而在經驗世界中則是“道生物”或“物生物”。這里的“可能世界”是一個只有邏輯性而沒有時間的境域,“道”在這樣的世界中類似于康德所講的“物自體”。從某種意義上講,道是本根但不是實體,物是實體而不是本根,“道”在“道物”關系之中占據主導地位,于是“道無終始,物有死生”(《莊子·秋水》),有限的“物”與無限的“道”之間,必然地存在著某種張力,所以莊子主張“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莊子·秋水》),以“道”的無限性超越主觀成見,進而獲取生命的永恒觀照。即使是人之死生問題,也可由“道”之化來予以安頓,“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忽然而已。……已化而生,又化而死”(《莊子·知北游》)。能創生萬物的“道”,在莊子這里被形象地稱為“生生者”,能夠“覆載天地,刻雕眾形”。至此,關于莊子思想中的“道”,可以做如此總結:在確保“道”的無限至上性、確認對“道”孜孜追求的同時,將“道”與經驗世界中的“物”“死生”等相溝通,“行于萬物者,道也”,(《莊子·知天地》)獲得了周行遍在、萬物皆受其覆載的面相。莊子這樣的邏輯推衍和理論拓展,使道家思想一方面保持了以“道”觀世界的視角,維護了“道”與經驗世界的差異性,另一方面又打通了“道”與經驗世界間的溝通,以此加深對“有”的世界的承認以及深刻理解。
以上是老莊關于“道”的概述。而對于“道可得學邪”這一問題的討論,還應以理解“學”為前提。寬泛意義上的“學”既涉及外部對象,又與人相關。縱觀先秦哲學,最重視“學”問題的為儒家,從《論語》開宗明義的“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論語·學而》)到荀子的“學不可以已”(《荀子·勸學》),無不把“學”置于重要地位。細究儒家“學”之思想,均以“為己”“成己”為目標,并與為學和為人、做人和做事難以相分,體現出目的與工夫、主體與對象相結合的特征[4]。而在奉行“無為”觀念的老子那里,以“學”為代表的一切知識活動不足取,囿于“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道德經·五十三章》)。老子否定“學”、否定“知識”的這種觀念,在莊子那里得以認可并傳承。但莊子把這種“否定之知”局限于經驗世界的認知,原因在于經驗世界里認知對象的不確定性,亦即“夫知有所待而反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莊子·大宗師》),而且“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莊子·齊物論》),以及作為“學”之主體的人,也無法擁有一套統一的認知標準:“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莊子·齊物論》)。認知對象的不確定性和認知主體的標準不一,使經驗世界里的“學”本身難以獲得確定的知識內涵。缺乏可靠性的知識“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莊子·齊物論》),此消彼長,在經驗世界里難以完成,甚至成為心靈之墮落、遠離真我之障累。即使是“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莊子·秋水》)或“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莊子·山木》)的行為,在莊子看來都應予以破除。莊子意識到指向經驗的“學”有所困,所以主張以“齊是非”“薄辯議”等方式來破除。同時,莊子對于以超越與溝通超經驗世界之外的認知或學,則給予積極關切,因為“知之所至,極物而已。睹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莊子·則陽》),亦即表明以經驗為對象的“學”難以超越“物”,而“睹道”之人則不隨“物”消逝,作為第一原理的“道”既不細究“物”之起源,也不討論“物”之所終止,所以“不知深矣,知之淺矣”(《莊子·知北游》)。依據對象的不同,莊子在這里對“學”這種認知活動進行了適當區分,亦即以經驗萬物為對象的“學”和以超越經驗的“道”為對象的“學”。前者要給予否定,而后者需要予以肯定。以“道”為指向的“學”,不僅是破除經驗知識之障累、否定形骸之自我的手段,而且還是觀賞情意之自我、接近“真知“的修養工夫。故而莊子將前者所獲得的成果稱為“小知”,后者所獲得的成果稱為“大知”,但“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小知不及大知”(《莊子·齊物論》),唯有“去小知而大知明”(《莊子·外物》)。
基于“道物關系”存在現實張力的認識,秉持“向道而學”觀念的莊子,在《大宗師》中展示完“道”周遍于各種神化人物以及與之相應的活動之后,通過南伯子葵與女偊的對話,提出了“道可得學邪”問題。“南伯子葵問乎女偊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莊子·大宗師》)“道可得學邪”這一問題的提出,既反映了莊子對否定經驗認知活動的現實反思,又折射出探尋道、堅守道的理論旨趣,以及對形而上理論的自覺追求。
二、“道可得學邪”問題的展開
關于“何為道”“何為學”,“道”和“學”各自具備怎樣的特征屬性,以及二者的關系如何等問題,學界的論著業已汗牛充棟,而關于“道可得學邪”問題的討論,卻鮮有涉及。而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歸納起來無外乎劃分為兩類,即“不可學”和“可學”。關于“道不可學”的回答,可依此展開:一是認為“道”不可“學”,所以人應該通過自身的努力超越“道”,追求比“道”更具主宰性的形上主體。以此為出發點,遂衍生出超越“道”為價值根源之說,而把“道”放入次級地位之中。而這樣的觀點,在以“道”為最高地位的道家那里,是不能接受的。二是承認“道”之主宰地位,并獨立于人無以企及的領域,由此而推衍出人以及人之認知或自覺能力在該領域中根本無可作為,所以人應敬畏或遠離“道”及其領域,而自求自身的超越,即離經(經驗世界)離“道”。這樣的觀點,接近于神權主義。關于“道可學”的回答,亦可這樣展開。一是承認“道”可學,但不承認“道”為超越經驗之主宰,而是將“道”歸類于經驗世界、事實意義上的“必然”,或為經驗世界所凝練,于是要求人要了解事實的必然規律,并以此為人做事的依據。這樣的觀點類似“命”,承認“道”在客觀領域對人以及人的活動行為的限制,并不存在于人自覺意志之中,從而否定了“道”的主宰性和超越性,以及人的自覺主宰性。類似的觀點后來被漢代道家所推崇:“天道與人道同,天人相通,精氣相貫”(《老子河上公章句·四十七章》)。“道”的形而上色彩逐漸退去,地位不斷下降。從莊子對經驗世界之否定觀點出發,這樣將“道”跌落為經驗中的“必然”,也是其加以否定或破除的對象。這確實不是莊子對“道可得學邪”問題的回應。二是莊子的立場。此觀點是先區分“道”與“學”,并對作為“學”的自覺主動與作為“道”的客觀限制同時承認,各自劃定領域,然后以“道”為“學”之目標,發揮人之認知能力在“學”中彰顯“道”、把握“道”,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莊子·大宗師》),亦即經驗性的認識不能背離形而上的“道”以及對天性的認識,從而完成兩個不同境域或世界的溝通,達至“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莊子·大宗師》)。這樣的觀點既不完全崇拜“道”的超越獨立性,也不以物事代替價值,或以自然代替價值,無超離舍棄的神權主義之傾向,更無跌落經驗的庸俗主義之窠臼,而是道家一以貫之的“道通為一”原則。
秉持“向道而學”觀念、承認“道可學”觀點之后,莊子就與之相涉的“跟誰學”“如何學”“誰能學”等問題逐一進行了回應。
在回答“道可學”之后,必然涉及“向誰學”的問題。通覽莊子思想,與儒家提出“圣人”一樣,他也提出了自己的理想人格,即“真人”——“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莊子·大宗師》)。“真人”有時又被稱作為“至人”——“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莊子·天道》)。但無論是“真人”抑或是“至人”,不僅以“道”為其內在規定,而且在知或行中堅持不違“道”。在《大宗師》中,莊子運用了大量篇幅對真人的形態進行了全方位展示,在世俗中“不逆寡,不雄成,不謨士”,在面臨外部世界時“登高不憟,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在日常生活中“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在對待生死問題上“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欣,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等等。莊子就“真人”的如上描述,實際上將“道”給“人格化”了,“借‘真人’的體相,來說明‘道’的大用,兼以示范于人類,期以‘以人合天’”[5](p198)。從認識論維度看,莊子的如此用意不僅在于將道“人格化”,而且告誡世人可通過“學道”以取法真人,擺脫外物之奴役,“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莊子·大宗師》)。以“道”來“人格化”的“真人”,在這里成為“學道”“體道”的理想標準。基于此,莊子進一步強調“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莊子·大宗師》),其中的“真知”就是“道”,這就意味著唯成為“真人”后方能忘知,方能掌握以“道”為內涵的“真知”。所以,關于“向誰學”問題的回答,莊子指的是具有“真知”的“真人”。
另外,關于“向誰學”的問題,還可以回到《莊子》文本,結合上下文的邏輯來考察。如前文所說,“道可得學邪”這一問題是莊子在《大宗師》篇中提出來的。而在提出這一問題之前,莊子先是從“天人關系”的角度切入,討論自然與人“不相勝”的關系,再者描述具有“真知”的“真人”體道的境界,以揭示“道”與自然、與人不相離的關系,接著以“大化同流”的觀點講述人對于生命的認識,然后是集中性地描述了“道”的無形、永存和無限性等特征,最后就在南伯子葵與女偊的對話中,提出了“道可得學邪”問題。通過這樣的邏輯梳理發現,“道”是本部分內容討論的中心,包括與天人、與真人、與生命等都是圍繞“道”而展開。其中的“真人”,實際上就是“得道”之人。當討論完“道是什么”“得道之人是什么”等問題之后,從邏輯上也就出現“道可得學邪”的問題,或者說“道可得學邪”是對前兩個問題的進一步展開。如此一來,莊子在以“真人”回答“得道之人是什么”問題時,已經為“道可得學邪”問題相涉的“向誰學”提供了答案,亦即具有“真知”的“真人”。
對“如何學”問題的回答,既涉及學之方法又包括學之次第。在《莊子》一書中,涉及道“如何學”的方法頗多,如“自省”“反視內聽”“吾喪我”“坐忘”“心齋”,等等,這里選擇具有代表性的“坐忘”和“心齋”論述之。
“坐忘”是莊子提出的重要“學道”方法。在《大宗師》中,莊子借用孔子和顏回的對話,對“坐忘”做了較為系統的描述:“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謂坐忘’”(《莊子·大宗師》)。從社會維度看,以“坐忘”的方法來“學道”,必須先把與世俗文明相關的“仁義”“禮樂”忘卻。這是“學道”的前提要求。進而,再忘卻自己的肢體,排除自己的聰明,亦即“離形去知”。“離形”亦即消解由生理所激起的貪欲,而“去知”則是消解由心智導致的偽作,依此體現了“學”道同一過程的兩個不同側面。與“坐忘”學道方法類似的,還有“心齋”。“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耳止于聽,心止于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莊子·人間世》)。從方法論的角度看,“心齋”這樣的“學道”方法首先要專心一致,脫離感官之束縛,破除心中各類雜念,“應物而不滯于心”,然后用集“虛”的方法以至道,因應無窮,從而達至空明之境界。“心齋”方法重點在于集中精力、專心一致,亦即“一志”,同時還要以虛待物,忘卻一切,亦即“集虛”。“虛”的運用既有方法論的意義,又有意境上的意味。而這樣的學“道”法,與如今獲得共識的學習方法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一致性。綜合起來看,無論是“坐忘”還是“心齋”,都主張在“向道而學”中“喪我”,亦即在雜亂紛紜的經驗世界中離形去知、一志集虛,以達至“道通為一”的境界。
“如何學”過程的次弟,莊子繼承了老子“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為”(《道德經·四十八章》)的工夫。莊子在《大宗師》中借女偊之口,具體闡明了“學道”之過程:“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圣人乎?不然,以圣人之道告圣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徹;朝徹而后能見獨;見獨而后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莊子·大宗師》)。學道不僅在時間上有“三日”“七日”“九日”等過程,而且在各階段上也出現“外天下”“外物”“外生”“朝徹”“見獨”“無古今”以及“不死不生”等次弟,唯有在超越生死、古今之后,最后方能歸于“攖寧”,亦即讓一切歸于寧靜,終能統攝于“道”。接著,莊子又借女偊自修過程羅列了“學道”之步驟:“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于謳,于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莊子·大宗師》)。學道首先是從間接經驗開始,如文獻、傳聞、傳誦、聶許等,同時又與直接經驗相關,如需役、于謳等,統一于人的體悟過程之中,最后經過玄思、參寥之后,在疑始處獲得了“道”。從“聞諸副墨之子”開始一直到“疑始”,這一過程經歷了多個步驟,前后相繼,循序漸進。所以,莊子對于“道可學”過程的展開,是要從世俗的直接經驗,到親歷其親,然后層層解脫,以達到至虛至靜的“玄思”和“攖寧”,即與老子“致虛極,守靜篤”的境界相同。這樣的“學道”工夫,是由外而內、損繁至簡,具有明顯的漸次性和過程性,與后來禪宗主張的“頓悟”在本質上具有明顯的差異。
關于“誰能學”的問題,可以回到《莊子》文本看看女偊是如何回答的。“南伯子葵問乎女偊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圣人之才而無圣人之道,我有圣人之道而無圣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圣人乎?不然,以圣人之道告圣人之才,亦易矣”(《莊子·大宗師》)。南伯子葵先是驚嘆于女偊的外貌,詢問后得到的原因是“得道”,于是就接著提出“道可得學邪”的問題。而女偊的回答是“不可以”,但“不可以”指的是像南伯子葵這樣沒有“圣人之才”的人,接著女偊就對“圣人之才”與“圣人之道”進行了區分,較之于“圣人之才”,“圣人之道”更具有決定性意義。“圣人之道”是“學道”的重要前提,像卜梁倚這樣即使擁有“圣人之才”的人,都有可能學不成,不過告訴他是比較容易的。結合文本上下的邏輯內容看,莊子在這里并非真正強調南伯子葵能否“學道”,而是以“圣人之才”和“圣人之道”的標準,對哪些人可以“學道”哪些人不可以“學道”做出適當的區分。當然,這樣的區分方式引起了唐君毅的質疑,認為道家沒有做到“有教無類”,比不上儒家“人人皆可成堯舜”的觀點[6](p395)。暫且不討論該觀點,莊子在這里的這種劃分已經回答了“誰能學”的問題。其實,莊子并未否定常人成為真人的可能,也未反對常人學道的觀點。在《大宗師》“意而子見許由……此所游已”一段中,莊子認為盡管曾經受到過儒家仁義“黥”、世俗是非“劓”的人,都可以通過自我改造,放棄已有的規定和價值規范系統,依然可以進入一個新的“學道”“體道”過程。
三、“道可得學邪”問題的延展
自蘇格拉底之后,人們圍繞“美德是否可教”問題而展開的不休爭論,儼然成為西方哲學史上的一道亮麗風景,也成了理解西方哲學思想的關鍵鑰匙。而莊子提出的“道可得學邪”哲學命題,是中國哲學史上關于“道可學”的最早立論,可與“美德是否可教”經典哲學命題相媲美。
莊子之后,接著關注“道可得學邪”哲學命題的是荀子。他在《解蔽》中言:“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壹而靜。心未嘗不臧也,然而有所謂虛;心未嘗不兩也,然而有所謂壹;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荀子·解蔽》)。荀子這里提及的“道”與莊子的“道”在內涵上可能有所差異,但在回答“道可得學邪”問題時,態度是極其鮮明的,亦即承認“道可學”,并將“學道”的方法總結為“虛壹而靜”,與莊子的思想一脈相承。《淮南子》單列《修務訓》論述了“學”的重要性,認為達到“圣人無憂”和“通而無為”的途徑是“學”:“所以為人之于道未淹,味論未深,見其文辭,反之以清靜為常,恬談為本,則懈墮分學;縱欲適情,欲以偷自佚,而塞于大道也。今夫狂者無憂,圣人亦無憂,和以德也;狂者無憂,不知禍福也。故通而無為也,也塞而無為也同,其無為則同,其所以無為則異。故為之浮稱流說其所以能聽,所以使學者孳孳以自幾也”[7](p229)(《淮南子·要略》)。在“學”之目標和方法上,直接繼承了莊子“道可學”的精髓。
南北朝時期的僧肇在討論“佛性”如何安立實成時,借用了道家“為學日益,為道日損”的方法,認為:“況乎虛無之數,重玄之域,其道無涯,欲之頓盡耶?書不云乎,為學者日益,為道者日損。為道者,為于無為者也。為于無為,而日日損,此豈頓得之謂?要損之又損之,以至于無損耳。”[8](p219)“損之又損之”的方法,本質上就是莊子強調的“向道而學”之法。唯有運用這種漸悟的工夫,才能理解“虛無之數”,到達“重玄之域”。
蘇東坡明確反對“道可學”。他在解釋《系辭》的“道”時說:“陰陽交而生物,道與物接而生善。物生而陰陽隱,善立而道不見矣”,所以“學道而自其繼者始,則道不全”[9](p296)。而這樣的觀點在朱熹那里受到了嚴厲批評:“繼之者善,言道之所出,無非善也,所謂元也。物得是而成之,則各正其性命矣。而所謂道者,固自若也。故率性而行,則無往而非道。此所以天人無二道,幽明無二理,而一以貫之也。”[10](p3466)二人關于“道”的理解可能有所偏重,在此不做嚴格區分,但對于“道可得學邪”的態度卻異常鮮明。朱熹的主張是:“學者學夫人事,形而下者也;而其事之理,則固天之理也,形而上者也。學是事而同其理。即夫形而下者而得其形而上者焉,非達天理而何哉?”[11](p325)這樣的觀點在王陽明那里得到了附和:“夫道必體而后見,非已見道而后加體道之功也;道必學而后明,非外講學而復有所謂明道之事也。”[12](p75)后來,作為永嘉學派代表人物的葉適,對朱熹“以學致道”的觀點提出了指責,亦即“皆以學致道而不以道致學”[13](p554),并對不同的學習者做了考察:“以子夏之為儒,猶戒其小人也,而況余人乎!夫儒者不考于德而徇以學,則以學為道之病乎。”[14](p181)“學”若不與“道”結合起來,純粹為了知識而學習的人,猶小人也,則“學以致道”的人則是君子,遺憾的是,葉適這里的道與本體意義上的道相去甚遠,更偏向于對道德意義上的道的探索,代表了中國哲學中一向“學以成德”的傳統。
通過以上論述看出,“道可得學邪”這一哲學命題的提出,對中國哲學之發展以及理解中國哲學理論之旨趣具有特別意義。就莊子本人而言,這一哲學命題體現了莊子思想中的“道”是“道通為一”的“道”,“學”是“向道而學”的“學”,亦即在本體論上繼承于老子,始終以“道”作為第一原理,關注“何為道”“何為世界主宰”等形上問題,在認識論上關涉“學”之可能與限度,以及“真知”標準及謬誤區分等理論問題。處理與此相關的天人關系,應該堅持“天道與人道相結合”的基本原則,因為在“道”的總體原則之下,每每滲透有“人”的價值追求,從“向道而學”到“以道觀之”,便不難看到這一點。進而在更深沉的層面上,反映了以莊子為代表的道家對形上理論的自覺追求,以及對天人關系的自覺處理。
就早期中國哲學(尤其是先秦)而言,“道可得學邪”哲學命題的提出以及相關問題的探索,直接體現了先秦諸子對終極原理的關注和推崇。但理應注意到,在對這一最高原理的探索下,又包括的有“如何認識世界”“如何更好地存在”等現實問題的關切。從而奠定了中國哲學發展始終注重形上理論探索但又不限于形上視域、基于生活但又不限于生活世界的理論品格,從早期的陰陽五行、成己成物、天人相應、道通為一,到后來的格物致知、知行合一、工夫本體,以及晚近的體用不二、良知坎陷,都不難看到這一脈絡。
就中國哲學衍化而言,在以時間先后為序來梳理哲學發展之過程的基礎上,有必要以抓住一些關鍵的基本哲學命題,厘清不同學派和人物如何的回應與主張,由此來揭示哲學的內在邏輯和發展脈絡。而莊子提出的“道可得學邪”哲學命題,就具備這樣的演化特征和學術價值。在形而上層面上,與這一問題相涉的“道”“學”關系問題,亦即本體與認識的關系問題。盡管各家各派關于本體論和認識論的界定,以及二者關系的理解莫衷一是,但對“道可得學邪”問題都做出積極的回應和獨特的見解。這些回應和見解,一方面反映了中國哲學對本體論和認識論等基本哲學問題的關切,另一方面也體現了中國哲學理論的內在發展理路。一言以蔽之,“道可得學邪”哲學命題體現了中國哲學的智慧旨趣和獨特品格。
四、結語
與“美德是否可教”相媲美的“道可得學邪”哲學命題,最早由莊子在《大宗師》中提出。莊子一方面繼承了老子“道”的思想,另一方面又將“道”與“物”“死生”等相溝通,以此將追求道的工夫延伸至經驗世界。與此相關聯的“道”之工夫——“學”,被莊子作了適當劃分,亦即以經驗萬物為對象的“學”和以超越經驗的“道”為對象的“學”,前者獲得的知識是“小知”,應給予否定,后者獲得的知識是“大知”,須給予肯定。關于“道可得學邪”問題的回答,一般分為“可學”和“不可學”兩類。秉持“向道而學”的莊子,明確支持“道可學”。并且,可以通過“坐忘”“心齋”等方法跟著“真人”學。莊子強調了“學道”工夫的次弟,主張由外而內、損繁至簡,與后來禪宗的“頓悟”在本質上具有明顯的差異。莊子并未否定常人成為“真人”的可能,也未有反對常人學“道”的觀點。
縱觀中國哲學史,各家各派雖然對“道”和“學”有不同的界定和詮釋,但關于二者之間的關系,亦即“道可得學邪”的討論始終存在。而在這背后,則是中國哲人對“何為世界”“何為道”等形上本源的自覺追問,以及對“如何獲取知識”“人如何生存”等現實問題的深沉關切,蘊含著中國思想的獨特智慧和哲學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