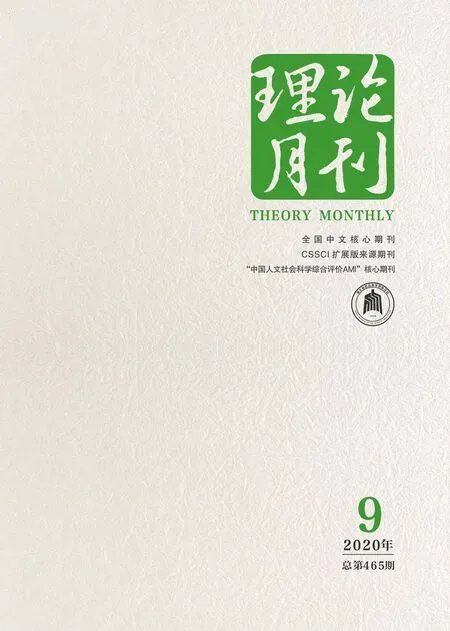21 世紀初美國非虛構作家筆下的中國社會巨變
□楊 巍,孫小孟,劉新民
(1.重慶文理學院 外國語學院,重慶402160;2.南京大學 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江蘇 南京210023)
一、引言
20 世紀五六十年代,“非虛構寫作”的概念從美國盛行一時的“新新聞報道”中延伸而出。相較于注重功能性與時效性的新聞寫作,在忠于素材“真實性”的同時兼顧了文本的藝術性與深刻性,這類以藝術性姿態敘述歷史記憶與社會現實的文學作品在西方世界引發了閱讀浪潮并廣受好評。21 世紀之初,改革開放的中國大地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由此,吸引了一批美國的新聞工作者與外教來到中國,他們旅居中國與無數普通國民一起生活,汲取靈感,感受著中國改革浪潮中的瞬息萬變,旅居中國多年后,他們撰寫出了一系列震撼人心的非虛構作品。主要代表作者及作品有:彼得·海斯勒的《尋路中國:從鄉村到工廠的自駕之旅》(2011,下文簡稱《尋路中國》)《江城》(2012)《奇石》(2014);邁克爾·麥爾的《再會,老北京》(2013)《東北游記》(2017);馬修·波利的《少林很忙》(2014);張彤禾的《打工女孩》(2013);喬治·夏勒的《最后的熊貓》(2015);史明智的《長樂路》(2018)等,這些作家以見證者的角度記錄和描述了當時中國人民的真實生活和情感經歷。
在《尋路中國》一書中,美國記者彼得·海斯勒特為讀者講述了一個中國北方因工業發展而處于鄉村劇變中的小家庭由農轉商的曲折命運。彼得·海斯勒的夫人、美籍華人作家張彤禾(2013)在她的代表作《打工女孩》一書中,描述了中國南方城市——東莞兩個學歷不高的鄉村打工妹以及她們在大城市的打工生活。鄉村打工妹是當時中國無數打工女孩的縮影,張彤禾以飽滿的筆觸描繪了這些掙扎在社會底層的女孩們辛苦乏味的工廠生活、努力闖蕩的奮斗身影以及曲折復雜的心路歷程[1](p25-197)。而在北京楊梅斜竹胡同生活了多年的邁克爾·麥爾(2013)則親眼見證了北京城由舊時閑適而鮮活的老胡同到迎接奧運會時那壯觀的變革,在他的代表作《再會,老北京》一書中,其以一個“老北京居民”的身份描繪了他對胡同文化消逝的無比惋惜[2](p36-269)。這些美國作家以傾聽者和親歷者的身份,把他們旅居中國大江南北的所見所聞加以藝術性地敘述,以逼近現實而非完全復刻現實的方式,帶給廣大讀者許多最真切的異域體驗。
二、時代變遷:宏觀歷史下的個體命運勾勒
在宏觀歷史的洪流下,個體命運被無限地微觀化。不同于對中國整體社會發展的關注,這些非虛構作家把重心放在了細碎的個人生活體驗上。在創作的過程中,這些美國作家通過與中國普通百姓建立信任、友好的對話,敘寫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與情感體驗;他們既是傾聽者,又是這段歷史的親歷者。
(一)攫取個體命運的典型代表
“中國女婿”邁克爾·麥爾在撰寫《東北游記》之前,曾在吉林市的荒地村住了兩年,這兩年里他與荒地村的所有普通村民一樣睡炕頭、燒柴火,在這段時間里,邁克爾·麥爾把自己形容成一個趴在墻上的蒼蠅,靜靜地聽人們講述自己的故事,他結合自己的主觀情感運用藝術性敘事的方法將一個個真實生動且感人的故事記錄了下來。為了探尋東北農村那些被遺忘的歷史,他坐著綠皮火車暢游了四萬多公里。荒地村屬于典型的東北鄉村,位于吉林和長春之間,是無數個東北鄉村中的一個縮影。在改革的浪潮中,荒地村也出現了欣欣向榮的發展態勢,現代化與工業化的洪流改變了荒地村落后的面貌,在他的筆下,荒地村歷史的痕跡已幾近消逝。隨著鄉鎮企業東福米業的發展以及全產業鏈的現代化推進建設,這個曾經破敗荒僻的東北鄉村已經發展成為東北的“大糧倉”。農業現代化的轉變和新農村的建設讓農民們過上了現代化的生活。人們的生活煥然一新,歷史僅存在于他們的記憶中。《東北游記》一書中隨處可見邁克爾·麥爾對過去的荒地村的追思,他不僅表達了自己對傳統農耕文明的向往,而且也對中國的未來寄予了無限的憧憬。在書中,邁克爾·麥爾(2017)感嘆道:“我很清楚,在東北,能夠對中國的過去一探究竟。但沒有料到,在荒地,我能一瞥這個國家的未來。”[3](p15)
隨著城鎮化改革浪潮的持續推進,中國迎來了近代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人口遷移。無數普通人順應時代的潮流,懷揣著夢想與忐忑來到異鄉拼搏。這些來自鄉村的務工者以外來者的身份來到陌生的大城市,面對陌生的環境謹小慎微。而這些旅居中國的美國作家也以外來者的身份觀察這些來自鄉村或是其他城市的移民和遷徙者。“外來者”對“外來者”的二度審視賦予了美國作家們更加獨特的視角以及更加細膩曲折的情感體驗。在《尋路中國》《打工女孩》等作品中,作者和他們的觀察對象往往都是流動的。彼得·海斯勒駕車跨越了中國的大江南北,宏觀層面,他看到了規模浩大的人口遷移;微觀層面,他見證了這場人口遷移中的個體在城鎮化、現代化浪潮中的生命體驗[4](p18-154)。作為旅居中國的外國人,他以獨特的視角,觀察著這場以人口遷移為典型特征的中國城鎮化的社會變動,同時,他還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去與那些經歷著時代變遷的普通人進行交談,以窺視社會變動下的個體命運。在彼得·海斯勒(2011)看來,無數生活在中國各階級的普通人民還來不及做出判斷,就已被卷入了洶涌變幻的洪流之中,亦如那些離開鄉村、懷揣夢想前往城市務工的年輕男女,亦如那些棄農從商、踏入復雜社會與利益漩渦的老實農民。
(二)藝術性敘述客觀的真實
在這些非虛構的作品中,真實發生的歷史事件與形形色色個體的“口述史”構成了客觀的真實,作者們通過文字敘述呈現出的事物背后的暗流構成了情理的真實,在寫作中流露出的主觀情感構成了主觀精神的真實。《尋路中國》等非虛構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具備鮮明的個體特征,是時代洪流中萬千普通人的縮影;如此選材,不僅能從龐大的社會中窺探個人,而且能以個人的命運反窺社會。這些美國作家把普通人“口述”的經歷與情感進行藝術加工,將這些瑣碎的片段拼接成了時代變遷下具有連貫性和整體性的個人命運圖景。在《打工女孩》一書中,作家張彤禾通過敘述兩名鄉村打工妹的個人生活,描繪出了當時中國無數女性打工者群體的曲折命運。她們中的許多人來自鄉下,懷著對大城市生活的向往和對復雜社會的畏懼來到城市,費盡周折地努力改變自己的命運。在書中,她給讀者展現了這些鄉村打工妹是怎樣從懵懂無知到諳熟都市生存的規則,以至完成脫胎換骨般的蛻變。打工妹群體在陌生的環境中,她們內心的迷惘與向往被重現在這些非虛構作品中,這種以個體普遍命運管窺社會流徙的呈現方式引起了無數讀者的共鳴。
除了張彤禾筆下的東莞打工妹,其他旅居中國的美國作家還以獨特的視角勾勒出了處境、經歷各異的人物個體,他們均是當時大環境的一個個縮影。例如,邁克爾·麥爾筆下從東北村莊走向大世界的妻子,她在城市中經過一番闖蕩后陪丈夫麥爾回到荒地村生活。當麥爾為農村恬靜舒適的景色而著迷時,妻子卻表示,外人看起來美麗的村子對村里人來說單調乏味,許多村里人都向往外面大城市里的生活。又如,彼得·海斯勒在《尋路中國》中書描寫的魏子淇一家由農經商的經歷。魏子淇為了脫貧致富,不斷嘗試新的經商途徑,在這個過程中,這名曾經淳樸實在的農民慢慢地學會了人情世故,從最初的窘迫到后來以“拉關系”的方式逐漸獲得成功,個體在社會變革中的細微經歷與情感變化被他生動真實地呈現了出來。而史明智(2018)則在他的《長樂路》中,以一條街上幾名主角過去的經歷與現在的生活為片段,拼接出了中國改革開放后幾十年的歷史變遷畫卷。書中的文藝青年CK 在現代大城市中感到精神上的空虛與迷惘,后來他與佛教結緣,由此找到了人生的真諦;花店老板趙世玲作為一名外來農民工,通過自己的努力開了花店立足于上海,但卻由于大兒子必須回到家鄉上高中,她的上海夢破滅了……[5](p23-147)。這些形色各異的人物都處在不同的社會階層中,在中國的社會變遷中有著不同的經歷和情感,但他們的迷惘與拼搏卻是共通的,他們的故事都是時代變遷下的微觀寫照。洪治綱認為,步入后現代社會,工業與信息技術的發達將每一個人類個體都被包裹在信息洪流所形成的仿真文化中[6](p62-71)。信息的多樣化及其密度讓“真實”成了一種稀缺品,普通人的生活形態被符號化,現代人在這樣的時代困境下愈感孤獨。這些美國作家筆下的非虛構作品呈現出被現代龐大信息流所埋沒的“真實”,讓所有經歷過時代變革的讀者都產生了心理上極大的共鳴。
三、客觀真實與主觀情感:旅居他鄉中的情感激蕩
“非虛構寫作”的概念起源于20 世紀50 年代初的“新新聞主義”,這種新聞寫作理論主張記者發揮能動作用,從幕后走到臺前,在報道中重現社會現實。“非虛構寫作”繼承了“新新聞主義”中發揮記者能動性的特點,作者在敘事中以個人的身份出現在現場,在對現實進行記錄的同時抒發自己的主觀感受。不同于“新新聞主義”的是,“非虛構寫作”屬于文學領域,在注重新聞真實性和客觀性的同時又具有強烈的個人色彩,并兼顧了文本的藝術價值[7](36-39)。本文中提到的作家彼得·海斯勒曾任《紐約客》駐北京記者,張彤禾曾作為《華爾街日報》的記者在中國生活了10 年。除這兩名資深記者之外,其他的作家也都在創作的過程中運用田野調查方法,并使用了大量新聞報道寫作技巧,從而撰寫出了一部部既“克制”又帶有主觀色彩的非虛構作品。這些文本中的“克制”既體現在語言上,又體現在情感上。但即便是客觀敘事,非虛構文本中也會帶有作者本人的主觀立場。而在目睹社會現實時,這批作者的外國人身份又給予了他們更加直觀且強烈的異域體驗,他們的種種情感波動均呈現在了他們所寫下的文字中。
(一)對傳統農耕文明的追思
中國社會在轟轟烈烈的城鎮化進程中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社會巨變在這些美國作家的非虛構作品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在來到中國之前,農村與城市的巨大差距就已經烙進了他們的觀念意識中,這也成了他們作品中的一個重要的主旋律。不同于將寫作重心放在城市文明和都市生活的大部分中國作家及新聞記者,彼得·海斯勒等人的文本中蘊藏著對于農耕文明的追思以及對現代城市文明的批判性思考。傳統農耕文明作為過去生活的象征,給予了這些美國作家精神與心靈上的滿足感和歸屬感。同時,他們真切的筆觸讓無數曾生活在舊時中國農村或是對傳統農村生活懷有向往的人們深受感動。邁克爾·麥爾在《東北游記》的前六章中耗費大量的筆墨敘寫了自己在東北的生活經歷,他在一個片段中寫道:“炕的旁邊是一張圓桌,上面擺滿了熱氣騰騰的豐盛飯菜,有回鍋肉、炸蘑菇、蒜蓉野菜。每家每戶的窗子幾乎都有墻那么大,包著塑料紙,隔熱防風。用來蒸飯的米就來自窗外的一畝三分地。做這些飯菜的大鐵鍋嵌在一個水泥灶里,生火也是用稻草秸稈。”東北農村的生活在他的筆下無比質樸真實,就連一頓普通的農家飯,也能讓無數曾在農村生活的讀者感同身受,回憶起舊時鄉村的氣味。盡管許多生活在中國農村的底層人民迫切地渴望走出農村,去大城市闖出一番天地,但是這些美國非虛構作家在目睹了這一切之后,卻仍然表現出一種對農耕生活的向往與追憶。農耕生活相對于擁擠的城市生活于他們而言是一方凈土,帶給他們的是一絲安寧,傳統鄉村是他們在喧囂的城市外返璞歸真的喘息之地。
(二)對中國世情社會的切身體驗
彼得·海斯勒在駕車環游中國的途中逐漸掌握了中國社會的“潛規則”,在《尋路中國》中,他筆下的魏子淇為了經商,學會了通過給人遞煙、請人吃飯以拉近關系。書中還提到了魏子淇的智障大哥。在三岔村,幾乎沒有人理睬這個癡癡傻傻的智力障礙者,但彼得·海斯勒卻從智障大哥身上看到了他對與人交流的渴望。一開始,村里只有男孩魏嘉會和他一起玩,但魏嘉長大之后,感受到了村里人對智障大哥的輕視,于是他漸漸地也和別人一樣不再理會智障大哥。魏子淇對經商關系網的摸索以及智障大哥在村里被孤立的窘狀無不讓彼得·海斯勒陷入沉思。癡迷于中國功夫的馬修·波利曾接受過美國的精英教育,為了在少林寺學習功夫,他不得不托中間人向少林方丈獻上紅包。面對每個月1300 美元的學費,馬修曾感到十分震驚,他曾以為少林寺就像電影里一樣,是一個不摻雜金錢利益的清凈之地。在少林寺生活了幾個月后,馬修學到了中國人拉近關系的方式,學會了像中國人一樣劃拳陪酒,最后成功砍價。作為少林弟子的馬修·波利在書中還提到了自己給和尚們當英語翻譯,并在酒桌上為少林寺談生意的故事。不同于一開始的震驚,他開始漸漸接受了少林寺被“商業化”“利益化”的事實。他在《少林很忙》一書中寫道:“來少林寺前,在我的想象中,這是一座風雨飄搖中的寺廟,結果卻發現這里到處是商業陷阱。”[8](p97)雖然在中國學習功夫時經歷了種種波折,但馬修·波利在回到美國之后,仍然無比懷念在少林寺的生活,他還收了一些徒弟,先后送了約50人來少林寺學功夫。美國動物學家喬治·夏勒在中國花費了五年時間研究大熊貓的生活習性,這名熱愛自然、熱愛動物的專家為了保護和研究稀有的大熊貓而來到中國。他說:“命運和機會讓我選擇了中國,我把頭腦中的GPS 固定指向了這個國家。我對這個國家的最大貢獻,就是帶動了一批具備專業素養的本地學者,他們將為荒野保護而奮斗,同時激勵了年輕的研究者全身心投入生態保護,追尋自然之美。”[9](p21)然而,在《最后的熊貓》中,他敘寫了自己在推進熊貓項目中感到的種種失望。中國社會的復雜潛規則讓喬治·夏勒感到十分無措,作為一名外國專家,他想直言自己對熊貓問題的困惑,但對問題過于直白的剖析,卻會讓人感到不快,文化的習慣的沖突讓他久久難以釋懷。在對熊貓問題困惑和中國社會的復雜情感下,喬治·夏勒寫下了《最后的熊貓》一書。面對飛速發展的中國社會以及復雜的社會世情,這批來自美國的非虛構作家在對客觀現實進行忠實繪寫的同時也無一不抒發自己的主觀情感。他們對中國的情感混雜著對傳統農耕文明的懷念與對現代化文明的驚嘆,盡管他們對混雜著思想文化差異所帶來的問題、遭遇的困境感到迷惘痛苦,但他們仍與他們筆下的一個個在社會困境中拼搏的鮮活個體一樣,以樂觀的態度期待著中國在未來的改變。
四、文化之橋:多重視角下中國邁向世界舞臺的真實寫照
根據人類學家的觀點,若是以自己民族的文化立場對其他民族的價值觀念進行評判,則很容易產生偏見。而非虛構作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真實地重現歷史和社會現實,規避那些源于個人中心主義或民族中心主義的偏見[10](54-57)。彼得·海斯勒等美國作家通過在中國的長時間旅居生活,開始不斷地嘗試理解中國、認同中國、融入中國。他們帶著西方資本主義的文化背景與價值觀念與中國社會不斷磨合,在學習漢語與中國文化的同時不斷深入了解中國各地的地域文化與社會習俗。正如第一章所述,這些美國作家在融入中國的過程中,以外來者的身份審視中國,但出于他們多年來對中國文化與中國社會的了解,他們又能以中國居民的身份審視中國在改革開放后迅速發展并逐漸邁向國際舞臺的進程,這種特殊的雙重視角為他們提供了更加開闊的角度,使他們在審視中國走向世界的過程中,思路變得更為多元化且更具包容性,并能更清醒地看到中國當下的社會現實,為中國內外的讀者呈現出更為客觀的中國社
會[11](34-37)。
自改革開放以來,曾經封閉的中國打開了通向世界的大門,中國人開始積極擁抱世界,世界也不再是一個僅具象征意義的符號,在中國飛速發展的信息化社會中,世界的輪廓開始變得清晰可見。《再會,老北京》等非虛構作品真實再現了“在中國管窺世界”的情形,比如邁克爾·麥爾筆下轟轟烈烈籌辦2008 年北京奧運會的北京城,讓麥爾驚嘆于中國力量的同時又惋惜消逝的胡同文化。他說:“我寫這本書的目的是告訴人們,我們曾經居住在21 世紀的北京,這是一種怎樣的生活方式。當我剛開始寫這本書的時候,我以為我所寫的是傳統建筑,但后來發現,鄰居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這些角色有了自己的命運。我想念曾經生活在老北京胡同里的每一天。”
然而,跨國身份也給這些美國作家帶來過諸多不便。彼得·海斯勒、邁克爾·麥爾等人無不因跨國身份而在旅程中觸犯過種種禁忌,或因為中西文化價值觀的不同,在旅途中引發過各類沖突。與彼得·海斯勒等其他旅居型作家不同的是,少林寺是癡迷少林功夫的馬修·波利的最主要居所,他在苦練中國功夫的同時,體驗到的是“少林寺”這個狹小卻復雜的人情社會。20世紀90年代,少林寺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象征,已經走在了邁向國際舞臺的前列。少林寺的和尚們時常會去海外進行巡演,同時,少林寺平日里也會接待許多來自英國、法國、美國等世界各地的游客和記者。馬修(2014)在《少林很忙》一書中曾寫道,在當時的中國,嵩山少林寺已經成了許多歐美游客在中國旅程中的重要景點。有著跨國身份的馬修在少林寺的學習始終被和尚們加上了一種“外交”性質。馬修在給少林方丈釋永信包了1111 元的紅包后,成功地進入了少林寺開始學習。在學習過程中,師父建議馬修把少林寺寫在書里,向全世界傳播少林寺。在一次“打群架”的時候,少林寺的和尚們不帶馬修,和尚們告訴他,如果他在斗毆中受了傷,少林寺在國際上的名聲就會被損害。
置身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國以開放的姿態擁抱世界。在中國接受西方價值思想影響的同時,無數外國友人被中國的獨特文明與大好河山所吸引。對于彼得·海斯勒等旅居作家而言,他們在體驗中國社會的過程中吸收了中國文明,在帶著自己的特殊身份看中國的同時,也借助中國積累的經驗反觀世界。彼得·海斯勒在中國生活了十余年,作為一個幾乎已完全融入中國社會的美國人,他發現自己看中國和看世界的視角正在發生變化——中國成了他的參照物。這樣的視角讓他能夠對美國的文化和價值觀進一步反思,“美國人”身份的淡化讓他在思考中國與世界之時變得更加客觀。這批美國非虛構作家的作品為外國人看中國提供了更為多元的視角。雖然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已經逐步邁進國際舞臺,但世界對中國仍然留存著“封建”“落后”“封閉”等刻板印象。《尋路中國》等作品呈現出中國社會巨變中的個體命運,它們讓廣大西方讀者改變了因資料缺失而對中國原有的刻板印象,看到了改革開放浪潮下的真實中國。
五、結語
回望中國20世紀的紀實作品,如沈從文的《邊城》(1934)、蕭紅的《呼蘭河傳》(1940)、陳忠實的《白鹿原》(1993)等,雖然它們都帶著“真實的影子”,但與新世紀非虛構文本不同的是,這些作品的素材大多來自作家們童年的鄉鎮生活記憶,作家通過對自身記憶進行重組,用“非虛構”的話語構建出一個個“虛構”的故事。而以彼得·海斯勒為代表的美國作家創作的非虛構文本則是以介入性的姿態深入中國的每一個角落,通過“在場的言說”豐富文本的內涵,同時試圖尋找反映社會現實與豐富文本藝術性之間的平衡。
過去,世界對中國的想象停留在片面的宣傳與主觀臆斷中。這些旅居中國的外國作家們在記述中國的同時融入中國,成為中國社會圖景中的一部分。在被信息洪流包裹的現代社會中,他們通過對當代中國個體生命的真實敘寫讓讀者見證了宏大歷史潮流下的多元生命姿態。對于此類非虛構作品的讀者來說,中國不再僅僅是“神秘的東方古國”或“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等單調的形象,他們從書中看到了發展迅速且復雜多變的中國現代社會圖景,以及這幅現代社會圖景之下一個個有血有肉、有思想、有靈魂的鮮活個體。然而,在城鎮化與工業化的浪潮中,這些作家為傳統農耕文明的消逝以及個體融入現代社會的困窘也表現出了難以言喻的憂傷,他們對個體生命的觀察賦予了文本的真實性,而他們主觀的情感激蕩則增添了文本的藝術性和深刻性。通過外國學者的視角不僅讓世界看到了中國,也讓中國人能夠重新審視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