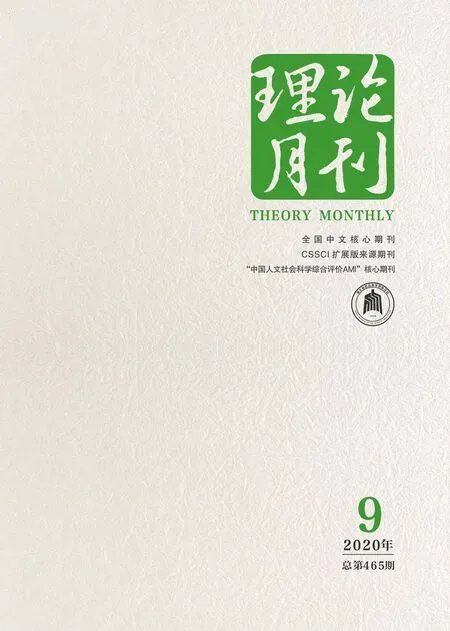“古田會議決議”記憶之場建構(gòu)的四個(gè)維度
□馮思淇
(河南師范大學(xué) 中國共產(chǎn)黨革命精神與中原紅色文化資源研究中心,河南 新鄉(xiāng)453007)
1929 年的古田會議,以在建黨和建軍原則上的原創(chuàng)性載入中國共產(chǎn)黨發(fā)展的史冊。圍繞古田會議的召開所形成的古田會議精神,成為中國共產(chǎn)黨革命精神譜系中的重要一環(huán)。對古田會議的研究,近些年一直是黨史黨建研究的熱點(diǎn),并取得了長足進(jìn)展,召開了多次相關(guān)學(xué)術(shù)會議,涌現(xiàn)出一批有分量的專著和論文。研究集中在古田會議的歷史地位和意義、古田會議與黨的建設(shè)以及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同時(shí),研究也存在著“重述輕論”的傾向,尤其是在如何傳承好古田會議精神上缺乏理論建構(gòu)。因此,本文嘗試運(yùn)用諾拉的記憶之場理論,以《中國共產(chǎn)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別稱古田會議決議,以下簡稱《決議》)文本為研究對象,從理論、歷史、實(shí)踐和價(jià)值四個(gè)維度闡述如何傳承好古田會議精神。
一、理論維度:《決議》文本記憶之場的學(xué)理基礎(chǔ)
建構(gòu)記憶之場需要學(xué)理支撐,涉及歷史學(xué)、文化學(xué)以及社會記憶的相關(guān)理論,將尊重歷史的客觀性與記憶之場的建構(gòu)性結(jié)合起來。諾拉的記憶之場理論為研究古田會議精神提供了新的理論視角,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給我們提供了建構(gòu)記憶之場的基本立場,歷史與邏輯的統(tǒng)一是我們研究的基本方法。
(一)借鑒記憶之場理論,以新的理論視角介入中國共產(chǎn)黨革命精神研究
記憶之場理論的提出者是法國歷史學(xué)家皮埃爾·諾拉。這一理論提出的歷史背景是20 世紀(jì)70年代法國“經(jīng)濟(jì)快速增長的終結(jié),戴高樂主義、共產(chǎn)主義和革命觀念的消退,國外壓力的強(qiáng)烈感受”[1](p205-219),使得傳統(tǒng)的民族主義出現(xiàn)衰落。諾拉指出:“之所以有記憶之場,是因?yàn)橐呀?jīng)不存在記憶的環(huán)境”[2](p4),導(dǎo)致人們迷失在“龐大得令人頭暈?zāi)垦5牟牧戏e累和深不可測的資料庫”中。在諾拉看來,記憶之場指的是“一切在物質(zhì)或精神層面具有重大意義的統(tǒng)一體”[2](p87),這種場所可以是檔案、紀(jì)念物,也可以是重大事件或重要文獻(xiàn),即在經(jīng)歷了歷史沉淀后仍然對現(xiàn)代具有價(jià)值意義的符號象征。社會記憶理論認(rèn)為,歷史越久遠(yuǎn),人們對過去的記憶就越模糊。只有不斷喚醒、激活、重構(gòu)、刻寫人們的社會記憶,才能克服歷史遺忘和歷史謊言,構(gòu)筑起當(dāng)下的精神家園。記憶之場的理論旨趣在于試圖超越拉維斯主義和年鑒學(xué)派進(jìn)而重構(gòu)法國歷史,從記憶中發(fā)現(xiàn)歷史,重樹法國歷史的神圣性,提升國民的民族認(rèn)同感。也就是想“借助‘記憶之場’為法蘭西動一場手術(shù),就是將整個(gè)法蘭西變成‘記憶之場’”[2](p85)。記憶之場理論為我們重新審視中國共產(chǎn)黨革命精神的生成與發(fā)展提供了新的理論視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jìn)入了新時(shí)代,我們的未來愿景是建設(shè)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強(qiáng)國,需要熔鑄中國精神。我們借鑒記憶之場理論,不是一種對已逝事物的懷舊的印記,而是對民族復(fù)興美好未來的希冀與期盼,自覺將中國共產(chǎn)黨革命精神作為實(shí)現(xiàn)理想的精神動力。古田會議的《決議》文本就是一個(gè)很好的記憶場所,我們從文本的字里行間中透視歷史、關(guān)照當(dāng)下,有助于破解承載著中國精神的“基因密碼”。總之,諾拉的記憶之場理論是立足當(dāng)下去重構(gòu)法蘭西民族文化。我們借鑒記憶之場理論需要在尊重中華民族歷史的基礎(chǔ)上,從當(dāng)下中國的實(shí)際出發(fā),在長時(shí)段上建構(gòu)新時(shí)代中國共產(chǎn)黨革命精神的社會記憶。
(二)立足唯物史觀,從當(dāng)時(shí)實(shí)際出發(fā)建構(gòu)記憶場所
1929 年6 月14 日,毛澤東在《給林彪的信》中強(qiáng)調(diào):“我們是唯物史觀論者,凡事要從歷史和環(huán)境兩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3](p74)唯物史觀是我們考察現(xiàn)實(shí)的人及其歷史發(fā)展的科學(xué)理論。唯物史觀堅(jiān)持從當(dāng)時(shí)當(dāng)?shù)氐膶?shí)際出發(fā),得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反對從經(jīng)驗(yàn)或現(xiàn)成原則出發(fā)去“裁剪事實(shí)”。記憶之場的建構(gòu)必須建立在科學(xué)歷史觀的基礎(chǔ)之上,從現(xiàn)實(shí)的人的活動出發(fā),揭示歷史發(fā)展的必然性以及歷史主體在歷史活動中表現(xiàn)出的主觀能動性。諾拉指出:“記憶之場是我們民族歷史的關(guān)節(jié)點(diǎn)。”[2](p31)《決議》文本的訂立是實(shí)際斗爭需要的產(chǎn)物,而不是毛澤東個(gè)人的主觀臆想。當(dāng)時(shí)的紅四軍力量相對弱小且成分復(fù)雜,在人數(shù)上只三四千人,成分上包括游民、農(nóng)民、學(xué)生等非工人階級分子,思想上難以統(tǒng)一。同時(shí),紅四軍面對的敵人是數(shù)倍于乃至十幾倍于紅軍的國民黨正規(guī)部隊(duì)和地方軍閥部隊(duì)。而且經(jīng)過“大革命”的失敗,共產(chǎn)黨員遭屠殺多達(dá)十幾萬,黨的組織也遭到嚴(yán)重破壞。如何在險(xiǎn)峻的斗爭環(huán)境下生存下來并不斷發(fā)展壯大,而且要把紅軍鍛造出一支不同于軍閥、土匪的新型軍隊(duì),是一個(gè)關(guān)乎革命前途的重大問題。從開辟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到開辟贛南閩西革命根據(jù)地,毛澤東在調(diào)查研究的基礎(chǔ)上進(jìn)行深入思考,得出建黨建軍的正確原則和經(jīng)驗(yàn)總結(jié),集中體現(xiàn)在《決議》文本中。建構(gòu)古田會議的記憶之場,必須走向歷史深處,從《決議》文本看當(dāng)時(shí)的社會歷史條件和紅四軍面臨的問題以及采取的應(yīng)對之策。
(三)堅(jiān)持歷史與邏輯相統(tǒng)一,邏輯再現(xiàn)歷史的來龍去脈
歷史是現(xiàn)實(shí)社會中的人們活生生的實(shí)踐活動,邏輯是人們的理論思維工具和成果,表現(xiàn)為概念、判斷和推理等形式,以及對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的思維的規(guī)律性認(rèn)識。我們在尊重歷史客觀性的基礎(chǔ)上,從認(rèn)識上再現(xiàn)歷史,揭示歷史發(fā)展的規(guī)律性。而不是如黑格爾那樣,將歷史看成是“絕對精神”的外化。記憶之場不是簡單的歷史再現(xiàn)而是建構(gòu)。諾拉指出:“記憶不是回憶,而是身在現(xiàn)在,對過去的統(tǒng)籌布局和管理。”[2](p91)對古田會議決議文本記憶之場的建構(gòu)是要通過“解釋它的結(jié)構(gòu),確立它的層次,分辨沉積的部分與流失的部分,剝離出它堅(jiān)硬的內(nèi)核,揭露假象和錯(cuò)覺,讓它變得清晰起來,道破它的未明之意”[2](p87),升華為中國共產(chǎn)黨乃至中華民族的“某種共性”的象征性元素。古田會議討論通過了毛澤東主持起草的《中國共產(chǎn)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這是當(dāng)時(shí)有針對性地解決紅四軍存在的問題所取得的成果,可以從爭論的產(chǎn)生、矛盾的激化、問題的解決三個(gè)階段來認(rèn)識。首先,爭論緣起于離開井岡山之后紅四軍處于游擊狀態(tài)所導(dǎo)致的思想混亂,上至領(lǐng)導(dǎo)人下至普通黨員和士兵,對紅四軍的前途發(fā)展未有清晰認(rèn)識,圍繞黨的領(lǐng)導(dǎo)、民主集中制、根據(jù)地建設(shè)等問題出現(xiàn)了爭論。毛澤東和朱德分別寫給林彪的信的公開則使“朱毛之爭在軍內(nèi)公開化”[4](p37)。此時(shí),中央派曾在法國留學(xué)、蘇聯(lián)學(xué)習(xí)過的劉安恭來到紅四軍,并委以臨時(shí)軍委書記兼政治部主任,但劉到來后竟提出紅四軍領(lǐng)導(dǎo)人分為了兩派,并試圖限制前委的領(lǐng)導(dǎo)權(quán),要“前委只討論行動問題,不要管其他事”。劉的做法對爭論擴(kuò)大化起了推波效應(yīng)。其次,中共紅四軍七大和八大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反而使?fàn)幷摂U(kuò)大化。1929年6月22日,紅四軍黨的七大召開,大家暢所欲言但莫衷一是,會議決議中對不少問題“都作了折中平衡、息事寧人的批評和回答”[5](p60),對單純軍事觀點(diǎn)、極端民主化、流寇思想等非無產(chǎn)階級的思想觀點(diǎn)沒有克服。1929年9月下旬,朱德主持召開紅四軍黨的八大,此時(shí)陳毅去了上海,毛澤東在蛟洋養(yǎng)病,這次會議大家“七嘴八舌,毫無結(jié)果”[6](p220)。最后,陳毅帶來了中共中央的“九月來信”,信中肯定了毛澤東的“工農(nóng)武裝割據(jù)”思想,要求紅四軍官兵維護(hù)朱德、毛澤東的領(lǐng)導(dǎo)權(quán)威,明確毛澤東仍為前委書記。在紅四軍黨的九大上,毛澤東、朱德、陳毅等關(guān)鍵人物本著怎樣把黨建設(shè)好、把軍隊(duì)建設(shè)好、推進(jìn)革命發(fā)展的目的,最終在達(dá)成共識的基礎(chǔ)上實(shí)現(xiàn)了新的團(tuán)結(jié)。客觀地講,大革命失敗后革命處于低潮,中國共產(chǎn)黨人對革命的方式和道路問題,思想出現(xiàn)分歧在所難免,這種現(xiàn)象不僅在紅四軍存在,在其他紅軍甚至中央領(lǐng)導(dǎo)中間也存在。正所謂真理越辯越明,在爭論中形成共識并堅(jiān)定貫徹之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優(yōu)點(diǎn)之一。
二、歷史維度:《決議》文本為推動中國革命發(fā)展提供新因素
《決議》文本記憶之場的建構(gòu),需要從整個(gè)中國共產(chǎn)黨革命史的長時(shí)段來考察古田會議決議,著眼于考察該會議為推動中國革命發(fā)展提供了什么新因素。這主要集中在樹立新的意識形態(tài)、形塑新的組織架構(gòu)、鍛造新的革命力量三個(gè)方面。
(一)《決議》文本樹立新的意識形態(tài)
自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至“大革命”失敗,這一時(shí)期黨在政治斗爭和軍事斗爭方面尚不成熟,基本上是按照共產(chǎn)國際指示行動,沒有提出符合自身利益和本國國情的思想和理論。“大革命”失敗后,毛澤東率領(lǐng)秋收起義隊(duì)伍開辟了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開始探索中國革命的新道路。既然是探索,就必然會出現(xiàn)多種思想觀點(diǎn),通過不同思想觀點(diǎn)之間的相互碰撞,逐漸樹立起中國無產(chǎn)階級政黨的意識形態(tài)。在開辟贛南閩西革命根據(jù)地過程中,通過批判黨內(nèi)存在的錯(cuò)誤思想來樹立新的意識形態(tài)。《決議》文本在第一部分逐一指出單純軍事觀點(diǎn)、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點(diǎn)、絕對平均主義、主觀主義、個(gè)人主義、流寇思想和盲動主義殘余共八個(gè)方面的錯(cuò)誤思想意識產(chǎn)生的原因及危害,幫助同志們實(shí)事求是看待當(dāng)前斗爭。這在1929 年4 月5日《紅軍第四軍前委給中央的信》以及6月14日毛澤東同志寫給林彪的信中已有論述。同時(shí),《決議》規(guī)范了黨內(nèi)批評的原則,明確指出:“黨內(nèi)批評是堅(jiān)強(qiáng)黨的組織、增加黨的戰(zhàn)斗力的武器”,黨內(nèi)批評要“抓大放小”,聚焦在政治和組織上的錯(cuò)誤,不能將黨內(nèi)批評變?yōu)檫M(jìn)行個(gè)人攻擊的工具。新的意識形態(tài)體現(xiàn)在對紅軍的科學(xué)定位、加強(qiáng)黨的領(lǐng)導(dǎo)、依靠群眾以及重視根據(jù)地建設(shè)的思想。紅軍是新型軍隊(duì),它不同于國民黨軍隊(duì)的重要特點(diǎn)就在于黨指揮槍,而不是槍指揮黨。中國共產(chǎn)黨早在“三灣改編”時(shí)就“把支部建在連上”,以黨委、支部的書記擔(dān)任同級黨代表,實(shí)行黨委、支部領(lǐng)導(dǎo)下的首長分工負(fù)責(zé)制,從制度上保證黨的集體領(lǐng)導(dǎo),防止個(gè)人專權(quán)。《決議》中明確指出了紅軍的性質(zhì)是“執(zhí)行革命的政治任務(wù)的武裝集團(tuán)”[3](p79),革命的政治任務(wù)是由中國共產(chǎn)黨來制定的,最終目標(biāo)是要實(shí)現(xiàn)人民解放,建立全國政權(quán)。軍隊(duì)必須貫徹落實(shí)黨的主張,除了打仗還賦有宣傳、組織、武裝群眾,建立革命政權(quán)的任務(wù)。總之,新的意識形態(tài)是在黨的領(lǐng)導(dǎo)下,依靠人民群眾,以農(nóng)村根據(jù)地為依托,通過武裝斗爭的形式,逐步取得革命勝利。
(二)《決議》文本形塑新的組織架構(gòu)
首先,精簡機(jī)構(gòu)統(tǒng)一指揮。通過黨內(nèi)斗爭和實(shí)踐比較,毛澤東使大多數(shù)人贊同取消軍委①井岡山時(shí)期紅四軍設(shè)有前委和軍委,但在實(shí)際斗爭中由于指揮不統(tǒng)一而不斷受挫。1929年2月在尋烏召開的前委會上作出了暫時(shí)撤銷軍委,權(quán)力集中于前委的決定。后劉安恭同志到紅四軍后又主張?jiān)O(shè)立軍委。,使權(quán)力集中于前委。軍中的政治系統(tǒng)和軍事系統(tǒng)“在前委指導(dǎo)之下,平行地執(zhí)行工作”[3](p113)。這樣可以保證命令統(tǒng)一,避免多頭指揮,貫徹執(zhí)行高效而有力。與之配套的是強(qiáng)調(diào)民主集中制,側(cè)重在集中指導(dǎo)之下的民主,消除極端民主化錯(cuò)誤思想。堅(jiān)強(qiáng)統(tǒng)一的指揮使得紅四軍化為一只“鐵拳”,打開了贛南閩西革命根據(jù)地的新局面。不過兩三年的時(shí)間,于1931 年創(chuàng)建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成效巨大。其次,嚴(yán)格組織程序,提高入黨條件。黨員的質(zhì)量直接決定政治任務(wù)和軍事任務(wù)的完成情況,不能太過隨意。《決議》中重新規(guī)定了入黨條件:“(1)政治觀念沒有錯(cuò)誤的(包括階級覺悟);(2)忠實(shí);(3)有犧牲精神,能積極工作;(4)沒有發(fā)洋財(cái)?shù)挠^念;(5)不吃鴉片、不賭博。”同時(shí),還提出了加強(qiáng)黨員的教育,提高黨員的覺悟。再次,強(qiáng)調(diào)黨的紀(jì)律。毛澤東從政治高度看待紀(jì)律,指出:“軍紀(jì)問題是紅軍一個(gè)很大的政治問題”[3](p69),必須從嚴(yán)。《決議》中重申了鐵的紀(jì)律必須遵守,強(qiáng)調(diào)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的原則,強(qiáng)調(diào)堅(jiān)決及時(shí)地執(zhí)行上級的決議和命令,當(dāng)然也包括執(zhí)行“三大紀(jì)律,八項(xiàng)注意”。當(dāng)時(shí)已經(jīng)將紅四軍的紀(jì)律改編成了朗朗上口的“口號”,反復(fù)傳唱,建構(gòu)起集體記憶。不過與現(xiàn)在我們所熟知的“三大紀(jì)律,八項(xiàng)注意”的內(nèi)容有所不同。
(三)《決議》文本鍛造新的革命力量
首先,通過宣傳爭取革命群眾。《決議》指出了紅軍宣傳工作的任務(wù)和地位。其任務(wù)是“擴(kuò)大政治影響爭取廣大群眾。”其地位是“紅軍第一個(gè)重大工作”[3](p96)。可見,宣傳工作在當(dāng)時(shí)是排在第一位的,超過了軍事斗爭。宣傳工作的對象很廣泛,包括城市貧民、婦女、青年,甚至包括流氓無產(chǎn)階級和地主武裝的民團(tuán)和靖衛(wèi)團(tuán)。宣傳的方式要多樣,比如傳單、布告、宣言、壁報(bào)、革命歌謠、畫報(bào)、娛樂活動、化妝宣傳、開群眾大會等。宣傳的形式應(yīng)因地制宜、因?qū)ο蟮牟煌扇〔煌男问健P麄鲀?nèi)容上要簡潔,宣傳的節(jié)奏要快。宣傳隊(duì)伍建設(shè)方面,人員配備要精干,有計(jì)劃地進(jìn)行培訓(xùn),保證足夠的經(jīng)費(fèi)等。此外,優(yōu)待敵方的俘虜兵和傷兵,也是繼續(xù)政治宣傳所必要的。其次,通過政治訓(xùn)練打造革命士兵。革命士兵與舊軍隊(duì)中的士兵的根本區(qū)別在于政治立場。《決議》中要求全軍上下從軍、縱隊(duì)到支隊(duì),都要上政治課,班級設(shè)置上分為普通班、特別班和干部班三類,做到全覆蓋。講授內(nèi)容上要求政治訓(xùn)練,編寫內(nèi)容豐富的教材,從黨的政策、革命觀、軍隊(duì)的紀(jì)律、國內(nèi)外軍隊(duì)的比較、革命故事和歌曲等共十九個(gè)方面。政治教育方法符合教育的基本規(guī)律。《決議》在政治訓(xùn)練制度化方面也做了詳細(xì)規(guī)定,將政治教育的方式分為集合講話和個(gè)別談話,言語上照顧到不同對象、環(huán)境和態(tài)度等,可謂“情真意切”。此外,還包括士兵的娛樂活動、對新兵、俘虜兵和青年士兵的特別教育,要讓他們知曉紅軍的生活習(xí)慣、價(jià)值觀、組織系統(tǒng)等。最后,通過廢除肉刑、優(yōu)待傷病員等鞏固革命陣營,提振部隊(duì)?wèi)?zhàn)士的革命熱情和勇氣。
三、實(shí)踐維度:《決議》文本的物質(zhì)性、象征性與功能性呈現(xiàn)
建構(gòu)記憶之場需要在實(shí)踐上具有可操作性,具體規(guī)定如何做才能實(shí)現(xiàn)記憶之場的建構(gòu)。諾拉指出:記憶之場是實(shí)在的、象征性的和功能性的場所,三者同時(shí)存在僅程度不同。其中,檔案文獻(xiàn)、重大事件、教科書、協(xié)會組織、儀式等都可以成為記憶之場從而喚起集體記憶。在實(shí)際操作上,深入挖掘和闡發(fā)《決議》文本的隱喻,需要物質(zhì)性呈現(xiàn)、象征性呈現(xiàn)與功能性呈現(xiàn)相結(jié)合。也就是通過多種途徑喚起當(dāng)代人對古田會議的社會記憶。
(一)《決議》文本記憶之場的物質(zhì)性呈現(xiàn)
物質(zhì)性呈現(xiàn)指的是古田會議召開前后留存下來的實(shí)物。諾拉認(rèn)為:“所有關(guān)于記憶的歷史和學(xué)術(shù)研究,不管它涉及的是民族記憶還是社會心態(tài)記憶,都須與實(shí)物,與事物本身打交道,所有這些研究都努力以最鮮活的方式把握實(shí)在。”[2](p31)檔案、紀(jì)念館、口述史、紅色故事就是“對一個(gè)逝去的、脆弱的過去的不容置疑的見證。”[2](p64)首先,檔案是“旨在承載記憶或用于記錄的公共文本”[2](p482)。現(xiàn)有的文獻(xiàn)檔案有的是對贛南閩西根據(jù)地時(shí)期的檔案文獻(xiàn),如中共龍巖地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編的《閩西革命根據(jù)地史》,中共福建省委黨校黨史研究室編的《福建革命根據(jù)地革命斗爭史資料選編》,古田會議紀(jì)念館編的《古田會議文獻(xiàn)資料》《見證古田會議》;有的是專家學(xué)者的論著,如蔣伯英、藍(lán)榮田編著的《閩西革命根據(jù)地史話》,蔣伯英著有《1929 朱毛紅軍與古田會議》,楊慶旺著的《中共重要會議會址考察記》;還有的則見于相關(guān)人物傳記中,如《毛澤東傳》《朱德傳》《陳毅傳》等。這些文獻(xiàn)檔案以其客觀性和權(quán)威性,成為建構(gòu)古田會議精神記憶之場的重要載體。其次,口述史的整理。口述史一方面可以生動地再現(xiàn)歷史,填補(bǔ)重大事件和普通民眾生活經(jīng)歷中那些沒有文字記載的空白,并為歷史研究提供新的視角、方法和啟示,也可以表現(xiàn)出當(dāng)時(shí)人們的社會心理的發(fā)展過程。另一方面,口述對象盡管參與了歷史,言說的都是自己的親身經(jīng)歷甚至是一些鮮為人知的細(xì)節(jié),但由于生活環(huán)境、工作崗位、文化水平、價(jià)值取向的不同,對同一事件擁有不同的記憶,甚至有些個(gè)體記憶與文獻(xiàn)資料的記載截然相反。口述史料的這種相對不可靠性需要文獻(xiàn)史料的補(bǔ)充,將口述史料與文獻(xiàn)史料相互印證。例如陳毅、肖華等老同事的回憶錄《回憶中央蘇區(qū)》,中共龍巖地委編的革命回憶錄《閩西的春天》,蕭克的回憶錄《朱毛紅軍側(cè)記》,還包括一些單位對當(dāng)年老紅軍的采訪。這樣可以多角度、多層次地再現(xiàn)活生生的歷史。再次,紀(jì)念館建設(shè)卓有成效。福建的上杭、龍巖等地建有“古田會議會址”“古田會議紀(jì)念館”“毛澤東才溪鄉(xiāng)調(diào)查紀(jì)念館”“中央蘇區(qū)(閩西)歷史博物館”等,保存文物豐富,成為重要的紅色文化資源。最后,紅色故事的搜集整理。《古田之光》將閩西革命小故事匯集成冊,內(nèi)容包括當(dāng)時(shí)的領(lǐng)導(dǎo)人和普通革命群眾,比如《毛澤東病中當(dāng)紅娘》《張鼎丞請客》《在紅色的交通線上》,細(xì)化了人物的日常生活,展現(xiàn)了人物的喜怒哀樂的心理態(tài)度和性格特征,為理解歷史打開了一扇“窗戶”。隨著5G、VR、人工智能技術(shù)的普及,紀(jì)念館的數(shù)字化以及紅色故事的虛擬再現(xiàn)成為傳承紅色文化的新手段。
(二)《決議》文本記憶之場的象征性呈現(xiàn)
象征性呈現(xiàn)指的是記憶之場通過某個(gè)事件或某個(gè)僅有少數(shù)人體驗(yàn)過的經(jīng)驗(yàn)而描繪了大多數(shù)人的特征。《決議》文本作為黨的建設(shè)和軍隊(duì)建設(shè)的重要文獻(xiàn),我們可以從它的歷史背景、人物活動、出臺過程、價(jià)值意義中提煉古田會議精神,作為建構(gòu)記憶之場的象征性呈現(xiàn),使記憶之場變成“一切在物質(zhì)或精神層面具有重大意義的統(tǒng)一體,經(jīng)由人的意志或歲月的力量,這些統(tǒng)一體已經(jīng)轉(zhuǎn)變?yōu)槿我夤餐w的記憶遺產(chǎn)的一個(gè)象征性元素”[2](p87)。古田會議精神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還未有界定和專門研究。隨著時(shí)代變遷,古田會議所具有的價(jià)值意義超越時(shí)空,“以一種新的、更加燦爛的面目出現(xiàn)在人們面前”[7](p53-56),反映了中國共產(chǎn)黨對治黨治軍規(guī)律的自覺把握,在實(shí)踐中,以官方的紀(jì)念儀式弘揚(yáng)古田會議精神。每逢五或十,都會有關(guān)于古田會議的紀(jì)念活動,結(jié)合現(xiàn)實(shí)問題闡發(fā)弘揚(yáng)古田會議精神。1979 年12 月,福建軍民在福州舉行紀(jì)念古田會議召開50 周年大會,提出要加強(qiáng)黨的建設(shè)和精神文明建設(shè),自覺抵制資產(chǎn)階級自由化思潮。1989 年,中共福建省委在古田舉行紀(jì)念古田會議60周年大會,中央領(lǐng)導(dǎo)出席,發(fā)出了“弘揚(yáng)古田會議精神,切實(shí)加強(qiáng)黨的建設(shè)”的號召。此外,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也不斷重申古田會議確立的基本原則。據(jù)統(tǒng)計(jì),黨的歷屆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共有16次。其中前15次會議僅有3次不是在北京(1934年在瑞金召開,1937年在陜西省三原縣云陽鎮(zhèn)召開,1958 年在廣州召開),其余均在北京召開。最近的一次是2014年召開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特別選在古田召開。當(dāng)天,習(xí)近平總書記帶領(lǐng)全體中央軍委委員一起參觀了古田會議會址和古田會議紀(jì)念館,瞻仰毛主席紀(jì)念園,與部隊(duì)基層干部代表一起吃“紅軍飯”。他在會上強(qiáng)調(diào)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軍隊(duì)的生命線,回顧總結(jié)了我軍政治工作的優(yōu)良傳統(tǒng),要求大家把先輩們用鮮血和生命鑄就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一代代傳承下去。這同時(shí)也是為了紀(jì)念古田會議召開85 周年,體現(xiàn)了黨中央撫今追昔、不忘人民軍隊(duì)初心,打造新時(shí)代革命軍隊(duì)的鮮明意志。
(三)《決議》文本記憶之場的功能性呈現(xiàn)
功能性呈現(xiàn)指的是記憶之場承擔(dān)了記憶的塑造和傳承的職責(zé)。哈布瓦赫指出:“人們不能只是在思想中再現(xiàn)他們生活中以前的事件,而且還要潤飾它們,削減它們,或者完善它們,乃至我們賦予了它們一種現(xiàn)實(shí)都不曾擁有的魅力。”[8](p91)實(shí)踐中可以通過詩歌、話劇、電影、郵票等藝術(shù)形式紀(jì)念古田會議。例如打油詩“蘇區(qū)干部好作風(fēng),自帶飯包去辦公,日著草鞋干革命,夜打燈籠訪貧農(nóng)。” 表達(dá)了群眾對蘇區(qū)干部好作風(fēng)的贊譽(yù)。還有“韭菜花開一桿心,剪掉髻子當(dāng)紅軍;保佑紅軍萬萬歲,婦女解放真歡心。”表達(dá)了婦女參加革命的熱情。為了紀(jì)念中國人民解放軍誕生50 周年,歌頌毛主席帶領(lǐng)人民群眾為革命和建設(shè)建立的豐功偉績,1977年福建省軍區(qū)政治部、龍巖地區(qū)革委會編寫的詩歌集——《古田頌》。其中有一首詩《工農(nóng)紅軍到古田》:“工農(nóng)紅軍到古田,紅旗飄揚(yáng)社下山,解開窮人枷和鎖,勞苦工農(nóng)喜連連。工農(nóng)紅軍到古田,革命烽火紅滿天,努力翻身鬧革命,擴(kuò)大紅軍保政權(quán)。工農(nóng)紅軍到古田,貧苦農(nóng)民分到田,租捐稅債一掃盡,口唱山歌心里甜。”反映了當(dāng)時(shí)人民群眾對共產(chǎn)黨根據(jù)地建設(shè)的支持擁護(hù)。1979年為紀(jì)念古田會議召開50 周年,由中國音樂家協(xié)會福建分會、福建省文化局音樂工作室編輯《紀(jì)念紅軍入閩、古田會議50 周年新創(chuàng)作歌曲匯編》。2012年和2016年,話劇《古田會議》和電影《古田會議》上映,產(chǎn)生巨大反響。郵票是傳承、記載和彰顯一個(gè)國家或地方歷史的重要載體。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為弘揚(yáng)革命傳統(tǒng),郵政部門曾三次發(fā)行古田會議會址的郵票,第一次是在1971 年9 月25 日,第二次是在1974 年4 月1 日,第三次是在2009 年12 月28 日,以此來紀(jì)念古田會議,傳承和銘記古田會議精神。
四、價(jià)值維度:在歷史發(fā)展中賦予《決議》文本時(shí)代意義
社會記憶貫通歷史發(fā)展的全過程,反思過去,關(guān)照當(dāng)下,展望未來。記憶之場是一個(gè)身份和意義建構(gòu)的過程。諾拉指出:記憶之場不僅僅“以它的名稱為基礎(chǔ),搜集著和它身份相符的東西,但同時(shí),它也在不斷地深化著自己的含義。”[9](p112)《決議》文本記憶之場的建構(gòu),其價(jià)值在于有助于我們強(qiáng)化中國共產(chǎn)黨的初心使命,提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認(rèn)同,凝聚實(shí)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fù)興的積極力量。
(一)把握過去,強(qiáng)化中國共產(chǎn)黨的初心使命
阿萊達(dá)·阿斯曼總結(jié)意義與記憶的關(guān)系時(shí)指出:“記憶制造意義,意義鞏固記憶。意義始終是一個(gè)建構(gòu)的東西,一個(gè)事后補(bǔ)充的意思。”[10](p149)記憶之場的建構(gòu)過程實(shí)質(zhì)上就是對歷史記憶的意義建構(gòu)過程。我們對待自己國家民族的歷史應(yīng)懷有敬畏之心、充滿溫情。習(xí)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九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走得再遠(yuǎn)、走到再光輝的未來,也不能忘記走過的過去,不能忘記為什么出發(fā)。”[11](p345)20世紀(jì)初的中國,面臨亡國滅種的危機(jī)。中國共產(chǎn)黨自誕生之日起,就自覺擔(dān)負(fù)起挽救民族危亡的責(zé)任,為民族復(fù)興和人民幸福而奮斗。不管敵人多么強(qiáng)大、形勢多么險(xiǎn)峻,也毫不畏懼和退縮。從“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到“將革命進(jìn)行到底”,從“大膽地試,大膽地闖”到“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biāo)”,折射出的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初心。建構(gòu)《決議》文本記憶之場,要求我們正確看待中國共產(chǎn)黨的革命史,從大歷史的視野中認(rèn)識古田會議確立的建黨建軍原則對中國革命勝利的歷史意義和世界意義,提高維護(hù)黨的政治核心地位和黨中央權(quán)威的自覺性。
(二)著眼當(dāng)下,提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認(rèn)同
社會記憶往往被統(tǒng)治者視為“合法化”的資源。諾拉指出:“記憶到歷史的過渡讓每個(gè)群體都肩負(fù)起了義務(wù),那就是通過自己群體的歷史復(fù)活,從而重新定義自己的身份。”[9](p103)通過建構(gòu)《決議》文本的記憶之場,理解中國共產(chǎn)黨的優(yōu)良傳統(tǒng)、紀(jì)律規(guī)矩、道德情操和情懷擔(dān)當(dāng),深刻認(rèn)識黨指揮槍、民主集中制、群眾路線、根據(jù)地建設(shè)、思想政治工作等原則對中國革命勝利的價(jià)值意義,理解中國共產(chǎn)黨與其他政黨的區(qū)別所在,深刻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選擇的必然性,它所具有獨(dú)特的制度優(yōu)勢、鮮明的理論品質(zhì)和深厚的文化底蘊(yùn)。在馬克思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三位一體”中把握我們從哪里來、我們做過什么、我們是誰的問題。柯林武德曾說過:“認(rèn)識你自己就意味著認(rèn)識你能做什么;而且既然沒有誰在嘗試之前就知道他能做什么,所以人能做什么的唯一線索就是人已經(jīng)做過什么。因而歷史學(xué)的價(jià)值就在于,它告訴我們?nèi)艘呀?jīng)做過什么,因此就告訴我們?nèi)耸鞘裁础!盵12](p11)我們就是要在一個(gè)個(gè)的記憶場所的建構(gòu)中,使人民群眾明白中國之所以是當(dāng)下的中國的歷史脈絡(luò),增強(qiáng)“四個(gè)自信”,提高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認(rèn)同。
(三)面向未來,凝聚民族復(fù)興的積極力量
記憶之場旨在“將當(dāng)下與過去連接在一起并展望未來。”[13](p140-157)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實(shí)現(xiàn)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qiáng)起來”的歷史跨越,越來越接近民族復(fù)興的光輝前景。黨的十九大,習(xí)近平總書記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jìn)入了新時(shí)代。站在新的歷史起點(diǎn)上,我們應(yīng)清醒認(rèn)識到實(shí)現(xiàn)民族復(fù)興面臨的困難和風(fēng)險(xiǎn)是前所未有、復(fù)雜多樣的,需要進(jìn)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diǎn)的偉大斗爭。一方面,必須堅(jiān)持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lǐng)導(dǎo),發(fā)揮集中力量辦大事這個(g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大優(yōu)勢;另一方面,必須團(tuán)結(jié)一切可以團(tuán)結(jié)的力量共同奮斗。唯物史觀認(rèn)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黨與人民群眾同呼吸、共命運(yùn),始終保持血肉聯(lián)系,就能凝聚起實(shí)現(xiàn)民族復(fù)興的偉力,這種力量是任何反動勢力都打不倒的。這是歷史所昭示出的基本規(guī)律。不忘本來,才能開辟未來。我們積極建構(gòu)《決議》文本的記憶之場不是單純的存儲,而是創(chuàng)造力、想象力的綜合,也就是阿萊達(dá)·阿斯曼所說的文化記憶的“力”。這種“力”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創(chuàng)造力,也是人民群眾的創(chuàng)造力,它指向未來。未來中國向著建成富強(qiáng)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強(qiáng)國目標(biāo)前進(jìn),最終達(dá)到共產(chǎn)主義的理想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