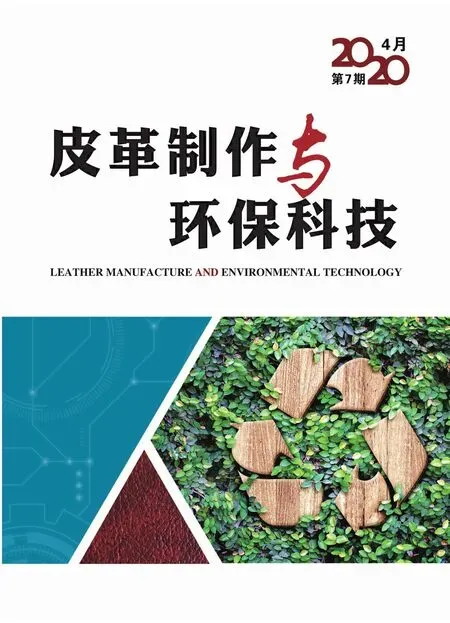新形勢下環境監察執法問題探析
李 浩 張 曄
(1.濉溪縣環境監察大隊 235100 2.安徽財經大學 233030)
0 引言
環境監察執法是一種具體的、直接的,從微觀角度切入,為環境提供保護的執法行為,由我國環境保護行政部門進行統一監督、具有強制性。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經成為新常態的情況下,對基層環境監查執法問題進行系統性地梳理并加以完善,已經成為保證國民經濟朝綠色化發展的重要途徑。
1 新形勢下環境監察執法工作存在的主要問題
1.1 基層執法中的問題無法一概而論
人民群眾、社會各級機構雖然對“環境保護”等有關字樣較為熟悉,但在實際監察執法過程中,由于問題較為復雜,實際情況無法一概而論,致使執法機構與部分單位、個人之間陷入無休止的“糾纏”。比如在國內新冠肺炎疫情趨于穩定之際,政府部門為了促進經濟發展,為城市生活增加“生氣兒”,使“地攤兒經濟”重出江湖。然而理想很豐滿,現實卻讓人大跌眼鏡。在我國很多城市本就狹窄的街道,個體商戶不僅肆意占用公共場合,甚至“借助”大量外來車輛搶占停車位,將后備箱改為“展銷位”,嚴重影響了正常的交通。當其離開時,原本整潔的地面留存了大量垃圾。基層執法人員將心比心,他們對于“擺攤兒”十分理解,但這并不是肆意破壞環境的理由。此外,如果執法僅僅圍繞“罰款”展開,則問題無法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此外,我國環境監察執法技術力量支撐不足。環境監察執法機構的發展尚未進入良性軌道,基層執法人員的裝備和技術水平嚴重落后,不能給執法帶來足夠的技術支撐。與公安系統相比較,城市隨處可見的監控系統,對于打擊偷盜、惡性犯罪等社會治安案件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然而無論是設備還是政策,都不能給基層環境監察執法提供足夠的支持。且由于違法成本較低,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不良行為的“囂張氣焰”。
1.2 群眾普遍未能對環境監察執法工作形成深入認知和理解
針對一些民營企業的污染物排放問題,生態環境局下屬的環境監察大隊肩負的責任重大。如工業品生產企業、礦山開采、工程建設項目中對于噪聲、廢渣、廢水、廢氣排放、污染物產生數量等均在其監管范圍之內。但總體而言,執法群體的數量與被執法單位、組織之間永遠無法在量級上達到“平衡”。而在“一對多”的監察執法模式下,群眾普遍未能對環境監察執法工作形成深入的認知和理解。與交通執法類似:當一群人結隊闖紅燈時,交警可能放過大部分人,針對其中的部分個體進行批評教育以及違規處罰。此時,受到處罰的個體往往產生“看似有理實則無知,對法律的適用原則缺乏足夠了解”的想法。如“我犯了錯我認,但他們也違規了,為什么不處罰他們”等,在執法人員數量不足的情況下,“選擇性執法”在世界各國均通用,且在法律中有明文規定,即確實觸犯法律,受到行政處罰的人,不得以“他人違法未接受處罰”為由,干擾執法人員的正常執法,甚至強硬地要求執法人員“給出說法”。換言之,在執法力量不足的情況下,對違法行為進行“認倒霉”式的隨機監察處罰,在法律上存在彈性空間。在環境監察執法中,基層群眾,單位、其他社會機構,對有關法律的認知和理解存在偏差,經常出現“無理取鬧”的情況,使執法工作無法深入開展。一些居心不良的非法利益獲得者,甚至將此種行為視作一種常規的對抗執法方式[1]。
綜上所述,環境監察執法任重而道遠,需要克服的困難依然較多。
2 新形勢下解決問題,提升環境監察執法水平的有效方式
2.1 建立完善的基層環境監察執法體系
“環境保護”既是宏觀層面的總體戰略規劃,又是基層監察執法中必須長期慎重對待的重要課題。因此,建立完善的基層環境監察執法體系是新形勢下解決問題、提高環境監察執法水平的基礎。首先,政府有關部門應當出臺更加詳細的政策及法律,對一切破壞環境的行為進行說明和解讀。只有當執法部門手中切實握有法律武器,能夠基于條文給出切實的懲罰依據時,執法才能“名副其實”。其次,從教育方面著手,從根源上改變年輕人的思維認知。環境保護與發展長期處于對立狀態,很多企業的發展正是以破壞環境為代價。采取強制性的手段要求其改變模式,在理論上雖然是正確的,但現實中的可操作性較低。如一些中年甚至是老年人,其工作、生活習慣早已形成,無法從內心深處改變某些根深蒂固的觀念。而執法的對象無法繞開人,在法治社會保留基本的“人情味”,是執法體系絕不可忽視的重點內容。因此,我國上海、杭州等城市“從娃娃抓起”,圍繞垃圾分類進行科普教育的方式,是從長遠角度出發的正確行為。當社會整體真正形成環保觀念,并養成既定習慣時,基層環境監察執法工作的難度自然能夠減小。最后,執法人員自身的專業性需要大幅度加強,如果在執法過程中,出現亂扔煙頭等不良行為,為被執法對象做出錯誤示范,則執法工作也難以開展[2]。
2.2 加大資金投入,為基層環境監察執法提供新型設備和政策支持
完整的監察執法體系并非通過理論的研究,以及形式上的“響應”即可形成,而是需要足夠的資金投入,為基層環境監察執法提供特定的新型設備以及政策支持。如前文提到的教育方面、法律方面的政策,能夠在很大程度輔助環境監察執法工作。但重點需要放在執法本身。首先,對基層環境監察執法的定性,即生態環境局下屬的環境監察大隊究竟擁有何種權力,在其能力范圍內,可以對何種程度的破壞環境行為開展執法工作,能夠起到的真實效果是否達到有關政策、法律的要求等。如果時至今日,社會各界對此類基礎性問題的認知依然處于模糊狀態(甚至執法機構自身都不清楚),既使資金到位,也無法切實轉變為提升執法水平的必要的工具。其次,有關環境執法方面的政策,如前文所述,需要更加清晰,否則執法人員的底氣不足,對于違法行為無法提出針對性的說法,則會使執法工作陷入全面被動。最后,執法設備的購入,可以參考歐洲發達國家的配置情況,進行全面提升[3]。
2.3 加大宣傳的力度、廣度
宣傳工作并非“動動嘴皮子”那般簡單。只有通過輿論,使正確的觀念深入人心,人民群眾才會給予基層環境監察執法工作更大的支持。比如電梯內吸煙、亂扔煙頭、小區內寵物隨地大小便等惡習,已經對城市居民的正常生活造成了極大困擾。但普遍存在的現象是,生活中似乎未見到對此類違法行為進行較為嚴厲的懲罰。我國古代著名的寓言故事“掛羊頭賣狗肉”,深刻揭示了這一道理——如果執法機構的言行不一,社會整體監管“放任”其發展,最終傷害的只會是全體國民。上述行為看似“微小”,不會對環境造成“實質性”的危害。但“小中見大”,如果社會中形成“破壞環境沒事”的風氣,則人們永遠無法理解環境監察執法工作的意義所在。因此,加大宣傳力度,“對就是對,錯就是錯”,自下而上,在社會整體形成真正的環保理念,從而為執法工作提供支持。
3 結語
時至今日,我國人民對環境保護的認知依然停留在表層,在基層執法單位開展日常工作的過程中,未能在整體上給予充分理解及幫助,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基層環境監察執法工作難以高效開展。因此,國家宏觀和人民微觀兩個角度,均需要調整,使環境監察執法工作能夠切實發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