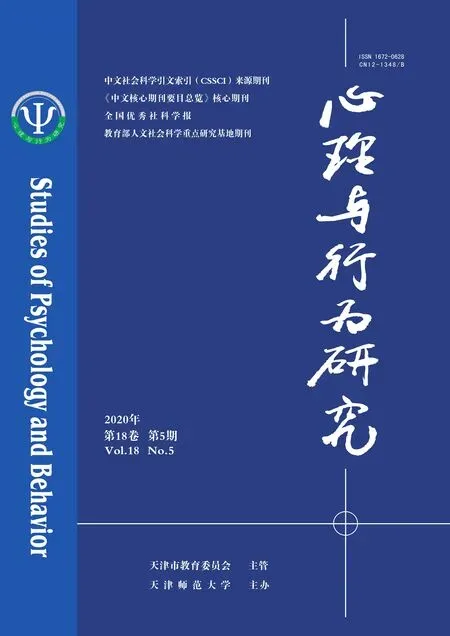父母沖突頻率與青少年生活滿意度的關系:青少年行為反應的中介作用 *
朱雨純 張 碩 張新荷
(西 南 大 學 心 理 學 部,重 慶 400715)
1 問題提出
生活滿意度(life satisfaction)是個體依據自身所構建的一定標準對自己持續一段時期或大部分時間的生活狀況進行的總體性認知評估(Shin &Johnson, 1978),它被認為是整個行為功能和積極心理健康狀況的關鍵指標,可能會擴展研究領域對青少年應對發展任務和挑戰的能力的理解(楊強, 葉寶娟, 2014; Proctor, Linley, & Maltby, 2009)。因此,探究青少年生活滿意度的影響因素及其作用機制對促進青少年的適應性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國內外針對生活滿意度的研究發現,在以中學生為對象的研究中,積極的家庭環境、父親或母親的情感溫暖均與青少年的生活滿意度之間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陳志英, 2017; Dew & Huebner,1994),母親的拒絕則與青少年的生活滿意度之間具有顯著的負相關(江穎穎, 2016),家庭關系尤其親子關系與青少年生活滿意度間的關聯是研究的主要方向。按照Bowen(1978)提出的家庭系統理論,整體家庭關系往往會因為父母沖突而遭到破壞,父母沖突本身也是一種比較常見的家庭人際沖突形式(Simons, Whitbeck, Melby, & Wu, 1994)。父母沖突是指發生在父母之間由于對待某件事情或事物的態度、興趣或目標等存在分歧或矛盾進而產生言語或非言語形式的攻擊行為。可依據其沖突發生的頻率、強度、內容、風格以及沖突是否得到解決等特征或角度來具體加以界定(池麗萍, 2005; 王明忠, 王夢然, 王靜, 2018)。多項研究表明,父母沖突會導致青少年一系列內、外化問題的產生,如青少年抑郁、焦慮、攻擊行為、反社會行為等(王娟娟, 王宏偉, 潘娣, 宋廣文, 2018;王藝瀟, 2017; 夏天生, 劉君, 顧紅磊, 董書亮, 2016)。因此,父母之間的沖突和分歧是與兒童和青少年福祉相關的重要因素(Cummings & Davies, 1994),是影響青少年生活滿意度的重要方面。
眾多研究表明,作為父母沖突的重要特征,發生頻率對青少年的心理適應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高頻率的父母沖突會導致青少年對家庭的生活滿意度降低,并減少其對父母的尊重,表現出顯著高的攻擊、同伴排斥、孤獨、抑郁等行為或情緒表現(梁麗嬋, 邊玉芳, 陳欣銀, 王莉, 2015;Plunkett & Henry, 1999)。而生活在高頻率父母沖突家庭中的青少年男性可能會認為在戀愛關系中帶有侵略性的言語和行為是合理的,并很難控制自己的憤怒情緒(Kinsfogel & Grych, 2004)。可見,父母沖突頻率對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具有一定的預測作用。過往研究關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指標大多選擇體現消極心理狀態的變量,關注父母沖突與青少年消極心理狀態的關聯性,而本研究著重挖掘父母沖突與青少年積極心理狀態的關系,探討父母沖突頻率對青少年整體生活滿意度的影響。
當直面父母沖突時,子女通常會對父母沖突進行認知評價或做出行為反應。國外研究發現,兒童介入父母沖突的行為與其適應問題呈顯著正相 關(Mueller, Jouriles, McDonald, & Rosenfield,2015);面對父母沖突,不同性別的青少年應對行為及其后續影響存在差異,介入父母沖突、提出個人看法等積極且支持性的應對行為可以有效緩解女孩內化問題的發生,而回避、忽視等消極的應對行為則與男孩的內化、外化問題呈顯著正相關(Nicolotti, El-Sheikh, & Whitson, 2003)。國內研究者則有不同的發現,楊阿麗、方曉義和林丹華(2002)的研究認為無論青少年面臨父母沖突時采取積極或消極的應對策略,使用頻率越高,其出現的問題行為越少,主觀幸福感越強。這些研究提示面對父母沖突時,青少年當下的行為反應與其后續內在的心理變化與心理適應密切相關。同時,鄧林園、許睿和方曉義(2015)的研究表明父母沖突頻率與青少年采取回避、否認等消極應對策略呈現正相關,與采取介入沖突、積極解決問題等積極應對策略呈現負相關,可見父母沖突頻率會對青少年的行為反應產生影響。因此,探討父母沖突對青少年生活滿意度的影響機制時,引入青少年的行為反應,探究其中介作用是具有可行性的。
綜上所述,本研究將初中生作為調查群體,探討父母沖突與青少年生活滿意度之間的關系,以及青少年的行為反應在二者間所起到的中介作用,其中以父母沖突頻率作為父母沖突特征的指標。以期能夠佐證前人關于父母沖突頻率與行為反應的關系等方面的研究結果,并為降低父母沖突對青少年生活滿意度的負面影響提供新的視角與方法,有效幫助青少年身心的健康成長。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1)父母沖突頻率顯著影響青少年生活滿意度;(2)父母沖突時青少年的行為反應顯著影響生活滿意度;(3)青少年的行為反應在父母沖突頻率和生活滿意度之間起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被試
采用方便抽樣方法,選取河北省保定市與重慶市兩所中學青少年群體進行測量。研究發放問卷420 份,以在場景想象的確認性題目“你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想象自己的家人處于剛才所示的場景”中選擇“完全不可以”、數據錄入時場景類別缺失、單親家庭及數據空缺項超過半數為數據篩除標準,篩選出有效問卷366 份,有效率為87%。其中,女生181 名,男生185 名;中學七年級151 名,八年級215 名。被試平均年齡為13.44±0.78 歲。
2.2 研究工具
2.2.1 青少年學生生活滿意度問卷
采用張興貴、何立國和鄭雪(2004)編制的青少年學生生活滿意度量表,共計36 道題目,分為以下六個維度:友誼、家庭、學業、自由、學校、環境。采用7 點計分(1=完全不符合,7=完全符合),量表總得分越高表明學生生活滿意度越高。本研究中,該問卷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93,效度指標擬合良好(χ2/df=2.50, AGFI=0.92, CFI=0.86,IFI=0.87, RMSEA=0.05)。
2.2.2 父母沖突時青少年行為反應問卷
采用由張新荷(2016)編制的父母沖突時青少年行為反應問卷以及場景想象的確認性題目。該問卷采用場景想象法,主要是為了規避讓青少年回憶真實發生過的父母沖突場景帶來的心理負擔與沖擊。
該問卷從夫妻沖突的模式及內容考量,設定兩種父母沖突場景。夫妻之間通常采用“要求-退縮”的溝通方式解決問題,一方總是以情感要求、嘮叨、責備和抱怨等形式同對方討論彼此關系中的問題,另一方則總是以捍衛自己、消極應對、不采取任何改變或退縮(如沉默或離開)等形式逃避討論(Stanley, Markman, & Whitton,2002),可見“要求-退縮”的溝通方式可能體現為“主張(嘮叨、責備、抱怨)-主張(捍衛自己)”的模式,也可能表現為“主張(嘮叨、責備、抱怨)-回避(沉默、離開)”等。另外,國內相關研究發現,“妻子要求-丈夫退縮”的溝通方式顯著多于“丈夫要求-妻子退縮”,并且男性在沖突解決策略的回避維度得分上顯著高于女性(畢愛紅, 胡蕾, 牛榮華, 吳任鋼, 2014; 曾紅, 林漢生, 武曉艷, 明偉杰, 2010)。夫妻沖突的內容多樣,以家庭事務意見不同而引發的沖突最為常見(王大任, 李守強, 楊阿麗, 2003),同時“EASS2006 東亞家庭”大規模調查顯示,關于家務活分工產生的爭吵、沖突是此類夫妻沖突中較為普遍的(巖井紀子, 保田時南, 2014)。因此,最終確定了夫妻因家務分工產生意見分歧,并且相互主張個人意見(圖1)和一方主張一方回避(圖2)的想象場景。為保證問卷分配的隨機性,研究者在調查中將兩種場景的問卷各設置為每個班級總人數的一半并且隨機發放給學生填寫,最后收集到主張-主張場景的問卷203 份,主張-回避場景的問卷217 份。

圖1 場景一:主張-主張場景

圖2 場景二:主張-回避場景
行為反應共11 題,由介入行為因子的7 道題目和回避行為因子的4 道題目構成,采用4 點計分(1=完全不符合,4=非常符合)。介入行為因子為青少年直接參與并干預父母沖突,如題例“我會試圖說服父母中的一方或雙方以制止他們吵架”;回避行為因子為青少年會主動回避父母沖突,對父母無任何應對行為,如題例“我會去其他地方,比如躲進自己的房間,或者到外面去”。本研究中,問卷的介入行為因子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71,回避行為因子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72,問卷的效度指標基本達到可接受水平(χ2/df=4.14, AGFI=0.89, CFI=0.85, IFI=0.86, RMSEA=0.08)。
2.2.3 父母沖突頻率
父母沖突頻率的衡量指標題目為:“你的父母之間會出現剛才所示場景那樣的吵架嗎?”,采用4 點計分(1=完全沒有,2=基本沒有,3=有時,4=經常)。
2.3 數據處理及分析
采用SPSS22.0 進行數據的相關分析,采用Bootstrap 方法并運用Mplus7.4 統計軟件進行數據的中介效應檢驗。
3 結果與分析
3.1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采用Harman 單因子檢驗對共同方法偏差進行了統計確認。結果表明,未旋轉時共生成12 個因子,第一個因子解釋11.36% 的方差變異,小于40%的臨界標準(周浩, 龍立榮, 2004),說明本研究中共同方法偏差影響較小。
3.2 各變量之間描述統計與相關分析
對兩個場景下的各變量進行描述統計和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見表1。結果發現,在主張-主張場景中,青少年的生活滿意度與父母沖突頻率呈顯著負相關,介入行為與生活滿意度呈顯著正相關,回避行為與生活滿意度呈顯著負相關;在主張-回避場景中,青少年生活滿意度與父母沖突頻率呈顯著負相關,介入行為與生活滿意度呈顯著正相關,回避行為與生活滿意度呈顯著負相關,回避行為與父母沖突頻率呈顯著正相關。
3.3 父母沖突時青少年行為反應的中介效應檢驗
以兩個不同場景下父母沖突頻率為自變量,青少年生活滿意度為因變量,父母沖突時青少年的行為反應(介入行為和回避行為)為中介變量,按照溫忠麟和葉寶娟(2014)提出的新中介檢驗流程進行中介效應檢驗。主張-主張場景中,父母沖突頻率與青少年的介入行為及回避行為這兩個變量均未存在顯著相關,主張-回避場景中,父母沖突頻率與青少年的介入行為的相關不顯著,因而對主張-主張場景中的兩條路徑和主張-回避場景中介入行為作為中介變量的路徑進行了Bootstrap 法檢驗,中介效應均不顯著。
主張-回避場景中,父母沖突頻率對青少年生活滿意度的全效應回歸系數顯著(c=-18.90,p<0.001),按中介效應立論。由表2 可知,父母沖突頻率對中介變量青少年的回避行為的預測效應不顯著(a=7.74,p>0.05);將自變量父母沖突頻率與中介變量回避行為同時納入模型,回避行為對因變量生活滿意度的預測效應不顯著(b=-0.56,p>0.05),因此用Bootstrap 法進行檢驗a與b的乘積,結果顯示置信區間[-11.38, -0.48]不包含0,間接效應顯著;父母沖突頻率對因變量生活滿意度的直接效應顯著(c’=-14.58,p<0.001)。a與b的乘積與c’同號,青少年的回避行為在父母沖突頻率和生活滿意度間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應占總效應的比例為[7.743×(-0.559)] /(-18.90)×100%=22.90%。

表1 各變量間的描述統計和相關矩陣

表2 父母沖突頻率-回避行為-生活滿意度中介的回歸分析(主張-回避場景)
4 討論
4.1 父母沖突頻率、青少年的行為反應與生活滿意度的關系
本研究結果顯示,父母沖突頻率與青少年生活滿意度呈顯著負相關。這與相近研究的結果一致,如消極父母婚姻狀態會使青少年生活滿意度降低(王金霞, 王吉春, 2005),高頻率的父母沖突會使青少年對家庭的生活滿意度降低,并感到自身發展和家庭穩定受到威脅(孫瑩, 2011; Plunkett &Henry, 1999)。因此,父母沖突是青少年整體生活滿意度的重要影響因素,父母沖突頻率越高,對父母沖突感知敏銳的青少年評價其生活滿意度越低。
青少年的介入行為與生活滿意度呈顯著正相關,而回避行為則與生活滿意度呈顯著負相關。這與前人研究結果存在部分差異,楊阿麗等(2002)的研究顯示,不論是積極應對行為還是消極應對行為都可以有效減弱父母沖突給青少年帶來的心理影響,這可能是因為對青少年行為反應的定義和分類有所不同,該研究中的個別消極應對行為在本研究中屬于介入行為。例如,“面對父母沖突時青少年尋求他人幫助”被該研究歸類為消極應對行為,具體含義是獲取他人支持,以緩解父母沖突的消極影響而非借助他人力量來介入父母沖突;而本研究中,尋求他人幫助的內容沒有限定,因而其內涵可能更為豐富,既包括通過尋求他人幫助以干預父母沖突,也包括在他人支持下緩解父母沖突的負面影響。另外,牟英(2011)指出,相對于尋求他人幫助,回避行為更加指向內部,是消極行為和情緒的體現。因而本研究將尋求他人幫助歸為介入行為,本研究中的回避行為更多體現的是與父母和他人保持距離,獨自處理或放置父母沖突的影響。總之,本研究認為,比起參與并干預父母沖突或向外部尋求他人幫助,面對父母沖突時直接的回避行為可能更容易使青少年沉浸在消極情緒中,并受到這一消極事件的持續影響。
4.2 青少年的行為反應在父母沖突頻率與青少年生活滿意度之間的中介作用
首先,在主張-回避場景中,青少年回避行為在父母沖突頻率與生活滿意度間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應占總效應的22.90%;中介效應表明,當父母沖突呈現主張-回避的消極交流形式時,父母沖突頻率越高,則青少年的回避行為越多,生活滿意度越低。本研究中,關于主張-回避場景中回避行為的中介作用,父母沖突頻率與回避行為反應的關系與鄧林園、許睿和方曉義(2017)的研究結果相一致,即父母沖突頻率與青少年回避行為呈顯著正相關。另外,家庭“溢出”假說(spillover hypothesis)和父母沖突代際傳遞的研究結果表明,父母的沖突關系所裹挾的消極行為和情緒如果不能夠很好地解決并且多次發生時,一方面,父母回避式的消極應對方式會讓青少年擔憂家庭生活,甚至讓他們處于焦慮和抑郁的生活狀態,增加他們的生活壓力;另一方面,還會引導青少年的社交方式,他們會模仿父母對沖突的處理方法(Kinsfogel & Grych, 2004; Peris,Goeke-Morey, Cummings, & Emery, 2008)。以上研究表明父母沖突通過多條路徑影響孩子的心理適應與發展。在本研究中,青少年因反復經歷父母的主張-回避型沖突而影響其對生活滿意度的評價,同時通過觀察學習回避沖突這一應對方式,在面對父母沖突時有所使用,而且可能將其外化到生活的其他領域,因此作為消極行為和情緒體現的回避行為,會進一步影響青少年對自我生活滿意度的評價。
其次,在主張-主張場景中,父母沖突的頻率與青少年回避行為相關不顯著,這與鄧林園等(2017)的研究結果存在差異,體現了不同的父母沖突形式對青少年行為反應的影響。兩種場景的不同之處在于,在沖突當下,雖然前者的緊張性更強,但父母雙方都表達了個人的意見,這可能是協商問題的前奏;后者伴隨一方的回避,場面的緊張性減弱,但可能給夫妻關系留下隱患,不利于問題的解決。張錦濤、方曉義和戴麗瓊(2009)發現建設性溝通對夫妻的婚姻質量有正向預測作用,而回避式溝通則對夫妻婚姻質量有負向預測作用。因而主張-回避型父母沖突的頻率越高,青少年對沖突解決和父母關系的評價越消極,越容易采取回避行為;但在主張-主張場景中,無論沖突頻率如何,青少年還受到對沖突解決、父母關系的評價等認知要素的影響,使其在回避行為的選擇上沒有差異。
再次,關于介入行為,在主張-回避場景和主張-主張場景中的中介效應均不顯著。有研究表明,無論父母沖突的頻率如何,只要是在青少年面前直接展開的沖突,青少年就會主動地、有選擇性地介入其中(鄧林園等, 2017)。因而本研究中直面父母沖突的青少年可能基于頻率以外對父母沖突的感知要素來決定選擇何種介入行為。例如,面對父母沖突,從沖突強度、應對效能等可能產生影響的因素分析,無論沖突的類型與頻率,青少年如果認為該沖突強度弱且自己有能力幫助父母緩解,則傾向于選擇介入;而青少年如果認為該沖突強度強且自己無法幫助父母解決問題,則傾向于放棄介入。可見,與行為反應相關聯的認知要素值得進一步探討。
最后,本研究證實了父母沖突對青少年生活滿意度的影響,也證實了在主張-回避的父母沖突場景中,青少年的回避行為在父母沖突頻率與青少年生活滿意度之間的中介作用。作為中介因素,青少年的回避行為不僅影響了其生活滿意度,同時也進一步干預父母沖突頻率與其生活滿意度的關系。在實際生活中,如果青少年反復經歷父母主張-回避型沖突,父母和援助者可以考慮從青少年的行為反應入手,通過調整回避行為以減輕父母沖突的負面影響。不過,本研究還存在一些局限性。第一,父母沖突時青少年的行為反應固然重要,但與其密切相關的復雜認知,如對父母關系、沖突解決、沖突強度、應對效能等的評價同樣值得深究,未來研究可將認知與行為進行整合討論。第二,在使用場景想象法時,只關注了青少年感知的父母沖突頻率,對其主觀感知的沖突強度與內容等缺乏考察,未來研究中需要更加全面地把握青少年感知的父母沖突特征;同時,為了提高對父母沖突頻率評定的有效性,測量題目數量有待增加;并且,父母沖突的模式也可進一步多元化,考察“妻子要求-丈夫退縮”以外其他模式的影響;總之,場景想象法的運用尚不夠成熟,有待進一步完善。
5 結論
(1)父母沖突頻率顯著負向預測青少年生活滿意度;(2)青少年的介入行為與生活滿意度呈顯著正相關,青少年的回避行為則與生活滿意度呈顯著負相關;(3)在主張-回避場景中,青少年的回避行為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應占總效應的2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