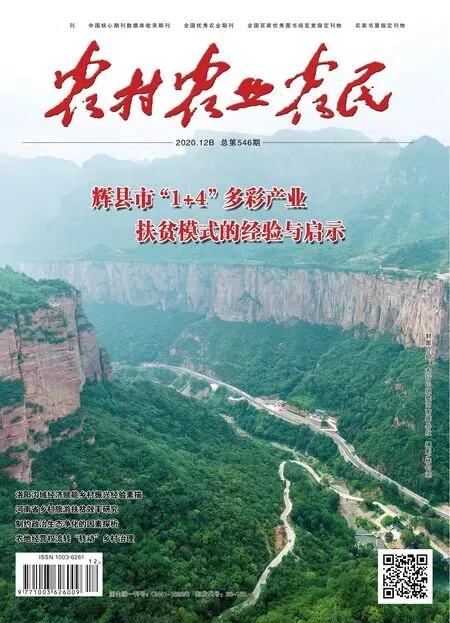河南省鄉村旅游扶貧效率研究
——基于河南省10 個縣市的數據
劉 祎 王 芳 秦國偉 田明華
鄉村旅游扶貧作為一種“授人以漁”的扶貧方式,是精準扶貧的重要支柱,可以通過增加土地經營權流轉收入、資產股權收入、務工收入、農副產品收入等途徑實現貧困戶增收,截至2020 年,政府預計通過發展旅游業實現中國1200 萬人口脫貧,約占全國脫貧人口的17%。 當前,在鄉村旅游扶貧領域的相關文獻中, 學者們的研究視角主要集中在鄉村旅游扶貧的理論基礎研究、鄉村旅游發展的減貧效應研究、不同發展模式的差異研究等方面,而關于效率測算的研究則多選取傳統DEA模型展開實證分析, 該模型無法同時從投入與產出兩方面進行測算, 也無法考慮非期望產出的問題,因此測算結果有偏誤。 針對這兩大缺陷,學者們將傳統DEA 模型改進為SBM-DEA 模型, 使結果更加準確。 眾所周知,河南是農業大省,但其山地丘陵占44%以上,也是一個山地大省,“造山、造水、造中華”,具有豐富的地理、文化、歷史資源。 近年來鄉村旅游發展很快,例如2019 年河南十一黃金周46%的旅游者選擇了鄉村旅游, 游客高達3050 萬人次,因此成為鄉村扶貧的重要途徑。 由此,本文選取河南省10 個縣市為研究區域, 運用SBM-DEA 模型與ML 指數綜合測算鄉村旅游的扶貧效率,衡量是否存在效率損失,并有針對性地加以改進,以充分發揮鄉村旅游扶貧作用。
一、數據與方法
(一)研究區域與數據來源
選取河南省10 個縣市作為研究樣本, 具體包括鞏義市、蘭考縣、固始縣、永城市、長垣市、鄧州市、滑縣、鹿邑縣、新蔡縣與汝州市。 其中,蘭考縣、固始縣、滑縣與新蔡縣為貧困縣,其余縣市為非貧困縣。 數據均來源于歷年《中國縣域統計年鑒(縣市卷)》《中國農村貧困監測報告》及中經網統計數據庫。
(二)指標構建
參照國家旅游局公布的旅游示范區基本考核原則與六大考核指標,圍繞鄉村旅游扶貧,構建鄉村旅游扶貧效率評價指標體系(詳情見表1)。

表1 鄉村旅游扶貧效率評價指標體系
(三)研究方法
根據已有文獻的做法, 選取SBM-DEA 模型與ML 指數進行實證分析,公式為:

其中,ρ 為鄉村旅游扶貧效率,若ρ=1,說明完全有效,若ρ<1,說明存在效率損失,有改進空間;和分別為投入值、 期望產出值和非期望產出值;和分別為和的松弛值;為權重。


二、結果與分析
(一)SBM-DEA 模型測算結果分析
測算結果顯示(詳情見表2),2016~2019 年,河南省鄉村旅游扶貧的綜合效率、 純技術效率與規模效率在各市縣之間具有顯著差異。

表2 河南省10 個縣市鄉村旅游扶貧效率測算結果
綜合效率方面,2016~2019 年這10 個地區的綜合效率均值分別為0.56、0.49、0.47 與0.54,說明扶貧效率一直處于較低水平,反映出所研究地區旅游扶貧規劃水準和技術應用水平不高,因此,需要盡快突破鄉村旅游發展瓶頸,實現旅游扶貧提質增效。 相比較而言,2016~2019 年,蘭考縣鄉村旅游扶貧效率最高, 連續4 年保持DEA有效;其次是鹿邑縣、鞏義市與固始縣,除個別年份外,基本保持有效水平;其他地區的綜合效率值均在1 以下, 表明其存在不同程度的效率損失,其中,滑縣、汝州市與永城市3 個地區的效率值接近于0, 反映出這3 個地區鄉村旅游扶貧幾乎是無效的。鄉村旅游扶貧在貧困地區與非貧困地區的扶貧效率均值分別為0.63 與0.44,說明其在貧困地區更加有效。
純技術效率方面,2016~2019 年,所研究地區的純技術效率均值分別為0.58、0.71、0.71 與0.89,呈上升趨勢,說明鄉村旅游經營管理技術處于快速提升階段。 比較而言,鞏義市、蘭考縣、固始縣與鹿邑縣的純技術效率值最高,基本為1,說明其純技術效率有效;汝州市、永城市與滑縣的純技術效率提升最快, 已從2016 年的幾乎無效發展到2019 年的完全有效。 純技術效率在貧困地區與非貧困地區的均值分別為0.76 與0.70,雖然相差不多,但是仍可以看出其在貧困地區更具技術溢出效應。 各年標準差計算結果分別為0.41、0.37、0.33 與0.19,說明各市縣純技術效率差異在逐漸縮小。
規模效率方面,剔除個別異常值,2016~2019年研究地區的規模效率均值分別為0.87、0.66、0.56 與0.63,整體處于中等有效水平,且呈現下降趨勢,說明近年來鄉村旅游的規模集聚效應逐漸弱化,因此,需要提高旅游資源配置效率,加快調整產業規模。相比較而言,在研究地區中,規模效率最高的是蘭考縣與鄧州市,規模效率始終保持DEA 有效;其次為鹿邑縣,基本接近理想值1;規模效率最低的是汝州市與滑縣,幾乎無效。 規模效率在貧困地區與非貧困地區的均值分別為0.68 與0.58,說明其在貧困地區更能發揮規模集聚效應。 此外,規模效率各年標準差計算結果分別為0.24、0.43、0.42 與0.42, 表明各市縣之間規模效率差距較大,大體呈擴大趨勢,也反映了綜合效率的地區差異主要來自于規模效率的差異。
從2017 年開始,純技術效率整體上高于規模效率,說明河南省鄉村旅游扶貧綜合效率的提升主要依賴純技術效率的提升。
(二)ML 指數測算結果分析
測算結果顯示(詳情見表3),2017~2019 年所研究地區全要素生產率指數均值分別為1.06、1.20 與1.46,均大于1,說明旅游扶貧效率呈遞增趨勢, 反映了河南省鄉村旅游發展正處于快速發展階段, 具備帶動區域經濟發展與提升民眾生活水平的潛力。 在此期間,扶貧效率始終保持上升狀態的有永城市、鞏義市與鄧州市,年均增長率最高的是滑縣(64.67%),其次是新蔡縣(50.62%)與永城市(30.70%),反映了這些地區鄉村旅游資源得到有效整合、配套政策逐步完善、技術應用水平顯著提升。 此外,各年標準差計算結果分別為0.37、0.36 與0.64,說明各地區鄉村旅游扶貧效率進步速度差異顯著,進步率低的地區應積極學習借鑒其他地區的成功經驗。

表3 河南省10 個縣市鄉村旅游扶貧的ML 指數變化
技術效率變化層面,2017~2019 年技術效率指數均值分別為1.02、0.96 與1.02,基本圍繞1 上下波動,說明技術效率幾乎沒有提升,且各年標準差計算結果分別為0.09、0.15 與0.22,變化幅度逐漸擴大, 反映出各市縣之間技術效率差距不斷拉大。 技術進步層面,2017~2019 年技術進步指數均值分別為1.03、1.25 與1.40,說明鄉村旅游扶貧技術進步效率處于加速提升階段, 且各年標準差計算結果分別為0.28、0.26 與0.41,表明各地區之間技術進步程度不均衡,差距逐漸擴大。純技術效率指數與規模效率指數基本接近于1,反映了絕大多數地區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基本保持在原有水平,鄉村旅游經營管理技術水平和產業規模總體保持穩定。 此外,在研究期間內, 技術進步變化指數均值整體上大于技術效率變化指數,反映出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主要依靠于技術進步,因此需強化鄉村旅游技術層面的改進創新。
三、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基于河南省10 個縣市的面板數據,運用SBM-DEA 模型與ML 指數綜合測算鄉村旅游的扶貧效率。結果表明,河南省鄉村旅游扶貧效率整體上較低, 且在各縣市之間具有顯著差異,其扶貧效果在貧困地區更加明顯。具體而言,純技術效率呈上升趨勢,經營管理技術快速提升,其在貧困地區更具溢出效應;規模效率呈下降趨勢,集聚效應逐漸弱化,其在貧困地區更能發揮規模集聚效應; 相比較而言,純技術效率高于規模效率,綜合效率的提升主要依賴于純技術效率的提升。
(二)建議
應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大力發展鄉村旅游特別是貧困地區的鄉村旅游,注重區域間發展的平衡。 研究結果顯示,河南省鄉村旅游扶貧效率較低,且在各縣市之間具有顯著差異。 因此,一方面各縣市應在鄉村旅游發展上給予更多的政策優惠,積極推進供給側改革,以“旅游+”為手段,創新鄉村旅游發展新業態,通過與“互聯網+”聯合使當地獨特的旅游資源得到最大力度的宣傳,通過與當地產業融合優化產業結構,實現旅游資源產業化,以便更好地發揮其減貧效應。 另一方面,應完善鄉村旅游規劃體系,聯合多個縣市構建度假聯盟,延長旅游線路,壯大產業規模,使得各地區貧困人口在最大范圍內享受到鄉村旅游發展的紅利;同時,政府部門應建立聯動扶貧的互動機制,及時溝通交流,學習彼此的發展經驗,以縮小扶貧效率的差距。
應將發展重心放在純技術效率的提升上,積極創新要素配置方式,發揮規模集聚效應。河南省10 個縣市的研究結果顯示,純技術效率呈上升趨勢, 規模效率呈下降趨勢,綜合效率的提升主要依賴于純技術效率的提升。因此,在純技術效率提升方面,各部門應各司其職,凝聚發展合力,切實做好規劃設計、就業人員培訓、管理政策制定、營銷推廣、數據統計等基礎工作,積極推進生態旅游、全域旅游、低碳旅游等新型發展形態, 突破以經濟效益為導向的定勢思維,激發多元主體的活力,因地制宜地選取鄉村旅游發展模式, 充分挖掘當地獨特的民俗文化內涵,發展野地露營、兒童教育、民俗農家、田園養老等高級業態, 努力實現全產業鏈式的開發性與包容性發展。 在規模集聚效應發揮方面,應促進資金、人力、土地等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實現資源要素的協調投入,開展廁所革命、民宿擴點、停車場擴建、休憩觀景涼亭改造等一系列活動, 完善鄉村旅游的安全與基礎設施建設,提高游客承載量和滿意度,同時選取具有同質化的鄉村旅游項目進行規模化擴張、連鎖式經營,發揮鄉村旅游經營示范點的帶動作用,鼓勵和扶持當地居民特別是貧困戶參與鄉村旅游發展,形成規模效應與聯動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