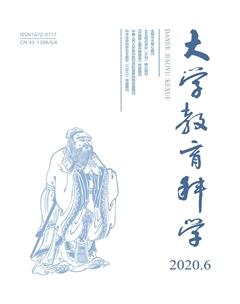超越“五唯”:大學排名的治理與監管芻議
譚曉斐 楊連生
教育評價最主要的目的之一是以評促改,但實踐過程中教育評價的“指揮棒”逐漸異化,“五唯”就是教育評價異化的集中體現。大學排名作為高等教育評價的一種方式也存在“唯論文”“唯獎項”的問題,它與“五唯”互相推動、互為表里,這種過度量化、極度簡化的評價誤導了公眾、挾持了高校,給高等教育帶來了實質性損害。張應強認為:“排行已經泛濫成災,給學者及其所在單位開展嚴肅認真的學術研究造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應該是‘破五唯要重點治理的對象。”[1]雖然2020年初教育部、科技部共同頒布的《關于規范高等學校SCI論文相關指標使用樹立正確評價導向的若干意見》涉及大學排名問題,但是還沒有把大學排名作為一個專門的治理對象,對一些基礎問題與對策問題還缺乏理性思考。比如:大學排名提供的是一種知識還是一種信息?大學排名的活動屬性是怎樣的?其背后的影響機制又是怎樣運作的?本文以上述問題為切入視角參與超越“五唯”問題的討論。
一、為什么要對大學排名進行治理與監管
政府對于排名的立場無論是規范、監管還是取締、優化,都離不開以下三點依據:一是排名結果是怎樣性質的知識或信息;二是排名主體的動機是什么;三是大學排名具有怎樣的影響與功能。
(一)大學排名的知識屬性:所提供信息的知識含量
如果大學排名是一種有效的、有益的知識生產行為,那么這種行為應該得到鼓勵與支持。但問題的關鍵是:大學排名是否創造了有價值的新知識?馬克思將知識定義為“在實踐基礎上產生又經過實踐檢驗的對客觀實際的正確反映”[2],深刻地指出了知識應該是“對客觀實際的正確反映”。大學排名用論文發表數量、引用率等可量化指標來代表高校科研能力,用生師比、研究生數量等指標代表高校教學水平,其所采用的多數二級指標并不能真正代表一級指標,加上本身充滿語言偏見、地區偏見、學科偏見,所以排名結果并不是客觀實際的正確反映。尤其是多數大學排名都是以片面和偏見為基礎的,不能有效反映大學質量、大學精神、大學文化以及師生情感體驗等關鍵方面,所以,相關排名結果也就很難反映大學的本質。排名與“五唯”共同的失誤之處在于,它們認識世界的方式是極度簡化的,故而形成的結論通常會以偏概全、“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從知識的類型來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將知識分為“知道是什么的知識”“知道為什么的知識”“知道怎么做的知識”“知道是誰的知識”四種類型。大學排名顯然不屬于上述四種知識的范疇。因此,從嚴格意義上講,與其說大學排名提供的是一種知識,不如說它提供的是一種信息。那么,這又是怎樣性質的信息呢?
大學排名機構在逐利動機的驅動之下,主觀地篩選、收集和加工大學的相關數據,并將統計結果以分數和名次的形式呈現出來。排名次序能夠簡便地告訴公眾哪些是好大學,但是很難告訴公眾這種“好”是在何種意義上的“好”。排名機構既沒有能力也沒有動力去為公眾普及排名的“專業知識”,它們害怕公眾真正理解排名的性質與缺陷,甚至會有意回避排名的不足,鼓吹自己排名的科學性、權威性。這種失真的、扭曲的信息具有一定的誤導性或者欺騙性,會影響學生和家長在擇校時的判斷和選擇。因此,大學排名提供的是一種充滿偏見和誤導的商業信息。
(二)大學排名的活動屬性:營利行為還是公益行為
大學排名作為大學評價的一種方式,必須以最高的專業水準進行,這種專業性決定了大學排名既不能屈服于利益,也不能僅僅為了滿足公眾的需求,而應該客觀、公正地對大學做出評價。因此,大學排名的意志必須是獨立的、非交易性的,不能染上商業氣息。
然而,從排名主體來看,極少見到由官方組織、公共組織或者專業學術組織提供的排名,而多數排名是由個人、商業媒體等機構提供的;從行為動機來看,排名主要是一種營利的商業行為,而非服務政府、服務大眾的公益行為。排名雖然在結果上可能對社會公眾具有一定參考價值,但是在動機上與營利性商業公司一樣,都是為了利潤,而不是為了知識生產與創造。商業屬性突出、公益屬性淡薄,具有這樣屬性的活動應該受到怎樣的法律法規制約呢?幾乎所有的商業行為都要遵循一定的法律規范與行業標準,如食品藥品、手機通信、服裝紡織等行業,都有相應的行業規定與質量標準。如果大學排名結果是一種商品,那么對這種商品的質量檢驗與監控就不能缺失。
(三)大學排名的影響機制:被動關聯、捆綁銷售
“聲譽對大學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大學競爭實質上是聲譽競爭”[3],大學排名通過影響大學聲譽進而在一定程度上裹挾和控制大學。大學聲譽的形成與大學身份和大學形象具有密切聯系,“大學首先通過自身實踐行為建構大學的身份,其次通過一定的溝通交流渠道傳播大學的形象,最終在與內外部利益相關者的長期互動中形成相對穩定的社會聲譽”[4]。可見,大學聲譽是大學形象與整體價值的外顯形式,良好的聲譽可以幫助大學獲取更優質的生源和更多的資源。而大學排名則會塑造公眾對大學的基本認知,對大學的社會聲譽產生直接影響。為了提高聲譽,大學不得不想方設法迎合排名指標。大學發展狀態與辦學質量的話語權在一定程度上被大學排名所控制,這顯然是大學排名的一種霸權。為此,通過發布看似科學的信息來霸占話語權,目的在于營利,這是多數排名的基本邏輯。
在這種霸權之下,大學排名對高校的辦學行為產生了負面影響。首先,論文數量被過分強調,催生高校“發表或者出局”的考核文化。“唯論文”,于是論文數量成了各種考核的重要指標,不僅給教師帶來沉重負擔,而且導致本科教學邊緣化;“唯論文”使得高校師生為發論文而急功近利,甚至出現學術不端行為。其次,大學排名以及“五唯”的評價方式,只重視能夠測量的即時性、外顯性的績效,助長了大學外延式增長,而忽略了內涵式發展。
二、大學排名的治理與監管措施
顯然,無論從上述哪個方面審視,大學排名都應該得到監管與治理。
第一,要思考誰有資格進行大學排名。目前這么多魚龍混雜的大學排名,有必要嗎?我們是否需要這么多五花八門的大學排名?排名的過程是把豐富多彩、多元復雜、鮮活深刻、充滿人性光輝的大學簡化、濃縮與抽象成一個個數字與符碼的過程,而這一簡化的結果,失真的風險很大。對于這樣一個重大議題,誰有資格和權力做出決策、發布結果,顯然不應是隨機的、自由的,不能停留在當前這樣毫無門檻與規制的“誰都可以排”的混亂狀態。也就是說,大學排名不同于一般的對一件私人商品的好評與差評,也不是一種普惠性、共享性的民主權利;相反,排名結果具有明顯的“公共產品”屬性,應該是一種嚴肅的、學科的、規范的專業判斷與權威判定的結果。那么誰會有這樣的權力與資格呢?大致有兩類主體可享有這樣的權力與資格:一類就是對大學具有絕對的行政管轄權的主體,比如政府、投資人、董事會;還有一類主體不是因為所有權與行政管轄權,而是因為具有高度的專業性而擁有資格。所以說,排名應由公共部門作出,或者由公共部門委托專業機構進行。當前的大學排名多數是由缺乏資質的個人與商業公司完成的,他們從事排名的動機是謀利,且其從事排名的資格和專業性都值得懷疑。這也是目前的大學排名過度泛濫,排名的依據、方法與結果又不夠科學的原因之一。因此,必須設定大學排名的準入門檻,建立排名機構的資質審核制度,不通過資格認證就不得從事與公開發布排名。
對排名機構進行監管與治理,目標之一就是以“清流”對沖“濁流”、營造風清氣正的學術環境。對于排名監管與治理應該綜合運用法律、行政與稅收等多種手段,對不同類型的排名應采取不同的干預方式,有的可以直接干預,而對于境外排名機構只能間接影響。比如,教育部、科技部在2020年初頒發文件規定“高校、高校主管部門及其下屬事業單位”不得“發布SCI論文相關指標、ESI指標的排行,不采信、引用和宣傳其他機構以SCI論文、ESI為核心指標編制的排行榜”,表明行政管理部門已經通過釜底抽薪的方式對大學排名進行監管。這一文件是排名治理上邁出的第一步,但不是針對所有排名的專項治理文件,所能規范的對象僅限于“高校、高校主管部門及其下屬事業單位”,治理的問題也僅限于與“SCI”“ESI”有關的問題,還不能起到對排名進行全面、系統治理與監管的作用。顯然,這方面還大有文章可做,還有較大的政策空間。
第二,在通過資格準入制度過濾和取消部分大學排名后,還要對剩余大學排名的過程與結果進行監管。首先,要對排名的主體進行規范和限制。現有的大學排名主體主要是個人、公司和少數民間組織。這些營利性的排名機構是利用大學的信息賺取利潤的,所以應該給大學付費,而不是向大學索取“贊助”,因為大學一旦“贊助”就極有可能影響排名的公正性,進而在排名過程中就可能出現造假、游說、賄賂等現象。為此,監管大學排名首先要抵制不正之風、切斷利益鏈條,在對大學進行財務審計之時,要查看大學辦學資金是否直接、間接地流向了排名機構。其次,要對排名發布的周期與類型進行規范。多數機構會按年度發布大學排名結果,但是大學發展與變化往往需要一定的時間,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年度排行”會激發大學的短期功利行為,因此排名的發布周期應該受到監管。大學排名機構每年發布的榜單中經常會出現幾所名次波動較大的院校,其中不排除某些高校“確有進步”,但也有可能是大學排名機構為了吸引公眾眼球的嘩眾取寵行為。也有些排名在團隊、方法與結果上都存在欠缺,只是某些機構“個人”的自娛自樂行為,但經常冠以“權威發布”之說。排名亂象叢生遠不止如此,故排名理念、信息采集、指標設定等關鍵環節都應受到一定的監管與規范。
第三,對排名的理念與方法進行優化。事實上,以高校的整體辦學水平作為比較與評價對象是不科學的,因為無論采用怎樣的指標都無法完全涵蓋大學的所有方面,即便涵蓋了也是勉強為之,未必科學、公正。所以,排名機構應化“唯”成“維”,從多個維度對大學進行評估,并分別對大學的某一方面進行單項評估,使得不同的大學排名能真實地反映出大學的某一個方面,盡量避免整合、加權這種缺乏公信力的統計方式。
現在的排名基本上是一種“強盜邏輯”,多數情況下高校未經許可就被拉入局中。而今后理想的做法應當是,排名機構先和高校溝通,讓高校有權選擇自愿參與或拒絕。當然,高校聯盟也應發揮作用,比如C9聯盟、華5聯盟等,可以集體宣布退出大學排名,或者發表聲明抵制未經許可的排名。為了超越“五唯”,大學排名機構應在政府的支持與推動下建立排名行業協會,制定多元化的分類評價標準。同時,有關管理部門也要對排名機構進行分類管理。總體而言,無論是超越“五唯”還是排名的治理與監管,尚都處于起步階段,還需要各類主體共同研究、穩步推進。
參考文獻
[1] 張應強.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評價及其治理——基于對“唯論文”及其治理的思考[J].西北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04):24-34,117.
[2] 廖蓋隆,孫連成,陳有進,等.馬克思主義百科要覽·上卷[M].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93:278.
[3] 蔣凱.聲譽追尋下的大學迷思[J].大學教育科學,2018(06):4-12,119.
[4] 季小天,江育恒,趙文華.大學社會聲譽的形成機理初探:基于“身份—形象—聲譽”分析框架[J].江蘇高教,2019(08):2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