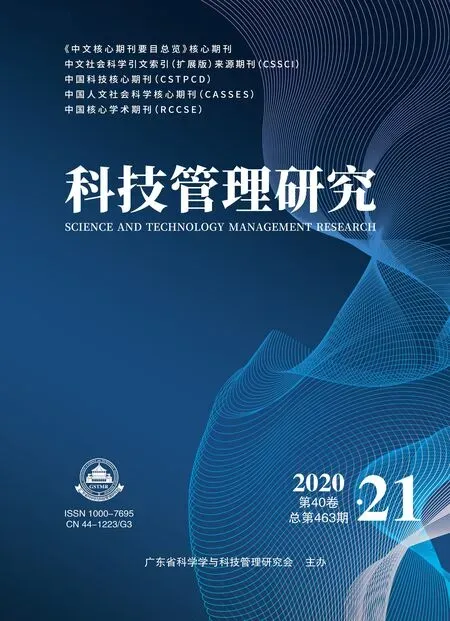市場導向型基礎研究
——反向路徑下的技術創新邏輯
雷小苗,李正風
(1.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北京 100191;2.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北京 100084)
基礎研究是攻克關鍵核心技術和促進高科技產業發展的知識源泉。基礎研究有兩種不同類型:一是“自由探索型基礎研究”,主要是基于對現象或事實的觀察來獲得新知識,而不考慮任何特定的應用或使用,因而不會為具體的實際問題提供商業化的解決方案,而是提供解決問題所需的思想、方法、概念、原理等[1],由科學家好奇心驅動的;二是“市場導向型基礎研究”,根據產業發展和市場需求進行基礎研發,是更有針對性的開展研究探索,意味著企業更加關注市場狀況,包括顧客當前及潛在需求、競爭者行為等,由商業利益驅動。
本文提出的“市場導向型基礎研究”目前尚沒有學者進行過系統闡述,而類似的提法包括“面向產業的基礎研究”[2]、“產業驅動型基礎研究”[3-4]等,但仍然與本概念存在不同之處。從中國的實踐來看,近年來,基礎研究成果如專利、論文等數量與日俱增,但相應的關鍵核心技術仍依賴進口,這說明高校基礎研究與產業需求存在“脫節”問題,也說明高校基礎研發的成果轉化率低,不足以支撐中國高科技產業發展需要[5]。要解決這一問題,就需要科學地分析基礎研究和產業發展之間、學術界和產業界之間的互動機理和機制,有效鏈接基礎研發和市場需求,深入研究“市場導向型基礎研究”,以使大學與企業良性互動,全面支撐起我國高科技產業的發展。
本文從技術創新的邏輯基礎談起,分析了正、反兩種不同路徑下的創新邏輯,并進行對比,同時系統闡述了“市場導向型基礎研究”的內涵特征、國際實踐經驗、政策建議。
1 技術創新的邏輯基礎:創新雙螺旋模型
根據熊彼特創新理論,技術創新過程需要一條完整的創新鏈條,完整的創新鏈是從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到技術開發和產業化應用、規模化發展的全過程。創新是經濟發展的本質規定,創新的主體應是“企業”。根據這一理論基礎建立起如圖1 所示的雙螺旋創新結構模型。

圖1 創新雙螺旋模型
由知識傳遞和轉化的路徑角度看,基礎研究有兩種類型,即正向路徑的“現象導向型基礎研究”和反向路徑的“市場導向型基礎研究”。
1.1 現象導向型基礎研究:正向路徑下的創新邏輯
正向路徑下的“現象導向型基礎研究”(curiosity driven),主要由科學家好奇心驅動,核心在于自由探索。它的創新邏輯遵循“基礎研究→應用研究→產品開發→商業實現”,如圖1 所示。這種類型的基礎研究的目的是建立一個知識庫,以便理解基本原理。它以現象為導向,由科學家對科學問題的好奇心或興趣所驅動的,雖然短期來看不能幫助實踐者解決日常問題,也沒有強烈的應用目的,然而它激發了新的思維方式,可能會產生開創性和革命性的思想、概念和應用。例如,正是基于純粹的數學研究,現代計算機技術才得以存在。這種類型的基礎研究為未來產業發展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和生長點。目前在中國主要由自然科學基金支持,研究主體是大學和科研機構。
1.2 市場導向型基礎研究:反向路徑下的創新邏輯
反向路徑下的“市場導向型基礎研究”(industry demand driven),主要由商業利益驅動,核心在于鏈接市場需求。它的創新邏輯遵循“商業實現→產品開發→應用研究→基礎研究”,如圖1 所示。這種類型的研究是根據產業發展和市場需求進行基礎研發,是更有針對性的開展研究探索。市場導向意味著企業更加關注市場狀況,包括顧客當前及潛在需求、競爭者行為等,并據此調整企業基礎研究方向及企業戰略。
1.3 產業適用視角下兩種類型基礎研究的對比
從整個科技發展角度來說,正向創新路徑下的“自由探索型基礎研究”與“反向創新路徑下的市場導向型基礎研究”同樣重要。但從具體產業來看,兩者所適用的產業類型不同,這與兩者的創新邏輯有關。
正向路徑下的“自由探索型基礎研究”更適用于前瞻性的新興產業。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一是從正向路徑的創新邏輯來看,知識生產到技術開發到應用遵循“基礎研究→應用研究→產品開發→商業實現”的邏輯方向,而前瞻性的新興產業往往其技術產生具有不確定性,技術的萌芽源于基礎研究的突破。二是從歷史發展脈胳來看,比如20 世紀計算機通訊,互聯網產業,這些技術是基于科學家的自由探索發現而成長起來,進而發展成了上世紀的新興產業。因此,在當代的人工智能、基因技術、X 技術等新興產業領域,正向路徑下的“自由探索型基礎研究”仍然有助于促進未來未知技術的發展與突破。
反向路徑下的“市場導向型基礎研究”更適用于成熟型高科技產業。原因如下:第一,成熟型高科技產業的技術相對成熟,自由探索的萌芽點較少;第二,高科技產業的應用目的明確,如醫療裝備、航空發動力、智能汽車等;第三,滿足客戶和市場的需求是決定高科技產業成敗的關鍵,比如經濟性、安全性、多樣性,舒適性等。由此可見,高科技產業的市場針對性、應用明確性、技術成熟性就決定了對于做強高科技產業來說,“市場導向型基礎研究”更為重要。美國施樂公司曾作為一個反面典型被管理學家們告誡企業應注重市場驅動型基礎研發。施樂公司的科學家曾沉迷于好奇心驅動的科學發現,而忽視了對接市場的技術創新,使基礎研究的方向發生了偏離,與公司的戰略和產業發展相脫離。導致該公司一方面擁有大量的發明專利,但另一方面企業的競爭力在斷崖式下降。由此可見,唯有倡導市場驅動型基礎研究,才會使基礎研究方向更明確、更有針對性,也會促使科學突破與產業技術的關系更密切。
2 市場導向型基礎研究的內涵特征
自由探索型基礎研究具有一定的偶然性,需要社會各界創造良好的創新環境,不能通過規劃來實現,其突破過程也具有長期性;而在全球經濟瞬息萬變的今天,將技術成熟型高科技產業做大做強,是增強國家競爭力的有效手段。相比于正向路徑的自由探索型基礎研究,反向路徑的市場導向型基礎研究具有四大內涵特征。
2.1 與市場需求的鏈接強度大
從目前中國產業發展現狀來看,研發投入的快速增長并沒有帶來產業核心技術突破能力的同步增長,也就是說基礎研究的成果與產業的實際需要在某種程度上存在脫節現象。據相關數據統計,2000年中國研發經費約為0.089 6 億元,2017 年增長到1.75 萬億元,研發投入占GDP 比重(研發強度)則由0.90%上升到2.12%。2017 年中國基礎研究經費為920 億元,比上年增長11.8%;基礎研究占研發經費的比重為5.3%,較上年提高0.1 個百分點。從研發活動主體看,2017 年企業研發經費為13 733 億元,比上年增長13.1%;公立研究機構和高等學校研發經費分別為2 418.4 億元和1 127.7 億元,分別比上年增長7%和5.2%[6]。然而,在這一時期,持續增長的研發經費投入并未帶來中國產業核心技術創新的同步提升,許多高科技產品,如集成電路、基礎軟件、航空發動機、液晶面板等,其核心技術對外依賴度仍然很高。
這種脫節現象的產生,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反向路徑下的“市場導向型基礎研究”機制不健全。市場導向型基礎研究強調:企業在充分感應市場信號的基礎,將市場信號反饋給學研機構,使學研方更有針對性地開展知識積累和原始創新,從而提升整個創新鏈條的創新效率;與此同時,企業要加強其自身基礎研究的經費投入和人才投入。而從目前全國基礎研究經費的投入路徑來看,一方面企業基礎研究經費投入極低,低于0.5%,企業基礎研究人才匱乏,研究能力局限;另一方面大學和科研機構作為基礎研究的重要平臺,與企業之間的合作目前在很多高校已全面展開,但是因學研機構和企業兩者之間的知識勢差過大、企業基礎研究成果承載能力有限、學研機構研究方向不夠聚焦等原因,產學研合作效率仍然不高。因此,加強產學研合作是市場導向型基礎研究的內涵要求。
2.2 科研人員的積極性高
“市場導向型基礎研究”中參與基礎研究的科研人員的積極性將會更高。原因有二:其一,市場導向型基礎研究采用的是反向創新路徑,在這一路徑下,企業及時感應市場需求和技術發展需要,進而將這些技術需求中的知識突破點反饋給學研機構,同時也會通過資金投入、人員流動等方式加大與學研機構的合作,資金的注入和流動的機會會增強學研機構內參與基礎研究人員科研的積極性;其二,通過企業反饋市場需求,進而調整基礎研究方向,有助于增強學研機構基礎研究成果的轉化率,進而有助于激發科研人員進一步加強基礎研究的熱情。
2.3 研究成果的可轉化性強
基礎研究成果屬于公共品,具有放大作用和擴散效應。專利是基礎研究成果的重要形式,中國高校的專利問題表現為“四高三低一缺失”,這種經費投入高、產出數量高,而轉化率低、收益率低的現象,歸根到底是由學研機構與產業界的脫節和錯位造成的。從相關統計數據看出,2018 年中國專利申請量為154.2 萬件,但專利轉化率仍然低于10%,中國高校情況與之類似。而相比之下,英國劍橋大學在2008 年專利轉化率已達到47%,美國斯坦福大學專利轉化率也接近20%。從市場導向型基礎研究的理論模型可以看出,反向創新路徑的實施,有助于從創新鏈條的尾端入手,以企業的技術需要帶動學研機構的基礎研究突破,促進高校與企業的深度合作,有效鏈接起市場需求和基礎研究,從而解決基礎研究的投入大、數量高,轉化率低等問題。
3 市場導向型基礎研究的國際實踐經驗
歐美發達市場經濟國家是二元結構的科技創新體系,即企業以技術創新為主、大學以基礎研究為主[7],雖然也有少量的公立科研機構,但規模一般較小且以軍事戰略為主。而中國的公立科研機構在國家創新體系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科研機構體系龐大且覆蓋全面[8],研發經費和研發人員占比高[9]。但中西方國家的創新邏輯基礎仍然是一致的,國外在自由探索型基礎研究、市場導向型基礎研究、創新路徑的選擇[10]等方面的實踐經驗仍然值得我們借鑒。
3.1 自由探索型適時轉向市場導向型基礎研究
20 世紀80 年代中期對美國來說是一個分水嶺,20 世紀80 年代中期之前,美國在基礎研究方面,美國企業采用集中研發實驗室的形式,由企業集中預算資助實驗室,創造了大學般的氛圍,為科學家提供選擇調查問題的自由和解決問題的方法,科學家具有研究的自主性,自由遵循有希望的線索,進行了長期的研究,而不太關心成本或應用。這種基礎研發是由科學家的好奇心驅動的自由探索,也就是現象導向[11];20 世紀80 年代中期之后,情況發生了很大的改變,日本、韓國、臺灣在科技上的崛起使美國的霸主地位受到了挑戰,同時日益激烈的全球競爭促使美國為了降低成本、縮短產品周期,由企業集中研發實驗室轉為部門分散研究。強調研發與業務的合作關系,科學家們必須從客戶那里獲取研究基礎研究的想法,以及通過商業部門獲取他們的研究經費。這種基礎研究是明顯的客戶導向和市場導向,目的性較強。美國猶他州立大學商學院的Stacey Barlow Hills 通過對164 個不同的高技術組織的高級管理人員進行采樣,結果表明,成功的企業是那些表現出相對高水平的客戶驅動和競爭者驅動[12]。顧客驅動有利于響應明確的顧客需求,從而使高科技產品更具市場[13]。同時他們也指出,這些競爭優勢最終是要歸因于蘊涵于產品中的基礎研發。
類似的轉變同樣發生在日本、德國、加拿大、尼日利亞等國,相同之處在于這些國家的基礎研究同樣是依賴于大學和企業[14]。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隨著日本產品在全球市場的份額越來越高,日本企業集體性地加大市場導向型基礎研究的力度,據統計,約有3/4 的日本企業開展過基礎研究,面向產業需求,長期加強與產業關聯度較高的關鍵性基礎科學和核心技術的研發,例如在日本化工產業,之所以這些企業的化學研究水平較高,是因為其基礎研究方向與市場產業技術趨勢相呼應。甚至有些醫療企業還培養出了諾貝爾獎獲得者,比如在2002 年獲得諾貝爾獎的田中耕一就供職于醫療器械和分析儀器制造商島津制作所,這個公司的戰略定位即是致力于通過基礎研究來實現在生命科學診斷方面的技術突破,這種戰略定位有利于基礎研究成果迅速轉化為商業產品。
3.2 “架橋梁”促進反向路徑下的產學研合作
德國、英國、葡萄牙等多國學者通過案例總結了國外技術轉移形式,如專利、技術轉讓協議、創建新公司、技術聯盟、生產許可證、商業化協議[15]或大學技術轉移辦公室(TTO,Technology Transfer Office)[16]。他們普遍認為,雖然業已存在多種形式的技術轉移方式,但是在技術供給方和需求方之間,即大學和企業之間仍然存在著灰色地帶,這一灰色地帶被稱作“死亡谷”[17]。正是由于這一灰色地帶的存在,因此雖然大學在基礎研究方面成果顯著,但是技術的需求方即高科技企業難以獲得這些成果,從而難以轉化為產品,實現其商業價值。
因而,歐美各國通過搭建更有效的橋梁以跨越死亡谷。在美國,幾乎所有的研究型大學都設立了技術轉讓辦公室TTO 來管理這些關系和促進商業知識轉讓,將至少一些他們的知識存量轉移給企業。在加拿大,將大學開發的技術與潛在的商業化機會聯系起來的大多數努力都通過技術轉讓學術辦公室(TTO)進行。在葡萄牙,TTO作為一種相互關聯學術界和產業界的機制,將大量大學的知識存量轉移給企業,促進了知識在大學與企業之間的流動。TTO 機制在歐美發達國家的實踐已經相當成熟,且在科研成果轉移中、在促進產學研合作中發揮了重大作用。與此同時,還通過高科技產業園區、企業孵化器、合作研究、合同許可等方式,促進產學研合作。
TTO辦公室引進或培養了大批技術轉移經理人。這些經理人要懂技術,能跟科學家對話,要懂市場,能跟企業進行商務談判;懂法律,如合同法、專利法等。美國密歇根大學的技術轉移辦公室的專業團隊在風險事務、技術許可事務、法律事務、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專業人數將近50,而且都是世界名校高學歷人才,具有豐富的技術評估和許可經驗,比如從事技術許可事務的有來自馬里蘭大學的生物學博士,也有世界名企工作經歷者。這是目前我國高校技術轉移辦公室無法比肩的。
3.3 宏觀政策推動學術產業交融
英國諾丁漢大學的Joanna Poyago-Theotoky 比較分析了英國和美國的學術產業關系異同及其對基礎研究轉移到高科技產業的影響,其研究發現美國在20 世紀80 年代的多項政策措施,如《貝爾法案》《拜杜法案》《國家合作研究法》《先進技術計劃(ATP)》等,使大學和產業關系更為緊密,使大學的技術商業化的速度和效率提升,從而保證了美國的領先地位[18]。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和歐洲的大學和公共實驗室一直是基礎研發的主要參與者。1980 年,美國《拜杜法案》(Bayh-Dole Act)標志著美國專利要求的一個重要例證。拜杜法案之前,美國的創新方式是:基礎研究成果在公共機構中構思出來的,并被投入公共領域,通過完全自由競爭的進入私人研發公司,旨在發明質量更好的產品,從而引發專利競賽。拜杜法案之后,創新方式轉化為:新概念、新知識是在公共研發部門被發明,它受到專利的保護,具有無限的法律壽命[19]。這不僅有利于公立大學和實驗室的財務狀況(目前它們正受益于專利使用費),也有利于創新和增長,并且提高了美國的長期創新率。
通過上述歐美等國的發展歷程分析發現,歐美各國在不同階段都或多或少通過宏觀政策引導、科研成果轉化中介組織等加強了產業界與學術界的聯系,在基礎研究階段就已經植入了明確的市場導向,這在一定程度上幫助了這些國家在激烈的全球競爭中勝出。
4 市場導向型基礎研究促進技術創新的政策建議
4.1 健全新型的產學研協同創新機制
建立和健全產學研協同創新、協同進化、深度合作的體制機制。推進產學研合作,促進新知識、新技術的研發和應用,關鍵是建立產學研協同創新、協同進化、深度合作的體制機制。一是拓展產學研合作的深度,在促進技術轉移的同時,以產業需求為導向,推進從技術開發到基礎研究的多層次合作,實現從基礎研究到產業應用的全線貫通。二是完善產學研合作的長效機制,建立促進前沿共性技術供給的多方合作平臺和示范基地,形成能夠有效發揮企業、大學和社會資本各自優勢和積極性的合作機制。三是對涉及多部門、多行業的新興產業領域,聯合企業、高校、第三方機構等,建立國家創新協作平臺,形成跨行業、跨部門協同創新的管理模式。四是有效發揮大學學科齊全、人才眾多的綜合優勢推進未來關鍵核心技術的超前研發,依托部分有條件的大學,吸收相關企業參與,共同建設前瞻性技術研究院,加強未來關鍵核心技術的超前預研。
4.2 提升企業的基礎研究成果承接能力
市場導向型基礎研究最需要激發的創新主體是企業。傳統的基礎研究中,企業處于創新鏈條的后端環節,在與學研機構的合作中選擇和接受來自高校或科研機構的知識、原理或技術。而事實上,企業由于直接對接市場,對市場的需求和技術趨勢最為敏感,加大對企業基礎研究投入,才能提高企業研究基礎科學的積極性,吸引更高端的基礎研究人才,從而更準確地把握和預測市場中技術發展的方向和趨勢,提高企業承接學研機構科研成果轉化的能力,更主動地向學研機構反饋基礎研究需求,更好地促進產學研合作,進而提升整個創新鏈條的效率。
提升企業基礎研究承接能力的關鍵是加大企業基礎研究投入。中美兩國在研發投入結構方面的差異,是造成企業的科研實力不同的主要因素。在美國,企業的基礎研究投入大、實力強,具備與大學平等、深入合作的能力;在中國,基礎研究經費主要來自政府,企業的基礎研究投入少[20],除了個別實力較強的企業之外,大部分國有企業、中小企業基礎研究投入少,學研機構和企業之間存在知識勢差[21],當企業與學研方的知識勢差過大,知識擴散將會變得較為困難[22-23],企業對學研機構的基礎研究成果的承接能力就會變弱,嚴重影響了高科技產業和新興戰略產業技術的創新[24]。市場導向型基礎研究需要改變現有的基礎研究投入格局,不僅需要政府加大對企業的基礎研究投入力度,同時呼吁企業自身加強基礎研究投入。唯有如此,科技型企業在國際市場競爭中才有實力識別技術發展方向,才有能力準確把握市場需求。
企業之所以不愿過多投入基礎研究的原因有三:一是當基礎研究被視為一種公共產品,具有公共屬性時,其產出是免費提供的,其消費是非競爭性和不可排他性的[25],就會產生“搭便車”現象,企業無法從自身的基礎研究中獲得全部收益。二是企業基礎研發的風險較高,一旦研發失敗,對企業的財務狀況和運營將會產生致命性的打擊,英國航空發動機企業羅·羅公司在RB.211 的基礎研制上投入了巨額資金,但由于對項目的風險估計不足,導致這個擁有相當實力的公司于1971 年不得不宣告破產,并由政府接管,然后才有機會東山再起。三是中國一直缺乏持續、穩定的企業基礎研究支持機制。因此,由大企業聯合小企業共同創新,分散企業創新風險,提升企業基礎研究成果承接能力。
4.3 完善高校TTO 的反向功能
反向路徑下的創新邏輯需要完善高校TTO 的反向功能。不論是在國內或是國外,大學和科研機構都是經驗和科學知識的儲存庫和生成器。TTO(Technology Transfer Office)機構具有雙向功能。所謂正向功能是指將學研機構的基礎研究成果轉移到企業;所謂反向功能是指將企業的技術需求反饋給學研機構。通過發揮正反功能,促進知識在學研機構與企業之間雙向流動。目前,國內高校已初步建立起TTO 機構,但大部分TTO 仍然僅發揮了其正向功能,而忽視了其反向功能。要完善其反向功能,就需要引進或培養大批專業的技術轉移經理人,不但要懂技術,能跟科學家對話;也要懂市場,可以跟企業商務談判;更加要懂法律,尤其是專利法、合同法等。
最后,基礎研究成果和關鍵核心技術之間的鴻溝不僅需要技術轉移辦公室(TTO)來彌補,更需要鼓勵民間成立經營性的實體中介,成長起眾多技術轉移中小企業,從而形成從基礎研究到應用研究到產品開發再到商業市場的完整、健康的生態鏈。這些中介企業深入調研企業實際需求,精準尋找與之相匹配的成熟技術,不僅有助于本校科研成果轉化,更有助于推動校際之間、區域之間、國際之間的成果交流。唯有越來越多的中小企業取得成功,才能夠使科研成果更順暢、更高效地轉化,進而在全國范圍內發展出成熟的科技成果轉移網絡,這將成為發展高科技產業的強大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