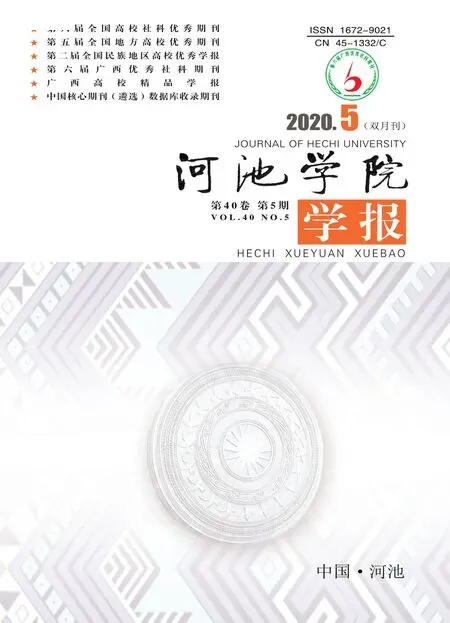文化空間視閾下洞頭媽祖祭典的傳承和保護
黃夢丹
(溫州大學 人文學院,浙江 溫州 325035)
媽祖信俗是中國首個信俗類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與陜西省黃陵縣的黃帝陵祭典、山東曲阜市的祭孔大典并稱為“中華三大祭典”[1]。媽祖祭典是媽祖文化的重要部分已受到社會各界的普遍關注,在對其實施保護方面也已達成了一定的社會共識。國內目前有天津市津南區、福建莆田市、浙江溫州市、海南海口市4個地方成功申請“媽祖祭典”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溫州市洞頭區的媽祖祭典是洞頭特色地域文化的縮影,其與湄洲媽祖文化同根同源,也與臺灣地區媽祖文化關聯緊密。洞頭媽祖祭典于2011年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擴展項目,成為國內第三個與媽祖文化有關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學界目前對媽祖祭典的討論主要集中在祭祀樂舞和祭典儀式的研究分析上,鮮有從文化空間角度切入的研究。有鑒于此,本文以洞頭媽祖祭典為研究對象,嘗試從文化空間視角出發對洞頭媽祖祭典文化的傳承與保護工作做一番探討。
一、非物質文化遺產與文化空間
“文化空間”概念最早出現在亨利·列斐伏爾1974年出版的《空間生產》這本書中。列斐伏爾在書中提出絕對空間、抽象空間、具體空間等空間概念,其中就包含了文化空間[2],此時的“文化空間”只具有語義學上的意義。199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的《人類口頭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條例》提到:“宣布人類口頭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針對的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兩種表現形式。具體而言,一種表現于有規可循的文化表現形式,如音樂或戲劇表演,傳統習俗或各類節慶儀式;另一種表現于一種文化空間,這種空間可確定為民間和傳統文化活動的集中地域,但也可確定為具有周期性或事件性的特定時間,這種具有時間和實體的空間之所以能存在,是因為它是文化現象的傳統表現場所。”[3]2這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首次使用“文化空間”一詞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專有名詞。此外該條例還明確提出非物質文化遺產包括兩大種類:一個是文化空間的形式,另一個是文化表現形式。200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將非物質文化遺產定義為“被各群體、團隊、有時為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的各種實踐、表演、表現形式、知識技能及其有關的工具、實物、工藝品和文化場所(文化空間)。”[4]149文化空間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概念再次出現,凸顯出文化空間之于非物質文化遺產存續的重要性。
在2007年第三屆東岳論壇——“文化空間:節日與社會生活的公共性”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國內著名民俗學家烏丙安先生呼吁“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當務之急就是搶救民俗文化空間”[5]。由此引發了學者們對文化空間的探索和思考。張博針對因旅游開發而導致非物質文化遺產生存空間縮小的現象,主張從文化空間入手進行保護,并提出三點文化空間特性:活態性、傳統性、整體性[6];向云駒對比、分析傳統“文化空間”和人類學“文化空間”的區別,歸納出人類學的“文化空間”的自然、文化、社會三重屬性。認為文化空間首先是一個文化的物理空間或自然空間,是有一個文化場所、文化所在、文化物態的物理“場”。其次在這個“場”里有人類的文化建造或文化認定,是一個文化場。再次,在這個自然場、文化場中,有人類的行為、時間觀念、歲時傳統或者人類本身的“在場”[7];烏丙安也認為文化空間是一個人類學的概念,它指的是傳統的或民間的文化表達方式有規律進行的地方[8];李玉臻從核心象征、核心價值觀,集體記憶與歷史記憶,符號和主體的角度對文化空間進行剖析,并提出要用文化生產與再生產的方式對文化空間進行可持續性保護[9];高丙中認為文化空間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某種自然或者某種存在被抽象化進而符號化,同時這種符號化的存在被賦予某種固定的意義,使得物的存在狀態由“物理的”存在向“人文的”存在轉換(1)高丙中在2007年6月“城市建設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論壇”上提交的論文《中國近世紀以來的文化空間與核心象征》具體闡述了這一觀點。。綜合國內眾多學者對文化空間理解,文化空間應具備三大基本要素:一是有可以依附的物理場所,二是有人參與的文化活動,三是在特定時間反復出現的活動。洞頭媽祖祭典作為信俗類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文化空間是其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土壤,其傳承和保護必然牽扯文化空間的方方面面。
二、洞頭媽祖祭典概況
洞頭是浙江省溫州市的市轄區,為溫州四大主城區之一。其地處浙南沿海、甌江口外,是全國14個海島縣之一、浙江第二大漁場。洞頭區總面積892平方公里,由168個島嶼和259座島礁組成,素有“百島之縣”“東海明珠”美譽。其中陸地面積100.3平方公里,戶籍人口15.4萬,常住人口約12.91萬,下轄北岙、東屏、元覺、霓嶼4個街道以及大門鎮、鹿西鄉,共計84個行政村。洞頭區南距臺灣省138海里,機動船僅需8小時即可達到。臺灣地區漁民與洞頭居民交流頻繁,其在漁汛期到洞頭生產、補給時,必前往島上媽祖廟祭拜,贈送錦幛。而洞頭漁民每逢造新船,必在船艙設龕供奉媽祖;漁汛開始和結束時,亦需至媽祖廟祭拜。
媽祖在我國東南沿海一帶俗稱“海神娘娘”,也稱“天妃”“天后圣母”等。媽祖原名林默,福建莆田人,史傳其16歲得授秘法,通曉天文地理、精通醫學,有驅邪治病和泅水航海的本領。傳說她羽化升仙后常在海中救護遇難漁船,因而被漁民奉為“航海女神”。體現中國海洋文化特質的媽祖信仰始于宋代,興于明清,繁榮于近現代。隨著影響力的擴大,媽祖從眾多海神中脫穎而出,成為沿海地區民眾信奉的“海上女神”。
媽祖祭典是媽祖信仰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最早出現于宋代,經過元、明的不斷發展和充實,到清代形成大型的媽祖祭典儀式。現代媽祖祭典儀式傳承了積淀千年的媽祖祭典文化,是一種“活態文化”,至今熠熠生輝。具體而言,媽祖祭典指的是以祭祀、習俗、禮儀、傳說、技藝、民間音樂舞蹈等非物質文化和廟宇、古跡、祭器等有形文化為表現形式的民俗文化,涉及民間藝術各門類,不僅展現鮮明的地方特色,還與傳統的歲時節日結合在一起,活動內容豐富。
“天下媽祖,祖在湄洲。”洞頭的媽祖信仰源自福建,至今已有400多年的歷史。相傳清乾隆年間, 福建惠安的漁民經常帶著全家在洞頭的北沙和東屏一帶進行捕魚作業,因為一呆就是1個多月,漁民又敬畏大海的無邊無際,所以會隨船帶上媽祖塑像。久而久之,為了更加方便祭拜,媽祖塑像就從船上被請到了岸上。當地居民在洞頭的東沙岙搭建一個茅草屋供奉媽祖,此為最初的媽祖廟。等到捕魚季結束,福建漁民帶著媽祖塑像準備回福建,不曾想在祭拜的時候,媽祖塑像的手足突然掉落,當地居民認為這是媽祖發出的一個信號——她不想離開,想繼續留在洞頭,于是這尊媽祖雕像便留在了東沙村。其后東沙和附近幾個村的漁民籌集銀兩, 按惠安媽祖廟的風格建造東沙媽祖宮,供東沙和附近幾村的村民奉祀。后來, 不僅當地漁民、海運者前來祭祀, 不少路過的臺灣漁民也前來祭拜, 因此媽祖宮香火不斷[10]89-100。目前洞頭6個街道建有媽祖宮14座,其中比較著名的媽祖宮有北岙東沙天后媽祖宮、元角沙角天后宮、中侖后垅天后宮以及正岙大德圣母宮。此外,媽祖和其他神靈合祀的宮廟有10座。洞頭區陸地面積不大,其中14個住人島卻有20余座媽祖宮,可見在洞頭媽祖信仰之盛。
作為洞頭媽祖文化核心的媽祖祭典以祭典為中心,以民間文化活動為輔助,是洞頭漁區盛大的俗信活動,其內容豐富多彩,可分為娛神和娛人兩大部分:在娛神方面有宮廟祭祀、船祭和家祭;娛人方面有迎火鼎、造新船及請令旗。洞頭媽祖祭典繼福建湄洲和天津津南區的媽祖祭典進入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后,于2011年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擴展項目。
三、洞頭媽祖祭典的文化空間
根據我們對文化空間的闡釋,洞頭的媽祖祭典無疑擁有特定的文化空間——媽祖祭典定期(媽祖誕辰和媽祖羽化成仙日)在媽祖宮舉行祭祀活動,并伴有一系列民俗文化展演,是一個集空間、時間和文化三者為一體的文化空間。根據媽祖祭典活動內容有側重,民眾的參與程度不一的情況,筆者將媽祖祭典的文化空間劃分為核心圈和非核心圈。核心圈即媽祖的信仰強盛,民眾參與度高,能充分展示媽祖文化特質的區域,這個區域以天后宮為圓心,信仰力由內向外逐漸遞減。由此看來洞頭媽祖祭典的核心圈是分布在洞頭各社區的天后宮,而其中最大的核心圈便是洞頭最早建造的天后宮——東沙天后宮。非核心圈即除天后宮外所有開展媽祖巡安活動的街道。洞頭媽祖祭典自形成伊始,洞頭民眾就一直堅持逢初一、十五去媽祖宮燒香禮拜,每年農歷三月二十三媽祖誕辰和九月初九媽祖羽化成仙日舉辦宮廟祭典。然而自2010年政府牽頭舉辦大型“媽祖平安節”后,媽祖祭典的文化空間——核心圈已然發生改變,由原先的宮廟祭典轉變為媽祖平安節活動,洞頭媽祖祭典的文化空間也因此被重構。
(一)洞頭傳統媽祖祭典文化空間的構成
就洞頭傳統媽祖祭典來說,從空間性上看,既包括舉辦祭典的26座媽祖天后宮,還包括媽祖出巡(迎火鼎)所經過的北岙街道、東屏街道、元覺街道和霓嶼街道;從時間性上看,每年農歷三月二十三媽祖誕辰日、九月初九羽化成仙日為東沙媽祖宮的春秋二祭;從文化性上看,媽祖祭典是以天后宮為物質載體,融媽祖文化與海島民俗文化為一體的活動。
傳統媽祖文化空間以娛神為主娛樂為輔,媽祖祭祀一直是媽祖祭典的核心環節,旨在消災解厄、祈禱興旺。因此有必要了解傳統媽祖祭典核心圈的祭祀活動——宮廟祭祀。本文以洞頭香火最旺、祭典程序最規范、內容最豐富的東沙天后宮祭典為詳細介紹對象,并以此作為探討洞頭媽祖文化傳承與保護問題的基礎。
在人員組織上,媽祖祭典活動開始前須選舉出首事會,首事會全權負責組織、安排祭典活動。首事會由16人組成,入選的首事均為當地名望高、捕魚技術精湛的船老大。這些首事細分成財務、采購、香火、抄寫、神事、安全、后勤等小組,每位分領不同任務,以確保活動順利進行。
在儀式活動內容上,宮廟祭典的核心內容是“做供”。做供的道場規模根據當年的年成來確定,有“大作”“中作”“小作”之分。一般情況下年成以“中作”居多。中作邀請師公10-12人,其中主祭(壇主)1-2人,陪祭立壇3人,助祭2人,鼓樂、五音3-4人。開祭前,先在宮廟里準備好祭祀用具并擺設,祭壇分為三層九壇——前、中、后三層,左、中、右三排,形成對稱,每壇由兩張長凳和一張四方桌搭成,四方桌架在長條凳上,每個祭壇下設祭拜臺,用木板搭成,上設草席、地毯供師公和信徒祭拜。中一壇為地壇,供地藏王菩薩,后一壇為神壇,供媽祖神,前一壇為天壇,供玉皇大帝,左邊三壇分為福星、壽星、財星,稱“三星壇”(圖1)。

圖1 東沙天后宮“做供”道場平面圖[10]93
信眾們在師公的帶領下,先拜媽祖壇,次拜地壇,再拜天壇,然后左壇轉右壇,巡回一周祭拜,拜畢,再轉到天壇,6人一組輪流祭拜,由師公分發給每人一支香,鞠躬三拜,再把香插入香爐,接過師公手中的一杯清茶或者黃酒,對著玉皇大帝飲盡。媽祖三月二十三日誕辰日正式開祭,在開壇時,師公領一眾人員念凈天法語。祭祀進入正式程序后,祭祀內容分以下流程:請水——請神——祭北斗——祭三界——請灶神——祭蘸進表——獻敬——玉皇赦——解厄——東岳醮——入敬。整個祭祀活動結束后即設平安宴,規模為20-30席,每桌的12道菜均以平安為題命名。宴后,還進行戲班子表演(以南戲居多)。一般情況下,媽祖羽化成仙日只“做供”,不演戲。
洞頭媽祖宮的祭祀形式多樣,有宮廟祭祀、家祭和船祭,以宮廟祭祀的程序最為規范,參與人員也最多。宮廟祭祀的廟宇有大有小,而無論大小均需限定參與人員的數量,因此宮廟祭祀的神圣空間有較高的私密性、神圣性。而這樣一種私密的空間更利于營造出莊嚴肅穆的神圣氣氛。媽祖誕辰這一天早晨,主持祭祀的首事們齊聚媽祖佛堂前,由廟祝卜卦向媽祖示意,把船老大的名字逐一念出來,逐個卜定,確定下一年祭祀活動的首事。
(二)洞頭媽祖祭典文化空間的重構
洞頭媽祖祭典的文化空間的變化發生在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媽祖祭典被評為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后,在地方政府的主持下將祭祀儀式和多項民俗活動整合成的新的節俗——媽祖平安節。媽祖平安節圍繞“同謁媽祖、共享平安”的主題,將媽祖祭典大禮、祈福道場、媽祖出巡、文藝展演、民俗商品展等多種活動形式融合在一起。自2010年首屆媽祖平安節舉辦后,就成為洞頭的年度盛事。節俗規模、影響力大大超過之前媽祖祭典。媽祖平安節的出現,改變了洞頭宮廟祭典的時間節律——原定于媽祖誕辰日舉行的祭典因為媽祖平安節的存在而提前了3-5天。媽祖平安節已經成為洞頭媽祖祭典活動中深具影響力的組成部分。從2010-2020年,“媽祖平安節”已舉辦10屆,每屆的舉辦地點在北岙東沙村和元覺沙角村之間輪換,其活動內容形式大致相同,均包括祭典大禮、祈福道場、文藝演出以及民俗展示等場景。接下來筆者以最近參與的第十屆“媽祖平安節”為例,探究新形勢下媽祖祭典文化空間的構成。
第十屆“媽祖平安節”于2019年4月27日9時在東沙天后宮附近一個呈三角狀的半島型海岸上舉行。主辦方是洞頭區人民政府,協辦單位是溫州市民族宗教事務局、溫州市文化廣電旅游局及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承辦單位是溫州市洞頭區人民政府北岙街道辦事處和洞頭區媽祖文化交流協會,指導單位是浙江省民族宗教事委員會、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廳、浙江省文物局。這屆“媽祖平安節”除了在北岙街道東沙港碼頭設立主會場,還在元覺街道和霓嶼街道設置了2個分會場。參與人員包括地方民眾、外地香客、政府人士、專家學者、旅游者、媒體人等近萬人,規模較往屆盛大。
從這一屆“媽祖平安節”主題“同謁媽祖 共享平安 兩岸同心 傳承文化”和標語“民間民俗 共享安福 民間民俗 多彩浙江 民俗風情展演鄉土印象”來看,組織者的意圖是將媽祖文化與洞頭民俗文化融合起來對外展示。平安節主題活動分為開幕式、祈福大典、海上巡安、文藝演出、品平安宴、兩岸同心媽祖文化沙龍這幾個流程。舞臺正中央擺放6張祭桌,桌上鋪設有吉祥如意、龍鳳呈祥涵義的帷帳,祭桌前的蒲團,為主祭和陪祭祭祀媽祖時所用。活動尚未開始,現場早已人頭攢動,負責航拍的媒體工作人員在舞臺兩側調試設備,各界人士則對號入座,前三排坐著政府人士和學者,第四第五排是臺灣地區嘉賓的位置,最后一排坐著民間信眾代表。祭典正式開始,鳴鼓鳴鐘三通,禮生就位,宣布進入領導環節。致辭結束后進入開幕式,先舉行“四海安瀾”匯水儀式——臺灣、福建、溫州蒼南、洞頭四地代表將家鄉的水共同匯入瓶內,寓意“天下媽祖、四海歸一、福澤百島” (圖2) 。

圖2 “四海安瀾瓶”匯水儀式
祈福大典是“媽祖平安節”的首個活動。禮炮聲響起,由8位漁民信眾抬著媽祖風架,在主祭人、陪祭人以及鼓隊、戲曲人物演出隊等的陪同下,登上舞臺接受信眾的祭拜。具體流程為:獻祭品——上香——行三拜禮(拜天、拜海、拜媽祖)——行三獻禮——誦祭文(主祭人誦讀)——請授平安令旗——行三叩禮——收香。禮成之后禮生宣布觀看海上巡安儀式。接著是媽祖威儀出行,由4人抬著媽祖風輦,在主祭人、陪祭人以及鼓隊,戲曲人物演出團隊的陪同下回到東沙天后宮安座(圖3)。

圖3 媽祖神像出巡游
活動至此,媽祖祭典中核心的祭祀儀式結束,之后就是文藝展演。“媽祖平安節”上表演的文藝節目每年都有新變化,這一屆的節目由“鄉音、鄉韻、鄉情”3個篇章組成,主要通過歌舞、器樂等形式展示洞頭媽祖文化和漁家民俗,如鄉音中的“紅圓紅”“地方謠”,鄉韻中的“烤船郎”,鄉音中的“迎火鼎”,都是富有洞頭地方特色的民俗風情。文藝展演之后,所有的活動參與人員開始享用“平安宴”,意在向媽祖表達感恩之情。每張飯桌擺12道有寄意的菜肴,如紫氣東來媽祖面、魚跳耳朵、順風耳朵等。
綜上,“媽祖平安節”是一個集政府會場、民間祭臺和民間文藝舞臺為一體的文化空間。相較傳統的媽祖祭典,“媽祖平安節”文化空間的變化表現在:第一,在物質空間上,從封閉、私密性較高的天后宮轉移到露天場所,從固定的宮廟搬到臨時搭建的舞臺上。舞臺祭祀等同于將媽祖從廟里請出來進行陸上的巡安,這是將傳統巡視過程的供節點放大,原先是廟里的祭祀最為隆重,而現在舞臺的祭祀替代廟祭祀成為最重要的環節。第二,將祭祀大禮、媽祖巡安以及民俗表演置于同一個舞臺展演,傳播力更強,活動的文化內涵更加豐富。第三,就近幾年的媽祖平安節的發展趨勢而言,簡化了祭祀流程,延長了文藝演出時間。傳統媽祖祭典以娛神為主娛人為輔,“媽祖平安節”則是以娛人為主娛神次之,文化空間的性質發生變化。第四,活動主體的變動。傳統媽祖祭典的組織者為船老大,“媽祖平安節”的主導、主持者。活動參與人員方面,傳統媽祖祭典僅限于道士、主祭、陪祭人、信徒等少數人,“媽祖平安節”則有政府人士、專家學者、媒體人、游客、外地信眾參與其中,活動主體日益多元化。
四、媽祖祭典文化空間重構背后的思考
在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中,洞頭媽祖祭典文化如其他傳統文化形式一樣,在現代文化的沖擊下因缺少各方關注和保護而式微。幸而在傳統文化復興浪潮推動下,洞頭媽祖祭典文化傳承和保護工作已初見成效。經歷了重構的洞頭媽祖祭典,開始煥發生機與活力,以“媽祖平安節”的面貌出現在大眾面前。但在重構的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不和諧的因素,若不加以重視,或將對媽祖祭典的久遠保護與傳承構成傷害。
(一)洞頭媽祖祭典文化空間重構的“后遺癥”
1.社區民眾參與積極性降低。洞頭媽祖祭典被納入“媽祖平安節”后,活動的組織方式發生改變,政府相關職能部門代替當地居民推舉的首事成為活動的主要組織、策劃者。熟悉祭奠事務的德高望重者,昔日的主導地位“旁落”,只需在祭典儀式上作為主祭人員走個過場。他們從祭典的組織者、負責人變成普通的儀式活動參與者,人數雖少,但由于在民眾中有號召力、影響力,事實上影響并降低了當地居民參與祭奠活動的積極性。
2.祭典的神圣性減弱。“媽祖平安節”與傳統媽祖祭典相較,存在著儀式空間上的明顯不同。前者在臨時搭建的舞臺上展演,考慮到活動主體來源的多元化及需求,主辦者簡化了祭祀流程的同時增加了節目的娛樂性。后者在封閉私密的空間里祭祀媽祖,嚴格走完繁瑣的儀式程序,莊嚴感、神圣性有充分的保障。神圣空間的日益消解是民間宗教節俗世俗化傾向的一種具體表現,從長遠的角度看,一些民間宗教節俗未必如主辦者(官方)所愿可以順利地保護并傳承下去。
3.缺乏鮮明的地方特色。媽祖信仰是中國沿海地區重要的民間信仰形式。沿海各地以祭拜媽祖為主題舉辦的節慶活動甚為常見。雖說“媽祖平安節”的節日名稱為洞頭媽祖祭典所獨有,但與湄洲的媽祖祭典和天津的媽祖祭典(皇會)相比,在儀式內容、流程的編排各方面沒有突出的特色,所產生的社會效益、社會影響力也不及后兩者。洞頭自2003年起全力構建“海上花園”后,“媽祖平安節”就成為洞頭“以節促游”的一種手段,政府希望借助“媽祖平安節”和旅游產品的聯動,打造全新的旅游形象。以第十屆媽祖平安節來說,主辦者規定凡是活動參與者皆可獲得一張景點體驗券。然而洞頭的旅游產品以觀光旅游為主,類型單一,缺乏體驗型和運動型的產品。現有的旅游產品還存在布局分散的不足,已陷入“難聚合,難連線”的困境[11]。就文創產品而言,目前有貝雕、漁家畫、漁燈、馬燈、剪紙等,而除了貝雕,其他產品均非本地所獨有,能展現洞頭媽祖文化特色的產品不多。未能充分認識到洞頭媽祖祭典文化空間獨特價值的地方政府,欲將媽祖祭典同旅游經濟捆綁生產出地域特色鮮明的文旅品牌,顯然還有很多的路要走。
(二)基于“文化空間”的建議
“媽祖平安節”的舉辦,是政府主導下媽祖文化保護與傳承工作的具體實踐。“媽祖平安節”舉辦的前后,也是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工作開展、媽祖祭典保護小組成立、媽祖宮廟修繕等文化保護措施并舉的時候,其成效值得肯定。就筆者看來,媽祖祭典的當代重構是歷史的必然,“旅游化生存”也可以是媽祖祭典文化持續發展的路徑之一。如前所述,文化空間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生存和發展的土壤,媽祖祭典文化的生存發展,離不開其所處文化空間的營造和存續,接下來筆者從物質空間、精神空間、行為空間三個層面對媽祖祭典文化空間的保護展開討論。
1.對物質空間進行合理管理。一是加強宮廟的修繕。洞頭北岙的東沙媽祖宮和元覺天后宮分別是省級、縣級文物保護單位,在維護、修繕方面有一定的制度保證,但也要關注其他非文物保護單位的天后宮的保護。即使城鎮建設需要,要拆撤一些百年古廟一定要慎之又慎。二是加強島內基礎設施建設。隨著活動規模的擴大,“媽祖平安節”現有舉辦地空間狹小,廁所、道路設置不能滿足節日開展需求的問題突出,基礎的完善、擴大迫在眉睫。三是加快開發展現地方民俗文化特色的文創產品。非物質文化遺產雖然以“非物質”形態存在,但都需要依附于一定有形物質載體。應利用洞頭獨特的媽祖祭典文化空間特性,生產出地方特色濃郁且符合當代審美需求的文創產品。
2.對精神空間——媽祖信仰力展開維護。媽祖信仰之根深蒂固,與漁民的生產實踐的實用功能及認識上的局限性有關。隨著現代化漁業生產技術的應用和推廣,漁業民俗中的禁忌、祭祀習俗及其帶有神秘色彩的觀念已經有所變化。但只要海上危險時刻存在,漁民祈求豐收、平安歸來的愿望不變,這些禁忌、祭祀習俗及其神秘觀念仍會長期留存,這是一種客觀事實,我們在談媽祖文化的保護與傳承時,應對此有清醒的認識。“媽祖平安節”娛樂性加強,神圣性減弱,固然迎合了部分“看客”對宗教節俗的世俗化的需求,卻以疏離民眾實際精神需求,使當地人對媽祖祭典逐漸失去敬仰乃至興趣為代價。要改變這種“得不償失”的狀況,節日的組織、主辦者需要重新規劃節目,盡可能還原媽祖祭典作為宗教祭祀的本來面貌,以此為基礎,作為洞頭媽祖祭典第一文化主體的當地居民才會自覺自愿地支持、宣傳并傳承原屬于他們的文化。
3. 調整完善行為空間。“媽祖平安節”的舉辦是多種社會力量合作的結果。其中,政府一方要明確自己的角色定位。作為組織、主辦者,宜在政策、資金、管理等宏觀層面上提供支持,而非在祭典操作這類細節問題上大包大攬。如遵照民間慣例,仍由通過民間推舉產生的首事負責祭典的工作,積極調動居民參與的積極性,維護其“當家做主”主體地位。
此外,在媽祖祭典傳承人的挖掘、培養方面,應在一年一度的節日之外多下功夫,切實遵循《浙江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條例》中規定的“各級人民政府應當支持代表性傳承人和代表性傳承單位開展傳承活動,支持的主要方式有:提供必要的場所;給予適當的資助;促進交流與合作;其他形式的幫助。”[11]從基礎教育著手,開設非遺相關課程培養青年傳承人,拓寬傳承人的培養途徑,鼓勵和支持非遺傳承人開展傳習活動。只有將傳承人的挖掘、培養落到實處,才能造就一大批懂得媽祖文化,也樂于傳承媽祖文化的傳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