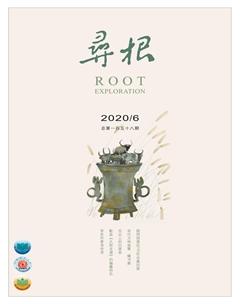“永州八記”“八愚”遺址及其他
呂國康

“永州八記”是柳宗元山水游記的代表作。“八愚”是柳宗元構建的園林勝景,為此寫有“八愚”詩及《愚溪詩序》,這是美的發現與創造,是子厚“甘終為永州民”的精神家園。“八記”“八愚”遺址的保護與利用,是擺在我們面前的緊迫任務。
永州刺史柳拱辰,于北宋至和三年(1056年)在東山建府學宮(文廟),“立子厚祠堂”,柳宗元得到重視。柳宗元去世兩百年后,宋徽宗頒發《初封文惠侯告詞》,追封柳宗元為文惠侯。南宋張敦頤說:“零陵極窮陋之區,先生居十年,披荊剪蕪,搜奇選勝,放于山水之間,而獨得其樂。如愚溪、鈷潭、南澗、朝陽巖之類,往往猶在,皆先生夕日杖履徜徉之地也。”(《柳先生歷官紀并序》)往事越千年,永州學人對“八記”遺址進行考察論證,基本上解決了“西山之爭”,對“鈷潭之謎”提出了新見。
《始得西山宴游記》為“八記”之首,西山所指是研讀“八記”美文首要問題。清代宗稷辰《永州府志》說:“西山在城西門外,渡瀟水二里許,自朝陽巖起至黃茅嶺北,長亙數里,皆西山也。”黃佳色《游西山》詩:“西山迢迢三五里,一山欲斷一峰起。”這是廣義的西山。柳文中的“西山”,單指哪座山,永州學者一說糧子嶺,一說珍珠嶺。兩山分別在愚溪南、北,與柳子廟相鄰。筆者贊同珍珠嶺說,2003年在《〈始得西山宴游記〉釋疑》一文中,從五個方面進行歸納,認為“西山”單指珍珠嶺,理由是:1.站在法華寺,極目遠眺,正西方正是珍珠嶺。視野往右是黃茅嶺,往左則望不到糧子嶺。2.珍珠嶺山頂呈圓形,沒有山尖,系紫色砂巖,土質薄,不長大樹,故“始指異之”。3.若將糧子嶺定為西山,因柳子草堂在愚溪東南,攀登西山不需過橋,則與柳宗元元和八年(813年)寫的《與崔策登西山》所述“聯袂度危橋,縈回出林杪”不符。4.從山勢而言,兩山比較,珍珠嶺要高峻。糧子嶺海拔158米,珍珠嶺海拔174米。從愚溪南岸有緩坡,通往糧子嶺山脊,而從北岸攀登珍珠嶺則顯得十分陡峭。5.明朝易二接的《零陵山水志·西山記》、清代宗稷辰的《永州府志·陸道圖說》描寫記載了珍珠嶺的特點與方位,說明珍珠嶺即西山。《徐霞客游記》也認為西山“當即柳子祠后圓峰高頂,今之護珠庵者是”。清代姜承基的《永州府志·永州府總圖》明確將西山標在愚溪北側。
2012年9月,湖南省文物考古所柴煥波研究員考察“永州八記”與“八愚”遺址,后發表了《永州山水千古頌 ?柳子遺址何處尋——柳宗元〈永州八記〉遺址考案報告》(《中國文物報》2013年5月10日),提出了不少新見。對于西山,他說:“通過實地調查,珍珠嶺吻合文本的描述。”還認為糧子嶺說主要是依據“鈷潭在西山西”(《鈷潭記》)一語。其實,理解“鈷潭在西山西”一語的關鍵在于現在西山的形態與過去有別,柳宗元時期珍珠嶺的山腳應接近瀟水河岸,包括現在的居民區。認識到這一點,“鈷潭在西山西”一語就可迎刃而解了。鈷潭、西小丘、小石潭均在愚溪下游、柳子廟附近,因與“八愚”密切相關,且存在較大分歧,容后再說。
《袁家渴記》開頭說:“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之可取者五,莫若鈷潭。由溪口而西,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麗奇處也。”蕪江現稱茆江。“永州八記”后四記中的袁家渴、石渠、石澗均在西山之南。袁家渴本是零陵朝陽街道沙溝灣社區前瀟水中的一段灣流,河灣中原有小山,上有美石巖洞,下有白礫草木。20世紀70年代修建南津渡水電站時,袁家渴恰在壩基護堤處,今只余一口小塘,大的自然環境依稀可辨,而柳子描寫風振草木的美景難覓。石渠位于沙溝灣社區兩山夾峙的田峒中,長約一里半。因修建南津渡水電站,石渠的下游及出口地段遭到破壞,但中游與上游部分尚存。柳子“遺之其人,書之其陽”的碑刻已不復存在。石澗位于沙溝灣社區諸葛廟村的田洞中,長約3公里。石澗上游因遭改水、挖塘而破壞。下游入瀟水處,因修建朝陽大道而改用地下涵洞形式,其余百多米基本保持原貌,田園風光依舊。小石城山在愚溪之北約3里,為一座高數十丈的石灰巖陡崖,宛如峭立的城堡,“望若列墉,入若幽谷”。這是“八記”中保存較完整的遺址之一,現有小徑直通山頂,山頂新修了寺廟。
“八愚”遺址
南宋汪藻說:“紹興十四年,予來零陵,距先生三百余年,求先生遺跡,如愚溪、鈷潭、南澗、朝陽巖之類皆在,獨龍興寺并先生故居曰愚堂、愚亭者,已湮蕪不可復識。八愚訪石亦訪之無有。”(《永州柳宗元先生祠堂記》)“八愚”遺址在何處?千百年來,眾說紛紜。
1.“呂家沖”說
1981年春,零陵師專陳雁谷先生根據柳子詩文的描述,沿愚溪尋訪“八愚”遺址,“確定八愚遺址在永州市河西東岳宮村呂家沖”。寫了《八愚遺址考》《柳宗元故居考》兩篇短文,還繪出了“八愚遺址示意圖”。陳先生的依據之一是:柳宗元于元和五年在《送從弟謀歸江陵序》中說“筑室茨草,為圃乎湘之西”。在《與楊誨之書》中說“方筑愚溪東南為室”。愚溪東南,在地理方位上屬呂家沖地段。二是與《愚溪詩序》所說“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步行里數相符。三是根據劉禹錫《傷愚溪詩》中“木奴千樹屬鄰家”“柳門竹巷依依在”的詩句判斷,愚堂后應非常開闊,適合種大片柑橘、竹林。這一帶屬糧子嶺西麓,至今竹木蔥蘢,綿延數里。這一發現可稱得上開創性的工作,“呂家沖”說得到了零陵文物部門的認可。但是,陳先生認定糧子嶺為西山,對鈷潭與“八愚”的關系未加關注,對“八愚”的認定與古今學者認為“八愚”在愚溪之北意見相左。更值得質疑的是,在唐代,河西是比較荒僻的,人煙稀少,直到清代康熙年間,零陵古城十二街十八巷二十五坊尚無柳子街,呂家沖離城更遠,柳為何在此卜居?另據了解,呂氏是清代才搬遷過來的。若柳子故居在此,為什么柳子廟不建在此處?
2.“柳子街120號”說
1986年9月,永州環衛所工人張緒伯經過多年的尋考,對“八愚”遺址有了新的發現,認為其遺址在柳子街120號至126號的愚溪北畔,當地老百姓稱此地為“十五亭”(意即愚亭)。亭保存到現代,橫跨柳子街,原造紙廠為運輸原料方便將其拆除。他的文章《永州“八愚”尋考及其他》在《西華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2期發表。1997年,下定雅弘教授在日本《中國文化論叢》第六號以長文述評介紹張的研究成果。根據柳文,他認為此段是愚溪風景“尤絕者”,其中“嘉木異石錯置”之奇景至今歷歷在目。至于它離溪口的距離,他經過換算,唐代的二三里約等于現在的0.4至0.6公里。他認為柳文是活地圖,對“八愚”方位、距離、形狀均做了描繪,按圖索驥,不僅尋訪到愚堂遺址,還對“鈷潭”“小石潭”遺址有新的見解。柳子街120號即“愚堂”原址,其房屋的巖石基座,是《鈷潭記》中“崇其臺,延其檻”留下的。《鈷潭記》的描述,是從愚溪上游開始的,“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是指節孝亭一帶的漩水灣,此處彎度最大;“畢至石乃止”,“此石”是指愚亭下方河床中的“溪石”,此大石民間稱“三角巖”,后來被炸掉了;“流沫成輪,然后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余,有樹環焉,有泉懸焉”,這才是真正對鈷潭的描述。從現場觀察,愚堂前的愚溪是一灣靜水,河道窄長,水面“清而平”,視野之內有十余畝,與文本吻合。他的觀點言之有理,自成一家,而且與民間流傳的柳宗元故居在柳子廟一帶相吻合。不足之處,其考察尚缺乏理性的分析,對“方筑愚溪東南為室”之意,將“為”解釋為動詞“流去”,句子譯成“(我)剛剛建筑了住房,愚溪從住房的東南方向流過去。”這有些穿鑿附會。從現場來看,這里風景確實“極佳”,但“潭”的形狀不明顯,故響應者寥寥。柳為什么命名“鈷潭”,這是一個比喻,古代的熨斗稱“鈷”,由長柄與圓斗組成,前面的溪流為柄,此處為圓斗,不失為一種解釋。柴煥波研究員認為張老對鈷潭、西小丘和“八愚”群景位置的確定,“突破古人舊說,質樸直觀,小疵大醇,并作了一些補證,以支撐“柳子街120號”說。
3.“鈷潭石刻”說
劉繼源先生多次對“鈷潭”及“八愚”進行田野考察,有了新的突破。他從與愚堂相關的景點入手,首先確定西山為“珍珠嶺”,并認為“鈷潭”在古刻有“鈷潭”三字的“山石”處,它是愚溪中一灣泓水,柳文“其始冉水自南奔流,抵山石,曲折東流”(《鈷潭記》)中,“山石”即西山西北道口山麓之巖石。劉在《柳宗元在永州部分遺址位置的探討》(《柳宗元詩文研究》,珠海出版社,2003年)中指出柳在愚溪有兩處住所:一是“八愚”中的“愚堂”,二是“方筑愚溪東南為室”的“草堂”。其依據是《愚溪詩序》:“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愚溪之上買小丘,為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為愚亭。池之中為愚島。”也認為“其尤絕者”即鈷潭及附近一帶,并將除愚溪、愚丘外早已荒蕪泯沒的“六愚”定位于今柳子街口鈷潭北坡上新建的居民區一帶。“家焉”是說柳已于元和四年(809年)冬移居于鈷潭上購置的民宅,即“愚堂”。“草堂”是據劉禹錫《傷愚溪》中“草堂無主燕飛回”定名。柳宗元元和五年(810年)后遷居愚溪東南的草堂,即位于原永州七中校園內。民國后期,唐耀先任零陵縣縣長時,曾在此建過“愚莊”。劉先生提出,《與楊誨之書》寫于元和五年春,此時柳尚在愚堂。“方筑愚溪東南為室”,方有正在進行之意,愚溪下流是一段由西南轉向東流的小溪,不能作為定東南方位的基準點。以愚堂作為定方位的基準點,則愚溪之東南可定位于七中校園一帶。這里水陸交通方便,當時有大片荒地。對于將“八愚”定位于呂家沖一帶,他認為“在柳宗元詩文中,尋不到只字片言為證,絕不能作依據,不然會貽笑大方!”至于將鈷潭定位于柳子街120號處的愚溪中,“是不妥的,因為該處既不位于西山道口,也不是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之處。電站壩址以下,河床大致是由西向東,并沒有‘旁廣中深的水潭”。劉先生的考證條理清晰,具有創見,特別是愚堂、草堂之說,令人耳目一新,筆者深表贊同。對柳子遷居愚溪及構筑草堂的原因,筆者寫過《從龍興寺到愚溪“草堂”——柳宗元在永州的寓所》,以補充劉說。對于“鈷潭”石刻處,永州學者大多認為此處為鈷潭。在劉先生之前,龍震球先生認為該處為鈷潭舊址。陳雁谷先生也持相同觀點,并認為柳文描寫與現狀相符。但何書置先生看法不同,認為此處非鈷潭遺址。他從地方志中尋找到依據。明代錢邦芑在《游愚溪記》中說:“問鈷潭所在,僧指曰:‘上行二百步即是,石上勒字可據。余竊疑焉。土人引自溪邊,有危石斜立,果勒‘鈷潭三大字。讀柳子厚記,西山西北道二百步得鈷潭,西山此去尚二里之遙,況山水形勢與柳文俱不合,意鈷潭當別有所在,或因陵谷變遷,失其故處,俗流不學,妄為附會,遂指此當之耶!”(康熙九年《永州府志·藝文志》)并經實地考察,認為“鈷潭遺址,即今距愚溪口約四里的順水灣”(何書置:《柳宗元研究》,岳麓書社,1994年)。順水灣即漩水灣,今呂家沖一帶。若將“鈷潭”石刻處確定為鈷潭,從而定位潭西小丘、西行百二十步的小石潭,西小丘不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的美景,小石潭既無“四面竹樹環合”,也不見“近岸卷石底以出”,更缺“小石潭”,這里純屬愚溪一截,參觀者無不搖頭。按照柴煥波的觀點,應將此處重新訂正為“小石潭”的真正所在,結果要形象得多,柳文“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隱約入目。戶崎哲彥教授在《“鈷”不是熨斗而是釜鍋之屬——柳宗元的文學成就與西南少數民族的語言文化》文中,對“鈷”一詞進行交叉探討,論述“鈷”并非“熨斗”之意,而是釜鍋之屬。易新鼎點校《柳宗元集》時,在《鈷潭》的題注中說“字,諸韻皆無從‘母者。《唐韻》作‘錛。下注云:‘鈷,錛也。……鈷錛乃鼎具。簡言之,鈷潭就是像釜鍋形狀的圓形潭。”
“永州八記”之鈷潭與“八愚”密不可分,鈷潭既是愚溪風光“尤絕者”,也是“八愚”之愚堂所在處。由于記于溪石之上的“八愚詩”石刻被毀,這一鐵證無跡可尋,故令人們苦苦探索。永州學者經過40年的不懈努力,取得了重大進展,離真相僅一步之遙。應從柳子街120號及“鈷潭”石刻處二選一,最終確定鈷潭及“八愚”。不管定位哪一處,愚溪草堂均在南岸原七中校園一帶。康熙《永州府志》載:“愚溪草堂,縣西一里,宣德初陳浩建,何惟賢有記。”可佐證。若將柳子街120~126號之愚溪定為鈷潭,北岸一帶即“八愚”遺址。從120號“愚堂”遺址“西二十五步”,為面積不到一畝的“西小丘”,“若牛馬之飲于溪”“若熊羆之登于山”的奇石歷歷在目。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便是“小石潭”,即“鈷潭”石刻處。那么,原定的西小丘、小石潭則應撤銷。這需要得到文物部門的認可。
保護與利用
由于宣傳不夠、保護不力,“永州八記”遺址的現狀令人擔憂。“永州八記”遺址群屬于一種歷史性的人文景觀,也有人稱之為城市歷史景觀,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與藝術價值。柴煥波提出“永州八記”大遺址保護,將從袁家渴至小石城山6.6平方公里納入保護范圍。設想很好,但因城市的發展實施有困難。劉繼源先生《關于籌建永州愚溪公園的芻議》更為現實。政府有關部門應編制“永州八記”遺址保護規劃,尤其是對前四記的遺址,盡快確定,納入保護規劃。
“永州八記”前四記均與愚溪相關聯,柳宗元在愚溪之畔的“愚堂”“草堂”生活了五年,他寫下《愚溪詩序》《愚溪對》《冉溪》《溪居》等10多篇與愚溪相關的詩文,嬉笑怒罵,皆成文章。還說“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鈷潭記》)洋溢著對鈷潭、愚溪的喜愛之情。自劉禹錫《傷愚溪》詩問世以來,文人墨客前來尋訪愚溪,寫下數以百計的懷念柳子的佳作。“八愚千古”,愚溪是一條多姿多彩的文化之溪。明代徐霞客兩次游永州,他說:“永州三溪:浯溪為元次山所居,在祁陽。愚溪為柳子厚所謫貶居地,在永州。濂溪為周元公所生,在道州。”“浯溪之‘吾有三,愚溪之‘愚有八,濂溪之‘濂有二。有三與八者,皆本地之山川亭島也。”(《徐霞客游記·楚游日記》)三條溪綻放三朵文化奇葩,關聯三大文化名人元結、柳宗元、周敦頤。
明代芝城八景中有“愚島晴云”,清代永州八景中有“愚溪眺雪”。愚溪下游遇珍珠嶺與糧子嶺之間的下伏石灰巖阻隔,流水便強烈沖刷、侵蝕、切割巖層,便形成了鈷潭等處的奇景。河床全石為底,系白色石灰巖,古稱“玉石港”。此是3.1~2.7億年前在海洋中由石灰質(碳酸鈣)沉淀而成的。愚溪下游生態環境保護較好,兩岸綠樹成蔭,清瑩透澈的溪水奔流不息,與柳子廟相映成趣。
柳宗元在永州生活了十年,先住龍興寺,后遷居愚溪之畔。他留下的678篇詩文中約500篇寫于永州,可以說永州十年是他創作的黃金時期。國內外游客訪柳時,都會詢問柳宗元曾住在什么地方。龍興寺已是千秋嶺小學校園,在原七中恢復愚溪草堂也無可能,或可在呂家沖修建小而精的愚溪草堂,體現永州建筑風格,將愚丘、愚泉、愚溝、愚池、愚亭、愚島等元素加進去,將柳子廟、柳子街、愚溪打造成研學基地,以供廣大游客尋訪“八記”“八愚”遺址,參觀柳子街、柳子廟,了解柳宗元的生平、創作、成就,體驗柳宗元筆下的永州山水,懷念一代宗師柳宗元。
(題圖:西山)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歷代柳宗元研究文獻整理及數據庫建設”(16BZW034)階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