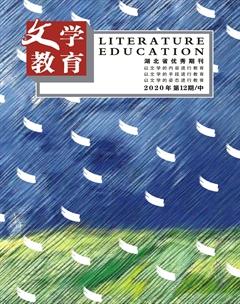在湖北省作協(xié)鄉(xiāng)村題材創(chuàng)作會議上的發(fā)言

今年的一個中心工作就是決戰(zhàn)決勝脫貧攻堅戰(zhàn)。已經(jīng)開展五六年的精準(zhǔn)扶貧工作將在今年圓滿收官,也必須兌現(xiàn)我們國家向世界宣布脫貧的莊嚴(yán)承諾,這是對所有脫貧攻堅戰(zhàn)隊員的嚴(yán)峻考驗,而我正是脫貧攻堅戰(zhàn)的其中一員。從2017年10月份開始參加精準(zhǔn)扶貧工作,直到今天,已有三個年頭。這是一件異常辛苦的工作,就在上周,從8月25日到29日,我每天都是六點半趕到村里,下午六點離開,參加脫貧攻堅戰(zhàn)的省級迎檢。這項工作雖然辛苦,卻有無法用語言描繪的意義,對于我個人而言,獲得遠(yuǎn)遠(yuǎn)超過付出,尤其是,這項工作給我?guī)砬八从械木裣炊Y,并引發(fā)我對當(dāng)下新時代社會轉(zhuǎn)型及寫作的思考。個人和時代不由自主發(fā)生了緊密聯(lián)系。但僅有聯(lián)系遠(yuǎn)遠(yuǎn)不夠,個人如何回應(yīng)時代巨變,而時代巨變下,我們的寫作將會發(fā)生怎樣的變化,從而完成兩者關(guān)系的構(gòu)建?這是每一個寫作者面臨的終生課題。
下面,我結(jié)合自己脫貧攻堅紀(jì)實作品《百里洲紀(jì)事》來談?wù)勎业恼J(rèn)識。
2017年下半年,我參加精準(zhǔn)扶貧工作,下鄉(xiāng)駐村成為常態(tài)。至此,我的生活環(huán)境發(fā)生了變化,一些氛圍也悄然改變。
我周圍的對象可以分為三大類:扶貧干部、所謂的貧困人群(為何用上“所謂”的限定語?因為這個群體的“老病弱殘”構(gòu)成的特征,表現(xiàn)在物質(zhì)上確實貧困,但精神上呢?“貧困”一詞難以概括,故而,我加上了限定語)、當(dāng)下精準(zhǔn)扶貧的鄉(xiāng)村或者說新農(nóng)村。
那是民心民情最集中的地方。
在那里,一日三餐、吃喝拉撒、生老病死……赤裸裸的物質(zhì)存在下,幾乎每天都有煩心的事情發(fā)生,那些事情總是融合了前塵舊事、現(xiàn)在的生存狀況和未來的思慮。它包含了時光的味道,呈現(xiàn)出厚重的歷史滄桑感,其復(fù)雜性迫使你去了解、去交流、去思考。關(guān)于生老病死,關(guān)于人心人性,關(guān)于時代環(huán)境,關(guān)于精神向度,絕大多數(shù)時候,這些事情會不由自主地跳出新聞媒體的框架,甚至以意想不到的面目出現(xiàn),沖擊人的心靈和頭腦。
精準(zhǔn)扶貧相關(guān)政策適時出臺并不斷加大力度,助推人類反貧困的脫貧攻堅戰(zhàn),這是上升到國策的大事。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要求出發(fā),把扶貧開發(fā)工作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四個全面”戰(zhàn)略布局,作為實現(xiàn)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biāo)的重點任務(wù),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和安排,全面打響脫貧攻堅戰(zhàn)。脫貧攻堅力度之大、規(guī)模之廣、影響之深,前所未有,取得了決定性進(jìn)展,顯著改善了貧困地區(qū)和貧困群眾生產(chǎn)生活條件,譜寫了人類反貧困歷史的新篇章。精準(zhǔn)扶貧的意義不言而喻。其目的也明顯,用簡短的詞語概括不外乎就是,挽救、救贖。
這項國策,對于文字工作者而言,記錄下來,既是責(zé)任,也是一個人以文學(xué)的面目回歸本源的最好途徑。當(dāng)我們摳掉那些繁縟的條條框框,只剩下其骨架和內(nèi)核時,國策與文學(xué)合二為一了。文學(xué)的功用,說到底,就是救贖。當(dāng)然,文學(xué)的救贖功用并非劍指他人,而是為自己。但寫作者在記錄當(dāng)下的瞬間,她或他又怎能是旁觀者或是記錄者?
是在場的參與者。
在那個地域,接近我們生命本源的地方,有生命的初心,有生命胚芽的倔強成長。任何一個外來者,都會嗅到致命的童年氣息和強烈的生活同感。
“命運”一詞,裹挾的暴風(fēng)雪,總是不定時地襲擊一個個脆弱的肉身。沒有誰能例外。而這些身處鄉(xiāng)村、以土地為生的人,不過因為條件的薄弱,代替我們早先感受了命運的暴風(fēng)雪,并將他們的痛苦和感知痛苦的心理及精神傳遞給我們,提供一個個參本,供我們感知、應(yīng)對。我在扶貧中,最經(jīng)常聽見的一句話是:千萬不要低估這個身處底層的群體的人性人心。
那些簡單的靈魂,因為地域限制而肉身衰朽,又因遭受疾病和意外事故的碾軋而生活困頓,但他們卻總在不經(jīng)意中,朝我們發(fā)出螢火蟲似的清亮光芒。讓人感受到鄉(xiāng)村這個母系詞語的最初溫暖。也要人感受到,我們這些對接的扶貧脫貧對象,經(jīng)常發(fā)生身份置換。
而今,我們結(jié)成對子,不過是時間的安排,要我們溯回,回到人生最初的地方,去與那些被漠視的、被丟棄的東西相認(rèn),去見證孕育了我們、現(xiàn)在快要成為廢墟的子宮、胎盤。
也只有那樣的瞬間,我們體會到,相識不相識都不要緊,大家就在一個場系中。場系里有一塊磁鐵,歸類我們,又讓我們彼此辨認(rèn)。我們這些同類用一個詞語概括就是,人民。而人民,更多的時候是指生活弱勢者。鄉(xiāng)村中的生活弱勢者人數(shù)龐大,遠(yuǎn)遠(yuǎn)超出了新聞統(tǒng)計的那些數(shù)字,因為評價的標(biāo)準(zhǔn)——生存現(xiàn)場,不再是單純的物質(zhì)方面,還有精神方面和心理方面。
可能在物質(zhì)和精神這兩方面,得到關(guān)注的非常多,而心理方面的卻十分匱乏。而在這樣一個高速發(fā)展的時代,沒有誰能避免心理問題,或多或少都存在,何況身處塵埃中的他們?心理疾病下的弱勢者,大多數(shù)時候,是以“貧困”面目顯形,換言之,“貧困”有多深,心理問題就有多深。假如當(dāng)下中國的敘事,不給予鄉(xiāng)村中弱勢群體的心理關(guān)注,是無法反映出這個龐大群體內(nèi)心的困惑的,從而也談不上心靈的真實。缺乏心靈層面的真實,解答不了內(nèi)心的困惑,脫貧攻堅戰(zhàn)也無法突破最后一公里的瓶頸。
作為文本,我想提供一個參考——從心理層面關(guān)注他們,形成正視,建立一種平等的交流姿態(tài)。在這樣的基礎(chǔ)上,解決這個龐大群體的心靈障礙,決戰(zhàn)決勝脫貧攻堅戰(zhàn),才有依據(jù)。關(guān)注鄉(xiāng)村弱勢群體的心理脫貧過程,正是《百里洲紀(jì)事》區(qū)別于其它脫貧攻堅紀(jì)實文本的地方。事實上,幫扶工作中,著重這個群體的心理脫貧,也是一種需要,溝通的需要,而溝通是最佳的相互認(rèn)同狀態(tài)。用心理學(xué)知識講,溝通就是自我認(rèn)知、自我發(fā)現(xiàn),還是自我啟動免疫系統(tǒng)。
而在溝通的一刻,我們就是一個整體。我們互為依靠、互為扶持、互為見證時,“人民”一詞,才有機會被呈現(xiàn)出浩瀚的態(tài)勢。說到底,“人民”將我們歸類的標(biāo)準(zhǔn)正是心靈和精神,而人民的底盤扎根在鄉(xiāng)村。那么,我不可避免說說自己對新時代鄉(xiāng)村的認(rèn)識。
曾經(jīng)有人擔(dān)心,中國的鄉(xiāng)村某天會消失在城鎮(zhèn)化的鐵蹄下,鄉(xiāng)村記憶也將被束之高閣,成為古董。這種擔(dān)心有必要。但我還是要說,“鄉(xiāng)村”對中國人而言,豈止是物質(zhì)的存在?它是千百年來延續(xù)的一種公眾情緒,早已融化于我們的血肉和骨髓里。因為,那細(xì)胞般存在的“鄉(xiāng)村”細(xì)節(jié)無處不在,它決定了我們的口味、方言和精神認(rèn)知,還規(guī)避了一些禁忌。這是源遠(yuǎn)流長的河流,是我們生命的根脈。
今天的鄉(xiāng)村承載了歷史的演變和時代的痕跡,是時間的綜合體,是變革中內(nèi)涵豐富外延廣博的新時代的鄉(xiāng)村世界。這樣嶄新的時代鄉(xiāng)村必然要產(chǎn)生相對應(yīng)的時代新人。而誕生于當(dāng)下鄉(xiāng)村的文學(xué)作品,也是復(fù)雜的,卻也考驗寫作者的思想認(rèn)識和生命體驗。無論如何,“鄉(xiāng)村”還是文學(xué)的母語胎盤,它是創(chuàng)作者的記憶,是田野記錄者的童年再發(fā)現(xiàn),還是生命根源的指認(rèn)和時代社會發(fā)展的見證。
它太過于中國化,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呼愁。故而,反映脫貧攻堅戰(zhàn)的鄉(xiāng)村紀(jì)實作品,我更愿意稱為中國敘事。這類敘述賜予寫作者的福祉就是,心靈在回溯中,會觸摸到生命的源頭;人生經(jīng)驗在扎根泥土中,將挖掘出時代轉(zhuǎn)型的總體脈絡(luò),完成個人與時代的對話和彼此建構(gòu)。
而現(xiàn)實的鄉(xiāng)村,就是精準(zhǔn)扶貧政策下的當(dāng)下鄉(xiāng)村。精準(zhǔn)扶貧政策的出臺,集中到一些物質(zhì)的補貼和一些保障制度的適時出臺,在一定程度上幫助了“貧困”人群脫貧。然而,有些事情,并非依靠物質(zhì)就能解決,比如鰥寡者的孤獨,比如精神疾病患者的心靈訴求,比如留守兒童缺失關(guān)愛和安全問題……太多太多,也過于復(fù)雜。歸根結(jié)底,精準(zhǔn)扶貧的農(nóng)村,面臨的問題仍是人性人心的問題,這也正是文學(xué)的要義所在。它給我們提供了思考,文學(xué)到今天,該去如何反映現(xiàn)實生活如何回應(yīng)我們所處的時代,該去如何書寫時代新人的心靈和精神?
《詩經(jīng)》里說,“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曾被渴盼了幾千年的夢想將在2020年實現(xiàn),精準(zhǔn)扶貧這項偉大社會實踐,對中國、對全人類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作家要以“我在”姿態(tài)去書寫當(dāng)下鄉(xiāng)村弱勢群體的生存現(xiàn)場,尤其突出他們的精神現(xiàn)場和心理現(xiàn)場。寫法上,要注重個體及其變化,這個變化著重于人物內(nèi)心和精神,而他們的內(nèi)心和精神絕不是孤立的,是在歷史和時代變化下的種種經(jīng)歷,他們作為時代新人,正在完成個體和時代的彼此構(gòu)建。
用個比方作為結(jié)束語。鄉(xiāng)村現(xiàn)場是一個母體般的存在,而寫作者就是一個坐在星空下的孩子,他們對外面的世界和變幻莫測的未來高談闊論,此時,鄉(xiāng)村現(xiàn)場就像專制而好奇的父親和母親,乘坐在歷史和時代雙重建構(gòu)的船舶上,駛進(jìn)我們的談話中來。
我們無法視而不見——這是我們共同的命運。
朱朝敏,湖北省作家協(xié)會簽約專業(yè)作家,代表作有長篇非虛構(gòu)《百里洲紀(jì)事》等,現(xiàn)居湖北枝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