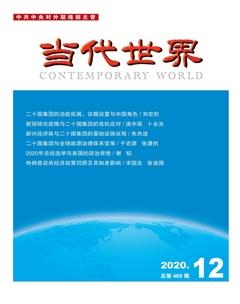新興經濟體與二十國集團的基礎設施議程
朱杰進

【內容提要】基礎設施議程在2010年二十國集團(G20)首爾峰會時被列為G20發展議程的關鍵領域,但此后G20基礎設施議程的穩定性并不高。雖然2014年G20布里斯班峰會建立了全球基礎設施中心,2016年G20杭州峰會建立了全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聯盟,但這些合作成果未能在隨后的G20漢堡峰會、布宜諾斯艾利斯峰會上得到有效延續。G20基礎設施議程的演進反映了新興經濟體對基礎設施建設的迫切需求與G20議程推進能力有限之間的矛盾。在此背景下,“一帶一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等新興經濟體關于基礎設施的新倡議和新型國際組織的建立,可以對G20的基礎設施議程形成有力補充,并發揮一定的倒逼效應,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進行更加公正、有效的變革。
【關鍵詞】G20;新興經濟體;基礎設施議程;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
【DOI】10.19422/j.cnki.ddsi.2020.12.003
作為當今世界最主要的國際經濟合作論壇,G20峰會的議程反映了全球經濟治理的發展趨勢以及主要大國的議題偏好。基礎設施是印度、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偏好的一項議題,在經歷了一段時間的博弈之后,該議題終于進入了G20峰會的議程,但基礎設施議題在G20發展議程中的穩定性并不高。2014年G20布里斯班峰會和2016年G20杭州峰會在基礎設施議題上取得的合作成果未能在其后的峰會中得到有效延續。本文旨在通過對G20基礎設施議題歷史演變的考察,分析新興經濟體在G20峰會中的議程推進能力,從而為新興經濟體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提供政策啟示。
基礎設施進入G20發展議程
早在2008年G20華盛頓峰會中就出現了關于基礎設施議題的討論,但由于發達國家的不支持,一直到2010年11月G20首爾峰會,基礎設施才被正式列入議程。2008年11月14日,第一屆G20峰會在華盛頓舉行,當時基礎設施不是會議的正式議程,但是時任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Manmohan Singh)在發言中提到要加強對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投資。辛格指出,由于這場金融危機是全球性的,它需要全球性的解決方案,在短期內要將危機控制住,在中期內要改革國際金融架構,以避免類似的危機再次發生。除此之外,中期內G20還可以加強對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的投資,以挖掘世界經濟增長的新動力。在世界經濟復蘇乏力的情況下,全球經濟中私營部門的投資動力正在減弱,這就使得加大公共部門投資基礎設施力度并帶動私營部門投資顯得格外重要。辛格認為,基礎設施投資可以發揮反周期的作用,刺激需求,為世界經濟恢復增長創造條件。但是,由于基礎設施投資最大的難題是缺乏資金,所以需要新的方式來解決融資問題。基于此,辛格特別建議,世界銀行、地區開發銀行可以考慮提供額外的500億美元貸款來刺激基礎設施項目投資,探討新的基礎設施融資工具。但是在G20華盛頓峰會上,由于七國集團(G7)領導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恢復流動性、重新穩定美國和英國的金融體系等問題上,“辛格倡議”(Singh Initiative)并未得到重視。隨后通過的《華盛頓峰會領導人宣言》提到,“我們鼓勵世界銀行和其他多邊開發銀行全力支持各自發展議程,歡迎世界銀行近期在基礎設施領域和貿易融資領域引入新的貸款機制,采取一些新的舉措。”實際上,G20只是原則性表示了對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的“鼓勵和歡迎”,并沒有出臺任何有關的實質性措施。
在2009年4月舉行的G20倫敦峰會上,時任英國首相戈登·布朗全力以赴推動G20各國做出經濟刺激計劃,向市場發出“現在金融危機的形勢已經被掌控”的信號。G20倫敦峰會的目標就是出臺巨額的經濟刺激計劃,顯示出G20各國團結一致,為全球金融體系的穩定注入強勁動力。G20倫敦峰會的這種“轟動效應”確實是G20取得的標志性成果,也遏制住了金融危機不斷蔓延的態勢。但是在基礎設施議題上,G20倫敦峰會成果中沒有涉及。
G20倫敦峰會之后,全球金融市場逐步穩定下來。美國出臺了巨額的經濟刺激計劃和銀行拯救計劃,美聯儲開始實施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同時還與歐洲央行、日本央行、瑞士銀行等主要央行簽署了雙邊貨幣互換協議,美元的流動性開始逐步恢復。2009年9月,美國舉辦G20匹茲堡峰會,重點關注國際金融監管改革,同時提出了G20在危機之后要努力實現“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框架”。美國、英國、加拿大等G7國家的財政部長在匹茲堡峰會上強調,G20要努力解決全球經濟的匯率失衡問題(Exchange Rate Misalignment),認為匯率的失衡才是導致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主要根源。美國開始利用自己最大經濟體的地位以及作為匹茲堡峰會輪值主席國的身份,將匯率問題作為G20的最重要議程。
實際上,在匹茲堡峰會之前,2009年7月,八國集團(G8)在意大利拉奎拉召開了峰會,并邀請中國、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等新興經濟體進行外圍對話。在G8拉奎拉峰會上,中國、印度、巴西、南非等新興經濟體代表都提出要把基礎設施列入G20匹茲堡峰會議程,認為基礎設施投資可以為解決全球宏觀經濟的難題提供幫助。但是,美國、英國、加拿大等G7國家并不這么認為,它們將匯率問題作為匹茲堡峰會的核心議程,認為這是解決全球宏觀經濟失衡的重要方案。
2010年6月,加拿大在多倫多舉辦了第四屆G20峰會。加拿大并沒有將基礎設施放進G20的議程,而是將匯率問題、經濟刺激計劃的退出問題等列為G20的主要議程。當時,中國、印度、巴西對于討論采取反周期的經濟政策很感興趣,包括擴大基礎設施投資。但是加拿大、英國仍然跟隨美國的步伐,將匯率問題、全球經濟再平衡以及相互評估進程(Mutual Assessment Process,簡稱MAP)作為峰會的主題,對基礎設施議題刻意進行了忽視。
2010年11月,作為第一個非G7主辦國,韓國舉辦了G20首爾峰會,并將基礎設施正式列入了G20峰會的議程。作為一個后發國家,韓國對基礎設施投資在本國經濟起飛過程中的重要性有著深刻的理解。在籌備首爾峰會的過程中,韓國意識到基礎設施議題的重要性,與廣大發展中國家以及相關國際發展組織進行了廣泛磋商。在首爾峰會上,韓國努力扮演G7國家和新興經濟體之間的橋梁:一方面,韓國繼續推進全球經濟再平衡和相互評估的議題,并牽頭制定了作為評估基礎的“參考性指南”(Indicative Guidelines);另一方面,韓國推動形成了《首爾發展共識》,確定了9個關鍵領域:基礎設施、人力資源、貿易、私營部門投資、糧食安全、抗風險增長、普惠金融、國內資源動員、知識分享。韓國將基礎設施列為G20發展議程的首位,并建立了G20基礎設施高級別專家小組,以審議多邊開發銀行推進基礎設施投資的狀況。至此,“辛格倡議”開始在G20中正式落地。
G20基礎設施議程的演進
雖然基礎設施在2010年首爾峰會上正式進入了G20發展議程,但除2014年G20布里斯班峰會和2016年G20杭州峰會外,多數G20峰會在這個議程上均未能取得實質性成果。同時,由于G20采取輪值主席國的制度,導致G20的基礎設施議程缺乏延續性和穩定性。
2014年11月,澳大利亞擔任G20的輪值主席國,認為G20的有效性正在大幅下降,未能實現新興經濟體對G20的預期;G20的發展議程已經被傳統的國際發展議程所取代,而新興經濟體的失望情緒正在轉化為創建專門從事基礎設施投資的新型國際組織的熱情。其中,“辛格倡議”已經在2012年金磚國家新德里峰會上轉化為創建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的倡議,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也在2013年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提出了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倡議。2014年,這兩家銀行已經基本完成了籌建談判,并于2015年開始正式運營。
與此同時,澳大利亞也意識到2014年世界經濟面臨減速的風險,開始認同印度、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觀點,提出G20需要刺激全球經濟增長,尤其是需要推動基礎設施建設。因此,澳大利亞在布里斯班峰會上推動G20建立了“全球基礎設施中心”(Global Infrastructure Hub,簡稱GIH)。在G20的帶動下,世界銀行也宣布成立了全球基礎設施基金(Global Infrastructure Facility,簡稱GIF),亞洲開發銀行也在布里斯班峰會上宣布要擴大基礎設施的項目投資。
作為G20在基礎設施議程上最具實質性的成果,全球基礎設施中心旨在通過分享其投資最佳實踐信息、投資策略和風險管理工具,促進、優化政府和社會資本對基礎設施領域的投資與合作。具體來看,全球基礎設施中心的主要功能是在基礎設施投資者與項目之間牽線搭橋,解決數據缺失問題并改善項目信息渠道,其資源包括數據配置、評估工具、知識平臺、項目渠道和先進做法等。
需要強調的是,雖然全球基礎設施中心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基礎設施投資領域的信息不對稱,但仍然不能高估G20布里斯班峰會在基礎設施領域所取得的成就。正如長期關注基礎設施領域的澳大利亞學者邁克爾·卡拉漢(Michael Callaghan)所言,要全面地看待G20全球基礎設施中心的作用,現在有觀點認為,這個中心能夠釋放數萬億美元的私營部門資金投到基礎設施領域,這是不準確的;這個中心能夠發揮一定作用,但擴大基礎設施投資并不是簡單改善數據質量。實際上,除數據問題外,改善投資環境、尋找基礎設施資金來源和制定嚴格的基礎設施項目標準更加重要。
2016年中國擔任G20輪值主席國,基礎設施成為G20杭州峰會的主要議程之一。2016年7月,在成都舉行的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上,中國充分發揮作為現有多邊開發銀行主要股東國和新型多邊開發銀行倡建者的影響力和話語權,成功推動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等全球11家主要多邊開發銀行發表了《支持基礎設施投資行動的聯合愿景聲明》,成為G20中國年的一大亮點。世界銀行提出,對能源、運輸、水利和衛生、信息通信等領域基礎設施的貸款占貸款總規模的30%—50%,對健康、教育等社會基礎設施的貸款約占5%—10%;亞洲開發銀行提出,2016—2020年間預計將700億美元資金用于基礎設施投資,約占同期貸款總額的70%;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2016年貸款規模為12億美元,2017年為25億美元,2018年為35億美元;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貸款規模2016年為15億—20億美元,2017年為20億—25億美元,2018年為40億—50億美元。
除此之外,中國還在G20杭州峰會上成功發起了“全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聯盟倡議”,以加強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項目的整體協調與合作。G20要求世界銀行作為聯盟的秘書處,與全球基礎設施中心、經合組織、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以及有興趣的G20成員一起工作,有力推動新老多邊開發銀行在基礎設施投資領域的合作。2016年9月,世界銀行與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簽訂合作諒解備忘錄,內容包括探索聯合融資項目可行性,推動聯合融資項目的知識交流,探索顧問服務方式,根據各自政策和程序,推動借調人員和員工交流等。2017年4月,世界銀行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簽署了諒解備忘錄,為兩個國際機構在各領域加強合作提供了一個整體框架,包括聯合融資、員工交流、分析調研等。
雖然G20杭州峰會在基礎設施議程上取得了豐碩成果,但在隨后的幾次G20峰會中,這一合作勢頭未能延續。在2017年德國主辦的G20漢堡峰會上,由于特朗普堅持“美國優先”的原則,使得峰會斗爭的焦點集中在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和應對氣候變化等議題上,無暇顧及基礎設施投資的議題。此次峰會僅僅在“非洲發展伙伴關系倡議”中提及“我們歡迎非盟的《2063年議程》和《非洲基礎設施開發計劃》”實際上,G20漢堡峰會并沒有真正涉及基礎設施議題。
在2018年G20布宜諾斯艾利斯峰會上,雖然輪值主席國阿根廷將基礎設施納入了會議議程,但主要是討論如何撬動私人部門的資金來參與基礎設施建設,強調要推動基礎設施作為一種獨立的資產類別。事實上,正是因為基礎設施投資周期長、利潤低,所以市場投資者不愿意進入這個領域,這才需要政府以及政府推動建立的多邊開發銀行等公共部門來發揮引導帶動作用。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說,布宜諾斯艾利斯峰會蛻變為G20的成員國政府“推卸”責任,認為基礎設施投資主要是一種市場投資者的行為。
在2019年G20大阪峰會上,主席國日本設置的核心議程是數字經濟、自由貿易和氣候變化,對于基礎設施議程則片面強調了“高質量”和“高標準”。與大多數新興經濟體主要關注基礎設施的資金和數量不同,G20大阪峰會通過的《G20高質量基礎設施投資原則》強調要重點考慮基礎設施全生命周期的成本、對環境和社會的破壞程度、抗自然災害的韌性、創造就業的機會、知識和專業技能轉移等。實際上,盡管基礎設施質量問題不容忽視,但目前并不存在統一的標準。基礎設施建設應充分考慮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發展實際和需要,當前的G20議程重點還應該是滿足發展中國家對基礎設施融資的巨大和迫切需求,而不能因過度強調“高質量”而導致投資不足。
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G20利雅得峰會只能采取視頻會議的形式,此次峰會雖然也涉及基礎設施議程,但只是空洞地重提了2018年達成的《推動基礎設施作為獨立資產類別的路線圖》和2019年達成的《G20高質量基礎設施投資原則》,缺乏任何實質性的政策舉措。在全球疫情肆虐和世界經濟深度低迷的背景下,如何應對疫情和重振經濟應該成為當下G20議程的重點,但不容忽視的是,基礎設施投資對疫情后重振世界經濟本來可以發揮較大的逆周期作用,而利雅得峰會對基礎設施議程顯然缺乏足夠的興趣。
G20基礎設施議程的前景展望
作為一項新興經濟體偏好的議題,基礎設施一開始難以進入G20議程,進入后也難以保持延續,這實際上反映了當前G20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一大困境:新興經濟體在G20中的議程推進能力仍然有限,與G20戛納峰會提出的“G20的創始精神是發達經濟體與新興經濟體平等地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目標相比,仍有相當的距離。例如,發達國家偏好全球經濟再平衡和匯率調整的議題,在G20峰會上領導人形成了初步共識,西方國家掌控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會跟進,參與到“相互評估”和“參考性指南”的制定過程中,從而使議程的延續性大大增強;而新興經濟體偏好的基礎設施議題,雖然發達國家在壓力下同意建立G20全球基礎設施中心,但該機制僅僅得到了澳大利亞、中國、韓國等少數幾個國家的資金支持,其職能定位也僅限于緩解基礎設施投資的信息不對稱,難以維持G20基礎設施議程的延續性。
進一步看,基礎設施在G20中屬于發展議程的一部分,而G20本身在發展議程上存在著先天不足。對發達國家來說,發展問題主要是指幫助低收入發展中國家實現發展,一般是由國際發展部或者國際發展署來負責,其核心是對外援助問題。而對新興經濟體來說,發展問題幾乎覆蓋了所有的政府部門,基礎設施就是其中一個突出的問題,其核心是經濟增長問題。反映在G20中,參與討論基礎設施議程的外交代表有7個國家來自外交部、5個國家來自財政部、4個國家來自國際發展部、1個國家來自經濟發展部、1個國家來自發展規劃部、1個國家來自商務部,另外加一個歐盟的代表。一般而言,來自外交部和國際發展部的代表更多是從對外援助的視角來看待基礎設施,而來自財政部和經濟發展部的代表則更多是從經濟增長的視角來看待基礎設施。十分多樣的代表結構使得成員國沒有一個統一的部門來進行議程對接,凸顯了基礎設施議程在G20中的復雜性和困難性。
在這種背景下,中國發起了“一帶一路”倡議,并推動建立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為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建設提供新的資金來源,對G20基礎設施議程形成了有力補充。此外,這些新的倡議和國際組織也會對發達國家主導的世界銀行和其他地區多邊開發銀行形成倒逼作用,以一種良性競爭的方式迫使這些傳統多邊開發銀行更加重視對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進行投資,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進行更加公正、有效的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