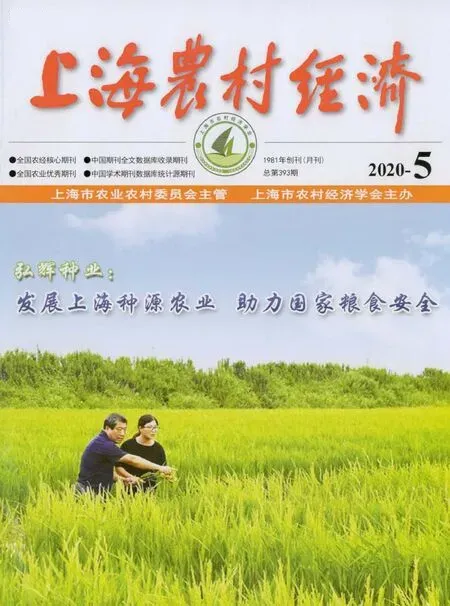增強應對突發事件沖擊的糧食安全保障能力
■ 程國強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加速擴散蔓延,有關國家對糧食安全的擔憂也日益增加。美國彭博社近期一篇新聞稿“多國紛紛禁止糧食出口”,拉開了全球糧食市場恐慌的序幕,全球糧食危機風險驟然上升。疫情及其引發的次生災害,使我國糧食安全保障再一次面臨重大挑戰。
一、全球糧食市場為什么會異動?
這次采取糧食出口限制措施的印度、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埃及、越南等十幾個國家,雖然并非糧食出口大國,但引發的全球糧食市場恐慌預期卻不可小覷。部分糧食產品國際價格應聲上漲,如2020年3月底泰國大米基準出口價漲至每噸550美元,為2013年8月以來的最高水平;越南大米價格每噸超過400美元,是2018年12月以來的最高價格。那么,這次國際糧食市場異動的成因是什么?
首先,疫情沖擊導致部分國家糧食供應預期趨緊
2020年3月中旬以來,隨著疫情逐步在全球蔓延,許多國家對糧食供應的預期趨緊。這不僅是他們對糧食安全強烈的憂患意識和危機思維,更是他們對2008年全球糧食危機的恐懼記憶。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爆全球金融危機,當時澳大利亞、阿根廷發生干旱天氣,引發全球糧價恐慌性上漲,并高位持續一年多,使全球37個國家爆發糧食危機,全球8.5億貧困人口遭受饑餓威脅。這次疫情引發的全球公共衛生危機,除部分國家已采取糧食出口限制措施外,還有可能隨著有關國家采取愈加嚴格的疫情防控措施,導致物流中斷、交易停頓,加之部分國家蝗災影響糧食生產,進一步引發全球糧食市場不穩定預期,使有關國家對糧食安全的擔憂隨之加大。
其次,部分外媒新聞是全球糧食恐慌預期的放大器
如彭博社3月25日發的新聞稿“多國紛紛禁止糧食出口”,雖然翻譯成中文只有500字,但直接推升全球市場的恐慌。一方面,這則新聞加劇了部分國家對糧食問題的擔憂。如最初只有2個國家限制糧食出口,但到目前為止,至少有12個國家加入限制糧食出口的行列。另一方面,引發了包括我國在內的國際糧食市場波動。特別是,雖然我國糧食庫存充裕,具有保障口糧絕對安全的堅實基礎,而且我國輿論引導及時,在總體上沒有出現糧價大幅波動情況。但部分涉農股票、期貨以及現貨市場出現上漲行情,部分地區的居民也出現囤糧現象。
第三,蝗災對全球糧食市場不穩定預期具有一定推動作用
據報道,70年來最嚴重的蝗災目前正沖擊埃塞俄比亞、肯尼亞、索馬里、南蘇丹、烏干達和坦桑尼亞等非洲國家的糧食生產,將給這些國家的糧食安全帶來威脅,對目前全球糧食市場不穩定預期具有一定推動作用。但從總體上看,蝗災對全球糧食生產的影響尚待進一步觀察。目前全球糧食供需形勢總體穩定,主產國沒有出現糧食減產、供不應求問題。特別是美國、巴西等部分主產國,糧價低迷、存在一定下行壓力。這意味著,即使后期全球糧食市場異動升級、爆發糧食危機,也不可能是因為全球糧食短缺而出現的危機。
二、疫情會引發全球糧食危機嗎?
新冠肺炎疫情目前已經席卷全球211個國家地區,截至5月16日,全球確診累計450萬例,死亡達35.5萬例。疫情對后期全球糧食市場的影響,主要取決于糧食主產國疫情的持續時間、防控舉措、影響范圍及其對糧食生產、貿易等的沖擊。特別需要警惕的是,后期全球金融市場流動性充分釋放后,國際投資資本若借機炒作農產品等大宗商品,全球爆發類似2008年糧食危機的風險將急劇增加。
第一,疫情對全球糧食生產與貿易的沖擊將進一步加大
疫情導致許多國家經濟進入停擺半停擺。盡管目前尚未對相關國家的農業生產形成明顯沖擊,但對相關農畜產品生產的影響已經初步顯現。據華爾街日報報道,美國主要肉類加工商泰森食品公司、嘉吉公司等,近期因部分員工感染新冠病毒而臨時停止部分工廠的運營,對肉類產品供給將形成不利影響。隨著疫情影響持續加深加大,部分農產品出口國或將采取更加嚴格的防控措施,有可能進一步導致糧食物流中斷、交易停頓,阻斷正常的國際貿易活動,推動形成國際糧食價格上漲預期。
第二,全球糧食市場不穩定預期有可能愈加惡化
若后期世界疫情仍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加之部分國家蝗災影響糧食生產,全球糧食市場預期有可能進一步惡化。目前雖然越南等國已恢復糧食出口,但不排除后期疫情惡化后,其他有關糧食出口國再度收緊出口,而部分進口國加大進口,最終有可能演化為全球搶購、限賣以及物流不暢的恐慌疊加效應,使全球糧情更加趨緊,全球糧食市場異動有可能進一步加大。
第三,投機資本炒作引發全球糧食危機的風險或增加
國際投機資本炒作引發全球糧食危機,是2008年全球糧食危機的深刻教訓。目前國際糧食市場環境雖然與2008年不盡相同,如目前糧食供需矛盾不突出、石油價格低迷、金融市場流動性尚未充分釋放等。這次疫情沖擊引發的糧食市場異動,也有著不同的成因和路徑,但后期真正的威脅,是來自國際投機資本對糧食市場的炒作。從時機上看,今后2個月是國際投機資本入場炒作大宗農產品市場的窗口期。一是,全球金融市場流動性將逐步釋放,巨量游資在美國股市進入高位后,極有可能轉向包括農產品在內的商品市場。二是,南美等主產國疫情防控或進入復雜期,有可能對物流、人員流動以及港口碼頭等運行產生重要影響。因此,后期在全球流動性充分釋放背景下,國際投機資本極有可能利用這個窗口期,通過誘導輿論、惡化預期來制造行情,伺機炒作大豆等大宗農產品市場,推動全球農產品價格從結構性上漲轉向全面上漲,釀成嚴重的全球糧食危機。而長期以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依然沒有實施有效的農業發展戰略,糧食安全仍然十分脆弱。若糧食價格高漲引發全球糧食危機,最終危及的將是發展中國家的糧食安全,尤其是直接威脅發展中國家數億人口的吃飯和生存。
三、中國的糧食安全保障體系與應對能力
如果今后一段時間國際糧食市場異動升級,乃至爆發全球糧食危機,必將對我國糧食安全形成深刻影響,由此引起國內消費者的擔憂。
(一)應對突發事件沖擊的糧食安全保障體系
解決好十幾億人口的吃飯問題,始終是我國治國安邦的頭等大事。按照“以我為主、立足國內、確保產能、適度進口、科技支撐”的糧食安全方針,按照“谷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的要求,不斷強化糧食安全保障能力建設,已建立形成符合我國國情糧情的糧食安全保障體系。綜合而言,我國糧食安全保障體系主要包括三個部分:一是以主糧為重點的國內糧食生產體系;二是應對各類突發事件和緊急狀況的糧食儲備體系;三是能夠有效利用國際糧食市場和農業資源的全球供應鏈。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以口糧絕對安全為核心的三位一體保障結構。國內糧食生產體系與儲備體系體現了“以我為主、立足國內”確保谷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的剛性要求,而全球供應鏈則反映了以保障口糧絕對安全為核心的“適度進口”政策設計,通過進口大豆、肉類等非主糧農產品以集中國內資源保口糧生產重點。三者互為支撐、協同一體,構成我國應對糧食安全風險的三位一體保障結構,也是多年來,我國成功應對國際金融危機、重大自然災害等各類突發事件對糧食安全嚴峻挑戰的根本支撐。
第二,不斷強化糧食安全保障能力建設。一方面,持續增強國內糧食生產能力,通過不斷加強農田基礎設施建設和科技投入,逐步實現“藏糧于地,藏糧于技”。自2004年以來,我國糧食生產實現連續16年豐收,從2003年的4.307億噸,增長到2019年的6.638億噸,連上2個億噸級臺階。特別是2015年以來,連續5年糧食生產能力穩定在6.5億噸以上的水平(國家統計局,2020)。另一方面,注重加強和完善中央和地方兩級糧食儲備體系建設。其中,中央儲備自2000年建立,主要擔負應對重大突發事件的戰略性保障功能,是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壓艙石”;對于地方儲備,要求主產區儲備規模保持3個月的銷量,主銷區保持6個月,產銷平衡區保持4個半月的銷量,是我國區域性糧食安全保障的重要支撐。
第三,統籌國內國外的農業資源配置機制。我國三位一體的糧食安全保障結構,逐步推進形成統籌國內外農業資源的配置機制,即“國內供給+進口補充”資源配置模式。以2017年為例,如果要保持我國農產品供需總體平衡,按照現行國內農業生產水平測算,約需要38.5億畝種植面積。從資源供給看,主要由兩方面構成,一是國內供給25億畝,即土地資源自給率為65%。其中,糧食17.7億畝,占國內種植面積的71%;其他非糧農作物7.3億畝,占29%;二是通過進口農產品來彌補國內不足的13.5億畝,即土地資源對外依存度35%。這種農業資源配置機制,實質是通過“適度進口”非主糧農產品,解決了35%的耕地缺口,以騰出國內寶貴的耕地資源來確保水稻、小麥生產。
(二)我國能夠有效應對疫情帶來的糧食危機風險沖擊
今后全球疫情若不能得到有效防控,后期全球糧食市場異動升級為糧食危機的風險將越來越大。但無論后期可能的糧食危機以怎樣的方式、在多大的程度上爆發,我國糧食安全保障體系均可從容應對。
特別是,如前所述的以口糧絕對安全為核心的三位一體保障結構,使目前我國糧食安全形勢處于歷史上最好的時期。例如,我國稻谷自2007年以來連續13年產大于需,小麥自2013年以來連續7年產大于需,具有長周期階段性供大于求特征,積累大量庫存,兩者庫存大體相當于全國一年的消費量(國家糧食和儲備局,2020)。與此同時,水稻和小麥進口依存度較低,進口主要用于品種調劑,占國內消費僅為1%-2%,具有保障絕對安全的物質基礎。因此,若國際糧食市場價格異常波動升級,對我國國內市場的沖擊將非常有限。相反,若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國內糧價上升預期,既有利于提高農民種糧積極性,對穩定今年糧食生產具有積極作用,也有助于消化積壓的糧食庫存,對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利。即使后期由于國際投機資本炒作引發全球糧食價格上漲危機,我國完善的糧食儲備調控體系和應急管理機制,將能夠有效發揮穩定市場預期、安定人心的壓艙石作用,實現糧食保供穩價目標。
但是,必須注重防范疫情對我國農產品全球供應鏈帶來的不確定性影響。我國主要進口大豆、雜糧、植物油等非主糧農產品,以騰出國內有限的農業資源守住口糧安全底線。因此,非主糧農產品全球供應鏈的持續性和穩定性,也成為我國糧食安全保障的重要方面。但是,需要關注以下幾個風險因素。一是疫情對全球農業生產的挑戰將逐步增加。美國、巴西、加拿大等糧食主產國是疫情較重的國家,4月下旬美國大豆進入播種期,需密切關注疫情對其農業生產的影響。二是全球疫情加速蔓延對全球農產品貿易沖擊日益嚴重。因全球疫情惡化,部分農產品出口國采取疫情防控措施,大豆等農產品進口貿易面臨較大的不確定性。三是后期若國際投資資本炒作大豆等農產品市場,將使我國進口企業和加工企業面臨巨大的價格波動風險,不僅進口成本會急劇增加,而且若防控不當,極易重蹈2004年、2008年國內大量加工企業破產倒閉的覆轍。對此必須高度重視,嚴加防范。
四、強化應對突發事件沖擊的糧食安全保障能力
針對當前全球糧食市場異動以及后期可能出現的全球糧食危機風險的嚴峻挑戰,要毫不動搖地堅持中央確定的糧食安全方針,及早謀劃應對策略和防范措施,進一步增強應對疫情等突發事件沖擊的糧食安全保障能力,為我國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第一,有效管理輸入性不穩定預期對國內糧食市場的干擾和沖擊
這是在當前嚴格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時,必須高度重視并嚴加防范的重大風險點。建議綜合施策,有效引導和管理預期,謹防市場恐慌、搶糧囤糧。在當前疫情防控的關鍵時期,尤其要注重確保國內糧食市場和流通的信息暢通、運輸暢通和物流暢通,進一步完善和強化應急保障機制,確保糧食流通有序、供應充足、價格基本穩定。
第二,進一步加強糧食生產能力建設
要進一步筑牢糧食有效供給基礎,確保6.5億噸糧食產能基本穩定。一要加強和完善農業支持政策體系,繼續推進農產品收儲制度改革,實施更加有效、合規的支持補貼措施,切實保障農民種糧基本收益,保護和提高農民種糧務農積極性。二要進一步加大對糧食主產區的支持力度,夯實地方重農抓糧的積極性和責任心,增強地方政府保障糧食安全的責任意識和大局意識。三要加大農業基礎建設支持力度,大力推進農業科技創新,有效提高糧食綜合生產能力。四要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農業轉型升級、高質量發展,提高糧食質量和品質。
第三,構建國家糧食安全保障風險治理體系
要按照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全面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建立從糧食生產到消費全程風險研判、監測預警、宏觀調控和管理體系,全面提升糧食安全保障的宏觀調控水平和風險治理能力。一是加強糧食全產業鏈風險調查研判,建立動態監測、實時預警機制,完善和優化宏觀調控,把糧食安全風險化解在源頭、防控在前端。二是建立糧食安全風險治理責任機制,壓實各級主體的責任。三是處理好糧食安全保障的常態與應急、政府與市場、中央與地方、生產者與消費者、國內與國際、當前與長遠等關系,建立和完善統一高效、協調有力的糧食安全保障風險治理體系。
第四,加強和完善重要農產品儲備體系
要進一步優化國家糧食儲備的區域布局,完善品種結構,健全物流體系,創新配送機制。建議以油肉糖棉等國內緊缺農產品為試點,通過連接進口機制和全球供應鏈,建立重要農產品商業儲備調節機制,作為國家儲備的補充,形成國儲、商儲相結合的重要農產品儲備調節和保障體系。
第五,強化農產品全球供應鏈管理
一要建立和加強全球農產品市場風險監測評估體系,進一步提高大豆等大宗進口農產品風險管理能力,有效應對和防控國際市場波動風險。二要加強和完善全球農業食品供應鏈管理,研究制定綜合支持政策,鼓勵我國企業深度融入全球農業食品生產、加工、物流、營銷及貿易產業鏈、價值鏈與供應鏈。
第六,加強國際糧食安全、貿易和投資政策協調
要加強國際協調,確保全球農業與糧食供應鏈安全運行與有效運轉,不斷完善和強化全球糧食安全治理,共同維護全球農業貿易和市場秩序。建議聯合歐洲有關國家以及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發起限制對農產品投機炒作、避免全球糧食劇烈波動的國際倡議,有效遏制投機資本擾亂全球糧食市場、引發全球糧食危機的行為。積極支持和參與聯合國機構開展的援助低收入、貧困國家糧食安全的國際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