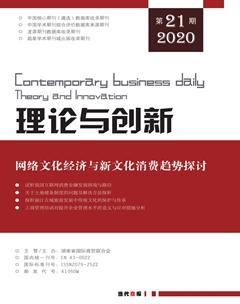從清末秀才到邊區部長
錢文瑞
1.和群眾打成一片
謝覺哉祖籍湖南寧鄉縣,從小學習勤奮,21歲時參加舉考試,中了清朝最末科的秀才。1936年6月7日,中央機關遷至保安縣(今志丹縣),謝覺哉被任命為中央西北辦事處內務部長秘書長。
謝覺哉十分樂意聽取人民的意見。1943年的秋天,一個姓白的老人來到陜甘寧邊區政府,要求反映問題。謝覺哉主動接見他,老人絮絮叨叨地向謝覺哉說道,自己小時候家里很窮,父母節衣縮食才送他讀了些書,但六七十歲了,一直沒有找到生活出路。老人還說:“我已經老了,你們政府今后對讀書人可要重視啊!”謝覺哉不僅不嫌厭煩,還很受觸動地說道:“新政權、新制度一定會發揮你們的作用。”之后,謝覺哉把他介紹給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又給當地領導同志寫了封親筆信,介紹了他的情況。老人拿到信后非常感激,走到哪里都說邊區政府好。
2.初創司法制度
1937年,謝覺哉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西北辦事處司法部長,當時陜北的司法工作還沒有走入正軌,謝覺哉深知司法工作對于鞏固邊區政權的重要性,于是親自調查分析了邊區司法的狀況。調査結果顯示:邊區人民嚴重缺乏司法知識和法律觀念,司法人員在工作時更是問題多多。有些人硬套書本條文,根本不考慮實際,而有些人則主要依靠經驗判案。針對以上問題,謝覺哉經常主持召開司法委員會會議,及時研究解決存在的問題。他還經常親筆寫信給各分庭庭長和各縣司法處長,具體指導意見和改進工作的方法。謝覺哉認為司法是專門業務,需要專門人才,因而創辦了中國革命司法史上第一個司法講習班和第一個司法研究會,來培養高理論水平、高業務水平的司法專業人才。
謝覺哉在延安時還兼任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院長,他親自審理和指導了許多案件,更是糾正了不少冤假錯案。謝覺哉剛當院長不久,省裁判部送來一件案子的卷宗要他批復。謝覺哉仔細審閱卷宗后了解到,案情即一個姓孫(外號叫“驢駒”)的人,伙同兩個人攔路搶劫,不僅謀財還害了性命,事實清楚,證據也確鑿。但審理此案的機關居然出現兩個重大失誤:第一,審理法院僅僅判了孫驢駒一年徒刑。謝覺哉批復說:“果真殺人,他是首犯,判一年太輕了!”第二,案件的受害人家屬嫌被告賠償得太少不愿意接受,而原判機關竟然將賠償的財物給充公了!謝覺哉在批復中又指出:“這是不公正的,應當合理賠償,照數交還事主。”原審判單位接到批復后,覺得很為難,他們認為此案一旦改判,會使司法機關顏面掃地,老百姓今后再也不信任法院的判決了。謝覺哉得知后十分生氣地說道:“前清判案是把批文掛在衙門上,上訴人抄著批子,就可以推翻原審衙門的判決。封建時代都能這樣,何況我們現在。司法威信的建立,在于斷案的公正和程序的合法,不在于是否改判!”
3.布衣部長
1938年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以后,謝覺哉被任命為史央黨校副校長。黨校坐落于延安小溝坪,不僅條件艱苦,經費也十分缺乏。學員在露天場地蹲著吃飯,學習時把窯洞的窗臺當桌子。為了改善學員們的生活,謝覺哉發動大家大力生產糧食蔬菜,自給自足。他還和其他干部商量后積極發動大家起上山伐木,去河邊撿鵝卵石,開荒,燒磚,愣是在沒有經費的情況下,組織大家蓋起了餐廳和大禮堂。學生自己生產的菜,送給他一點兒,要他在家里做飯改善生活,但他又將菜送交大灶,要大家改善生活。學員沒有被褥,他設法找來送到床前,而他自己的床上卻鋪著麥草。
1940年,陜北的嚴冬異常寒冷。謝覺哉辦公時不停地打寒戰,于是秘書就多燒一點兒木炭,使窯洞暖和一些。可是每當炭火燒得通紅使人覺得熱乎乎時,謝覺哉便把一部分紅木炭夾出來,用水潑滅。他說:“革命是長期的,現在困難很多,我們多節約一點兒,就能多為黨減輕一點兒困難。”延安大生產運動開展后,謝覺哉積極下地干活,他居住的小院落變成了后勤部的生產田地及小型的養雞場、養豬場。他在處理政務之余就是燒水、送飯,站在雞棚和豬圈旁數數,以防它們跑出院子。每當邊區政府和參議會的生產小組召開會議總結生產經驗、制訂生產計劃時,謝覺哉都參加并提出意見,讓生產小組多想辦法完成規定指標。
新中國成立后,謝覺哉還曾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內務部長、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等職務,承“上為中央分憂,玉為群眾解愁”的信念為新中國的政權建設、救災救濟、社會福利、法治建設等工作做出了巨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