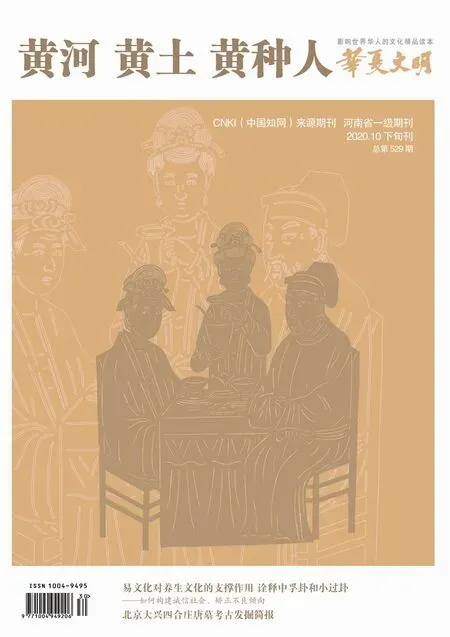論隋代移風易俗的變化和成效
□阮鑫
風俗好壞,關乎國家興衰存亡。 移風易俗作為統治者治國安民的利器, 歷來備受學者關注。 雖然學界對此有過許多突出的研究成果[1],但相對較為零散,且鮮有學者研究短暫的隋代的移風易俗問題。 在史料梳理中,筆者發現了隋代移風易俗的突出變化和成效,故擬對這一問題作重新探討。 不當之處,敬祈方家指正。
一、遣使巡省風俗
隋代繼承了歷代遣使巡省風俗的傳統。開皇元年(公元581 年)二月乙丑,“遣八使巡省風俗”[2]17。開皇三年(公元583 年)十一月己酉,“發使巡省風俗”[2]20。 開皇四年(公元584年)八月甲午,“遣十使巡省天下”[2]22。 仁壽元年(公元601 年)六月乙卯,“遣十六使巡省風俗”[2]46。 大業元年(公元605 年)春正月戊申,“發八使巡省風俗”[2]62。令人好奇的是,這些數目不定的巡省使是如何安排分遣的? 對這一問題,不妨從一些具體的巡省使入手。 比如長孫熾,“及高祖受禪,授左領軍長史,持節,使于東南道三十六州,廢置州郡,巡省風俗。大業元年(公元605 年)遷大理卿,復為西南道大使,巡省風俗”[2]1329。他巡省風俗的區域是東南道和西南道,以道為單位帶有明顯的“分道巡察制”的色彩。 關于這一制度,郭鋒先生已經有了較為明確的解釋:“大概在道武帝拓跋珪轉戰北方、立國建都平城前后,北魏統治者開始使用‘道’的概念來劃分地理區域,部署軍事行動。 至孝文帝時,已發展到以道為名命名大使、安排政務巡察等事宜了。”[3]隋文帝曾派遣楊尚希巡省淮南,柳彧、皇甫誕巡省河南、河北,虞慶則巡省關東諸道,這都可以印證隋代出現了分道巡省制度。 在開皇二年 (公元582 年),高祖下詔置河北道、河南道、西南道行臺尚書省,開皇六年(公元586 年)置山南道行臺尚書省,開皇八年(公元588 年)置淮南道行臺省。 東南道行臺,由后齊置,延續到開皇七年(公元587 年)。 周法尚在開皇中擔任過嶺南道安撫大使, 賀婁子干作為行軍總管出西北道。 這樣看來,在隋文帝時就形成了關東、河南、河北、西南、山南、淮南、東南、嶺南、西北九道。 唐太宗將天下劃分為十道,和隋代的分道巡省有著一致性, 仍然是以道作為巡察單位,遣使巡省。如貞觀八年(公元634年),李大亮為劍南道巡省大使,蕭瑀為河南道巡省大使。 因而,隋代巡省使的人數很有可能是依道而定。 唐太宗時國土面積、州縣數目遠大于隋代極盛時期, 所以隋代按照方位劃分的道數應當沒有超過唐太宗時的十道,八使、十使大概正是基于此。 另外,還存在一種以州為道的命名方式,如大業元年(公元605年),許善心“副納言楊達為冀州道大使”。 若巡省使以州為單位, 那人數自然會增多。 此外,之所以會有十六使,不排除一道兩使的情況,“大業初,刑部尚書宇文弼巡省河北,引絢為副。”[2]1684在這種情形下,兩使必然要有主次之分,這種主次與官位階品相關,比起納言楊達和刑部尚書宇文弼, 禮部侍郎許善心和司馬長史郭絢自然只能是副官。 必須注意的一點是,隋代道的設置是不固定的,沒有確定的范圍和數目,只是一種地理概念,而非確定的行政區劃。
巡省風俗制度經歷了兩漢、 魏晉南北朝的發展,已經不只是作為“風俗使”而存在。 事實上,兩漢的“風俗使”已經具備了多重作用,錄冤獄、禁苛暴、察吏治得失則是最為主要的內容[4]。 隋文帝和隋煬帝,也對巡省使的職責和功能做出過具體要求。 隋文帝在開皇三年(公元583 年)發使巡省風俗,因下詔曰:“朕君臨區宇,深思治術,欲使生人從化,以德代刑,求草萊之善,旌閭里之行。 民間情偽,咸欲備聞。 已詔使人,所在賑恤,揚鑣分路,將遍四海,必令為朕耳目。 如有文武才用,未為時知,宜以禮發遣,朕將銓擢。 其有志節高妙,越等超倫,亦仰使人就加旌異,令一行一善,獎勸于人。 遠近官司,遐邇風俗,巨細必紀,還日奏聞。庶使不出戶庭,坐知萬里。”[2]20這里,已經清晰地表明了巡省使的職責:賑恤百姓、推薦人才、獎勸行善、改善風氣、風俗獄治、上達圣聽。 其中,選拔人才這一職能被隋代統治者再三強調。 隋煬帝在大業元年(公元605 年)遣使巡省風俗時,也曾下詔:“若有名行顯著,操履修潔,及學業才能,一藝可取,咸宜訪采,將身入朝。 ”[2]62此外,隋代還多次讓地方官員舉薦人才,論其原因,大概是由于“隋承周制,官無清濁”[2]1663,黨固之譖流行,不同勢力明爭暗斗,新鮮血液匱乏。 在穩定的人才選拔體系尚未建立之時, 借巡省風俗探尋各地有文武才干的人士確實可以起到一定作用。 這項制度還兼具一定的監察功能,無論是刑獄民情,還是吏治得失,使臣都須回朝向上匯報。 統治者通過派遣使臣巡察地方風俗民情, 褒獎孝悌節義之家,賑恤鰥寡孤獨、篤疾之人,訪尋有德行、有才能者,考察地方官員治理狀況,達到了解國情、調整政策的目的。 如虞慶則等在開皇十年(公元590 年)巡省關東諸道還后,上奏:“五百家鄉正,專理辭訟,不便于民。 黨與愛憎,公行貨賄。 ”上仍令廢之[2]1207。 隋文帝在巡省使上奏之后改變了五百家設一鄉正的做法,對鄉官選拔產生了有益的影響。
除常規的巡省風俗使之外, 還有臨時派遣、擔負某一任務的巡省使。 在開皇初,長孫熾“持節,使于東南道三十六州,廢置州郡,巡省風俗”。長孫熾的任務就是廢置州郡。比較特殊的一點,在于他是“持節”巡省,也就是代表皇帝親臨,因而權力更大,可以直接處置地方事務。 巡省使常常與賑恤使、監察使、巡察按察巡撫等使重合,開皇三年(公元583 年),“楊尚希拜瀛州刺史,未之官,奉詔巡省淮南。 還除兵部尚書”[2]1253。 開皇六年(公元586 年)正月壬申,“遣民部尚書蘇威巡省山東”[2]23。 開皇十五年(公元595 年) 七月甲戌,“遣邳國公蘇威巡省江南”[2]40。 開皇十七年(公元597 年)三月庚午,“遣治書侍御史柳彧、 皇甫誕巡省河南、河北”[2]41。 蘇威、柳彧、皇甫誕都是作為巡省使派遣到地方的官員,但其擔負的任務不同,蘇威是賑恤山東饑民, 柳彧是奏察貪污不稱職官吏,皇甫誕是安定、撫恤河南、河北流民。 因為這一時期不同大使之間的界限并不清晰,所以巡省使往往也會兼有其他大使的職責。 作為巡省使的大臣官職不固定,回朝后一般會得到賞賜或晉升。 長孫熾獲授太子仆、加諫議大夫,攝長安令;楊尚希歸后被提拔為兵部尚書;蘇威兩年后遷吏部尚書;柳彧不僅得到賞賜,還拜為儀同三司;皇甫誕則升任大理少卿。 巡省使作為中央和地方的流動中介,受詔出發,上奏即止,其權力大小完全是由皇帝規定而非職位本身賦予,只在巡省期間可以干預地方的部分政務,不具有實際軍政權力。 其最基本的職能就是巡省風俗、舉賢進能、旌表孝悌,這些都是關乎教化的職能, 和地方官員的權力沖突極小,而但凡觸及地方利益的,一般都由皇帝指定職權,又由親信、職位較高者出任,或者給予特權。 長孫熾、柳彧是持節巡省,蘇威是便宜從事,權力都很大。 這樣出使地方時處理事務的阻力就會大大減少。
二、中央機構巡省風俗
隋煬帝時期巡省風俗制度發生了明顯的轉變。 隋煬帝在大業元年(公元605 年)發八使巡省風俗,大業三年(公元607 年)巡省趙、魏。 在之后的史料中,很難再找到煬帝遣使巡省風俗的證據。 那么,巡省風俗的任務由誰承擔? 這個問題,從大業三年(公元607 年)的官制改革中似乎可以窺見一些端倪。
隋煬帝重置謁者臺。 在南北朝官制中,謁者臺多與朝會禮儀之事相關;而到了隋煬帝時期,謁者臺改頭換面,“謁者臺大夫一人,掌受詔勞問,出使慰撫,持節察授,及受冤枉而申奏之……次有議郎二十四人, 通直三十六人,將事謁者三十人,謁者七十人,皆掌出使”[2]796。從對謁者臺規定來看, 謁者臺已經成為掌管出使巡省的機構。人數達到了三四百人,規模龐大,中央根據事情大小差別,派遣不同品級的使臣出使。 這與隋文帝時期的遣使巡省有明顯的區別:此是正式的中央官職,不是臨時派遣。 巡省官員有正式的品級,有具體的職掌,而不是由他官兼任、 因事而變, 且為持節察授, 比起隋文帝時特殊任務才能使持節的狀況,使臣的權力有所擴大和普及。 張虔威在任謁者大夫期間,隨隋煬帝巡幸江都,以本官代理江都贊治,當時淮南太守楊嘗與十余人同來謁見:“帝問虔威曰:‘其首立者為誰? ’虔威下殿就視而答曰:‘淮南太守楊。 ’帝謂虔威曰:‘卿為謁者大夫,而乃不識參見人,何也? ’虔威對曰:‘臣非不識楊,但慮不審,所以不敢輕對。 石建數馬足,蓋慎之至也。 ’帝甚嘉之。 ”[2]1558仔細斟酌隋煬帝的話,不難察覺謁者大夫和地方長官應當是有比較密切的關系,謁者臺確實承擔了巡省地方的責任。
隋煬帝還設立了司隸臺,“司隸臺大夫一人,掌諸巡察”[2]797。隋煬帝將巡察區分為畿內和畿外。 畿內設別駕兩人,分察東都和京師;而畿外設刺史十四人,分部巡察。 如此一來,煬帝將全國分為十五個監察區,巡察地方狀況。 煬帝盛選天下名士任司隸官,并特意設立六條作為職掌,六條中主要包括察地方官政績、豪強侵害、賊盜隱匿、德才顯著。 隋代的“六條”,關注地方官員的行政能力, 監察對象也是品官;而漢代的“六條”,監察重點在于限制、打擊地方郡守、豪強勢力,防止他們相互勾結,監察對象是二千石及其子弟。 司隸官每年二月巡省郡縣,十月回奏。 許多才學出眾之人都曾擔任過此職:“大業五年(公元609 年),朝東都,帝令司隸大夫薛道衡為天下群官之狀。 道衡狀稱(敬)肅曰:‘心如鐵石,老而彌篤。’”[2]1685這是薛道衡作為司隸大夫匯報各地官員考績。 李德饒德行甚為當時所重,“大業三年 (公元607年),遷司隸從事,每巡四方,理雪冤枉,褒揚孝悌”[2]1670。澄清獄治、旌表孝悌,也在司隸臺職權范圍內。 由于名聲顯著,房彥謙被征授司隸刺史,據史書描述:“彥謙亦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凡所薦舉,皆人倫表式。 其有彈射,當之者曾無怨言。 ”[2]1565這表明,司隸官不僅有監察彈劾地方官員的職責, 而且還有舉薦人才的權力。 司隸臺這一設置,在大業前期發揮過重要作用。 如翟普林在大業中,以孝感為司隸所奏,擢授孝陽令[2]1669。 不過,在御史大夫裴蘊專權之后,罷司隸刺史以下官屬,增置御史,司隸臺的監察舉薦功能已大不如前。
謁者臺和司隸臺都是巡察地方的機構,但是謁者臺官是接受皇帝臨時詔令出使撫慰、巡省察授、懲惡揚善,使臣為持節出發,短期巡察,歸后上奏。 與此不同的是,司隸臺官有固定安排,要定期巡察地方,目的是考察吏治狀況,發掘品行高潔或者才優干濟之人,在性質上和御史臺更加接近, 兩者相互配合以監察百官。 謁者臺和司隸臺長官都是正四品,而地方長官上郡從三品,中郡正四品,下郡從四品。 相比而言,官品并不高,所以兩臺常常只能通過上奏使監察生效。
巡省風俗承擔者的轉變, 反映著潛在問題的嚴重性和革新制度的必要性。 遣使巡省風俗,既可以加強對州縣的監察,又不會權力過大產生威脅。 但就其本質而言,仍是臨時派出的使者, 沒有名正言順處置地方事務的權力,在行事時多會受到地方的阻礙,并且移風易俗本就是潛移默化、徐徐圖之的長期任務,而依靠巡省使短暫活動展開的移風易俗顯然時效性非常短,效果也極其微弱。 所以,隋煬帝實行了變“使”為“官”,擴大職權,固定常設的方法, 設謁者臺和司隸臺分管地方風俗獄治、安撫慰問、招賢禮士、考核政績。 但實際上, 遣使巡省風俗和中央機構巡省風俗的方式并不完善, 最終產生效果的是地方官員主動進行的移風易俗活動, 這是移風易俗效果最為明顯、持久的重要因素。
三、地方長官移風易俗
移風易俗的實行主要依靠地方長官,即刺史、總管。 隋初“以州統縣,刺史之名存而職廢”[5]。刺史的軍權被取代,其職掌與之前的太守更為相似,作為行政長官,只處理一州之事務。 總管在隋滅陳之后逐步由軍事職能向行政職能轉變,隋文帝逐漸削弱總管軍權,使軍政分離。 這些趨勢都將地方長官的權力指向了民事、行政,因而移風易俗、教育教化地方民眾變成了地方官的主要職掌。 在隋代,“關中本位政策”[6]指導下的移風易俗具有強烈的針對性,若就《隋書·地理志》中《禹貢》九州之地而言,移風易俗主要集中在揚州、荊州、冀州、豫州、梁州,還包括嶺南地區。
隋文帝平陳之后,在江南地區實行“太平之法”[7],移風易俗。 這次移風易俗,與江南巡省使蘇威有莫大的關系, 他在巡察中意識到江南地區民風散漫、 文教不行, 因而厲行教化,還奏后更是建議嚴加管理戶籍。 從中央下達的強制命令造成了地方的恐慌和動亂,“陳之故境,大抵皆反。 大者有眾數萬,小者數千,共相影響”[8]5529。 蘇威的短期巡省并不能從根源上解決問題,江南地區“其俗信鬼神,好淫祀,父子或異居”[2]886。 自東晉以來,政治權力和學術話語權被世家大族和地方豪強把控,民間禮儀淡薄、風氣開放、文化多樣、工商業發達。 這種植根于大眾的風俗很難改變,就算有所改善也容易復發。 于是,在江南之亂平定之后, 隋文帝以晉王楊廣為揚州總管, 鎮江都。 楊廣與江南文化淵源較深,他的妻子是梁明帝的女兒,有才學,對江南文化很是了解。這暗示著隋文帝對江南地區的移風易俗由簡單粗暴、強制轉向了綏撫、徐徐圖之。 楊廣積極拉攏江南聲望之士如陸知命等人招降叛賊, 之后更是主動“習吳音”[2]625融入江南文化,“招引才學之士諸葛潁、虞世南、王胄、朱玚等百余人以充學士”[2]1424, 籠絡了大批江南士族輔助自己。 地方官員如蘇州刺史劉權,同樣遵循綏撫政策,“于時江南初平,物情尚擾,(劉)權撫以恩信,甚得民和”[2]1504。江南地區的移風易俗, 以順其民情、 得其民心的方式展開,地方長官的作為也很快見到了成效,民風大變,日益淳樸,漸歸于禮。
古冀州之地是 “重災區”。 尉迥之亂后,“時東夏初平,物情尚梗,高祖以(和)洪有威名,令領冀州事,甚得人和”[2]1380。 趙煚在高祖踐祚后不久也擔任冀州刺史, 此時冀州仍然存在風俗輕薄、 市井百姓奸詐的情況,“趙煚為銅斗鐵尺,置之于肆,百姓便之。 上聞而嘉焉,頒告天下,以為常法”[2]1251。 冀州需要反復移風易俗,鄰近的相州也有類似問題。 樊叔略在高祖還未受禪之時就任汴州刺史,后來朝廷聽說了他的名聲遷為相州刺史。 梁彥光在開皇初擔任的是岐州刺史,甚有惠政,在開皇五年(公元585 年)左右遷任相州刺史[2]1675。 開始,梁彥光依照以前的做法以靜鎮之,但鄴都俗雜,百姓奸詐,多生是非,并未見效,于是坐免。 一年后,他又主動請任相州刺史,改弦易調,變其風俗,“發摘奸隱,有若神明,于是狡猾之徒,莫不潛竄,合境大駭……彥光欲革其弊,乃用秩俸之物,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圣哲之書不得教授。 常以季月召集之,親臨策試……于是人皆克勵,風俗大改”[2]1676。可以看出,相州的治理難度同樣很大。 古冀州之地究竟存在什么問題? 從趙煚、梁彥光的治理手段看,共同點在于民眾狡猾輕詐、不務農桑、工商業發達、淫巧成俗,之所以會形成這一風氣,其根源在于“魏郡,鄴都所在,淫巧成俗,雕刻之工,特云巧妙,士女被服,咸以奢麗相高,其性所尚習,得京、洛之風矣”[2]860。 這里曾是北齊的統治中心, 鄴都輻射下的古冀州之地耳濡目染,被鄴都所同化。 再者,北齊亡之后, 士族多遷徙至關中, 遷徙而來的多是技巧、 商販及樂戶之家, 這使得教化的難度加大。 對此,樊叔略、梁彥光不約而同地采取先立法并嚴格執法的方式以法止亂。 樊叔略立銅斗鐵尺, 統一度量衡, 讓奸詐之商無機可乘。 梁彥光嚴懲犯法之人, 嚴格打擊不法行為, 在打擊奸詐之人之后又采用懷柔政策安撫百姓,開設學校講學授禮。 軟硬兼施,懲惡揚善,風俗大治。 經過幾任刺史的不懈治理,“風俗頗移,皆向于禮矣”[2]860。
古豫州之地尚商賈,好機巧,輕禮義,重財物。 而汴州尤具代表性,它是西漢梁孝王的封國,“邪辟傲蕩,舊傳其俗”[2]843。 此地之人多從商,有心機、善算計、趨利,來此牟利的外地人眾多,商業繁榮,人流雜亂。 隋文帝以此為患,于是任命令狐熙為汴州刺史。 令狐熙到任后首先整頓工商業, 嚴格限制交易的時間和地點, 加強對戶籍的管理, 散居之戶勒為聚落,外來之戶令歸其本,決遣滯獄,并以法令保證政令順暢執行[2]1386。 最后,這一區域也達到了務農桑、重禮文的治理目的。
梁州之地頗為保守落后。 “質樸無文,不甚趨利。 性嗜口腹,多事田漁,雖蓬室柴門,食必兼肉。 好祀鬼神,尤多忌諱,家有人死,輒離其故宅”[2]829,呈現出華戎混雜,貴賤懸殊,胡俗與漢俗并存、各自流行的局面。 此地畏疫風氣猖獗,一人病疫,闔家避之,因而病者多死。 岷州刺史辛公義曾做出過改易, 他將病人都集中安置在自己的廳事,晝夜同處,還常常親自照顧病人, 以此證明與病人接觸不會傳染。“其后人有病者,爭就使君,其家親戚固留養之,始相慈愛,風俗遂變。 ”[8]5525也只有這種身體力行的教化方式, 才能讓那些不受禮樂規范的民眾信服。 古梁州之地還包括蜀地,這里的百姓沉溺享樂,很少有功名文學的追求,宗族、親情觀念淡漠,工藝精巧,專于盈利,蠻夷力量強大。 梁毗任西寧州刺史之時,發生過蠻夷酋長喜好金器為此相互爭奪屢動干戈的事件。 梁毗借諸酋長以金遺己的機會, 教導他們:“此物饑不可食, 寒不可衣。 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耶?”[2]1479梁毗以身作則,不收賄賂,不愛虛物,使得蠻夷深受感動,停止爭斗,和平相處。
嶺南之地潮濕多雨, 居民多受瘴氣影響患病乃至死亡, 所以壽命普遍不長。 臨海地區,多奇珍異寶,外地商賈來此致富。 但此地蠻、夷、獠眾多,風俗輕悍、直率好斗、重財輕義、不知禮儀、原始落后,保持著諸多陋習、荒習。 酋長作為蠻夷的部落首領, 往往各自為政,有著不同的利益訴求,若是地方長官無法處理好地方酋長之間的關系,極易引發沖突。因而,隋文帝不得不慎重安排地方長官。 他任命令狐熙為桂州總管,并且許以便宜從事,刺史以下官員都可由其授予。 令狐熙也沒有辜負文帝的期望,以恩惠取信于人,招撫各溪洞渠帥,于是各蠻夷部落相繼歸附,“為建城邑,開設學校,華夷感敬,稱為大化”[2]1386。 令狐熙通過整頓吏治、建城安居、開設學校,使百姓生活得到保障,既可免受侵擾,又能接受文化熏陶,自然安居樂業、風俗大化。 之后,對此地移風易俗的官員還有乞伏慧。 他也是一位頗有經驗的官員,在曹州、齊州、荊州等地都曾有過政績,文帝命其領潭、桂二州總管三十一州諸軍事,所管轄的地方包含桂州、潭州、荊州,“其俗輕剽, 慧躬行樸素以矯之, 風俗大洽”[2]1378。 乞伏慧躬行矯之,以身作則,以德化人,也起到了作用。 嶺南地區因為環境閉塞,民眾無知愚昧,盛行武力,面對這種環境,長期安撫勸善、率先垂范不失為一個好方法。
四、結語
隋代的移風易俗制度上承兩漢、 魏晉南北朝,下啟盛唐,這一時期巡省風俗使的職能比前代更為復雜, 為唐代使職細化埋下了伏筆。 再者,隋代兩代統治者的移風易俗的方式大不相同, 深刻體現了移風易俗任務的反復性和長期性, 而地方官員的移風易俗最具成效,這為后代乃至當今提供了有益的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