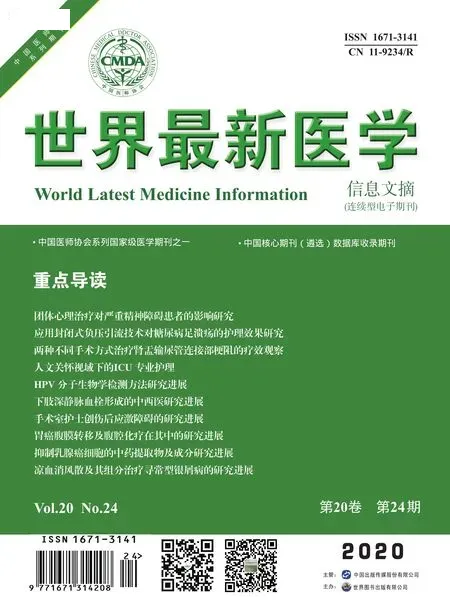從溫病理論探討對幽門螺桿菌感染性胃炎的認識
楊博
(甘肅中醫藥大學,甘肅 蘭州)
0 引言
幽門螺桿菌(Helicobacter pylori,Hp)感染性胃炎是一種感染性疾病,也是一種傳染病,是一種臨床常見病。其所導致的臨床癥狀不典型,甚至可能沒有任何不適癥狀,主要表現為非特異性消化不良的癥狀,如上腹部不適、飽脹感,甚至會有燒灼樣疼痛或者鈍痛等,可伴有食欲減退、噯氣、反酸、惡心等癥狀。癥狀的出現與否無明確的節律性,有時候進食可以加重癥狀。嚴重者可以導致消化道出血,發展為貧血。疾病進一步惡化,會導致泌酸腺彌漫性萎縮,出現腸化生及上皮內瘤變,最終發展為胃癌。溫病是指由“溫邪”侵襲人體所致,具有傳染性和流行性的一類疾病,與現代醫學傳染性疾病聯系比較密切[1],衛氣營血辨證及三焦辨證是溫病學的辨證體系的主要部分。Hp 感染性胃炎作為一種傳染性疾病,與溫病學說關系密切,根據其發病特點可歸屬于“伏氣溫病”的范疇,而且根據其臨床特征可歸類于溫病學的“濕溫病”,結合衛氣營血辯證及三焦辨證,可以進一步認識其發病傳變及治療。
1 幽門螺桿菌是一種濕熱之邪
幽門螺桿菌是Hp 感染性胃炎的病因。明·吳又可在臨床實踐中發現瘟疫病的發生不同于以往的“六淫”致病,而是認為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致病,其在《溫疫論·原序》[2]中云“夫瘟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其中“異氣”致病“種種不一”,故其又統稱為“雜氣”。《溫疫論》曰:“雜氣為病最多,舉世皆誤認為六氣”。故由此看來Hp 導致Hp 感染性胃炎的發生,不屬于“六氣”及“七情”致病的范疇,而是屬于“雜氣”致病的范疇。根據臨床研究,中醫學普遍認為Hp 是一種濕熱之邪。唐丹丹[3]對510 名Hp 感染性患者進行中醫辨證分型,發現脾胃濕熱型占41.18%,是最多的證型。朱亞楠[4]通過對136 例慢性萎縮性胃炎患者辨證分型并觀察其證型與Hp 感染之間的關系,發現脾胃濕熱證患者Hp 陽性率為62.07 %,高于脾胃虛弱、肝胃不和、胃陰不足三型,差異有統計學意義。陳鳳麗等[5]通過對慢性胃炎患者進行辨證分型,檢測各證型患者Hp 滴度水平,隨后統計分析慢性胃炎常見中醫證型與Hp 滴度水平間的關系,發現慢性胃炎證型中以濕熱阻胃證、脾胃虛寒證最多,肝氣犯胃證次之;Hp 滴度水平在肝氣犯胃、脾胃虛寒、濕熱阻胃證型中呈現遞增趨勢。李培彩等[6]通過文獻研究發現,HP 相關疾病多見脾胃濕熱、肝胃不和和脾胃虛弱。陳瑤等[7]發現HP 相關性胃病的中醫證型以濕熱證和肝胃不和證為主,中醫證候要素以熱、濕、氣滯為主。楊閃閃等[8]通過對Hp 與脾胃濕熱證相關性進行探討,認為Hp 與脾胃濕熱證關系密切。綜上所述,Hp 不同于“六淫”邪氣,且是一種濕熱性質的邪氣。
2 Hp 感染性胃炎具有傳染性
2014 年在日本京都召開的“幽門螺桿菌胃炎全球會議”上提出的《幽門螺桿菌胃炎京都全球共識》認為Hp 胃炎是一種傳染性疾病[9]。Hp 可以在人-人之間進行傳播,感染者及被污染的食物及水源是最主要的傳染源。口-口和糞-口是其主要傳播途徑,以口-口傳播為主。前者通過唾液傳播,后者通過感染者糞便污染水源傳播。明·吳又可[2]已經認識到了溫病的傳染性,因“其延門合戶,又如搖役之役,眾人均等之謂,”因而稱之“溫疫”,此即為《溫疫論》得名之由來。《溫疫論》云:“此氣之來,無論老少強弱,觸之者即病。邪自口鼻而入…邪之所著,有天受,有傳染,所感雖殊,其病則一”,不僅說明了溫病具有特殊的傳播途徑,而且感邪之后發病癥狀類似,Hp 感染性胃炎的傳播即是通過口腔攝入被污染物,Hp 定植感染后形成以脾胃系統病變為主要表現的一種疾病。清·薛雪在《濕熱病篇》[10]中提出“濕熱之邪從表傷者,十之一二,由口鼻入者,十之八九”。也說明了溫病特殊的傳播方式,不同于傷寒等從皮毛而入的受邪方式。
3 從溫病論治Hp 感染性胃炎的探討
Hp 感染性胃炎臨床表現不典型,甚至臨床可見攜帶Hp 者并沒有明顯不適癥狀。可見Hp 感染后具有一定的潛伏期,從發病類型來看,孫易娜[11]認為Hp 感染性胃炎屬于“伏邪溫病”。Hp感染作為一種濕熱之邪,感染人體發病后主要證型為脾胃濕熱。因為疾病主要表現以脾胃系統癥狀為主,根據其特征可以歸屬于“濕溫病”范疇。Hp 感染性胃炎臨床多見病程較長,且傳變緩慢,纏綿難愈,容易復發,與濕熱類疾病性質類似。
2018 年全國中西醫整合治療幽門螺桿菌相關“病-證”共識中認為Hp 感染性胃炎臨床常見脾胃濕熱證癥見:上腹痞滿或疼痛,口干或口苦,或口干不欲飲水,食欲減退,伴有惡心或嘔吐,小便黃。舌紅,苔黃厚膩。[12]從衛氣營血辨證,則此證屬于氣分證,濕熱內蘊,邪氣雖甚但是正氣未衰。從三焦辨證來說,此證屬于邪在中焦,濕熱中阻證,濕熱留戀氣分,彌漫三焦。總體治療上應該以清利脾胃濕熱為原則,根據臨床表現,辨別濕熱的偏重程度進行處方。清·薛雪撰《濕熱病篇》[10]提出“濕熱病屬陽明太陰經者居多,中氣實則病在陽明,中氣虛則病在太陰。”實則陽明,虛則太陰在對濕溫病的臨床治療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導意義。中氣的盛衰是疾病轉化的重要因素,如果中氣充實則疾病偏向陽明胃腑,邪氣熱化,多為熱重于濕,如果中氣偏于衰弱不足,則邪氣從濕而化,病變趨向于向太陰脾臟發展,最終導致濕重熱輕之變。對于濕熱病的治療,臨床上以分解濕熱,使濕邪去,熱邪勢孤為主要的原則。2018 年全國中西醫整合治療幽門螺桿菌相關“病-證”共識中所給的處方即是《霍亂論》中治療濕熱并重的連樸飲。如此則臨床中治療上也可以選擇三仁湯或甘露消毒丹等清熱化濕類方劑加減。
4 通過溫病進一步認識Hp 感染
Hp 的感染不僅僅與中焦脾胃相關,而且其可以導致多種疾病。目前研究發現Hp 感染與過敏性紫癜關系密切。王芳芳[13]等通過對在該院就診的過敏性紫癜患兒及對照組行免疫印跡法檢測血清Hp 相關抗體,最后發現Hp 感染可能是過敏性紫癜發病的因素之一,殺滅Hp 可以提高臨床療效。黃永輝[14]通過對比復發性過敏性紫癜患兒及對照組的Hp 陽性率發現觀察組患兒的Hp陽性率71.67%明顯高于對照組健康兒童的25.00%,觀察組中Hp陽性患兒有69.77%出現腹痛,明顯高于Hp 陰性患兒的腹痛發生率41.18%,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包淑貞[15]等使用抗Hp 藥物聯合常規藥物治療過敏性紫癜患者,對照組給予常規藥物治療,發現實驗組治愈率(71.43 %)與好轉率(21.43 %)顯著高于常規組治愈率(48.65 %)與好轉率(10.81 %),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實驗組復發率(11.90%)顯著低于常規組(40.54%),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因此認為Hp 感染是過敏性紫癜發生的病因之一,增加抗Hp治療有助于過敏性紫癜患者病情改善。綜上所述,Hp 也是導致過敏性紫癜的病因。況且Hp 感染性胃炎若病情較重,也可以出現胃黏膜糜爛出血,導致便血甚至缺鐵性貧血。由此看來,Hp 相關性疾病導致出血,從中醫學角度看來有“熱迫血行”的內在機理。
溫病的正常發生與發展,通常包括衛氣營血四個階段,當疾病發展到營分證或者血分證時,會出現熱甚動血的癥狀,可以出現斑疹隱隱以及多臟腑或多部位的出血。《濕熱病篇》[10]提出“濕熱證,上下失血或汗血,毒邪深入營分,走竄欲泄。”其中“汗血即張氏所謂肌衄也。”指出了濕熱之邪內蘊日久,具有化燥入血,熱甚動血的可能。其治療上則用犀角地黃湯加減以清熱涼血散瘀。并且他也強調“大進涼血解毒之劑,以救陰而泄邪,邪解而血自止矣”。強調針對病因進行治療。聯系之前的Hp 感染性胃炎癥狀屬于氣分證,那么此階段的癥狀明顯屬于營分證及血分證。故聯系疾病發生和發展,動態來看,無論是Hp 感染性胃炎還是Hp 相關性過敏性紫癜,都是Hp 感染后兩個不同的階段,在治療上均可以通過溫病學思想的指導進行相應的治療。
5 結論及展望
綜上所述,Hp 感染性胃炎屬于溫病的范疇,Hp 是一種濕熱邪氣,具有一定的傳染性及流行性。從發病類型來講是“伏邪溫病”,臨床癥狀主要表現在脾胃系統,屬于濕熱類溫病,臨床以氣分證中的濕熱阻滯中焦證型最為常見。Hp 感染性胃炎并非只有常見的氣分的濕熱中阻證,臨床與Hp 相關疾病較多,其中過敏性紫癜可以視為營分證。
Hp 感染后并不一定就會出現脾胃系統癥狀,那么這部分沒癥狀的患者,應該就屬于“伏邪”的范疇,對于伏邪溫病,吳又可的達原飲是重要的方劑,那么在其治療Hp 感染卻沒有明確臨床癥狀者是否會有明確療效?如果可以從氣分證和營分證來認識Hp 感染性胃炎及Hp 相關性過敏性紫癜,那么還有沒有處于其他階段的Hp 相關疾病。也許溫病及Hp 相關性胃炎的關系不僅僅如此,葉天士作為溫病大家,在治療胃病方面有很大的成就,這兩者之間并不僅僅只是個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