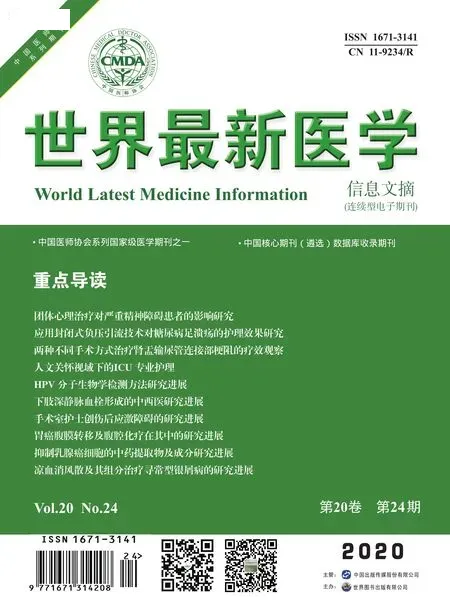宮頸腺癌研究進展
馬丹,肖琳
(重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婦產科,重慶)
0 引言
宮頸癌是最常見的婦科惡性腫瘤之一。我國目前為宮頸癌的發病大國,據國家癌癥中心數據統計,2015 年我國女性宮頸癌的發病率在惡性腫瘤中排名第六,僅次于肺癌、乳腺癌、結直腸癌、甲狀腺癌和胃癌,占比6.25% ]。宮頸癌類型多樣,鱗癌最為常見,其次為腺癌、腺鱗癌,以及其他少見類型,如透明細胞癌、神經內分泌癌等。近年來資料顯示,宮頸腺癌發病率逐年上升,相比鱗癌,腺癌是一組具有不同形態、病因、分子驅動和預后的異質性腫瘤,在宮頸癌中占比可達20%[2][3]。此外,腺癌趨于年輕化,在年輕女性中的發病逐年上升,其易發生淋巴結轉移、深間質侵犯、脈管轉移、不易早期發現、對放化療不夠敏感,患者預后較差 。所以,對于宮頸腺癌的診治是婦科醫生所面臨的一大挑戰。本綜述旨在對宮頸腺癌發病相關因素、臨床病理特點進行闡述,以期對臨床治療提供幫助,從而制定出更好的診療措施。
1 組織病理學分型
1.1 WHO 分類
宮頸腺癌的組織學類型呈現多樣化,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關于宮頸腺癌的最新分類(頒布于2014 年),將宮頸腺癌分為:普通型宮頸腺癌(常見型,占比80%-90%,腫瘤由大小不等的腺體和乳突組成,原位腺癌是這類癌的前體)、粘液腺癌(腫瘤細胞中存在大量的細胞質粘液,分胃型、腸型、印戒細胞型)、絨毛管狀腺癌(可表現為乳頭狀、息肉狀、絨毛狀,腫瘤細胞由數個分支的乳頭構造,乳頭表層包裹假復層柱狀上皮,細胞異性不明顯)、子宮內膜樣癌、透明細胞癌、漿液性癌、中腎管癌、混合性腺癌-神經內分泌癌[5]。
1.2 IECC 分類
基于宮頸腺癌病因學和生物學行為,國際宮頸腺癌的標準和 分 類(International Endocervical Adenocarcinoma Criteria and Classification,IECC)為宮頸腺癌的分類提供了一個新的框架--將是否感染人乳頭瘤病毒(human papillomavirus,HPV)對宮頸腺癌進行分類,分為:1、HPV 感染相關腺癌,包括典型的宮頸腺癌、腸型腺癌、印戒細胞腺癌、絨毛管狀腺癌、侵襲性層狀黏液分泌癌;2、非HPV 感染相關腺癌,包括胃型腺癌、腎型腺癌、漿液性腺癌、透明細胞腺癌、子宮內膜樣腺癌、惡性腺瘤[6]。
宮頸腺癌分型多樣,由此提醒婦科醫生在對原發性宮頸腺癌的診斷時應注意兩個問題:(1)與來自宮體的腺癌相鑒別;(2)認識宮頸腺癌的各種類型。
2 發病因素
2.1 HPV 因素
宮頸腺癌的發生多與HPV 持續性感染有關,尤其是高危型HPV 感染,如16、18、31、32、33 型等。事實上,約有90%女性在一生中會發生一過性的HPV 感染,大多數女性可通過自身免疫清除感染,只有在機體免疫力降低、局部創傷、微環境變化等因素影響下,機體無法清除感染的病毒,發生病毒的持續性感染(間隔4-6 個月或6-12 個月的相鄰2 次隨訪中,同一患者的宮頸檢測樣本均顯示HPV 陽性且為同種類型),進而引起病變。近年來,宮頸腺癌的發生趨于年輕化,可能與年輕女性處于性活躍期有關。性活躍期女性易發生宮頸柱狀上皮外移,相比鱗狀上皮,柱狀上皮在性生活過程中更容易發生損傷。
和宮頸鱗癌一樣,HPV16 型和18 型亦認為是宮頸原位腺癌和浸潤性腺癌中最常見的類型[7][8]。Silvi[8]等通過對全球38 個國家14249 名患者進行HPV 檢測發現,在宮頸腺癌中,16 和18型陽性率占比約82%,而16、18、45 型在所有宮頸腺癌患者中占比可達94%,相比16 型,18 型和45 型更容易導致腺癌的發生。HPV 為細胞內病毒,其致病基因片段主要為E6、E7 片段,該片段分別與宿主細胞P53、Rb 基因整合,導致細胞周期失調控,細胞進入增殖活躍狀態,發生異型增生,從而導致腫瘤的發生。
2.2 HPV 以外因素
對于部分宮頸腺癌患者沒有檢測到HPV 感染,其可能與腫瘤細胞免疫逃逸、表觀遺傳變異、基因突變以及慢性炎癥導致的腫瘤微環境改變等因素有關[9]。除HPV 感染外,宮頸腺癌的發生尚有HPV 之外的危險因素,如性生活開始年齡早、多個性伴侶、多孕多產、其他性傳播疾病史、激素類避孕藥使用、肥胖、超重和血清中單純皰疹病毒-2(HSV-2)陽性等,這些因素單獨或聯合HPV 共同作用,均會使罹患宮頸腺癌的風險增加[10]。
3 臨床特點
3.1 臨床表現
相對鱗癌,腺癌患者以內生型常見,臨床癥狀隱匿且缺乏特異性。部分患者可能出現接觸性出血(性交或婦科檢查后出血)、不規則陰道流血、白帶增多、陰道排液等,而部分患者可因病變存在宮頸管內,或浸潤癌較小,無自覺癥狀,其宮頸外觀無異常,肉眼難以發現,多數由宮頸脫落細胞學檢查及陰道鏡檢查發現。文獻報道,通過對10 年宮頸腺癌患者病例資料統計分析發現,因癥狀就診從而發現宮頸腺癌的患者中,排在前3 位的臨床癥狀為陰道不規則流血、性生活后陰道流血、陰道分泌物異常,分別占37.37%(37 例)、34.34%(34 例)和8.08%(8 例)[11-13]。
3.2 查體
宮頸腺癌體征多樣,內生型患者僅表現為宮頸粗大、質硬、桶狀改變;進展期外生型患者可表現為宮頸糜爛、觸血、宮頸菜花樣贅生物等;部分不典型患者甚至可表現為子宮飽滿、子宮增大、盆腔包塊等。因此,婦科醫生對于有不規則陰道排液、查體宮頸表面光滑或宮頸粗大質硬的患者應引起重視,警惕宮頸腺上皮病變可能。對于可疑病變的患者應行進一步的細胞學、病毒學及陰道鏡檢查。
3.3 輔助檢查
在陰道鏡檢查中,發現以下圖像應高度懷疑宮頸腺癌,包括:①隆起的病變;②宮頸表面腺開口異常增多、擴張、不規則分布;③乳頭樣病變;④上皮芽形成;⑤紅色斑點狀病變;⑥異形血管形成;⑦高度上皮病變;⑧兩個或更多的鱗狀上皮病變被腺樣上皮分隔開來[14]。同時,強調在陰道鏡下活檢時行頸管搔刮術。
3.4 生物學行為
相比宮頸鱗癌,宮頸腺癌在確診時期別較晚,更具有侵襲性,易于發生深間質浸潤、脈管浸潤、淋巴結轉移等。葛莉莉等[15]通過對569 例IA2-IIA 期宮頸癌患者研究發現,淋巴結轉移率為25.13%,其中,116 例宮頸腺癌患者中51 例患者發生盆腔淋巴結轉移,453 例鱗癌患者中92 例發生盆腔淋巴結轉移,宮頸腺癌的淋巴結轉移率顯著高于鱗癌,且腺癌患者發生高位轉移、多站轉移、雙側轉移的比例高于鱗癌組,腺癌患者比鱗癌患者更易發生早期別淋巴結轉移。余雪琛等[16]對292 例早期宮頸癌患者回顧性研究亦得出相似結論。宮頸腺癌在細胞學上表現出強大的異質性,生物學行為較鱗癌不同,病理及臨床診斷均存在一定困難,這可能是腺癌與鱗癌在臨床特點及預后差異的原因。
4 腫瘤標記物
宮頸鱗癌有其特異的腫瘤標記物,即鱗狀細胞癌抗原(Squamous cell carcinoma antigen,SCC),而宮頸腺癌目前仍缺乏特異性的腫瘤標記物,這也是宮頸腺癌在診斷、療效評估及隨訪監測中較宮頸鱗癌困難的原因之一。目前,對于宮頸腺癌患者的血清學檢測主要包括糖類抗原125(cancer antigen 125,CA125)、癌胚抗原(carcinogen-embryonic antigen,CEA)、癌抗原19-9(cancer antigen 19-9,CA19-9)以及免疫相關因子(如白介素6、白介素8、血管生成因子)等。
4.1 CA125
相比宮頸鱗癌患者,宮頸腺癌及腺鱗癌患者血清CA125 水平顯著升高,文獻報道,20%~75%的宮頸腺癌患者存在CA125 升高[17]。多項研究認為血清CA125 水平是影響宮頸腺癌預后的獨立危險因素,且與腫瘤臨床分期、分化程度、癌灶大小及是否有淋巴結轉移密切相關[18-20]。Beata 等[20]通過檢測宮頸腺癌患者術前CA-125、CEA 以及細胞因子水平,發現CA-125 的診斷敏感性高于CEA 及細胞因子,且在多因素分析中,CA-125 水平是影響預后的獨立因素,其血清學濃度與臨床分期呈正相關。
4.2 CEA
CEA 是一種非特異性的腫瘤標志物,腫瘤細胞的基因調控障礙,CEA 合成和分泌就會增加,梁指榮等[21]通過對宮頸腺癌患者術前CEA 水平進行檢測,認為宮頸腺癌患者術前血清CEA 檢測值若超過臨界5ng/mL,則與腫瘤大小、淋巴結轉移及浸潤程度相關,且與患者臨床期別有一定相關性,表明CEA 檢測水平可用于判斷宮頸腺癌的浸潤情況。
4.3 CA19-9
CA19-9 對宮頸腺癌的診斷也具有一定的意義,文獻報道CA19-9 在27%宮頸腺癌術后及化療后數值迅速降低,并且它的數值與腫瘤體積密切相關;同時,CA19-9 局限在癌瘤組織中,而不存在于正常組織中,故CA19-9 可作為宮頸腺癌復發和進展的腫瘤標記物,進行隨訪監測[22]。
5 治療
目前,宮頸癌的治療主要根據臨床分期進行個體化治療,2018 年國際婦產科聯合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FIGO)對宮頸癌分期進行了更新,把影像及病理學納入新分期,美國國立綜合癌癥網絡(NCCN,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公布《2019NCCN 宮頸癌臨床實踐指南》[23],根據不同的期別,結合患者保留生育功能的意愿,進行不同范圍的手術和/或放化療的個體化治療。
腺癌是影響宮頸癌預后的獨立危險因素,而對于宮頸腺癌的治療主要參照的是宮頸鱗癌。周娟等[24]通過研究發現,根治性的子宮切除術結合同步放化療可以改善鱗癌患者的預后,但對于腺癌患者卻沒有明顯改善,表明宮頸腺癌對放化療不敏感,且放化療對年輕腺癌患者卵巢功能會導致不可逆的損害,所以,對于宮頸腺癌的治療應強調根治性手術的重要性。當前宮頸腺癌的免疫治療日益倍受關注,其中包括HPV E6、E7 基因免疫治療以及過繼性T淋巴細胞免疫治療,都在進行臨床試驗研究當中[25]。
6 預防
2017 年8 月,中華預防醫學會婦女保健分會組織制定了《子宮頸癌綜合預防指南》提出了宮頸癌的一、二、三級預防[26]。
6.1 一級預防
一級預防包括健康教育和預防性接種HPV 疫苗。由于部分宮頸腺癌的發生并不是由HPV 驅動的,在目前的HPV 疫苗接種時代,非HPV 相關腫瘤的相對發病率可能會增加,這也是目前宮頸腺癌發病率逐年上升的原因之一。
6.2 二級預防
二級預防為適齡婦女的定期宮頸癌篩查。目前對于宮頸癌的篩查,主要選擇的是宮頸脫落細胞學和HPV 檢查的聯合篩查,研究表明,宮頸脫落細胞學聯合HPV-DNA 檢測有助于提高宮頸腺癌和宮頸原位腺癌的診斷率,有效降低臨床誤診和漏診的發生[27][28]。通過對331818 名女性進行隨訪發現,將HPV 檢測與細胞學相結合,還可以更早地發現宮頸癌(尤其是腺癌)高危女性[29]。目前我國對于宮頸癌的篩查亦推薦細胞學與病毒聯合檢測。由于HPV16、18 型與宮頸腺癌發病密切,專家共識認為,建議對HPV16 和18 型陽性者直接轉診陰道鏡;對于HPV 陰性者,因腺上皮病變細胞學表現不典型,大部分仍表現為鱗狀上皮內病變,細胞學檢測結果在非典型鱗狀上皮細胞(atypical squamous cells of undetermined significance,ASCUS)及以上患者建議轉診陰道鏡[30]。
由于宮頸腺癌的病灶多位于頸管內,宮頸脫落細胞學檢查假陰性率高,且腺上皮病變相對少見,加之其組織學類型的特殊性,對其癌前病變的評估較鱗狀上皮病變困難,陰道鏡視野暴露差,從而增加了宮頸腺癌早期診斷的難度[3,31]。所以婦科醫生在采集標本時應盡可能的暴露宮頸,將標本刷伸入到頸管內,對于可疑頸管內病變的患者,可考慮行頸管搔刮術。
6.3 三級預防
三級預防為根據臨床分期,結合患者生殖需求和個人意愿,選擇合適的手術方式(是否切除子宮和卵巢),結合放化療等的綜合治療。
7 結語
目前我國仍是宮頸癌的發病大國,其中,宮頸腺癌的發病率逐年增加,究其病因,除與HPV 感染相關外,還尚有HPV 感染以外的因素,此外,我國仍有一大部分女性缺乏相關預防知識,沒有足夠的醫療資源使每一位女性有條件接受疫苗及宮頸癌篩查,加之宮頸腺癌其本身所特有的腫瘤異質性,其在生物學行為上表現出與宮頸鱗癌的差異,其發生發展更為隱匿,增加了宮頸腺癌早期診斷的難度,導致其確診時期別晚、淋巴脈管轉移發生率增加,且宮頸腺癌對于放化療的低敏感性,進一步導致患者預后不良,給婦科醫生在其治療策略上提出了新挑戰。
在臨床工作中,需要關注每一位就診患者的主訴,仔細的查體以及確切的輔助檢查,為每一位患者制定個體化的診斷及治療方案,提高和改善宮頸腺癌的有效篩查、早期診斷、遠期療效及監測隨訪,改善宮頸腺癌患者的預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