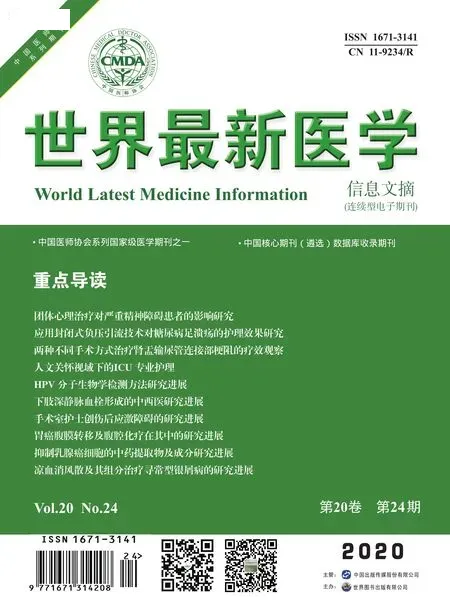偏頭痛的中醫診療進展
郭曉兵,劉海英
(1.山東中醫藥大學,山東 濟南;2.濰坊市中醫院,山東 濰坊)
0 引言
頭痛作為一種臨床常見病證在各級醫院神經內科門診頗為多見,在全球各類疾病負擔排名中亦高居第2 位[1],其中所占比最大的疾病即為偏頭痛。伴或不伴先兆的偏側、中重度的發作性頭痛是其典型臨床表現。我國偏頭痛發病率為9.3%[2],其疼痛所導致的生活質量下降嚴重威脅了我國人民的生命健康。現代醫學對于偏頭痛的認識已隨基礎醫學發展得到長足進步,但臨床常用的非甾體類解熱鎮痛藥所致的胃腸反應、曲普坦及麥角類藥物基層醫院藥源不足及引起繼發性高血壓等不良反應使患者對治療往往投鼠忌器,難于堅持。祖國醫學在其兩千多年的發展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有關防治偏頭痛的經驗,不僅具有療效顯著的特點,其具有豐富的治療方法與其辨證論治的特點亦契合當代個體化診療的潮流。本文旨在拋磚引玉,通過進一步總結傳統中醫學對于偏頭痛證治方面的相關認識以及近年來當代中醫工作者對于偏頭痛診療體系的發展與探索,以期在偏頭痛的臨床論治中獲取更好的療效,現綜述如下。
1 病因病機
古代醫家對于偏頭痛及其病因病機的認識在早期泛泛混于“頭痛”、”頭風”之中,如《足臂十一脈灸經》即已記載了足太陽經所主病變致與偏頭痛高度類似的癥狀,“足鉅陽之脈系于踵......是動則痛沖頭痛,目似脫”;《黃帝內經》已將風邪作為頭痛之病因,強調風邪在發病中的重要地位,如“風氣循風府而上 ,則為腦風”、“新沐中風 ,則為首風”;同時將“氣上不下 ,頭痛巔疾”作為內傷頭痛的總體病機,并從五臟立論,提出了肝郁氣逆致頭痛的理論,“肝病者,兩脅下痛引少腹……氣逆則頭痛”,開情志病因致病觀點之先河,并為后世醫家所進一步總結發揮。宋代《圣濟總錄》首載“偏頭痛”一詞,并將病因歸于正虛邪湊,“論曰偏頭痛之狀,由風邪客于陽經,其經偏虛者,邪氣湊于一邊,痛連額角,故謂之偏頭痛也”。從宋以后,每多醫家將“偏頭痛”作為一種獨立疾病單獨論述,其病因病機也逐漸明晰,將肝經氣滯作為重要病機,如陳士鐸《辯證錄》認識氣郁情志在偏頭痛發病中的重要作用,認為“郁氣不宣”,“又加邪風襲之于少陽之經”終致偏風頭痛;程國彭《醫學心悟》將偏頭痛的病機總歸于肝經陽盛上擾記有“偏頭痛,其痛暴發,痛勢甚劇,或左或右,多系肝經風火上擾所致”。近代以來,我國中醫工作者在繼承傳統認識的基礎上,廣泛實踐,積極探索,對偏頭痛的病因病機得到進一步的認識,可謂百家爭鳴:韓金霞[3]將現代醫學認識與中醫理論結合,認為瘀血是導致偏頭痛的重要因素,血瘀不通則作頭痛,反復發作;閆詠梅[4]認為風邪上擾,纏綿難愈,久而結聚伏痰、瘀血致腦絡不同而發頭痛;李曉麗等[5]總結劉福友教授的臨床經驗,將偏頭痛以虛實二分,虛者多歸于肝、脾、腎三臟不足,實者多責之風、火、痰、瘀,進一步明確了偏頭痛的臨床辨證思路;阮進榮[6]認為肝腎陰虛同樣為偏頭痛的重要病機,其多以偏側頭痛伴有睡眠質量差伴有腰膝酸軟等癥;何楊偉[7]繼承葉天士、徐大椿的觀點,將感受外風作為偏頭痛的夙因,清陽之氣受阻,氣血不通,阻滯經絡發為頭痛;陰曉健[8]等認為偏頭痛以血瘀為標,氣虛為本,并將其指導臨床,取得不錯療效。薛輝[9]等理順運氣學說,認為“火熱邪郁而上逆”、“寒邪外束致陽氣郁而上行”、“濕邪傷腎以及陽明”等時氣變動是誘發偏頭痛的重要病因,將偏頭痛的病因與生態、氣候變化相聯系,更符合臨床實際,為偏頭痛的發作的預測和預防提供了理論基礎。
2 中藥辨證施治
中藥治療作為中醫傳統療法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在臨床治療偏頭痛方面具有療效好、副作用小、治療費用低等特點[10]。目前臨床上對于頭痛病的主要辨證施治方法大抵分為以《內經》中臟腑陰陽學說為代表的“臟腑辨證”流派與以《傷寒論》為代表的“六經辨證”流派兩類,“六經”與“臟腑”辨證方法各有特點,各自均有不錯的臨床發揮和療效,特分述于下:
2.1 臟腑辨證學說
《黃帝內經》作為戰國到秦漢時期祖國醫學實踐的總結,其確定了中醫學臟腑理論的基本觀點,其內容中雖未能明確地提出“偏頭痛”的概念,但高屋建瓴地提出了臟腑辨證論治頭痛的基本原則,如《素問·刺熱論》 中即有實證頭痛從五臟熱盛論治的觀點,如“肝熱病者,小便先黃......其逆則頭痛員員”、“肺病熱者,先淅然厥......頭痛不堪,汗出而寒”等。《素問·通評虛實論》對虛證頭痛提到以脾胃為辨治著點,“頭痛耳鳴,九竅不利,腸胃之所生也”。自漢至唐中醫學對于頭痛病的認識仍處于積累臨床經驗過程中,尚未有系統性的頭痛辨證理論的提出。金元時期隨著臨床經驗的積累,已認識到“偏頭痛”為一類獨立的頭痛分類,但對于偏頭痛的治療內容仍混在雜“頭痛病”之內:易水學派總結前人經驗提出了“藥物歸經”及“引經報使”學說,張元素在《醫學啟源》中總結指出“頭痛須用川芎,如不愈,各加引經藥,引藥入各臟而觸痹。“太陽蔓荊,陽明白芷,少陽柴胡,太陰蒼術,少陰細辛,厥陰吳茱萸… …看何經,分以引經藥導之”,將臟腑辨證與臨床施治聯合起來,為后世的分經論治提供了基礎。朱震亨則進一步豐富了偏頭痛的辨證類型,提出了痰厥頭痛和氣滯頭痛的辨證分型,并新創半夏白術天麻湯等方劑以治療痰厥的頭痛。明清時期頭痛病的辨證論已趨完善,葉桂《臨證指南醫案》別具特色的提出了應用蟲類藥物治療氣血瘀阻型頭痛,并提出滋陰熄風法治療肝風頭痛的理論。王清任則在《醫林改錯·頭痛》中對類似偏頭痛樣的以反復發作為特點的頭痛提出了從瘀血論治的觀點,主要應用自立之血府逐瘀湯為其主方,“頭痛,忽犯忽好,百方不效,用此方一劑而愈”。
當代醫家在繼承關于傳統關于頭痛的辨證經驗的基礎的同時,對偏頭痛的理論也進行了充足的臨床實踐和總結,總體以“肝氣郁結”和“氣血瘀阻”為著眼點,強調氣血郁滯是偏頭痛的重要病機。毛麗軍[11]以解郁祛風通絡為則,應用柴芍藥止痛方(組成柴胡、白芍、白術、當歸、川芎、青風藤、枳殼、甘草)治療偏頭痛20例,并與常規氟桂利嗪膠囊組進行對比,中藥組較常規組有效率高(85.0%>77.5%);郭莉娟[12]等認識到偏頭痛患者臨床多伴有煩躁、郁結等證,故治療以舒肝郁、理肝氣、止痛為則,以頭風湯(陳皮、柴胡、茯苓、清夏、細辛、黃連、黃芩、赤芍、川芎、葛根、薄荷等)為主方,對照單用鹽酸氟桂利嗪膠囊組,頭痛癥狀及HAMD 抑郁量表(治療前19.13±4.52,治療后7.00±0.62)積分均有顯著改善,優于單純西藥組,差異有統計學差異;任鵬鳴[13]以《素問》中“是以頭痛巔疾,下虛上實”為理論依據,以肝陽上亢為基本病機,予天麻鉤藤飲方劑治療2 周,有效率達92.5%;鄭貴玲[14]報道治療偏頭痛當以理血祛風為則,重用調氣祛瘀中藥,如全蝎、地龍等,自行組方治療(組成:川芎、白芍、當歸、生地、桃仁、紅花、全蝎、地龍、牛膝、葛根、甘草),力求營血調和,血脈通利,頭痛息止。晏廷念[15]等應用通心絡膠囊(人參、水蛭、全蝎、赤芍、蟬蛻、土鱉蟲、蜈蚣、檀香、降香、乳香、棗仁、冰片等)治療辨證屬于氣滯血瘀證的輕中度偏頭痛患者,并與傳統西藥組(應用布洛芬緩釋膠囊、鹽酸氟桂利嗪膠囊)進行療效對比,治療組1 個月后的癥狀積分較傳統西藥組無統計學差異,但未發生明顯的不良反應,具有安全性強、療效相當的特點;鄭萬利[16]則將血瘀作為偏頭痛發病的軸因,將“治風先治血,血行風自滅”為治療原則,用血府逐瘀湯為主方,并按頭痛的部位及特點分經加減,太陽加羌活、防風,陽明加白芷、葛根,少陽加川芎、柴胡,太陰加蒼術,少陰加細辛,厥陰加茱萸、藁本,治療偏頭痛患者,尤其是伴有TCD 檢查提示椎基底動脈供血不足的患者,療效較單純西藥治療組顯著(93.6%>51.3%),且有統計學差異(P<0.05)。林強[17]傳承當代名老中醫金夢賢臨床經驗,認為“頭為諸陽之會、七竅集中之處”,故非芳化開竅、活血通脈之品不可治之“,治療上以活血通絡止痙鎮痛為則,常用“頭痛方”(組成細辛、僵蠶、全蝎、鉤藤、川芎、丹參)為基礎方并隨證加減,寒濕加用羌活、蒼術,熱盛合菊花、龍膽草、石膏,續性頭痛則補之以枸杞、生地,方藥精煉,用藥縝密,療效顯著,值得臨床工作者借鑒。李秀娟[18]則認為偏頭痛多病程纏綿,辨證當以內傷為主,當責之氣血失和,并通過進行血府逐瘀湯聯合針灸治療偏頭痛與常規西藥治療方案的對比,試驗組臨床癥狀改善情況及TCD 檢查結果均優于常規治療組。
2.2 六經辨證學說
六經辨證理論論治頭痛最早陳述于《內經》,在《靈樞·厥病》中已有關于分經證治頭痛的理論,“厥頭痛,面若腫起而煩心......取之足陽明、太陰”、“厥頭痛。貞貞頭重而痛。瀉頭上五行,行五,先取收手少陰,后取足少陰”;《素問·刺熱論》中亦記載有外感頭痛按時傳變的規律,“傷寒一日,巨陽受之,故頭項痛.......七日,巨陽病衰,頭痛少愈。”;并提出了頭痛的總體治則“調其陰陽”、“不足則補,有余則瀉”;漢代醫圣張仲景在繼承《內經》理論的基礎上,系統的創制了六經辨證理論體系,通過病性和病位的特點,將疾病分為六經并各立方劑治之,其中不乏對于頭痛病的論治內容。《傷寒論》中涉及頭痛病的條文共17 條,如“太陽之為病,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傷寒不大便六七日,頭痛有熱者,與承氣湯”、“傷寒脈弦細,頭痛發熱者,屬少陽”等。其雖未能如臟腑辨證流派系統的提出“偏頭痛、偏頭風”的概念,未能進一步探討專訪專治,但其分經癥候為辨證著眼點的特色,使其在臨床應用中更具有可操作性,療效顯著,自創立以來便被奉為金科。在“六經辨證”體系中,諸經皆可見頭痛,其中太陽病頭痛以惡寒為主要特點,其治法為疏通經氣,治療方劑以麻黃湯與桂枝湯加減為主;陽明病頭痛為陽明經感寒所致,證見身熱、無汗、小便自利,可以選擇葛根湯、白虎湯為其方劑;少陽頭痛可以脈弦細兼見發熱為提挈,每多為偏側頭痛,與西醫之“偏頭痛”的描述最為相近,治療則以小柴胡湯和解少陽,祛瘀通絡止痛;少陰頭痛為陽虛感寒所致,辨證特點為表證卻見沉脈,溫里兼用發汗為其主要治則,主方當以四逆湯加減;干嘔、巔頂疼痛是厥陰頭痛的主要癥狀,病機為中陽不足,寒邪凝滯經氣,主方為吳茱萸湯。后世經方醫家以臨床經驗為基礎,對六經辨證理論進行了豐富和發揮,不斷擴展了六經證治的應用范圍,使其廣泛應用與內傷與外感頭痛的辨治當中。劉燕平[19]報道一例以桂枝加附子湯加減(桂枝18g,白芍15g,白附10g,生姜5 片,大棗5 枚,炙甘草6g)治療頑固性頭痛取得顯效案例;雷虹[20]等總結了其門診頭 痛病例50 例, 以小柴胡湯加減為主方(柴胡12g ,黃芩、太子參、大棗各15g ,水半夏9g ,生姜、甘草各6g)進行治療,取得治愈38 例,好轉12 例,總有效率100%,無復發的臨床療效;楊雪峰[21]報應用吳茱萸湯加減(吳茱黃10g,黨參20g,生姜5g,大棗8 枚,當歸15g,半夏10g,白芍10g,藁本10g,蔓荊子 10g,代儲石20g ,陳皮10g,炙甘草5g)治療以頭痛、吐涎為主要臨床表現的辨證屬厥陰的頭痛患者(包括偏頭痛),療效顯著;王東海、金東明[22]等將辨證屬少陰的頭痛又總分為寒熱兩類,主張分別以芍藥甘草附子湯、四逆湯及腎氣丸治之,并應用黃連阿膠湯加補血填髓之品治療經后血虛虛火內生之頭痛,為臨床辨證頭痛提供了思路。王春華[23]以情志抑郁、臥立不安為辨證著眼點,報道了一例小柴胡湯加龍牡、遠志、丹皮治療月經相關性偏頭痛的驗案,切合《傷寒論》中“熱入血室”證的論述,效如桴鼓。梁麗麗[24]采取中西醫結合的療法,以麻黃附子細辛湯結合鹽酸氟桂利嗪治療偏頭痛患者,能有效緩解偏頭痛患者癥狀,減輕鹽酸氟桂利嗪所帶來的嗜睡、乏力等副作用,起到增效減毒的作用。
3 外治法
中醫的外治法諸如針灸、藥物外洗、藥枕、耳針、中藥浴足及穴位貼藥等方法,其較傳統中藥湯劑、現代醫學藥物療法有著簡、便、廉、驗的特點。早在先秦時期對于頭痛的治療即以針刺治療為主,《足臂十一脈灸經》即有“頭痛,脊痛......是鉅陽眽主治”的論述,即提出通過針刺太陽經穴位治療頭痛的觀點;《黃帝內經》則擴大了經絡論治頭痛的范圍,進一步明確不同特點頭痛的辨證歸屬,如“膀胱足太陽之脈......是主筋所生病者,痔瘧狂癲疾,頭囟項痛”、“膽足少陽之脈......是主骨所生病者,頭痛頷痛”等,并主張以針刺治療頭痛,系統的提出了針灸治療的原則、禁忌及針刺方法,如“汗出頭痛,身重惡寒,治在風府”、“刺諸痛者......從腰以上者,手太陰陽明皆主之”,“頭痛不可取于腧者,有所擊墮。惡血在于內”,“足陽明有挾鼻入于面者....對入系目本,頭痛引頷取之......損有余,益不足”等等。西晉皇甫謐《針灸甲乙經》則將頭痛病證單獨分章節論述,并詳述取穴,如“厥頭痛,孔最主之”、“頭痛身熱,煩滿,汗不出,曲差主之”、“風眩頭痛,少海主之”等。后諸代醫家逐步豐富,針灸治療頭痛理論日臻完善。中國中醫科學院針灸研究所更是于2010 年和2014 年兩次總匯纂出版了《偏頭痛針灸臨床實踐指南》,為偏頭痛的針灸治療提供了標準化模版和范例。當代我國的中醫學者結合臨床經驗,總結出了一系針灸施治頭痛的經驗,為辨治偏頭痛更提出了諸多著力點,如:陳勤[25]等通過對中外文獻進行分析,得出取穴多以以少陽經穴為主,同時“不受主、配穴分類、不同刺灸法”限制,取穴尤以風池、率谷、合谷為多,認為針灸治療偏頭痛當在分經取穴基礎上,重視特殊穴的應用。鄧國鵬[26]分析應用針灸結合中藥治療偏頭痛患者88 例,治療2 周后聯合針灸治療組療效較單純中藥治療組取得更好療效(93.18%>77.27%),能較少偏頭痛的發病頻率及持續時間,改善癥狀。彭玉琳[27]等通過文獻分析認為治療偏頭痛針灸取穴當以“足少陽膽經”穴位為主,應用表里經配穴法可獲得更好療效,并提出以經筋阻結不通,致“維筋相交”是偏頭痛的病因重要病因,當以隨痛處取經筋治療,取得良好療效。
其他的中醫外治法諸如藥物外洗、藥枕、耳針、藥物浴足等以其操作簡單、療效顯著等特點,極其容易在社會及基層進行廣泛推廣。早在《千金翼方》中即記載了通過吳茱萸濃煎外洗治療頭痛的方法。《太平圣惠方》中提出了吳茱萸葉包成藥枕外用治療頑固頭痛的治療方案。趙玉等研究耳針療法,分析通過腦干等耳穴刺激有助于緩解頭痛;劉小平等[28]通過對文獻進行研究復習,系統總結了穴位貼敷法治療頭痛的常用穴位、劑型選擇、常用中藥等,得出以“太陽穴配合阿是穴為主要臨床應用穴位,藥餅為常用劑型,蔥白、乳香為常用外治中藥等結論并進行了科學分析;畢臻[29]報道以耳針療法外治辨證屬肝陽上亢證的偏頭痛患者35 例,取穴額、顳、枕、交感、神門、皮質下等,與單純西藥組進行對照,以顱內動脈TCD 檢驗所示血流速度為療效評價標準,結論耳針組有效率(91.1%)較單純西藥組(74.3%)療效顯著,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江佳穎[30]通過應用中藥竹罐法(組方:石決明、珍珠母、當歸、川芎、赤芍、牛膝等)治療偏頭痛,日1 次2 周1 療程,發現其臨床療效較常規西藥組(氟桂利嗪)無統計學差異,副作用小,值得推廣。
4 總結
大量臨床經驗證明,中醫辨證論治在治療偏頭痛方面具有特色,其辨證詳具,理論完備,現實中應用往往可以收到良好的臨床療效。單純中藥、針灸治療療效顯著,復發率低,價格低廉為其特色。但目前頭痛的中醫證治仍有許多不足之處,表現為以下幾點:①中醫治療頭痛的方法繁雜,辨證體系龐多,很難為年青醫師掌握,不利于中醫治療方法的傳承。②單方、驗方、個案報道數目眾多,缺乏科學的療效評估和組方研究標準,不易重復證實,制約了其進一步發展。③目前對于復雜病因的頭痛治療仍缺乏廣為眾家共識的辨證方法,病機錯雜的頭痛病的治療規律仍需總結完善。④治療方法大多傳承以經典古方、古法為主,新方新法仍待進一步挖掘。目前關于體質辨證學說和運氣學說與偏頭痛相結合的研究尚為空缺,偏頭痛緩解期的相關治療方案尚待眾人拾階。⑤中醫對偏頭痛的診斷、治療評估標準欠統一標準。進一步發展中醫特色辨證療法,將中藥、針灸、外治方法結合現代醫學進行綜合治療已逐漸成為大趨勢,進一步完善、發揮中醫療法的特色和長處能進一步提高治愈率,減輕病人患痛,取得臨床療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