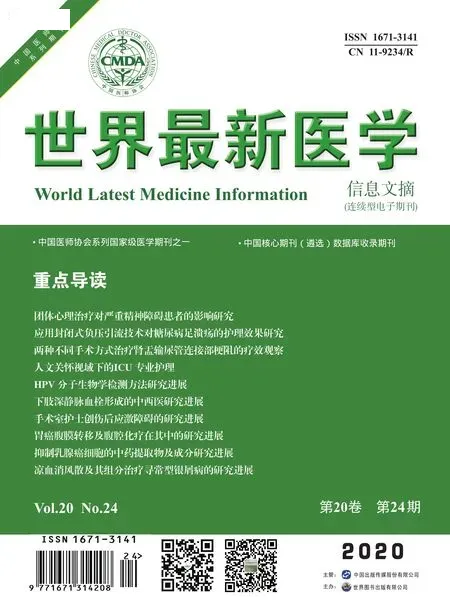旋覆代赭湯配合針灸治療頑固性呃逆的臨床應(yīng)用
慈瑞明
(內(nèi)蒙古赤峰市克什克騰旗蒙醫(yī)中醫(yī)醫(yī)院,內(nèi)蒙古 赤峰)
0 引言
呃逆是指胃氣上逆動(dòng)膈,以氣逆上沖,喉間呃呃連聲,聲短而頻,難以自制為主要表現(xiàn)的病證。古代典籍對(duì)本病的論述如:《靈樞·口問》說:“谷入于胃,胃氣上注于肺。今有故寒氣與新谷氣,俱還入于胃,新故相亂,真邪相攻,氣并相逆,復(fù)出于胃,故為噦。”《三因極一病證方論·呃逆論證》中說:“大率胃實(shí)即噫,胃虛則噦,此由胃中虛,膈上熱故噦”。《景岳全書·呃逆》:“然致呃之由,總由氣逆。氣逆于下,則直沖于上,無氣則無呃,無陽亦無呃,此病呃之源所以必由氣也。”“凡雜證之呃,雖由氣逆,然有兼寒者,有兼熱者,有因食滯而逆者,有因氣滯而逆者,有因中氣虛而逆者,有因陰氣竭而逆者,但察其因而治其氣,自無不愈。若輕易之呃,或偶然之呃,氣順則已,本不必治。惟屢呃為患,及呃之甚者,必其氣有大逆,或脾腎元?dú)獯笥刑澖叨弧H粚?shí)呃不難治,而惟元?dú)鈹〗哒撸俗钗V蛞病!薄蹲C治匯補(bǔ)·呃逆》“治當(dāng)降氣化痰和胃為主,隨其所感而用藥。氣逆者,疏導(dǎo)之;食停者,消化之;痰滯者,涌吐之;熱郁者,清下之;血瘀者,破導(dǎo)之;若汗吐下后,服涼藥過多者,當(dāng)溫補(bǔ);陰火上沖者,當(dāng)平補(bǔ);虛而夾熱者,當(dāng)涼補(bǔ)。”《臨證指南醫(yī)案·呃》“肺氣郁痹及陽虛濁陰上逆,亦能為呃。每以開上焦之痹,及理陽驅(qū)陰,從中調(diào)治為法。”古代文獻(xiàn)對(duì)本病就有著充分的認(rèn)識(shí),各代醫(yī)家都有著不同見解,各別醫(yī)家給出了該疾病的病因病機(jī),有的給出了治療方法,均有不同效果,本篇以仲景《傷寒論》中旋覆代赭湯為主,配合針灸的效果反饋。
本病發(fā)病在膈,與脾胃肺肝腎等臟腑病變相關(guān),基本病機(jī)為胃氣失降,上逆動(dòng)膈。治療以理氣和胃,降逆平呃為原則。根據(jù)各患者情況,辯證論治,標(biāo)本兼治。筆者根據(jù)近期工作接觸2 例頑固性呃逆患者,患者經(jīng)多方治療,見效甚微。余根據(jù)《傷寒論》中旋覆代赭湯加減,配合針灸,效果顯著。遂記如下。
1 病例
1.1 案1
患者王某,男性,年齡60 歲。患者于2018 年10 月,因腹脹、呃逆頻發(fā)4 月余入院,夜間為甚,長時(shí)間夜晚不能入睡。癥狀一直伴隨4 月余左右。病史:腦出血病史1 年。患者入院后給予西藥654-2 肌注,未緩解。根據(jù)患者癥狀,查舌脈為,舌淡苔黃膩,脈滑數(shù)。給予中藥及配合針灸治療。
中藥方劑以旋覆代赭湯加減:旋復(fù)花30g 代赭石30g 姜半夏20g 黨參20g 炙甘草20g 黃芩10g 黃連10g 貝母10g 海螵蛸20g雞內(nèi)金15g 陳皮20g 烏梅20g 牡丹皮15g 沙參15g 麥冬15g 五味子15g 茯苓20g 薏苡仁30g。日一劑,水煎服,早晚分服。配合針灸,針灸選取,舌針刺金津、玉液及舌下脈絡(luò);攢竹、中脘、建里、下脘、天樞、內(nèi)關(guān)、足三里、三陰交、太沖、太溪等穴位。
患者口服中藥加針灸治療二天后,癥狀明顯緩解,一周后癥狀消失,繼續(xù)治療一周后,癥狀完全消失,患者出院。一月后隨訪,未再發(fā)。
1.2 案2
患者張XX,男性,年齡50 歲。患者2 年前患腦出血后,病愈后,出現(xiàn)呃逆,前期時(shí)發(fā)時(shí)止,口服西藥鹽酸山莨菪堿片,可緩解。患者2019 年3 月,就診于我院,呃逆頻發(fā),不能自止。患者痛苦不堪,夜間不能入睡,給予西藥654-2 注射用肌注,可緩解一時(shí)。根據(jù)患者癥狀,舌脈情況。以及根據(jù)《傷寒論》“……氣上沖咽喉……。噫氣不除者……,旋覆代赭湯主之。”選用旋覆代赭湯加減,旋覆花30g 代赭石30g 姜半夏20g 黨參20g 甘草20g 黃芩15g 黃連15g 貝母15g 雞內(nèi)金15g 青皮20g 烏梅20g 牡丹皮15g 沙參15g麥冬15g 五味子15g 茯苓20g 山藥15g 百合20g 地黃20g 木香15g 砂仁10g 香附15g 厚樸15g 枳殼15g。以此方日一劑,水煎服,早晚分服。配合針灸,針灸選取,舌針刺金津、玉液及舌下脈絡(luò);膻中、中脘、建里、下脘、天樞、內(nèi)關(guān)、足三里、太沖、太溪等穴位。
患者口服中藥加針灸治療三天后,癥狀明顯緩解,一周后癥狀消失,時(shí)有一兩聲,繼續(xù)治療一周后,癥狀完全消失,患者出院。一月后隨訪,未再發(fā)。
2 臨床體悟
旋覆代赭湯出自《傷寒論》中方。其功效為降逆化痰,益氣和胃。主治胃虛痰阻氣逆證。本證系胃氣虛弱,痰濁內(nèi)阻所致。原“傷寒發(fā)汗,若吐若下,解后,心下痞硬,噫氣不除。”傷寒發(fā)汗后,又誤用吐、下之法,胃氣受傷,升降運(yùn)化失常,則津液不得傳輸而為痰,痰濁阻于中焦,氣機(jī)不暢,而心下痞硬。脾胃虛弱,痰氣交阻,則胃氣上逆,而致噫氣頻發(fā),或呃逆、惡心等。根據(jù)證治機(jī)理,方中重用旋復(fù)花為君藥,苦辛咸溫,其性主降,功擅下氣消痰,降逆止噫。代赭石重墜降逆,與君藥相伍,降逆下氣化痰,為臣藥。半夏祛痰散結(jié),降逆和胃;生姜和胃降逆,宣散水氣以助化痰;人參、大棗、炙甘草甘溫益氣,健脾養(yǎng)胃,以治中虛之本,俱為佐藥。炙甘草調(diào)和藥性,兼作使藥。諸藥相合,標(biāo)本兼治,共奏降逆化痰、益氣和胃之功,使逆氣得降,痰濁得消,中虛得復(fù)。
余根據(jù)此方加減運(yùn)用,得出案1、案2 中兩方。案1、案2 中患者均為腦血管病后,出現(xiàn)呃逆癥狀。腦血管病后,患者久病臥床后,出現(xiàn)胃氣虛弱,胃失和降,脾胃運(yùn)化功能失常,腸道津液暗耗,燥結(jié)難下,導(dǎo)致中下二焦郁阻不通,飲食難下,堆積于腸腑之中,周而復(fù)始,惡性循環(huán),上逆致呃。根據(jù)脾胃虛弱,運(yùn)化失常情況,余選用健脾和胃,開胸順氣藥物,如:雞內(nèi)金、陳皮、茯苓、薏苡仁、木香、砂仁、香附、厚樸、枳殼、山藥等藥物。根據(jù)腸道津液不足情況,余選用生地、沙參、麥冬、貝母等滋陰增液。根據(jù)腸腑不通,郁而化熱情況,選用黃芩、黃連等藥物瀉火解毒。
針灸方面以疏肝理氣,調(diào)和脾胃,降逆止呃為法。根據(jù)十二經(jīng)脈相為表里。根據(jù)《靈樞·經(jīng)脈》:“……其支者:從大迎前,下人迎,循喉嚨,入缺盆,下膈,屬胃,絡(luò)脾。”“……交出厥陰之前,上膝股內(nèi)前離岸,入腹,屬脾,絡(luò)胃,上膈,夾咽,連舌本,散舌下。”選用舌下針刺的方法,針刺時(shí),囑其患者憋氣,拔針呼氣,每次治療,針刺金津、玉液及舌下脈絡(luò)3-6 次。其余選用疏肝健脾,下氣通腑穴位,如:膻中、中脘、建里、下脘、天樞、內(nèi)關(guān)、足三里、太沖、太溪等。針刺1-2 寸,留針30 分。
呃逆在當(dāng)前臨床上是一種常見疾病,該疾病是由于人體膈肌產(chǎn)生不自主收縮導(dǎo)致的,對(duì)患者的影響較大,有些患者可自行緩解,但受到情緒、寒冷刺激等可再次發(fā)生,周而復(fù)始。有的患者則隨著病情不斷加重,甚至影響脾胃肺及腸道功能,長此以往更加大了患者心理的負(fù)擔(dān),導(dǎo)致如情緒焦慮、不能平臥、夜間不能入睡等,運(yùn)用西藥進(jìn)行治療,療效并不顯著,甚至容易給患者造成不良反應(yīng)。余運(yùn)用中藥配合針灸,不僅給提升了患者治療效果,而且縮短了治療療程,提高了患者的治療信心,減少了不良反應(yīng)情況。
余運(yùn)用此方治療頑固性呃逆10 余人,均有療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