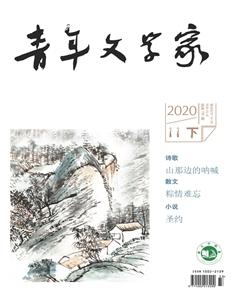中國傳統小說模式重塑與其意識形態探究
基金項目:主客體傳承關系中的華裔文化重構——以湯亭亭系列小說為中心;項目級別:校級;項目編號:XSYK18038。
摘? 要:本文將從小說形式本身出發,對湯亭亭小說《女武士》中出現的各種中國傳統小說模式進行整理,并在此基礎上與作者(移民視角)對它們的重新塑造進行對比分析,探尋美國二代華裔移民內心的深層復雜意識形態投射。
關鍵詞:《女武士》;中國傳統小說模式;意識形態投射
作者簡介:王帆,講師,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碩士。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20)-33--01
1、前言
自美國華裔女作家湯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的小說《女武士》(The Woman Warrior)1976年問世以來,就引起了美國、中國各社會學術領域的關注,美國研究、人類學、民族學、女性研究、后現代、后殖民主義時代等研究視角的不斷涌現,探索小說所表達的政治、歷史、種族、文化等含義。與之前側重理論的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將從小說形式本身出發,對其中出現的各種中國傳統小說模式進行整理,并在此基礎上與作者(移民視角)對它們的重新塑造進行對比分析,探尋美國二代華裔移民內心的深層復雜意識投設。
2、無名女人與女鬼故事
女鬼故事最早出現在晉朝的《搜神記》,唐宋傳奇中多出現在愛情故事里,而在明清小說中成為典型鬼怪形象。此類故事是伴隨著男權社會對女性的壓迫加深而出現的,成為男性潛意識里的恐懼形象,其敘述方式的關鍵辨識特點大多集中在四點上:死亡、男性性侵害、復仇愿望及無理智的殘忍行為。從表面上比較小說中的死亡動機和形式,我們很容易得出無名女人與典型女鬼故事十分相似的結論,都源于女性的不貞潔,結局多為投井自殺,然而在具體情節上卻大相徑庭。
首先,傳統女鬼形象與無名女人表現出對于“貞潔”的追求與反抗之間的對立。傳統故事中,女性多受節烈觀的影響,為維護貞潔、名節,以死亡的形式將受到男性侵害的事實公開化,在道德上懲戒惡人,同時也為男權道德立牌坊。無名女人—即“我”的姑姑的死亡卻表達出作者對于節烈觀的強烈反抗。姑姑被強奸后懷孕后,強奸者便糾集一幫人,抄了她的家。她對于愛的向往,美的熱愛也被歪曲了通奸的證據,于是,“她抱起嬰兒,朝井邊走去。(湯亭亭)”直至死亡,姑姑也沒有說出“情夫”的名字。她的自盡代表了美好、善良的女性情感所遭受的摧殘,選擇與自己的女兒一同赴死正是她對所處世界殘酷性的控訴和對孩子的愛與保護。這死亡沒有牌坊作為獎勵,只有母親悄悄的話語,“別告訴任何人你有個姑姑。你爸不想聽到她的名字。她從來沒有出生過。(湯亭亭)”
其次,傳統女鬼故事大多以正反兩方的恨意消解、情感圓滿作為終局,而姑姑在死后卻被進一步抹去了其存在,怨恨無法消散。而男性在集體參與這場壓迫和懲罰后,出于潛意識里的對于報復的恐懼,刻意選擇了繼續打壓和遺忘;而姑姑則魂附“我”身,將這份來自女性的對于男性中心的集體共謀文化的恨意繼續傳遞下去。
可以看出,傳統故事的意識形態出自男性對于女性的道德約束與評價,在此之下的女性真實面貌是模糊的,其行為也是傀儡式的。湯亭亭賦予了無名女人內心的無奈與愛美之心,給了她選擇赴死的自我意識,在敘述中使其成為人本身。
3、白虎與武俠小說
武俠小說是我國通俗小說中一種比較成熟的類型樣式,從唐傳奇、宋話本一路發展下來,到清、明時期進入高潮階段,其中著名的作家有金庸、梁羽生、古龍等。其故事敘述模式特點為:男性俠客的神化;遭遇偶然性改變命運(跌落懸崖等)的機遇及復古的教條主義(爭奪古人秘籍等)。
從表面上看,作者在白虎的夢境中也遵循相似的發展套路:替父從軍的木蘭奇遇深山的老翁老嫗,學習武功、兵法,牢記國恨家仇,率領軍隊上戰場復仇的故事。但木蘭并不是被簡單男性化的強健女性勇士,故事中對于初潮的對話描寫坦蕩直白:
老嫗對我解釋道:“你已經成年,可以生兒育女了。”接著她又說,“可是,我們希望這幾年你先不要生。”
“那能不能用你教我的抑控之術止住流血呢?”
她說:“不可。”人總不能不拉屎撒尿吧,經血也是同理。隨它流吧。(湯亭亭)
而對于戰場上的懷孕生子,與傳統的被保護的孕期和不能見光的生產過程完全不同,孕中“我穿著改大的盔甲,看上去像一個孔武有力的粗壯大漢”(湯亭亭)。分娩后,“我”將臍帶晾在旗桿上,“那段臍帶隨著旗幟在風中獵獵招展。(湯亭亭)”沒有任何被保護的脆弱,也沒有不能見血光的羞恥。此外,故事中的“背后刻字”與傳統上男性以傷痕為英勇,女性以暴露身體,傷痕為恥的文化心理也完全相反,木蘭、岳飛和“我”已融合為一,改寫了傳統女性氣質,將女性本身與強健、無畏、冒險精神結合起來。
然而,木蘭故事的重塑從表面上看是令女性振奮的,是英雄的被看見,但這場虛構的女勇士的浪漫華麗復仇故事本身的血腥正是來自于對于自身所處地不被看見的“鬼”身份的傳統文化處境意識的悲切吶喊。
4、巫醫與鬼故事(試膽)
試膽故事是傳統鬼故事中最具有特色,也是常被講述、改編為電影、電視的類型之一,說的是在鬧鬼的荒村、破廟,或廢棄建筑中,人主動與鬼進行正面遭遇和較量。《女勇士》中的母親便是生活在形形色色的鬼之間的勇士。
在醫學院時,母親遭遇的是壓身鬼,即民間俗稱的“鬼壓床”。母親的較量方式與傳統鬼故事里人以反抗、掙扎、尖叫、念佛經等畏懼逃離壓身控制不同,母親與鬼叫陣“你贏不了,你這石頭蛋”、“我不會讓步,不論你怎么折磨我,我都受得了。你以為我怕你,那你可想錯了。對我來說,你沒什么神秘的……”(湯亭亭)她背誦醫學課要學的功課,以自身的力量對抗鬼,果敢勇猛。在美國生活時,到處都是報童鬼、的士鬼、巴士鬼、警察鬼、滅火鬼、查表鬼、剪樹鬼、雜貨店鬼、送信鬼、垃圾鬼、社會工作鬼、護士鬼、牧師鬼、偷盜鬼、流浪鬼、黑鬼、白鬼、吉普賽鬼……母親時時與鬼生活、與鬼較量,養大了6個兒女,辛勞老去。
如果說醫學院遇鬼的故事還在傳統鬼故事的框架內,那么,在后一個故事中,“鬼”的概念得到置換和拓展,具有了超現實的意味。母親以中國家族文化概念為中心,在意識里將美國變為超現實的鬼世界。通過這個自我創造出的外在“鬼”空間,她使自己處于“人”的意識掌控空間的中心,邊緣化“美國主流文化”,在對抗的緊張性中保持個人身份的完整性與在異國生活下去的心理穩定性。而華裔女性所遭遇的與西方主流社會文化的隔絕也通過人鬼殊途的差異性展現出來,母親的奮斗史正是無數女戰士與“鬼”的半生對抗。
5、西宮外、胡笳怨曲與胡笳十八拍
胡笳十八拍是古代敘事琴歌,敘唱的是蔡文姬坎坷身世,思鄉幽情,別子隱痛,以及回歸故國所見所思的情與景。西宮外中久居香港的月蘭——母親的妹妹,去與美國的丈夫和女兒團聚,但丈夫與女兒都已經變成了美國鬼,思念之情猶在,而重逢已是面目全非。月蘭變瘋,而“我”成了厭惡自己的四不像,講著柔弱的美語和公鴨嗓的漢語,掙扎在“半人半鬼”的文化拉鋸戰之間。蔡文姬與她的匈奴孩子之間,故鄉的人們、上一代的英蘭們、月蘭們和第二代移民的我們之間都已變不同,唯有在琴聲中可以追思已不復存在的故鄉。
胡笳十八拍與之前的故事不同,更多觸動的是華裔在代際之間不斷改變、隔離之中的共同性,雖然華裔移民歷史與蔡文姬在故事模式上多有不同,但在情感上卻有相似的皈依。
6、結語
《女勇士》的各個故事中都不同程度、層次的引入了中國傳統故事,并以“我”的視角在現實與想象之間對其進行了重塑和改寫,在意識形態上烙上了對于傳統、外來文化的傷痕記憶與英雄主義想象,與其抗衡并最終以一曲凄切動人的歌聲與其共生共存下去。
參考文獻:
[1]湯亭亭,《女勇士》[M].新星出版社,2018年4月。
[2]何麗野:關于武俠小說的敘事模式[J].社會科學報 2001(1):1-2。
[3]胡穎峰:敘事的琴歌與琴歌的敘事[J].江西社會科學2009(3):37-43。
[4]劉木丹:《女勇士》的英雄觀探析[J].常州工學院學報2019(8):33-37。
[5]孫東苗:刻板形象的解構與英雄形象的重構[J].中共鄭州市黨委學報2006(4):130-32。
[6]王錚:母親的“鬼故事”[J].長春教育學院學報2014(17):48-49。
[7]衛景宜:改寫中國故事:文化想象空間[J].國外文學2003(2):1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