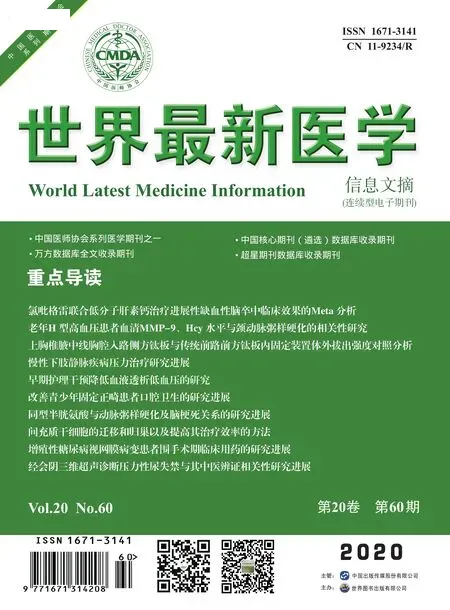缺血性卒中合并腦微出血的抗栓治療研究進展
王萌,郭愛紅,杜培培,加艷,賀慧芬,閆歡,王丙聚*
(1.延安大學咸陽醫院神經內科,陜西 咸陽;2.延安大學醫學院,陜西 延安)
0 引言
腦 微 出 血(cerebral microbleeds,CMBs) 是 腦 小 血 管病變的影像學標志之一,隨著影像技術的發展,CMBs 相關研究越來越多。近期關于合并CMBs 的急性缺血性卒中(acuteischemicstroke,AIS)患者抗栓治療的安全性受到了廣泛關注,抗栓治療在是否增加出血轉化風險和是否獲益大于風險方面存在很大爭議。本文就CMBs 的定義及流行病學特征、發生機制及抗栓治療的進展進行綜述,以期為臨床醫生全面評估抗栓治療獲益及風險、并制定合理的治療方案提供指導意見。
1 CMBs 的定義及在流行病學特征
CMBs 主要是腦內微小血管滲漏或破裂所致的含鐵血黃素和鐵蛋白沉積在血管周圍,表現為微小出血的一種腦實質亞臨床損害,臨床上一般無明顯的癥狀。CMBs 通常最先由影像學檢查發現,典型表現是T2*-GRE 或SWI 上直徑為2~10mm 的圓形或卵圓形的低信號病變,邊界清晰,周圍無水腫[1]。2008 年在健康人群中篩查CMBs 的發生率為11.1%,2015 年再次篩查時增至18.7%[2]。鹿特丹掃描研究發現CMBs 總體患病率較高,且隨年齡增長而增加,60~69 歲患病率為17.8%,80 歲以上時增至38.3%[3]。CMBs 在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中的發病率為22.9%~43.6%,在腦出血患者中的發病率為51.8%~82.5%,在混合性腦卒中患者中發病率為41.2%~70.2%[4]。不同種族間CMBs 的發生率也有差異,亞洲人群中的發生率約為4.6%,而其他種族人群中約為5.3%[5]。
2 CMBs 的發病機制
CMBs 的發病機制尚不清楚,目前大多認為可能是繼發于長期存在的高血壓或組織中淀粉樣蛋白沉積對血管壁的損傷[6]。高血壓主要引起腦小動脈硬化,透明物質沉積,纖維素樣壞死,微血管血液外滲,局部微小血管形成動脈瘤破裂,從而引起CMBs 形成[7]。高血壓患者中CMBs 的發生率相對較高,多累及大腦深部穿支動脈,病灶多位于深部或幕下區,與白質高信號、血脂異常、吸煙、抗血小板藥和高HCY 等引起腦血管疾病的危險因素關系密切[8]。Igase 等人報道CMBs與收縮壓呈正相關[9],Lyu 等人則認為舒張壓和收縮壓均為CMBs 的獨立危險因素[10]。腦淀粉樣血管病(cerebral amyloid angiopathy,CAA)是指由于血管壁的中膜和外膜發生淀粉樣蛋白沉積,從而導致局部小血管壞死和破裂出血[7],研究發現總是在Aβ 蛋白沉積區域最先出現CMBs 病灶[11],也有研究認為腦淀粉樣血管病是僅局限于腦葉出血的危險因素[12],Rannikm 等人的研究表明ApoEε4 等位基因是腦淀粉樣變性的危險因素[13]。Koo 等人研究發現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綜合征(OSAHS)可能會引起CMBs 的發生[14],此外炎性反應可能也是CMBs 形成的重要影響機制,研究發現在深部和大葉部位CMBs 與hsCRP,IL-6 和IL-18 增高相關[15],血腦屏障被破壞、內皮功能障礙、遺傳因素等均可能參與病變[16]。CMBs的發病機制復雜多樣,目前研究多認為高血壓及腦淀粉樣血管病是腦微出血的主要發病機制,其它因素可能也起到了重要的影響,需要進一步的深入研究。
3 CMBs 對抗栓治療的影響
對于AIS 患者進行抗栓治療可能引起出血,但放棄治療又有缺血性卒中復發的風險。對CMBs 患者使用抗栓治療是一個棘手但又不得不面對的臨床難題,因此評估治療的獲益與風險具有重要的臨床指導意義。
3.1 CMBs 對靜脈溶栓的影響
急性缺血性卒中發生在4.5 小時內且無靜脈溶栓禁忌癥時首選溶栓治療,但可能出現嚴重的并發癥--顱內出血,評估靜脈溶栓的獲益與風險對于制定方案及判斷病人預后至關重要。一項前瞻性隊列研究發現,CMBs 的存在(特別是高負荷和腦葉位置)是3 個月不良預后的獨立預測因子,并可能增加卒中再通后的腦出血風險[17]。Soo 等的研究納入了908 例中國AIS 患者,得出結論,腦出血的發生率和死亡率隨CMBs 數量的增加而增加,在CMBs ≥5 個的患者中,腦出血的發生和死亡風險似乎超過了溶栓治療的益處[18]。然而,也有研究發現當存在超過10 個CMBs 時,靜脈溶栓后腦出血的風險增加[19]。Wilson 等進行的一項隊列研究匯總分析表明,近期發生缺血性卒中或TIA 的患者,不論CMBs 的數量、分布以及所接受的抗栓治療的類型如何,腦微出血與隨后發生腦出血的相對風險比缺血性卒中更大,后續發生缺血性卒中的絕對風險均顯著高于顱內出血[20]。但是也有研究認為CMBs并不增加靜脈溶栓后的出血轉化風險[21,22],還有一些研究者認為接受靜脈溶栓治療的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腦出血的風險增加,但其臨床意義尚未確定,將CMBs 的存在作為靜脈溶栓的禁忌癥還不夠令人信服[23,24]。2019 年AHA/ASA 急性缺血性卒中早期管理指南指出:對于≤10 個CMBs 的患者靜脈溶栓是合理的;而>10 個CMBs 患者靜脈溶栓治療獲益無法確定[25]。
綜上所述,CMBs 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靜脈溶栓病人的出血轉化風險及其預后,但對于有靜脈溶栓治療適應證的AIS 患者不能因為存在CMBs 就放棄溶栓治療。CMBs 病灶越多時其出血轉化的風險可能性越高,多個研究發現>10 個CMBs 的患者溶栓風險增加,但其獲益與風險仍需要更多的研究來明確。
3.2 CMBs 對抗血小板治療的影響
抗血小板藥物廣泛應用于臨床,對心腦血管疾病預防及治療意義重大,腦出血是其最嚴重的并發癥,一旦發生就可能危及生命。多項研究表明在使用抗血小板藥物的AIS 患者中CMBs 的存在可能會顯著增加隨后發生腦出血的風險[26,27]。Qiu 等人的研究分析發現,接受抗血小板治療的患者中合并CMBs 時較無CMBs 者腦出血發生率明顯增高,而且單純腦葉CMBs 發生腦出血的風險高于非腦葉CMBs[28]。一項來自內蒙古醫科大學附屬醫院的研究發現,服用阿司匹林、氯吡格雷均會增加CMBs 和腦出血風險,且這兩種藥物引起的風險無明顯差異,長期接受(>5 年)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治療的患者發生CMBs 的風險高于短期治療者[29]。Wang 等人的研究顯示,與單獨使用阿司匹林相比,雙抗治療并未導致CMBs 數量的增加[30]。也有研究表明CMBs 的存在只與阿司匹林有關,與氯吡格雷、西洛他唑和噻氯匹定無關[31]。并不是所有的研究都觀察到存在CMBS 的患者使用抗血小板藥物出血風險增加,Imaizumi 等人的研究認為抗血小板藥物的使用對CMBs患者腦出血的發生無顯著影響[32]。
目前指南未對合并CMBs 的缺血性腦卒中患者抗血小板治療提供明確的指導意見,當腦微出血患者需要使用抗血小板藥物治療時,必須綜合評估其出血風險,謹慎但不是禁忌性使用抗血小板藥物。同時,與其他血小板藥物相比,阿司匹林是否與CMBs 的高風險有關,值得進一步臨床研究來確定。
3.3 CMBs 對抗凝治療的影響
合并房顫的缺血性卒中患者CMBs 的發生率約為30%[33]。目前抗凝藥物是心源性腦卒中防治的關鍵治療方法,出血是其嚴重的不良后果,因此深入了解CMBs 與抗凝治療關系對臨床醫生制定診療方案具有重要意義。Cromis-2是一項針對伴有房顫的缺血性腦卒中或TIA 患者進行抗凝治療的研究,結果表明CMBs 與顱內出血風險獨立相關[34]。Charidimou 等人的研究認為使用香豆素類抗凝藥物的病人CMBs 發生率更高,并且多出現于幕下及深部腦組織[35]。Cheng 等人研究發現華法林增加患者新發CMBs 的風險,且與嚴格的腦葉CMBs 相關性更高[36]。香港大學研究認為≥5 個微量出血與既往抗血小板和抗凝治療獨立相關,而混合部位微量出血與高血壓和既往抗凝治療獨立相關,但CMBs 的負荷和部位都不能預測缺血性卒中復發風險[37]。來自首都醫科大學北京天壇醫院神經內科的回顧性研究,得出結論,CMBs合并非瓣膜性房顫所致心源性腦栓塞的抗栓治療不會增加腦出血事件和死亡的風險[38],Wang 等的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結論,此外他們還發現接受口服抗凝劑治療的患者比未接受的患者存活率更高[39]。新型口服抗凝藥比加群酯、利伐沙班、阿哌沙班和依度沙班等在臨床上的應用逐漸增多,多項研究顯示新型口服抗凝藥并不增加新發CMBs 風險[40,41]。
目前關于CMBs 與華法林治療后腦出血的發生率爭議較大,考慮到房顫的高危害,建議行抗凝治療,但CMBs ≥5 個時使用華法林可能增加出血風險,需謹慎評估其風險與獲益,當使用華法林的出血風險過高時可以考慮新型抗凝藥。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目前研究表明新型口服抗凝藥物并不增加新發CMBs 風險,但所納入的樣本量均較小,結論仍需要大樣本及更長時間的研究觀察以進一步證實。同時,CMBs 的負荷及部位與抗凝治療之間的關系并不清楚,需要進一步研究探討。
4 總結與展望
綜上所述,CMBs 抗栓治療后出血轉化的風險可能會增加,尤其是CMBs ≥10 個時,但多數情況下還不足以作為改變抗栓治療方案的依據,也有研究指出CMBs 并不增加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抗栓治療后的出血轉化風險,因此仍然是一個有待探索的問題。期待接下來有更多的研究去探索腦微出血發病機制,明確血壓、淀粉樣變、血腦屏障破壞、炎癥因子、遺傳等與CMBs 的關系,根據發病機制尋找有效的預防及治療手段。同時仍需進行大規模、多中心、長時間的研究以進一步明確CMBs 及其部位與負荷與卒中抗栓治療的關系,從而對卒中防治提供更可靠的決策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