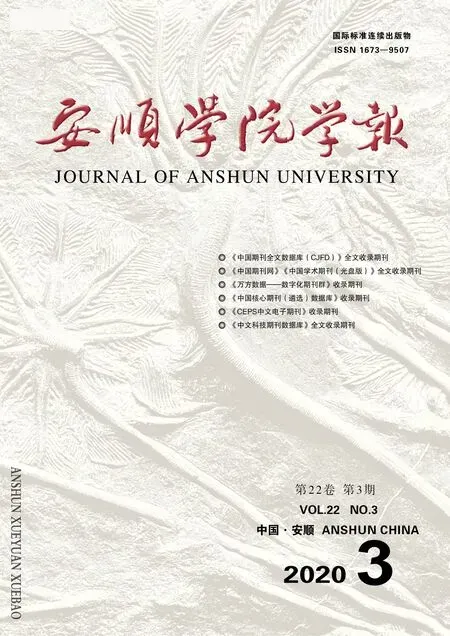論大花苗服飾的文化記憶及象征表達
(1.貴州大學歷史與民族文化學院,貴州 貴陽550025;安順學院政法學院,貴州 安順561000)(2.貴州大學歷史與民族文化學院,貴州 貴陽550025)
在符號學領域,繼索緒爾提出“能指”和“所指”二元結構模式之后,皮爾士開創了三元指號(sign)的結構分類圖式,其影響深遠。皮爾士把指號分為三組,即征象(sign)、對象(object)、釋義(interpretant),每一組下面又分三類,即“征象”分為質感符(Qualisign)、實在符(Sinsign)、常規符(Legisign),“對象”分為象似符(Icon)、標指符(Index)、象征符(Symbol),“釋義”分為特征符(Rheme)、命題符(Dicentsign)、思辨符(Argument)[1]。納日碧力戈教授采用九宮圖的方式進行列舉,這正好切合皮爾士將單一分類符所進行的組合,形成有區別意義的指號系統 。其中,將指號對象分為象似、標指和象征三類對物體符號意義的分析極為有用:(1)象似:指號與對象間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如照片與本人、地圖與地理區位之間的關系;(2)標指:指號與對象間彼此相關聯,有某種邏輯關系,如風帆與風、煙與火、子彈孔與子彈等之間的關系;(3)象征:與前兩種指號類別不同,象征指號與對象間關系是任意的、約定俗成的,沒有必然的聯系,如語言符號指代某事物等。經后來的闡發,皮爾士的指號理論超越了語言符號范圍并廣泛使用于非語言領域。基于其有效性,艾克在評價皮爾士指號理論時指出:“肖似記號(象似符,引者注)概念包含著大量建立在準確慣約法則和運作上的生產運作,其分類法和分析研究是未來一門發達的記號理論的任務”[2]。
一、 大花苗及其服飾
古時對苗族的分類通常按服飾或頭飾特點,如《百苗圖》中分為紅苗、黑苗、花苗等,這樣的分類依據沿用至今。今人何宴文根據服飾特點還可將苗族服飾分為“湘西型”“黔東型”“川黔滇型”“黔中南型”“海南型”等類型[3]。大花苗屬于川黔滇型、西部方言區,研究大花苗的學者習慣稱其為滇東北次方言苗族以區別于其他苗族支系。大花苗主要分布于滇東北、黔西北及川西南、川南等三省交界的廣大地區,小部分散居于南方各地,按照苗族學者苗青的觀點,大花苗遷徙至川黔滇交界地并以之為“托天之頂”而生存下來,其原因一是受到水西彝族的庇護,二是源于黔西北地處高寒,環境惡劣,易于逃避外界的侵犯。苗青認為,大花苗遷徙到今威寧一帶有兩條主要的遷徙路線,第一條路線,由北而南而西——而西北而西南的大遷徙。第二條路線,由北而中而西——而西北而西南的大遷徙[4]。兩條遷徙路線都起始于北方大平原,最終匯聚到黔西北威寧、赫章一帶,在人跡罕至、環境惡劣的高海拔崇山峻嶺中安頓下來,形成今天大花苗支系的族群基礎。
王文憲認為“大花苗是當年在中原涿鹿戰爭中跟隨蚩尤奮力殺敵的先鋒部隊,因為這支部隊勇猛,歷來受漢族、彝族等民族的排擠和殺害,才使大花苗在各種苗族支系中最悲慘。”①此觀點在大花苗傳唱的古歌中得到印證,如西部苗族古歌中敘述了大量的遷徙路線、戰爭場面、英雄人物等,其演唱時常常催人淚下。大花苗至今在婚喪嫁娶等場合中有遷徙舞的表演,而其與古歌演唱相契合慣使場面一度傷感。古歌、舞蹈與服飾互為表里的立體性表述,故使大花苗服飾在苗族遷徙文化的符號象征上可謂獨樹一幟。
大花苗族今天的居住環境,多為海拔較高的高山箐林,具有氣候寒冷、溫差較大、土地貧瘠、干燥少雨等特點。耕種與畜牧為他們的主要生計方式,基于山間環境適宜種植麻的特點,因此麻和羊毛成為大花苗服飾制作的主要材料。大花苗服飾形制簡單、色彩單一、圖案粗獷。首先,大花苗服飾主要由披肩、背牌、百褶裙三部分組成。其中背牌下方飾有垂蕤,垂蕤古時以布結作飾,如今改為串珠,垂蕤底端系有銅鈴,走路時可晃啷作響。據說大花苗服飾古時還有綁腿,后來棄而不用。男女服飾具有相同的披肩和背牌,唯一區別在于男服沒有百褶裙,因此有了男披肩內褂比女披肩內褂長而至腳踝。其次,大花苗服飾色彩單一,以紅白二色為主,外加少許青色。再次,大花苗服飾圖案幾乎為幾何紋樣,如菱形、鋸齒形、曲線等,圖案形大且簡單,大花苗因此得名。披肩及背牌的紋案采用挑花的制作方式,百褶裙則使用蠟染印制。披肩和背牌由麻線和羊毛線鑲嵌編織,而披肩下的白褂則全由麻線結構。其服飾分為兩種,一種是帶披肩的服飾,苗語稱“卓魯”,漢意譯為“換衣”。也有人把“卓魯”釋為“花衣”。一般在婚娶、節慶等場合穿戴;另一種是沒有披肩,完全由白褂構成的服飾,苗語稱“卓撮”,漢意譯為“笑衣”(一作“孝衣”解),主要在喪葬儀式中穿戴。大花苗服飾圖案的歷史遷徙象征意味,在服飾制作過程中極為嚴苛和穩固,加之服飾暗含有一定的祖先崇拜信念于其中,因而其形制規則不易變化,這對于一個無文字民族的文化記憶與傳承起到莫大作用,并被學界稱為“背在背上的歷史書”。
二、 大花苗服飾象征的表層結構
大花苗服飾是一套完整的符號體系,通過這套象征符號實現一定的文化標指,從而建構民族的精神內涵。與其他苗族支系服飾不同,大花苗服飾采用刻板的幾何紋樣,圖形簡單,經上千年歷史洗禮其形制較少變化。大花苗服飾具有鮮明的象征與記憶等特征,其圖形雖少了幾分靈動,然則卻多了幾許厚重。大花苗服飾象征的表層結構如下:
披肩紋飾表征“天地”“山川”“田園”。在大花苗族服飾的披肩上,以紅黑二色交錯、白色為底色,采用對稱的幾何紋飾,即邊上繡有鋸齒紋、波浪紋、螺絲紋,中間飾以菱形紋,菱形紋內又織斜方格紋等,其間留有大量空白。含義為每方圖案的上方代表“天”,下方代表“地”,左右代表“山川”,中間代表“田園”。
背牌紋飾表征“城池”。大花苗服飾中有一塊起裝飾作用的背牌,苗語稱為“勞搓”,形狀呈橫長方形,其圖案工藝以刺繡為主,兼用蠟染、挑花、編織,紋飾有菱形紋、鋸齒紋、凸字紋、云雷紋等。其具有“城池”的象征意義,是苗族祖先遷徙中被迫離棄的中原故地,背牌圖案線條的繁復刻畫了曾經的城池繁華。另說背牌還象征戰爭中的旗幟,在背牌下方墜有垂蕤,垂蕤跟旗須類同,而垂蕤底端的銅鈴,走動時發出“咣啷”聲,象征戰場上金戈鐵馬的廝殺聲響。
百褶裙紋飾表征“江河”。象征“江河”的圖形紋繡在百褶裙上,從裙邊及腰有數條約2厘米寬的蠟染幾何紋,在幾何紋飾間有大面積的白地,白地上下有2組回環繩辮紋和4組紅黑二色布條的平行線段,線段分為兩段的和三段的兩種類型。中部三段紅黑相間,疊壓平行的布條從上至下依次象征黃河(渾水河,苗語稱為“滌望滌垛”)、平原、長江(清水河,苗語稱為“篤納伊莫”)。白地象征著寧靜的天空。誠如苗族古歌所唱:
我們走一步望一步/望著江普這寬廣的地方/平整整的土地一丘連一丘/多可惜的地方啊/一定要留下個紀念/照田地的樣子做條裙子穿/把江普的瓦房繡在衣裳上/我可愛的家鄉江普呀/繡上花衣裙永遠叫子孫懷念[5]
大花苗服飾圖案自上而下的空間布局象征著苗族先祖遷徙路線的時空邏輯,即由中原一帶繁華的“城池”經高山、平原,跨過黃河、長江等河流,進入荒無人煙的高山箐林,最后落腳云貴高原的廣大地區。可見,與其說大花苗服飾是些形制簡單的象征圖案,不如說是一副崇高的故園遷徙圖。它通過歷史敘述的方式記憶富庶的祖籍故地,暗含苗族人回望故土的文化心理。
三、 大花苗服飾象征的深層結構
(一)大花苗服飾是一種歷史書寫
“歷史在兩個面之間搖擺。一方面,它是一種實踐,是一種現實;而另一方面,它則是一個封閉的敘述,一種由精神模式所組織并完結的文本。”[6]大花苗族的服飾超越了服飾的基本功能,儼然成為記錄苗族歷史的符號文本,與塞爾托所述相符,它既敘述歷史也觀照現實。從現實的面向看,作為苗族文化的母題無論“遷徙”或是“東方故里”,在苗族整個文化結構中演化而世代相傳,苗族人對傳說故土的眷念并非真的有朝一日要卷土故里,實際上是通過這些虛化的文化事實在歷代苗族人苦難的現實遭遇中樹立生存的信念,形如宗教想象著追溯天國的美好以增強對現實種種(大花苗等苗族支系的生存環境一般都比較惡劣)的忍耐,乃至在此基礎上實現諸如倫理、審美、超脫的生命意志和終極追求。
歷史是人對過去的追問和記憶,然而,常常受身體結構的局限,即面對時間的流逝和空間的轉換,人的記憶顯得無能為力。苗族學者楊昌國認為,苗族歷史記憶有許多母題,然而各苗族支系對共同的母題有不同的闡釋方式,有古歌、舞蹈、服飾標記等[7]。大花苗對歷史的記憶依托于服飾圖案的書寫,把遷徙史形式化地繪制在服飾上,形成一種獨特的記憶場。作為符號,圖案不同于古歌或舞蹈,其已凝固并較為穩定而不易變化。一般來說,族群歷史的記憶或儀式操演主要由某一族群中的文化精英掌管,如很多民族中的祭師或巫師作為文化掌管者,拋開其他文化職責,他們肩負著記錄和傳承歷史的文化使命。而大花苗族服飾的歷史記憶方式已經突破這種慣制,把祖先的歷史以幾何紋樣的方式記錄在服飾上,形成統一格式,人人都是歷史記憶的記錄者和傳播者,并千古流傳,生生不息。在大花苗族中,制作服飾成為苗族女人必備的能力,年輕女子總是跟年老婦女繼承服飾制作技藝,其中包括幾何紋樣的繪制規則、尺寸、顏色搭配等,從而把歷史記憶與文化慣習有機統合起來。
(二)大花苗服飾隱喻祖先崇拜
大花苗服飾的文化記憶暗含了祖先崇拜的文化心理。“文化是依賴象征體系和個人的記憶而維持著的社會共同經驗。”[8]不錯,“研究記憶的社會構成,就是研究使共同記憶成為可能的傳授行為。”[9]也即是說,集體記憶具有建構并維系某社會成為可能的作用,大花苗族的服飾作為族群的符號象征,在服飾的制作及其穿戴中沒有舉行一定的儀式,但對服飾紋樣的膜拜和祖先的記憶,已然超越了個體記憶的特點而成為集體記憶的共同表征。大花苗是一支因頻繁遷徙而徒增悲劇性的苗族支系,生活環境惡劣,歷史上曾受到其他民族的欺凌,并堅毅地延續至今,其中服飾起到了聊慰內心和精神寄托的作用。其一,服飾記載了大花苗祖先曾居住富饒之地,雖輾轉各處仍不忘回到祖先失卻的那片豐饒家園,即使死后也要把墳墓朝向東方。其二,大花苗族認為他們的祖先是蚩尤涿鹿戰場的主力軍,能征善戰,其服飾中的披肩作為戰袍的變體,基本能影射曾經浴血戰場的將帥概貌,并引以為傲,他們正是通過服飾等文化形態形塑了民族文化心理。
苗族一般自認為是蚩尤的后裔,進而把蚩尤加以神化并崇拜,形成祖先與神相交融的信仰特點。大花苗族沒有嚴格的關于蚩尤信仰的儀式,他們自古把服飾的符號象征作為信仰載體,予以慰藉,從大花苗語對其服飾的稱呼可見一斑。大花苗將其民族服飾稱為“撮魯”,即“換衣”之意。相傳蚩尤當年涿鹿敗走后受敵方追殺,為了讓帶傷的蚩尤逃避被追殺的危險,其中一個跟隨蚩尤左右的大花苗族祖先主動與蚩尤調換衣服,才使蚩尤順利逃過一劫。此后大花苗族一直按照當時蚩尤的戰袍規格制作衣服而傳承,并取名為“換衣”。“換衣”的傳承一是對蚩尤的紀念,二是以祖先戰場殺敵的忠勇告慰悲苦的現實生活。②
作為祖先記憶的符號,大花苗服飾由最初的遷徙歷史的回憶,逐漸演化成一種族群邊界的分劃符號,即它既在族群內部催生出成員間的團結,又在族群外部區隔與其他群體間的關系。這種區隔表現在,一則通過服飾模塑大花苗族歷來規避與其他族群之間如婚姻往來的文化標識,二則以服飾符號建構的邊界心理不斷加固大花苗對自我文化的認同和傳承。
(三)大花苗服飾實現文化認同
揚·阿斯曼認為:“群體與空間在象征意義的層面上構建了一個有機共同體,即使此群體脫離了它原有的空間,也會通過對其神圣地點在象征意義上的重建來堅守這個共同體。”[10]也即說,記憶的象征意義在于重建族群“共同體”,然而實現這個共同體必須借助于一個“神圣地點”。對于大花苗族而言,他們唯一表達“神圣地點”的符號載體就是服飾,他們借助于服飾上的符號象征體系去實現民族文化的認知乃至認同,進而建構這個“共同體”。源于服飾圖形的特殊性,按祖祖輩輩流傳下來的標準制作民族服飾成為大花苗女孩婚前的必備技能,她們首先必須深知每一個圖形的涵義,才能固守縫制技藝不得任意改變服飾特征。大花苗服飾與其他民族或苗族的其他支系有著顯著區別,他們對服飾符號象征意義的重視旨在通過服飾加深對族系內部的文化認知,進而實現族群認同的目的。大花苗服飾的傳承是在不斷增強族群自我意識的過程,當族群意識得以加強后反過來又增加族群邊界的認同感,這是一個辯證協進的過程。大花苗服飾把其記憶功能與族群身份認同有機結合起來,既能以服飾符號形式促進大花苗特有的文化特質的世代傳遞,也可在服飾生成的認同關系中實現文化對族成員的控制,促進族群內部的團結與和諧。
結 語
作為一種符號表征,大花苗的服飾圖案結構符合皮爾士的指號釋義。皮爾士認為指號三分法只是一種分析方法,目的在于理解符號體系的特性,現實中這些分析類別并不單獨存在,而是重疊和融合的整體,分析便是為了更好認知。因此,我們在本文中借助該理論以解釋大花苗服飾的象征涵義,其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理解一種文化物象,進而深刻地認識大花苗。大花苗服飾幾何紋案記載,諸如圖案中的菱形代表田園、矩形代表城池等,其最初采用的便是皮爾士提出的“象似”指號的標記法,通過描摹形似的方法把祖先在中原一帶失去的家園及其遷徙路線記錄在服飾上。這套象似符碼歷經上千年而傳承,其指號與對象間(曾經的家園)漸漸超出它原有的形似對應,成為民族文化的象征或族群的標識。這樣的變化可由指號的釋義得以說明,即皮爾士所說的“特征符”(又稱直接解釋項)演化為“命題符”(又稱動態解釋項),再到“思辨符”(又稱最終解釋項)的過程。其中 “特征符”分析特征表明必須把征象對象放入到對象產生的文化場域中,誠如大花苗服飾的符號意義只有在大花苗文化語境中才能呈現一樣。“命題符”表明征象通過自身以限制對象來指示釋義,可理解為服飾圖案對大花苗來說是一種族群邊際的文化標識。而“思辨符”表明征象直接規定釋義,從而達到其合理性,此處尚可理解為大花苗民對本族服飾符號的自我認同與歸屬感。事實上,“釋義”的三個類別之間表達了皮爾士指號征象與對象間的辯證推演過程,這正暗合大花苗服飾從表層符號到深層記憶內涵的演進。另則,誠如符號具有約定俗成特性一樣,大花苗服飾圖案所展示出來的象征符號也有一定的“社會規約性”,如皮爾士所說:“所謂象征符號就是被符號的解釋者如此理解或解釋的符號。當然,這種理解或解釋不是個人隨心所欲的,而是受到解釋者所處的社會或共同體的規范的制約的。”[11]。
注 釋:
①引自2017年訪王文憲錄音資料。
②根據王文憲口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