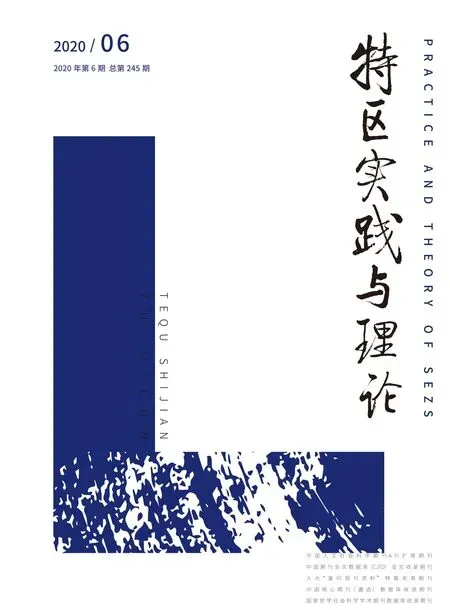深圳經濟特區綠色創新及效率研究
張雄化 張 超
一、引言及文獻綜述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創新驅動國家發展戰略,并將“創新”與“綠色”定為國家發展理念,強調經濟與生態和諧共生,已為國家實現高質量發展擘畫新路。一般認為綠色創新是一個合成概念,兼顧技術創新和綠色發展。其中,技術創新秉承產品創新、工藝創新和末端技術創新;綠色發展核心要旨為實現經濟社會效益和環境保護基礎上的生態效益提高。不難理解,綠色創新是期冀創新驅動發展下實現“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高產出”目標。因此,綠色創新是一種支撐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新模式和新動力。目前,如何使城市走上真正意義上的綠色創新發展道路?尚需理論支持和經驗總結。通過典型城市綠色創新發展實踐經驗提煉,挖掘其綠色創新內在機制,并實證分析其綠色創新規律,據此提出促進城市綠色創新資源利用及創新生態建立的政策,以期達到城市可持續發展目的。目前國內外注重對綠色創新作用及其效率研究,呈現如下特點:
一是綠色創新與經濟社會關系研究。一方面,綠色創新利于經濟發展。Hultman et al.(2011)和張振剛等(2014)證明綠色創新對經濟增長和發展作用巨大。Hillestad et al.(2010)研究發現綠色創新對特定行業企業及其形象極為重要。李婉紅(2015)、張倩(2015)、張旭等(2017)和王鋒正等(2018)基于波特理論證實行業企業綠色創新與政府環境規制存在雙向互作關系。明倩等(2020)針對中國制造業綠色創新現狀提出改善政策。另一方面,綠色創新利于社會進步。畢克新等(2014)和 Levidow(2014)研究表明,綠色創新對提高資源效率和減輕貧困具有正向影響。
二是綠色創新與區域經濟關系研究。金露露等(2019)將綠色創新分為技術推動型、市場拉動型和環境規制型,采用動態空間面板模型,研究發現長三角區域一體化對綠色創新存在正向影響。呂巖威等(2020)就中國區域綠色創新效率時空特點和收斂趨勢進行實證分析。 韓晶(2012)、付幗等(2016)、羅良文等(2016)和吳旭曉(2019)對地區綠色創新效率及演進規律、區域企業綠色創新效率及分解展開量化實證研究。Hultman et al.(2011)認為欠發達地區開啟綠色創新,應優先培養創新能力和創新生態。
三是綠色創新效率測算方法研究。一方面,利用 DEA 及擴展模型測算綠色創新效率。基于此,呂巖威等(2020)測算了中國工業企業綠色創新效率;吳旭曉(2019)評價了中國七大區域綠色創新效率。另一方面,利用指數法測算綠色創新效率。Perry(2009)構造三級指標體系評價美國加州綠色創新水平;黃曉杏等(2019)從八個相關指標構建了區域綠色創新系統成熟度指標體系。
現有文獻側重國家、區域和省際層面綠色創新研究, 較缺乏城市層面綠色創新研究,鮮有對城市綠色創新機制和發生原因的解釋。本文以沿海開放性城市深圳為例,通過揭示城市綠色創新作用機理,實證分析綠色創新效率及其影響因素,以期為解釋特區經濟奇跡和指導后發城市可持續發展,提供一定理論依據和經驗參考。
二、綠色創新典型事實和作用機理
(一)綠色創新典型事實
綠色創新分為四個階段。其中經濟特區從創新走向綠色創新,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為深圳創新起步階段,從20世紀80 年代至 90 年代初期,深圳開啟典型代工 OEM 模式,進行“三來一補”加工貿易, 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在當時屬于開創之舉,但該時期加工貿易的產品和技術均沒有自主知識產權。第二階段為深圳典型創新階段,從20世紀 90 年代中期至 21 世紀初期,深圳進入代工 ODM 模式,廣泛進行國際品牌貼牌生產,依然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但該時期深圳開始擁有一定的自主知識產權積累。第三階段為深圳創新向綠色創新轉型階段,從 21 世紀中期至黨的十八大之前,深圳代工 ODM 與自主 OBM 模式并存,即貼牌生產與自主品牌生產共存,但主要偏于 OBM,這一時期深圳產業由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轉型,企業普遍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第四階段為深圳典型綠色創新階段,從黨的十八大之后至今,在生態文明大背景下,深圳開始國家科學中心建設,聚焦高技術和知識密集型產業,以 PCT 國際專利不斷增長為代表,逐漸躋身國際城市和創新城市行列。
從創新試行到創新示范。以“先行先試”到“先行示范”實現區域功能從創新到綠色創新升級。深圳從改革開放之初,被迫“殺出一條血路”先行先試建立經濟特區;到推行自由貿易試驗區,加入CAPC(《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服務貿易協議》), 加大服務貿易,擴大同世界貿易往來;到實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打造引領經濟增長和科技創新的世界級增長極;再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布局五大發展戰略打造全球標桿城市,以彰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這個過程之中,深圳經濟特區建立到黨的十八大之前, 屬于深圳創新先行時期;黨的十八大之后到先行示范區提出之前,屬于深圳綠色創新先行時期; 先行示范區提出之后至今,屬于深圳綠色創新示范時期。
從城市創新轉向國家創新。從城市創新轉向國家創新和國家綠色創新。深圳從“三來一補”加工貿易——貼牌生產——模仿創新——自主研發設計,始終走在創新前沿。2008 年之前,深圳創新屬于城市層面創新;2008 年至黨的十八大之間,從本土城市創新轉向國家創新城市試點,則創新從城市層面上升為國家戰略;黨的十八大之后,隨著生態文明理念提出,深圳國家創新城市試點本質上已轉向國家綠色創新城市試點,而自貿區和“雙區”效應加速了深圳國家城市綠色創新步伐。
(二)綠色創新的機理
在綠色發展背景下的創新活動皆可稱為綠色創新。基于創新對經濟具有重大推動作用(楊朝輝,2015)、驅動社會生產力發展(張蕾,2014)、對生態文明建設發揮重大貢獻(張偉等,2015),因此將這一進步中的創新理解為綠色創新更為準確。即綠色創新既關注產品和技術創新,也關注創新作用下的經濟、社會和生態效果。以投入產出理論為基礎,綠色創新投入決定綠色創新產出,綠色創新投入和產出最終結果反映為綠色創新效率(見下圖):
一方面,綠色創新是一種綜合創新。綠色創新投入包括人、財、物和政策投入,即研發人員、研發經費、創新機構和創新類政策的投入等。綠色創新產出包括直接創新產出和間接創新產出。綠色創新直接產出被廣泛關注,通常利用專利、論文、軟件著作權和科技成果等技術進步指標衡量。綠色創新間接產出較容易被忽視,但實際上能產生較大經濟、社會和生態價值。包括:創新經濟產出,表現為新產品出口額、高技術產業產值和地區性 GDP 的增加; 創新社會產出,表現為社會生產力及民生水平的提高,以全員勞動生產率和工資水平等來衡量;創新生態產出,體現在經濟社會進步的同時污染排放量相應下降或者環境正向指標相應上升。因此,綠色創新是一種包涵直接技術創新、經濟創新、社會創新和生態創新的綜合創新。另一方面,綠色創新效率是一種綜合效率。在綠色創新投入作用綠色創新產出的過程中,直接創新產出對應直接創新效率;間接創新產出對應間接創新效率,并且在間接創新產出中經濟產出對應著創新經濟效率、社會產出對應著創新社會效率、生態產出對應著創新生態效率。據此,深圳從投入到產出的綠色創新效率,是由技術創新效率、創新經濟效率、創新社會效率和創新生態效率組合而成的一種綜合性效率(但非各效率的簡單平均)。
三、綠色創新效率實證分析
(一)變量選擇、數據來源及處理
本文依據前文學者研究和數據可得性選取研究變量及數據。其中,投入要素為研發經費、研發人員。產出要素中,直接創新效益產出為專利申請量、論文發表數量;經濟效益產出為高技術產品產值、高技術產品出口額、GDP;社會效益產出為工業全員勞動生產率;生態效益正產出為空氣優良率天數和能耗強度。以上變量數據均來源于《深圳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CNKI 數據庫和深圳市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對部分缺失數據采用移動平均法補齊,對價值型數據以 1979 年為基期進行物價指數平減。
在綠色創新機制下,深圳綠色創新投入和產出迅猛增長。一方面,創新投入增速極快。深圳從一個幾乎零創新城市起步到創新表現優異,尤其 2010-2019 年間,研發經費由 333.31億元增至1230 億元,增速為 269.03%;研發人員由 177756人增加到 393689 人,增速為121.48%。另一方面,創新產出增速更快。一是知識創新產出猛增。1979-2019 年發表論文數由 8 篇增長至 38440 篇,增長 4808 倍;1985-2019 年國內專利申請數量由19 件上升至262502 件,增長 13814.89 倍。二是創新產品產出激增。GDP 由 1979 年 1.96 億元上升至 2019年 26927.09 億元,增長 13737.31 倍;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幾乎從無到有,2019 年擴大至9230.85 億元,其中 2001-2019 年增長率高達598.59%;高技術產品出口額由 1979 年約 0元突破到 2019 年 1246.07 億美元,其中 2001-2019 年增長率高達 918.01%。三是社會勞動生產率大幅提高。工業全員勞動生產率由 1985 年 2.94 萬/人上升至 2019 年 32.15 萬/人。四是生態環境正效益大幅改善。1985-2019 年,空氣優良率天數由 180 天上升至 332 天;能耗強度由 0.49 元/千瓦時上升至53.46 元/千瓦時。相應變量描述性統計詳見下表:

變量描述性統計
(二)研究方法
DEA 模型測度效率。運用 DEA 方法測度創新相關效率時,定義直接創新效率變量包括:投入變量=研發經費+ 研發人員,產出變量=專利申請量+論文發表量;定義創新經濟效率變量包括:投入變量=研發經費+研發人員;產出變量=高技術產品出口額+高技術產業產值+GDP。定義創新社會效率變量包括:投入變量=研發經費+研發人員,產出變量=工業全員勞動生產率。定義創新生態效率變量包括:投入變量=研發經費+研發人員;產出變量=空氣優良率天數+能耗強度。定義綠色創新效率變量包括:投入變量=研發經費+研發人員;產出變量=專利申請量+論文發表量+高技術產品出口額+高技術產業產值+GDP+工業全員勞動生產率+空氣優良率天數+能耗強度。利用投入方向規模報酬可變的 DEA 模型時,可測算得到城市直接創新效率、創新經濟效率、創新社會效率、創新生態效率和綠色創新效率。
MALQUIST 指數法分解效率。對測算的綠色創新 DEA 效率采用 MALQUIST 指數分解法,將效率項分解為規模效率、純技術效率和技術變化,利用分解值大小判斷引起效率變化的主要原因。
TOBIT 模型解釋效率影響因素。因變量綠色創新效率取值介于 0-1,故采用 TOBIT 受限模型,對方程式兩邊取對數后檢驗自變量對因變量影響。參照陳景新等(2018)、李健等(2019)和李勛來等(2019)研究,選用區域開放、產業結構、環境規制、區域文化和政府資助等變量作為綠色創新效率影響因素。其中,區域開放程度=外商直接投資額占 GDP 比重;產業結構水平=第三產業比重; 環境規制水平=節能環保支出占一般公共預算支出比重;文化水平=大專及以上學歷人口占常住人口比例;政府資助水平=科技預算資金占一般公共預算資金比例。
(三)結果分析
綠色創新效率普遍高于其他效率。運用 DEA方法測算 1979-2019 年直接創新效率、創新經濟效率、創新社會效率、創新生態效率和綠色創新效率時,發現如下規律:
第一,創新驅動下深圳生態效率水平明顯高于其他效率。1979-2019 年,創新生態效率〉 直接創新效率〉創新經濟效率〉創新社會效率,均值分別為 0.746、0.647、0.638、0.542。表明深圳創新取得顯著的環境和經濟效益,反映深圳創新是考慮生態環境的創新。
第二,不同創新效率走勢出現一定分化。1979-2019 年,創新經濟效率、直接創新效率呈現波動上升走勢;創新生態效率以黨的十八大為時間分界點,在此之前其效率波動下降,在此之后其效率反轉并波動上升;創新社會效率呈現較明顯下降走勢。以上說明,長期而言創新對經濟貢獻明顯大于對環境和對社會的貢獻。
第三,各個時期不同創新效率及結構存在差異。改革開放初期創新社會效率最高,均值為0.848,表明改革初期創新對社會作用效果較大;20世紀90年代初到 21 世紀初,創新生態效率值較高,均值為 0.944,說明創新對環境破壞的影響相對較小;21世紀初到黨的十八大之前,創新經濟效率值最高,為 0.966,說明創新集中體現于對經濟強拉動作用; 黨的十八大之后,創新經濟效率仍然最高,與此同時直接創新效率達到歷史新高,說明深圳更加重視創新本身及其經濟轉化雙重效果。
第四,平均綜合效率總體呈波動上升趨勢。1979-2019 年,創新本身及經濟生活生態的平均綜合效率從 0.510 上升至 0.641,增長 25.69%,總平均綜合效率為 0.643。其中,改革開放至新世紀初期,平均綜合效率快速上漲;進入新世紀后,平均綜合效率才呈現波動上漲態勢。反映總體創新綜合效率在波動中前進,創新依然具有前景。
第五,綠色創新效率總體水平較高且呈現上升態勢。1979-2019 年,綠色創新效率均值為0.979。其中,改革開放初期三個年份效率為有效值 1,平均綠色創新效率為 0.945;20世紀90年代初到21世紀初,六個年份效率為有效值 1,平均綠色創新效率為 0.991; 21世紀初到黨的十八大之前,五個年份效率為有效值 1,平均綠色創新效率 0.994;黨的十八大之后,六個年份效率為有效值 1,平均綠色創新效率為 0.993。從中看出,不同時期綠色創新效率總體呈現上升趨勢。同時,比較歷年綜合創新效率與綠色創新效率發現,綠色創新效率不是幾個相關效率的簡單平均,歷年綠色創新效率均高于平均綜合創新效率。
技術進步是綠色創新效率提升的主要原因。深圳綠色創新效率提升的主要原因在于整個城市的技術進步。綠色創新效率 MALQUIST 指數分解表明,1979-2019 年,技術進步指數均值為 1.085,大于技術效率變化指數均值 1, 說明因技術變化而非管理變革促成效率提升,說明深圳無論在各發展時期技術進步總對綠色創新效率提升起決定作用。
影響綠色創新效率的主要因素為文化水平、產業結構和對外開放程度。TOBOT 模型較為適宜檢驗城市綠色創新效率影響因素。其中,對數極大似然值為 25.04,LR 卡方值為 16.63,通過 1%顯著性水平檢驗。城市文化水平系數值為 0.049,通過 20%顯著性水平檢驗;產業結構水平系數為-0.090,通過 5%顯著性水平檢驗;對外開放程度系數為-0.014,通過 15%顯著性水平檢驗。說明:城市人口學歷水平越高,越有利于綠色創新效率提高;第三產業比重越大,越不利于城市綠色創新效率提升,可能原因是服務業易脫實向虛,影響實體產業主導創新能力躍升;外商直接投資比重過大,越不利于綠色創新效率提高,可能的原因是外資企業對發展中國家更傾向于布局低端產業鏈和污染性行業。此外,其他解釋變量雖對綠色創新效率產生一定影響,但均沒有通過顯著性水平檢驗,故忽略。
四、綠色創新的原因解釋
企業家精神引領是深圳最寶貴的財富。創新經濟學的鼻祖熊彼特(1911)認為,企業家是社會經濟創新的主體,創新是企業家精神的靈魂。而典型的企業家精神為:建立私人王國(企業家是理想主義者);對勝利的熱情(企業家好勝心強);創造的喜悅(企業家展示個人價值感到歡樂);堅強的意志(企業家具有鋼鐵般的意志)。深圳市場主體是典型的民營中小企業及企業家,2019年中小企業家占整個企業家主體的 99.6%,是深圳創新創業創意名副其實的生力軍。
高技術產業是深圳持續發展的生命線。歷屆特區領導干部善于學習,對標全球先進城市經驗,制定產業政策對產業前瞻性布局。例如,深圳在“三來一補”貿易如日中天之際,果斷“騰籠換鳥”,淘汰低端落后產能,積極謀劃發展高技術產業、戰略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等。對高科技企業采用鼓勵研發、保護知識產權、引進海外人才、建立高等院校和科技園等產業配套扶持政策,使產業與城市及生態環境相得益彰協同發展。
人口和文化的多元化是深圳的源頭活水。一方面,空間經濟學家藤田昌久(2019)認為,深圳最大特點是人口和文化的多元化。其中,全市廣東人、湖南人、廣西人、湖北人、江西人、四川人分別約占 400 萬、300 萬、200 萬、180 萬、150 萬、100 萬,造就深圳開放包容大氣創新的文化特點。另一方面,從開辦經濟特區以來,南下干部、知識分子、企業家等紛紛集聚深圳,同時深圳通過接收高校畢業生、留學人員、外調人員,為城市發展儲備知識和人才。截至 2019 年底深圳人才存量已超 548 萬人。
金融資本環境是深圳發展的堅強后盾。金融學家麥金農(1973)指出發展中國家由于金融管理及制度不當,壓抑了本國經濟增長。深圳在金融改革開放上先行先試,率先建立深交所、平安金融等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區域金融載體,有效解決了特區經濟發展的資金不足問題。如 2019 年深圳人民幣存貸總額均超過 18000 億元,為深圳發展提供有力資金保障。
法治環境為絕大多數人的權益提供保護。深圳在中央精神上探索市場經濟十大體系和五大運行機制,結合特區立法權,為不同所有制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環境,并實施外來務工條例,保護了廣大勞動者權益。例如,2019 年深圳已頒布總法律 228 部,其中先行先試的法律 110 部,創新變通類法律 58 部。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是深圳日益從“創新驅動發展”遷移至“綠色創新驅動發展”。總體而言,以黨的十八大生態文明戰略提出為分界點,在此之前屬于顯性創新時期,在此之后屬于顯性綠色創新時期。
二是深圳綠色創新效率較高,技術進步起決定作用。改革開放后,綠色創新效率值在19 個年份為有效值 1,總效率平均值為 0.979,顯示深圳綠色創新水平較強;綠色創新效率指數分解整體表明,技術變化強于管理變化引致深圳綠色創新效率不斷提升。
三是深圳綠色創新效率的主要影響因素為城市文化水平、產業結構水平和對外開放程度。其中,高學歷人口比重越大越利于城市綠色創新效率提高。
四是民營企業及企業家和高技術產業等優勢是深圳綠色創新的不竭動力。民營企業和企業家及精神是深圳最為寶貴財富,為城市綠色創新提供土壤;高技術產業是深圳發展的生命線,為城市綠色創新插上翅膀。“土壤+翅膀”使深圳綠色創新綿綿不絕。
根據以上結論,提出如下對策建議:
首先,實施城市綠色創新發展戰略。一是明確綠色創新為國家戰略。加強頂層設計,政府從國家層面出臺綠色創新發展戰略規劃,納入各級政府考核體系。加強區域性政策扶持,對東部創新環境和生態環境優渥地區,率先踐行“兩山”理論,發掘自主創新和綠色發展措施。加強綠色創新城市試點和推廣,出臺城市綠色創新發展報告,宣傳推廣典型綠色創新城市經驗。二是制定城市綠色創新發展規劃。堅持綠色為本、創新為魂,以綠色創新驅動城市發展為指引,以編制“十四五”規劃為契機,針對產業和城市綠色創新制定評估標準、發展路徑和預期目標,實現綠色創新助推經濟、社會和生態協同發展。編制未來城市綠色創新發展議程,為實現全球標桿城市建設提供佐證依據。三是完善綠色創新相關法律。完善環境規制政策,落實企業環保稅,嚴格環境執法,決勝治水提質攻堅戰和推進大氣治理“利劍行動”。完善政府綠色采購制度,對綠色創新企業及產品優先扶持采購。善用特區立法權和知識產權法庭,實施最嚴格綠色知識產權和綠色專利保護,保護綠色創新行為。
其次,提高城市綠色創新資源利用效率。一是加大綠色創新投入力度。制定綠色創新認定標準,對企業綠色創新活動進行財稅金融等政策支持。鼓勵企業研發,逐年提高研發資金占 GDP 比重;在保障每年 30%市財政收入用于基礎研究上,鼓勵政府機構、企業和民間組織對研究型大學及機構的項目進行資金贊助。增加高校、科研院所和企業研發部門的職數,利用市區人才政策引進國內外優秀研發人員,提高研發人員數量和質量。利用國家科學中心建設機遇,吸引更多研究型大學、研究機構、實驗室、創新創意創業平臺等綠色創新載體落戶。二是運用先進數字信息技術輔助綠色創新。運用 5G、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等新一代數字信息技術對產業進行數字化升級,加快智慧城市建設和治理,實施智能性生態環境保護和監測,使綠色創新為城市經濟、社會和生態服務。三是改善綠色創新的影響因素。注重優化人口結構和城市文化水平,加大本土高學歷人才培養和大力引進外來高學歷人才。注重優化產業結構,聚焦實體制造業綠色創新,加大高技術產業技術和產品創新研發力度,對傳統制造企業加強工藝和末端技術創新,對服務業推廣先進技術和模式創新。注重優化對外開放結構,實施自主投資、自主研發設計和生產,擺脫國際價值鏈“低端鎖定”,利用外資以技術入股型外資為主,擴大對外開放和完善“一帶一路”市場,穩外貿與穩內需并重。
第三,完善城市綠色創新生態體系。一是綠色理念融入“軍—政—產—學—研—用”創新生態鏈。發揮軍民融合創新和政府引導創新的作用,在傳統“產學研用”創新鏈基礎上,建立“軍政產學研用”新型創新鏈,激發多元主體創新活力。同時,綠色理念融入新型創新鏈每一個環節及相應政策,實現創新過程綠色化。二是綠色理念融入“基礎研究+技術攻關+成果轉化+科技金融”創新生態鏈模式。深圳利用本土及外來“基礎研究+技術攻關”成果,借助優越市場環境,快速實現其市場轉化,并利用科技和金融作為其市場化轉化堅強后盾,據此形成深圳獨特創新生態鏈模式。目前,打造深圳綠色創新生態鏈模式,亟需綠色理念有機植入創新生態鏈模式。三是探索其他綠色創新模式。建立綠色教育制度,以學習知識、學習技能與社會生產實踐相結合為導向,探索產學研部門間的合作教育制度。建立綠色企業孵化模式,為企業綠色創新提供融資、管理、場地、學術交流等全要素服務,樹立綠色創新企業典范。建立綠色技術轉讓機制,激發大學和科研院所向產業界提供更多綠色專利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