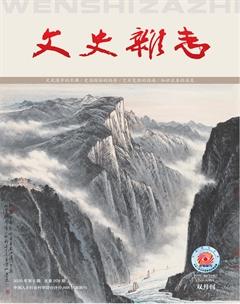國人取字有講究
彭華
![]()
![]()
![]()
![]()

摘?要:古代中國沒有“邏輯”這個詞,但并不等于沒有邏輯學。兩漢時期的學術領軍人物揚雄,不論是學術研究還是辭賦散文,均具有強烈的邏輯性。尤其是《法言》十三篇闡述,既有邏輯性也有系統性,比較全面地勾畫出儒家封建倫常的核心內容,也讓人看到揚雄所構建的新的儒家價值體系。揚雄在學術研究和著述中十分注重邏輯性這件事,可以給今天的人們在學習、作文、著述諸方面許多有益的啟示。
關鍵詞:揚雄;學術研究;著述;邏輯性;有益啟示
眾所周知,揚雄(前53—后18)是兩漢時期的學術領軍人物。之所以能夠“領軍學術”,除了他知識廣博,研究扎實,見解深刻外,就是著述眾多,且不論是學術研究還是辭賦散文,均具有強烈的邏輯性,讀之使人信服。其實,任何一篇成功的文章,必然有謹嚴的內在邏輯——思維層次清晰,結構勻稱合理,材料與中心緊密結合;反之來說,文章若是沒有邏輯性,就必然會導致思路混亂,沒有章法。由此看來,揚雄學術研究與著述的邏輯性這個問題,值得一論。
一、古人著文也重視邏輯性
“邏輯”是一個外來詞語,據考證,產生于1901年。
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中國著名的翻譯家和教育家嚴復(1854—1921)執教的北洋水師學堂遭到徹底破壞。他不得不于是年7月避難上海。由于匆忙離津,又失去了全家賴以生存的工作,在上海的嚴復連生活費都沒有了,只得靠翻譯來維持全家生活,甚至還得借債度日。當年10月,金粟齋譯書局請嚴復譯英國哲學家、政治學家和經濟學家John?mill(約翰·穆勒)所著的《Logical?systems:deduction?and?induction》。嚴復對這本書早有認識。他將書名譯為《邏輯體系:演繹和歸納》,首次在中國提出了“邏輯”一題。嚴復認為邏輯學是格物窮理的基本方法,也是西方學術迅猛發展的關鍵所在。他指出:邏輯學是規范思想語言的法律,是“一切法之法,一切學之學”,具有“察不遁之理,必然之數”的功能。[1]1901年4月29日晚,嚴復到上海名學會講演名學。在上海,嚴復一邊翻譯該書,一邊宣講名學《邏輯學》。1902年3月,嚴復譯成原著第1卷前半部,即《穆勒名學·部甲》,于1903年1月由南京金粟齋木刻出版。其后,原著第一卷其余部分陸續譯出。
古代的中國有“邏”字與“輯”字,按《辭源》的解釋,“邏”字的本義是偵候、巡邏之意,可引申為捕鳥的網,有網羅搜尋之義;“邏”字的組詞除用作名詞的邏娑外,能組詞的只有邏子、邏卒、邏所,分別指巡邏兵、巡邏士、巡邏哨所。“輯”字的本義指車箱,泛指車子,有和協、親睦,聚集、收集,整修,斂等含義,假借為編輯、輯錄等文字、書籍的整理工作。
據《漢語外來詞詞典》,“邏輯”一詞來源于英語Logic,也稱邏輯學,舊稱名學、論理學,指的是:思維的規律、客觀的規律性、研究思維的形式和規律的科學。[2]
古代中國雖然沒有“邏輯”這個詞,但并不等于沒有邏輯學。當代學者周文英《中國邏輯思想史稿》詳細論證了中國古代、近代的邏輯思想;溫公頤《中國古代邏輯史》對中國古代的邏輯史亦有詳細論述。[3]春秋時期“百家爭鳴”中的名家,以思維的形式、規律和名實關系為研究對象,其也被稱作“辯者”“察士”。名家以擅長論辯著稱。他們在論辯中比較注重分析名詞與概念的同異,重視名與實的關系,開創了中國的邏輯思想研究。在他們的影響下,中國歷代邏輯名家輩出,各有創新。
中國古代對于著文時如何考慮文章整體結構以及寫作技巧,有許多經驗甚至是理論,尤其講究立意、布局、結構和文辭,這其實也就是重視邏輯理論的指導。
元末明初的陶宗儀在《南村輟耕錄》中說:“作樂府亦有法,曰鳳頭、豬肚、豹尾六字是也。”[4]這里講的就是著文的邏輯性與技巧性。
作為兩漢時期學術領軍人物的揚雄,在他的學術研究與著述方面,充分體現出嚴謹的邏輯性。
二、揚雄賦作的邏輯性
揚雄早年極其崇拜司馬相如,“每作賦,常擬之以為式”[5]。他的《甘泉》《羽獵》諸賦,就是模擬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而寫的,其內容為鋪寫天子祭祀之隆、苑囿之大、田獵之盛,結尾兼寓諷諫之意,步步推導,邏輯性非常強。因為其用辭構思與司馬相如賦的華麗壯闊相類似,故后世有“揚馬”之稱。
《漢書·揚雄傳》記載:“(帝)登歷觀,陟西岳以望八荒,跡殷、周之虛,眇然以思唐、虞之風。雄以為臨淵羨魚,不如歸而結罔,還,上《河東賦》以勸。”說的是漢成帝登上歷山、華山,尋求商代、周代的遺跡,作出追懷堯舜圣世風尚的姿態。揚雄認為這樣追懷往古,羨慕堯舜時代,太不切合實際,就以“臨淵羨魚,不如歸而結網”比喻與其空想,還不如想辦法去達成目標更有意義。揚雄回京后就寫出了《河東賦》,委婉地讓帝王自省其言行得失,勸諫皇帝應該戒止游獵,實行德政。《河東賦》的諷諫,寓于宏富的鋪陳中,具有強烈的邏輯性。
揚雄寫得比較有特點又極具邏輯性的賦是他自述情懷的幾篇作品,如《解嘲》《逐貧賦》和《酒箴》等。《解嘲》通過揚雄自己和前代士人的比較,指出社會情況注定了士人的命運,時代決定了士人的作用,時勢變化決定了士人的地位。這些都是大環境所導致的,不是揚雄一個人可以改變的。因為揚雄不愿趨炎附勢去作官,就只有自甘淡泊來進行他的學術研究。文中揭露了當時權奸擅權、傾軋的黑暗局面:“當涂者升青云,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寄寓了作者對社會現實的強烈不滿。《逐貧賦》是別具一格的小賦,寫他惆悵失志,“呼貧與語”,質問貧何以老是跟著他。這篇賦發泄了他在貧困生活中的牢騷,多用四字句,構思新穎,筆調詼諧,卻蘊含著一股深沉不平之氣。《酒箴》是一篇詠物賦,主旨也是抒發內心不平的。
三、揚雄學術研究的邏輯性
揚雄后來對賦有了新的認識。他在《法言·吾子》中說,作賦乃是“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10]并認為自己早年的賦和司馬相如的賦一樣,都是似諷而實勸。這種認識對后世關于賦的文學批評有一定的影響。
揚雄轉而研究哲學,并在散文方面取得了相當的成就,如《諫不受單于朝書》便是一篇優秀的政論文,說理透辟,邏輯性強,筆力勁練,語言樸實,氣勢流暢。在文學技巧和邏輯思維上,揚雄的散文繼承了先秦諸子的一些優點,語約義豐,層層推進。同時代的桓譚、劉歆與揚雄都是當時的著名學者。他們經常在一起“辨析疑異”,這必然包含著一些邏輯問題。桓譚就評論揚雄的文章“文義至深,而論不詭于圣人”[6],這當然是說揚雄文章的邏輯性非常強。揚雄的散文對唐代古文家發生過積極影響,如韓愈“所敬者,司馬遷、揚雄”[7]。此外,他是“連珠體”的創立人。“連珠”“歷歷如貫珠”,層層推進,“辭麗而言約”。其繼揚雄之后,繼作者甚多,如班固、賈逵、傅毅、蔡邕。
揚雄敢于獨立思考,對當時的神學思想提出許多質疑。他模仿《周易》,將源于老子之道的“玄”作為最高范疇,在構筑宇宙生成圖式、探索事物發展變化規律時,吸收《老子》的精華,繼承氣說的思想,最后形成《太玄》一書。《太玄》中有許多辯證思想與邏輯思考,包括了天、地、人三方面,包羅萬象,以揭示整個宇宙的秩序。
揚雄學術著作中對后世影響最大的是《法言》。《法言》體現出極強的邏輯性,各篇相互關聯,又以一脈貫穿。該書問世后,很受學者重視,在社會上“大行”,[8]廣泛流傳。
《法言》成書于王莽稱帝前夕。《漢書·揚雄傳》記載揚雄自述該書寫作目的,主要是因為諸子各逞其智,詆毀圣人,多為怪迂析辯詭辭,以干擾世事,迷惑大眾,所以需要用圣人之道的法則予以批駁,以明辨是非,從而恢復孔子的正統儒學。在揚雄看來,孔子是最大的圣人,“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經營中國,終入大海;他人之道者,西北之流也,綱紀夷貉,或入于沱,或淪于漢。”[9]所以,要恢復孔子的正統儒學,就必須依賴孔子的經典。因為:“舍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舍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因此,“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要諸仲尼,說鈴也。”[10]
《法言》全書共十三篇。試看揚雄撰寫的目錄說明:
天降生民,倥侗顓蒙,恣于情性,聰明不開,訓諸理,撰《學行》第一。降周迄孔,成于王道,終后誕章乖離,諸子圖微,撰《吾子》第二。事有本真,陳施于億,動不克咸,本諸身,撰《修身》第三。芒芒天道,在昔圣考,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不可奸罔,撰《問道》第四。神心忽怳,經緯萬方,事系諸道,德仁誼禮,撰《問神》第五。明哲煌煌,旁燭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撰《問明》第六。假言周于天地,贊于神明,幽弘橫廣,絕于邇言,撰《寡見》第七。圣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冠于群倫,經諸范,撰《五百》第八。立政鼓眾,動化天下,莫上于中和,中和之發,在于哲民情,撰《先知》第九。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一概諸圣,撰《重黎》第十。仲尼之后,迄于漢,道德顏、閔,股肱蕭、曹,爰及名將,尊卑之條,稱述品藻,撰《淵騫》第十一。君子純終領聞,蠢迪檢押,旁開圣則,撰《君子》第十二。孝莫大于寧親,寧親莫大于寧神,寧神莫大于四表之歡心,撰《孝至》第十三。[11]
《法言》十三篇從《學行》開始,到《孝至》結束,緊扣儒家正統學說,又在邏輯上環環推進的理論闡述,使其成為繼《論語》《孟子》之后,正統儒學最經典的理論著作。
《法言》十三篇的邏輯關系可歸納如下:
《學行》:概述關于學習的幾個原則問題,強調學習對象必須是圣人和圣人之道;
《吾子》:論述學習對象,強調必須辨別圣人之道的真偽;
《修身》:論述目的,強調應該樹立“修身以成圣”的志向;
《問道》:論述學習方法,強調堅持圣道原則,抵制諸子邪說;
《問神》:論述圣人的思想體系,強調圣人之道的博大精深;
《問明》:論述圣人的行事原則,強調圣人“尚智”以明哲保身;
《寡見》:論述圣人的治國理念,強調圣人“尚德”以治理天下;
《五百》:論述圣人的卓越道德,強調圣人“詘身信道”的處世原則;
《先知》:論述圣人的政治理想,強調圣人希望建成一個“中和”的太平盛世;
《重黎》《淵騫》:品評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為世人學習仁義禮樂提供正面和反面的典型;
《君子》:論述圣人的人才標準,強調“進退以禮”“自愛自敬”和“以德益壽”;
《孝至》:論述孝道的標準和表現,強調“致帝者之用,成天地之化”是人君最大的孝道。[12]
《法言》十三篇,邏輯性與系統性一目了然,比較全面地勾畫出儒家封建倫常的核心內容,也能讓人看到揚雄所構建的新的儒家價值體系的大體框架。
四、揚雄著述注重文章邏輯性的啟示
兩千年前的大學者揚雄,在他的學術研究和著述中十分注重邏輯性這件事,可以給今天的人們在學習、作文、著述諸方面許多有益的啟示。
在現代漢語里,邏輯一詞在不同的場合具有不同的含義:有時指的是客觀事物的規律性;有時指的是思維的規律性;有時指的是研究思維的科學。不論哪種含義,都告訴我們:使用漢語時,無論是說話、演講,還是寫文章,都要講邏輯,必須講邏輯。
成功的文章必然有嚴謹的邏輯關系——思維層次清晰,結構勻稱合理,材料與主題緊密結合。
要突出文章的邏輯性,特別需要注意的是三個“要”:
一是要突出材料與主題的邏輯關系。一篇文章,主題是靈魂,材料是血肉,這是二者的邏輯關系。材料必須為主題服務,材料必須緊扣主題。若做不到這一點,就會出現“材料堆砌,不能達意;材料相抵,自相矛盾;遠離中心,偏離題旨”的毛病。
二是要突出事物發展的邏輯關系。文章是對客觀事物的記載,任何一件事情,就它的發展過程而言,總是離不開起始、發展、高潮、結局這幾個階段。只要按照這一結構形式寫作,作為記敘文的文章就會有始有終,結構嚴謹。而在議論文的寫作中,應該重視的是“事”與“理”的邏輯聯系。議論文的寫作,論點、論據、論證三者之間密不可分,論點是“帥”,論據是“兵”,論據、論證必須全方位為論點服務。因此,必須考慮怎樣才能使三者緊密結合,邏輯謹嚴。否則,就可能導致論點、論據兩層皮,出現層次不清,結構混亂,論證無力的情況。
三是要突出語言之間的邏輯關系。文章的語言好壞,直接關系到文章的成敗。一篇成功的文章,其語言首先應做到邏輯嚴謹,先說什么,后說什么,是按時間順序說還是按空間順序說,是先說主體然后闡述還是抽絲剝繭突出主題,都需要有一個明確的邏輯表達。決不能東扯一句,西扯一句,沒有主次,沒有順序。
只要按照這三個“要”去思考、去作文,文章的結構就必定嚴謹、新穎,好文章就自然產生了。
注釋:
[1]嚴孝潛:《邏輯學著作〈穆勒名學〉》,載《今晚報》2019年3月21日。
[2]高名凱、劉正埮:《漢語外來詞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4年版。
[3]周文英:《中國邏輯思想史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溫公頤:《中國古代邏輯史》,南開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
[4](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齊魯書社2007年版。
[5][8](漢)班固:《漢書》之《揚雄傳》,中華書局1999年版。
[6](漢)班固:《漢書》之《揚雄傳·贊曰》,中華書局1999年版。
[7](唐)柳宗元:《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載《柳河東集》卷三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9](漢)揚雄:《法言》之《君子》,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年版。
[10](漢)揚雄:《法言》之《吾子》。
[11]張震澤箋注《揚雄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17—418頁。
[12]本段論述,參見紀國泰《讀懂揚雄——關于揚雄及其〈法言〉》,載《〈揚子法言〉今讀》,巴蜀書社2017年版。
本文為四川省社會科學研究重點基地“地方文化資源保護與開發研究中心”課題《揚雄思想在學校的實踐研究》之子課題《揚雄教育思想下小學低段思維習慣和能力的培養策略研究》階段成果之一。
作者:成都市郫都區紅光學府高店小學校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