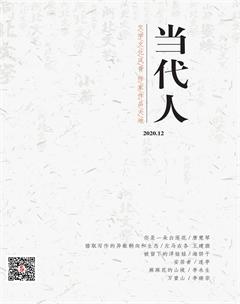聚合
讀大解的詩《沉默》,我也只能沉默。大解去過很多地方,看過很多山,寫過很多詩,收藏了很多石頭。我也收藏了很多石頭。大解的石頭,大多來自太行山;我的石頭,大多來自我與大解共同的故鄉燕山。燕山與太行山都在北方,血脈相連,它們是億萬年的兄弟。很多年前,在愚公的感召下,神搬走了太行山,大解追隨神的腳步,住到了太行山的附近,寫詩,撫石,思考。我也離開燕山的深處,遷徙到渤海之濱,在許多個寂靜的夜晚,一個人,在整座樓的最底層,那個叫做下房的一隅,像愚公挖山一樣,叮叮當當地開挖木質的底座,為我收藏的石頭穿上鞋子。于是,這些石頭,便高貴地佇立在人間。
喜歡上石頭,已經有許多年了,石頭是世間最永恒的物質。我們能用幾十年的人生時光,面對石頭,與亙古交談,是一種巨大的幸福。我們永遠也不知道石頭是怎樣誕生的,何時誕生的,更不知道石頭會怎樣死亡,何時死亡。面對石頭,我們為自己短暫如蜉蝣的生命感到羞愧。我們勿需懷疑石頭是有生命的,只是你沒有讀懂石頭,就像一條魚,永遠也讀不懂江河。
大解在他的長詩《悲歌》中說:“石頭有石頭的秘密 / 在沒有說出之前 他們將閉口 / 封鎖住內心……”慵懶如山的石頭,從不主動行走,從不輕易發出聲音。我常常一個人,在寂靜中,獨自面對石頭,我讀不懂它們的內心。正如大解所說,石頭有石頭的秘密,我無意窺視石頭的秘密,也無法理解它們的內心,我只能審視石頭的表面。在這些石頭的表面,我常常能看到一張張人的面孔,五官清晰,表情豐富。或許,那便是你在石頭上,讀出了自己。
我與妻總能在同一塊石頭上看出不同的畫面,讀出不同的意境。我常開妻的玩笑:女人總是看到局部,男人常能看到整體。或許,神也會說,人類只看到石頭,而神的眼里,永遠是一座山脈。在佛的眼中:所有的石頭,皆如恒河之沙;所有的生命,都是蒼生;所有的生死,都是輪回。
多年來,每逢春節,我都回老家與父母一起過年。家人忙著燉魚燉肉,我則自得清閑,上山撿石頭。萬木蕭索,日淡風冷,山陰處,偶有積雪。山下的村莊里,常有人呼犬吠之聲,隱約而至。時而有一團團白煙,在村莊的上空,如棉團一般爆出,繼而有爆竹聲傳來。歲月輪回,世間有無數悲歡離合,而山中的石頭,總是相安無事,靜默如初。我在眾多的石頭中間穿過,正如許多石頭,也曾在我的手中停留過,皆是瞬間。
老家的東山之東,三四十年前,曾有一座理石礦,人們將那些雪白或者墨綠的石頭開采出來,再粗暴地將其粉碎成顆粒均勻的理石米,用來裝飾到建筑物上,這些石頭便成了房子的皮膚。我在理石礦的遺址上徘徊,有一個巨大的磨盤,被遺棄在碎石之上,那是曾經用來加工理石米的器物,它也是一塊石頭,如君王一般摧毀了許多其他的石頭。
我在這個理石礦附近的河谷里,撿到一些很喜歡的石頭,其中有一塊,一半是白色理石,一半是綠色接近玉石,在我的客廳里置放了許久。有一天晚上,我忽然發現,那是一張極其冷峻的面孔,面龐瘦削,目光堅定,我興奮異常,更令我驚奇的是,這張面孔與大解的面孔無異。有一天,我將這塊石頭的照片與大解的照片比對著在微信里發給大解,大解說確實很像,但他又說:我抗議,太丑了!我只給大解發回一串笑臉。丑是美的另一種表達,所以,賈平凹將奇石稱作丑石。
燕山之中,與我距離最近的,有兩條河流,我經常去那里撿石頭。一條是青龍河,另一條是灤河,兩河皆東入渤海。
青龍河是我故鄉的河流,百年之前,曾舟楫其上,帆影點點,如今早已萎縮大半,或可涉足而渡。在青龍河兩岸,曾出土過一些石器與青銅器,先民濱河而居,磨石為器,創造了一個輝煌的石器時代。其后又冶石為銅,鑄銅銘文,開啟了一個新的文明時代。前些年,青龍河下游,以石筑壩,攔河蓄水,據說在高空俯瞰,河水恰似一條巨龍,隱匿于燕山之中,往來于天地之間,嘆為奇觀。我常開車去青龍河撿石頭,能有卵石鋪陳的河灘,已是難得。覓得佳處,河流已退至河灘一側,河水清澈澄明,寂靜流淌,河灘之上,眾石云集,一望無際,春風浩蕩,雁叫長空。此刻,若得美石,自會更加心曠神怡、喜不自禁。
去灤河略遠。初,走國道“三撫線”,幾乎與長城并行,一路向西,經過許多村鎮與田野,兩三小時,方抵達遷西境內,至灤河附近。泊車下河,適逢有大型挖掘機在河床作業,翻出灤河的許多陳年積存。
灤河更顯大氣磅礴,河床也寬闊許多,但整條河流早已被欺占攔截得面目皆非。多次去灤河,后改走京哈高速,再轉遷安支線,更加快捷。我在灤河撿了許多好石頭,灤河有一種黃黑相間的石頭,黃為枯葉之黃,黑為濃墨之黑,色彩豐富,圖案清晰,皮厚質細,造型飽滿。每遇之,總有驚喜。
在我的藏石中,最為喜歡的兩塊灤河石,一為“女媧”,直徑一尺有余,石頭正面,有一遠古女性側身浮雕半身像,目光上傾,仿若凝視天空,長發浴風飛揚,動感十足,面孔五官清晰,胸部線條流暢。我覺得,這就是煉石補天的女媧,這就是摶土造人的女媧,這就是如先祖如神靈一般的女媧。另一塊是“霸王別姬”,橫長亦一尺有余,正面有一男一女圖案。女子在前,身材窈窕,男子在后,孔武有力。二人牽手作別,難分難舍,生死相依,悲情十足。整體色黑如夜,二人身后,有黃色背景,一如火光熊熊、四面楚歌、人喊馬嘶的古戰場。后來,每至灤河覓石,下車后,必撮土焚香,感謝神靈厚賜,非為他故,只求內心虔敬。
在大解的家中,我見到過他從西藏帶回的石頭,那是一塊挺大的石頭,上面有袈裟紅的圖案。大解說,那是男神在飛舞,我欽佩大解的想象力,更羨慕他的慧眼與石緣。這塊石頭是大解花七張百元大鈔,從西藏空運到石家莊的。我想,這是高原之神在人間行走的費用,并不奢侈。
在西藏,我肯定不會放過撿石頭的機會。虔誠的藏民,用一些石頭,摞起了高聳的瑪尼堆,雪域高原,獵獵的風馬旗下,瑪尼堆不僅僅是一堆石頭,那些聚合在一起的石頭,充滿了佛性,那便是神之所在。
我在西藏帶回的石頭中,有一塊是在米拉山南側的尼洋河邊撿的。從拉薩去林芝,之后再返回拉薩,都要翻越米拉山口。米拉山海拔5013米,是拉薩河水系與尼洋河水系的分水嶺,山北為拉薩河,山南為尼洋河,兩河殊途同歸,最后皆入雅魯藏布江。我特別想帶回一塊米拉山的石頭,最后在碧水清波的尼洋河畔選中了這塊小石頭。它不大,已經被河水沖洗得毫無棱角,色澤烏黑,表面有淺淺的坑點,帶磁性。在西藏,彎腰在地上撿起一塊石頭,再站起身來,會氣喘吁吁,是一件很吃力的事。這塊石頭雖小,但我一直覺得,它帶有雪域神山的氣息,它更是我珍貴的西藏記憶之一。
另一塊,是我在林芝的南伊溝撿的。南伊溝在喜瑪拉雅山脈北麓,位于米林縣南部的南伊珞巴民族鄉境內,是縱深四十多公里的納伊普曲峽谷。傳說藏醫學鼻祖宇妥·云丹貢布曾在這里煉丹、行醫、授徒,是神秘的藏醫藥文化的重要發源地,有“藏地藥王谷”之稱。我在南伊溝撿到的這塊石頭,是我覺得最具神性的。我在路邊遇到它的時候,它靜靜地臥在草叢里,就像在那里一直等候我一樣,內心有種失散多年再次重逢的親切感。更神奇的是,它的顏色一如寺廟里的紅墻或者喇嘛的袈裟,呈暗紅色,并且整體圓潤,有燒灼痕跡,我的第一個想法,是西藏的火供天珠,天珠也是石頭。后來,仔細賞讀,我更相信它來自天上,因為它有一層厚厚的熔殼,并有微磁。
每夜,星河璀璨。一些石頭飛在天上,就是星星,一些星星落到地上,就變成了石頭。
我想,石頭與石頭,石頭與大地,大地與上天,上天與人,人與人,都有無限聚合的可能。
(王海津,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二級作家。有詩歌、散文等作品散見文學期刊。出版有詩集《走過原野》,散文集《鄉村碎片》《城市鳥群》《鵲雀窩溝村志――一個作家筆下的村莊記憶》,長篇報告文學《鐵骨春秋》等。作品入選中國散文排行榜、河北年度散文十佳排行榜。)
編輯:劉亞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