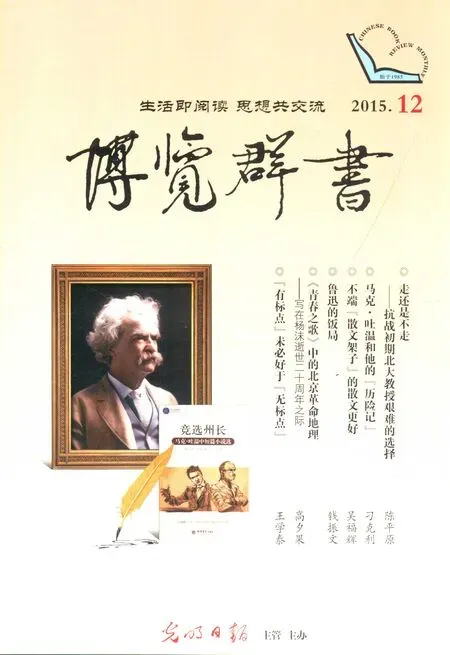當《中庸》遇到“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王樂
經歷了先秦時代的發育、成長、突破、對話、融合之后,中華文明在秦漢時代發展到了穩定成熟的階段。中華文明穩定成熟的重要標志,是一批被稱為“經”和“史”的文化經典得以確立。“經”代表著意義本源和價值準則,“史”代表著基于“經”之意義價值的歷史敘事和是非褒貶,“經史互為表里”共同構建了中華文明的價值基石和人間秩序。要理解中華文明的性質,必須回到“經”和“史”之中去探究文明的基因和內核。同時,正是通過一代又一代讀書人的探究、吸納、闡釋、重構,經史之學得以繼往開來、傳承光大,中華文明也在這個過程中實現了演化成長、其命維新。本期兩篇文章所討論的《中庸》和《史記》,一為經,一為史,都是中華文明成熟期所確立的文化經典。千載以還,這兩部經典深刻影響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歷史觀念,奠定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底色和文化品格。中國共產黨是在風雨如晦、家國危亡的近代中國成長起來的使命型政黨,自誕生之日起就以追求國家獨立民族復興人民解放為職志。這樣的歷史使命決定了,中國共產黨人必然要承接起中國傳統士君子的家國情懷、擔當意識、以天下為己任的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從中華文化經典中汲取思想資源和精神力量,通過不斷地自我修養、自我錘煉、自我完善,使得這個政黨真正能夠擔當起“中華民族先鋒隊”的責任。百年大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中華文化經典所積淀的歷史智慧和精神品格永遠是激勵中國共產黨人前進的不竭動力。
我們一次次凝望傳統,不是為了回到過去,而是為了面向未來。傳統不是固定不變的,傳統只有在不斷地與現代對話,不斷地與時俱進、推陳出新中才能重獲生機與活力。我們一次次重讀經典,也不僅僅是為了溫習先哲的思想和主張,更重要的,是要通過追尋經典之中數千年來一脈相承的內在價值,找到能夠回應、解答時代之問的歷史啟示和精神力量。因此,我們致敬經典的方式,就不是單純的傳誦吟詠,而是以“為往圣繼絕學”的氣概,在對經典的探究、吸納、闡釋、重構中,返本開新,繼續前進。惟其如此,經典才能常讀常新,傳統才能長青不老。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文史教研部副教授?田嵩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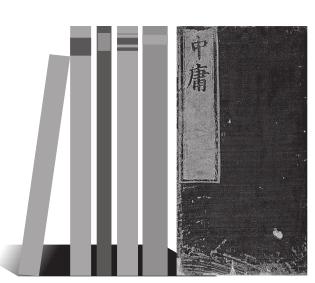
在中華文化經典中,傳統儒家的“四書”可謂是家喻戶曉。“四書”之中的《中庸》,不僅是傳統儒家文化的修養論、功夫論,更是傳統儒家思想體系中重要的辯證法與方法論,彰顯了傳統儒家的入世情懷和處世哲學。但從近代社會“西學東漸”以來,有部分人將《中庸》及“中庸思想”與“老好人”“沒原則”“折中主義”“妥協保守”等聯系起來,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對《中庸》及中庸思想的各種誤讀和錯讀。甚至有人將中國在近代的衰落和落后于世界歸結為是因為中國“太中庸”。實質而言,《中庸》是數千年前中國古代哲人面對當時“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所做出的哲學思辨與思維總結,作為儒家傳統文化的精髓,一直以來以其內蘊的人生哲理和道德智慧浸潤著中國人的心靈,指導著人們在現實的可能與不可能之間進行抉擇。
1874年,清末重臣李鴻章曾在其著名的《籌議海防折》中,全面地論證了中國在變局中所面臨的危險處境,稱之為“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而令他更難以想見的是,僅在他逝后十年,自詡“天朝上國”的大清帝國和中國綿延數千年的封建帝制,都在歷史的滾滾車輪下“零落成泥碾作塵”。中國亦從一個獨立自主的富強之國,日益淪落成了一個受西方列強侵略、欺壓和霸凌的貧弱之國,成為世人眼中的“東亞病夫”和“東方睡獅”。一時間,有人將包括《中庸》及其思想在內的綿延五千年的中華文明,視為是近代中國走向富國強兵和發展現代化的痼疾與桎梏。可以說,“中庸”作為儒家思想中一個至為關鍵的詞語,不但其內涵在現代中國社會中已經模糊不清,而且也是中國自近現代化以來備受誤解的一個概念。而中華民族所遭遇的“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啟示我們要不斷汲取《中庸》等文化典籍及思想傳統的精華,并結合新時代特點進行創造性轉換和創新性發展,進而“執兩用中”,不斷在危機中育新機,在變局中開新局。
內隱記憶的投射與積淀
《中庸》出自于《禮記》第31篇,寫成約在戰國末期至西漢之間。后經北宋理學家程顥、程頤極力尊崇,將其從《禮記》中抽出獨立成書,北宋大儒朱熹則將其與《論語》《孟子》《大學》合編稱為《四書》。在宋、元以后,《中庸》成為學校和官方教育的教科書和科考的必讀書。“中庸”思想則成為源自于生活實踐并指導生活實踐的思想哲理和人生智慧。據考證,“中庸”一詞是由孔子提出的。孔子在《論語·雍也》中指出,“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并且指出,“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冉求也退,故進之;仲由也兼人,故退之”“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對“中庸”一詞和“中庸精神”做出了界定和詮釋。在戰國時期,孔子后人孔伋(字子思)對“中庸”思想作了進一步的發揮和詮釋。子思將“中庸”從概念和“執兩用中”的辯證法與方法論,推進到世界觀和人生觀的領域。在《中庸》第一章中,子思提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在這里,他將“中”與“和”視為天地宇宙間最根本、最普遍的法則,認為人們如果自覺地遵循它,就會使得事物和諧發展,就可以使天地萬物各得其所、繁榮興盛。
從世界觀和人生觀來看,中庸其實是一種“和”的權衡。中庸作為傳統儒家文化的最高道德標準,含有中正、公正、平正、中和的涵義。“中庸”本身就是“用中”或“用常”之道,可以理解為研究、探求、認識和處理問題時合乎實際或一定標準的態度與方法。“中庸”所強調的“和”,一方面是多樣統一、和諧的意思,另一個意思則與“中”一樣,指恰當、適度。如《論語》“禮之用,和為貴”,《中庸》“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指的是調節、事之中節、恰到好處。中國傳統的思維方法論不認為對立、矛盾雙方之間有一條僵硬不變、截然不可逾越的界限,而是可以隨時節制,合于中道。儒家講“趣時”,也即根據時勢變化,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常規,采取適宜的措施。這里的“時中”,其實也包含了“趣時更新”的一部分內容。因為中是正道,所以不偏。“和”是天下通行的道路,是人生實踐中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它具有通過實踐追求以使現實與理想統一的意味。將“中和”的原理發揮到極處,人們就能自覺地進行自我修養、自我監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慎獨自修、忠恕寬容、至誠盡性,把自己培養成為具有理想人格,達到至善、至仁、至誠、至道、至德、至圣、合外內之道的理想人物,共創“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
社會發展“太中庸”的糾偏與權衡
中庸是和諧和順之道,也是求變發展之道。合禮的才合理,合理的才合禮,合理、合禮才是“中”。荀子說:“夫禮之于正國家也,如權衡之于輕重。”強調的就是如果要使國家和諧發展,就需要把握“中”,就像掌握那個“秤”稱量東西時重量的平衡。這才是“中”,也才能“中”。“中”不是簡單的數理意義上的“中間”,更不是“調和”或“折中”,它絕非一眼就能看透和判斷準確的。“中”的標準并不固定、絕不拘泥,它隨著條件的變化而變化。中庸是一個不斷糾偏的過程。此時“中”,換個時間未必“中”;此地“中”,換個場合未必“中”。
從辯證法和思維方法論而言,“中庸”其實是一種“度”的把握,是在紛繁復雜的矛盾中研究什么是事物所處的最好狀態以及如何達到這種最好狀態。這個“度”是因時因地而變的,它像“易”一樣難以確定,易是道,中庸亦是道,所謂“道可道非常道”,從這一點看,“中”就是天理、天道,它是一種心靈智慧和發展哲學,其本質是無法具體言說的。“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這其實是從辯證法和方法論的角度將“中”作為一個哲學概念提出來。古人說,用中為常行之道,中和為常行之德。“中”是天下最重大的根本,“無過無不及”,不偏不倚,即適度。“庸”又是“常”的意思。“庸”是天下不易的法則,不改變常規,即定理。而作為標準的“中”并不是處于與對立兩端等距離的中點上,也不總是固定和僵死在某一點上,而是隨具體情況、具體條件的變動而變動的。《中庸》及其思想強調矛盾對立的中和,使兩端都可以同時存在,都可以保持各自的特性,促進兩端彼此互動、兼濟、反應、轉化。在哲學上,就是把握對立與統一、質變與量變、肯定與否定之間的“關節點”或“度”,而越過這一界限,事物就會發生大的變化。但在多數情況下,這種方法論重視對立面的同一性,強調依存和聯結,以及兩極或多極對立間的中介關系及其作用。這是因為世界上的矛盾不一定都發展到一方消滅另一方的地步,需要在矛盾的統一之中取中和的狀況。而在這種“中和”狀況之中,既有矛盾、偏反、對立、斗爭,同時彼此滲透,彼此融合,共存共榮。因此,“中庸”吸納了天地自然對立調和、互動互補的原則,并以之調和人類自身與天地、與萬物的關系,達到中和的境地,使天地萬物與人如常地發展。在這個意義上說,中庸之道又是人間之道,可以用來調節倫常關系、社群關系。
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庸思想的認識與發展,也是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程中不斷與時俱進的。毛澤東常常把孔子及其學說從道德和哲學層面分開進行分析。他指出:“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歷史的看法。”“我們共產黨看孔夫子,他當然是有地位的,因為我們是歷史主義者。”毛澤東認為中庸觀念本身不是“發展的思想”,體現了保守性;但是從哲學上說,它“是從量上去找出與確定質而反對‘左右傾則是無疑的”,“‘過猶不及是兩條戰線斗爭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并進一步解釋說:
“過”的即是“左”的東西,“不及”的即是右的東西。依照現在我們的觀點說來,過與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時間與空間中運動,當其發展到一定狀態時,應從量的關系上找出與確定其一定的質,這就是“中”或“中庸”,或“時中”。說這個事物已經不是這種狀態而進到別種狀態了,這就是別一種質,就是“過”或“左”傾了。說這個事物還停止在原來狀態并無發展,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滯,是守舊頑固,是右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觀念沒有這種發展的思想,乃是排斥異端樹立己說的意思為多,然而是從量上找出與確定質而反對“左”右傾則是無疑的。這個思想的確如伯達所說是孔子的一大發現,一大功績,是哲學的重要范疇,值得很好地解釋一番。
毛澤東采用正反兩方面的辯證思維及運用兩條路線等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方法詮釋“中庸”,肯定“中庸思想”的積極因素,拓寬與豐富了“中庸”思想的含義。鄧小平在對傳統中庸觀繼承與發展的基礎上,靈活運用了“過猶不及”的中庸方法,光大了矛盾對立統一的內涵。他將“過猶不及”和“執其兩端, 而用其中”的中庸思想成功地運用到我黨新時期思想路線的確立上,明確提出既要反對右,又要防止“左”。他認為在事物對立的兩極間,在同一空間和時間的條件下,存在著廣闊的處于差異狀態的中間帶、中介項。他充分認識到了這些中間帶、中介項在事物穩定狀態中的重要作用,反對盲目地超越中間帶而走向極端,形成了政治領域著重防右,經濟領域重點反“左”的獨特的中庸方法,使傳統“過猶不及”的方法論在現代的改革開放中煥發出新的生機。鄧小平理論中的一個重要理念“韜光養晦”,本身就是一個十分中國方式的、充滿了中庸氣質的戰略思想。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
一個國家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與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和文化傳統密切相關的。解決中國的問題只能在中國大地上探尋適合自己的道路和辦法。
習近平總書記善于從蘊含中華幾千年深厚底蘊的傳統文化中汲取治國理政的智慧,又把閃爍著中華民族智慧結晶的思想在新的時代背景下進行了發展與創新。他不但多次使用和強調“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等出自《中庸》的經典名句,將“中庸思想”作為人的道德修養、官德建設以及社會道德建設的途徑,而且汲取了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對傳統的中庸思想有了新的繼承和發展。比如,中庸之道的本質在于以全局的視野和全面的方法看待世間萬物,在何為中的問題上,“中庸思想”的回答是“全為中”,這與習近平總書記的“既要綠水青山,也要金山銀山”的理念完全契合。再比如,底線思維是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中的一個重要思想和基本原則。毛澤東曾多次強調:“要在最壞的可能性上來建立我們的政策。”鄧小平也指出:“我們要把工作的基點放在出現較大的風險上,準備好對策。”這都源自于《中庸》講的“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等應對自然風險和進行社會治理的實踐智慧,實現了“有守”和“有為”的結合,體現了主觀與客觀、風險和機遇、質變與量變的關系,為我們更好決策、更有效開展工作提供了思維方式和領導方法。
入世處世的知時與時中
時代是思想之母。馬克思主義認為,凡某種理論的“出場”都基于一定的時代條件和特定的歷史背景。可以說,《中庸》及其思想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可能與不可能之中的“出場”與“在場”,有著一定的歷史必然性。作為思維方法,“中庸”強調均衡與協調,反對偏執和盲目,在事物發展的任何階段都必須注意天、地、人有機統一,反對盲目極端化,認為過度和不及都不能“致中庸”;作為思想方法,“中庸”是個體修身成長之道,是國家為政治國之道。(李學勤先生曾稱其為“周文王的遺言”) “人之所以為人”的道理在哪里,“人心”與“道心”之間的那個“中”是什么,怎樣“擇其兩端而用其中”,這些都應該成為人們在思維和現實中思考的核心問題。中國先哲們在討論人的自然性與社會性之間的關系,思考如何處理“我想怎么樣”與“應該怎么樣”之間的矛盾時,曾提出實現“中庸”的“十六字心傳”,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在新時代,既要站在歷史的制高點上,總結和繼承先秦儒家以來的文化傳統,也要整體、系統、動態地觀察世界,準確理解和完整把握《中庸》及其思想在新時代的內涵與意義。
中國在新時代所遭遇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是激勵中國人要在“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的大歷史中去實現各種可能與改變各種不可能,進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2018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提出一個重大論斷,即“當前中國處于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此后,他又多次重申這個論斷。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這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既是指當前復雜的國際形勢和國內情勢,也是指實現中國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變局。此變局既是對國際格局正在或即將發生巨大變遷的重大判斷,也是對國內情勢復雜性與不確定性加強所做出的重大判斷。放眼寰球,曾在全球化浪潮中高歌猛進的西方世界,出現了自工業革命以來的第一次全面頹勢。老牌強國云集的歐洲已陷入老齡化等諸多社會問題的泥淖,經濟增長疲軟乃至長期乏力。曾領人類啟蒙運動與工業現代化之先的歐洲,竟然日益成為沉沉暮氣之地,甚至被人戲稱或將成為人類的“博物館”。種種大變局、種種可能與不可能之間的艱難抉擇,導致西式“集體性焦慮”在西方世界日益蔓延,并或緩或急地影響世界變局和制約著現實世界的諸種可能與不可能發生歷史與時代的各種變遷。
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重要經典之一,《中庸》及“中庸思想”美妙和諧、辯證深邃,在時間的長河中深深印記在炎黃子孫的內心深處,在歷史的歲月里牢牢熔鑄在中華民族的血脈中。《中庸》有句名言,“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表面上看,“中庸”是在每日的飲食中,但味中有味,想體會其深層次的味道則是有難度的。實質而言,《中庸》及“中庸思想”的個中三昧,主要在于個體的內隱記憶與人生體驗,在于群體對和諧和順和求變發展的時空探索。而這種記憶和探索,則映照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個體的投射與積淀,展現了中華傳統文化時空發展的深厚傳統與傳承發展。
(作者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哲學教研部倫理學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