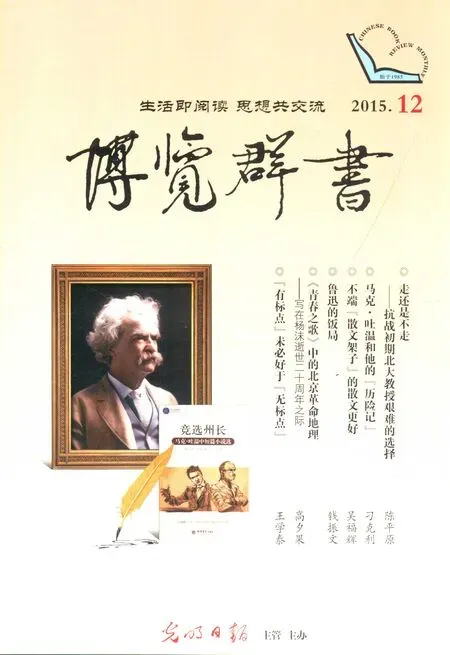看《近代中西醫的博弈》
周贇

中西醫的“博弈”能否實現雙贏?這個問題,恐怕經過了2019年末至2020年初的與新冠病毒的戰斗,已經可以說明,中西醫的博弈應該是可以雙贏的。然而至近代以來,尤其在細菌致病說出現以后,中西醫的博弈可謂你死我活。《近代中西醫的博弈》一書,敏銳地抓住了“細菌學”這一中西方治療邏輯的分水嶺,從一個常為人忽視的角度,重新書寫了近代中國醫學史。
西醫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希波克拉底, 他對治愈的基本認識,就是恢復身體的平衡與和諧。比如,身體發熱,就要冰塊或冷水來阻止;熱病初期不宜出汗,就用被褥捂汗或者催吐,甚至放血,等等,這樣的觀念一直綿延到近代。中醫雖然不會用這些方法,但追求“平衡與和諧”的思維方式是一樣的。
然而,當肉眼看不見的細菌被西醫發現以后,情況開始發生變化了。人們開始知道,感冒不是因為冷而是因為細菌或病毒;導致上吐下瀉的毒質,其實也是細菌或病毒。在抗生素被正式發現前,中西醫的交手還難以分出高下。直到抗生素被臨床運用,兩者才正式出現了重大分歧。中醫是科學還是迷信之爭,也借此甚囂塵上。民國以來,從學界到政界,對中醫的壓制甚至廢黜的思想,占據了當時社會思潮的主流。余云岫、吳汝綸、梁啟超、傅斯年等各界人士,都是批判中醫的急先鋒。當然,這也是中醫開始主動向西醫學習,并正視細菌學的重要動力。
中醫不談“氣”是不行的,這是中醫之為中醫的本質。中醫必須依據寒熱與氣候,即氣的對證治療,方能實現其治療目的。但氣在本質上是一種觀念存在,而細菌則是事實存在。在客觀事實面前,中醫是不得不妥協的。因此,要想兼顧兩者的唯一辦法,就是將細菌學納入中醫氣論的范疇中,用自己的話語對其進行重新消化、理解,亦即“再正典化”,由此出現了近代中西氣論與細菌論會通的“歷史模式”。不得不說,這實在是醫學史研究上的新面向。
《近代中西醫的博弈》一書非常專業,溫病、熱病、傷寒等概念,非具備一定專業知識者很難領會其中的微妙區別。但有一點我還是讀懂了,即近代中醫學人非常努力,他們一刻也沒有停止過向西醫汲取經驗教訓,在廢黜壓力最大的民國時期,不斷地嘗試把細菌學納入自身領域的思考之中,甚至結合中醫的原有傳統,取得了不少創造性的成果。
書中提到惲鐵樵的一個關于治療白喉的案例,正體現了中西醫匯通下的創見。惲鐵樵認為,若白喉伴隨太陽病癥狀,那么“太陽病解,不論何種病菌,皆漸就消滅”,認為這個結論適用于除了結核病之外的各種熱病。意思是癥狀判斷比病菌判斷更直接有效。且同一種病菌,進入身體不同部位,反應出來的癥狀是不同的,所以惲鐵樵認為,要追癥狀而不是追病菌。這里的思路就是,解決一個關聯性問題,那么根本性問題也就解決了,未必非要追求所謂“針對性”。
其實,惲鐵樵把焦點放在癥狀上是有一個前提的,即當時的驗菌能力并不精確,且化驗時間太久。但他總結出的道理是對的。今天我們又發生了類似的情況,即檢驗病毒的能力很精確,但是沒有針對性的抗病毒藥物,同樣也是束手無策,這就是與新冠病毒的抗爭。2020年2月,上海兒科醫院接受了兩名感染了新冠肺炎的輕癥兒童,一名10歲,一名1歲。當她們出院時,醫生在新聞發布會上介紹了他們的治療方案,即“對癥治療,輔以中成藥”,沒有使用抗病毒藥物。所謂的癥,是咳嗽的癥狀。緩解了咳嗽的癥狀,再輔以中成藥,基本上就達到痊愈的目的。2月20日出院的一名7個月女嬰,則只是服用了咳嗽藥水。既然沒有針對性的抗病毒藥物,不如曲線救國,通過抑制相關癥狀以及提高免疫力,實現治愈。這一思路,可能就是惲鐵樵的中醫抗菌思路。
中醫的確存在一些問題,但中醫從來也沒有故步自封,她學習、創新、提升,這就是科學精神。任繼愈先生是較早正視中醫科學性問題的學者,他提出,中醫保障了如此眾多之人口大國延續至今,豈能不是科學?為了進一步促進中醫的現代性轉型,恰當的批判繼承非常關鍵。比如李申教授發現,《呂氏春秋》不講五行和五臟的配屬問題,且《淮南子》中五臟與五官的配屬更與《管子》《內經》都不一致。他認為,五行對于中醫而言,其實是一個外來的理論,五行與五臟配屬的合理性,具有非常相對的意義。中醫界的鄧鐵濤先生也意識到這個問題,為了將五行的類比取象、生克乘侮與具體的臨床實踐區別出來,他建議將陰陽五行學說正名為“五臟相關學說”。醫學史學者區結成又進一步理清了中醫“辨證論治”的內涵,指出古代“辨證論治”的主旨是辨別傷寒與瘟疫兩種主要的“證”,而現代中醫所指之“證”,是“在致病因素作用下,機體內外環境,各系統之間相互關系紊亂所產生的綜合反應”,并且強調了疾病所處的階段性,即時相性,且這一點是中醫所特有的。梁頌名等學者還從實證角度發現,除了排泄功能外,腎臟還參與了鈣的吸收與代謝(維生素D3的活化),是骨骼代謝中的關鍵環節,與中醫“腎主骨”的說法不謀而合。
所以說,中醫學本身一直處在自覺發展的過程中。然而,發展離不開啟示,《近代中西醫的博弈》一書從中醫抗菌史的角度切入,固然開創了醫史研究的新視角,但其實它不僅有功于歷史研究,還有助于中醫現代醫學話語的建構。必須承認,中醫是一門未曾中斷過的,具有高度中國特色的科學,在今天的各類中醫院校,傳統醫古籍仍是必讀之書目。然而同樣的書,在不同的語境下讀出不同的新意來,才是對經典最好的傳承。《近代中西醫的博弈》一書就有這一啟發性意義。它通過回溯在細菌學影響下的中醫的“再正典化”,其實也是一種創新現代中醫話語的動力。今天我們反復倡導的對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不就是要于傳統中求出新意嗎?中醫抗菌的歷史語言建構告訴我們,差異如此之大的細菌論與氣化論尚且能夠對話,那么中醫現代醫學話語的建構當然也是可能的,而且我們絕不能怕走的太遠。借用惲鐵樵的話說:“吾儕研究所得,漸與古說相離,不中不西,亦中亦西,命之為新中醫。”這句話是積極的,而且應該是現代中醫發展的方向。質言之,這門古老的科學要想繼續造福華夏子孫,那就一刻也不能脫離求變求新。
(作者系上海應用技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